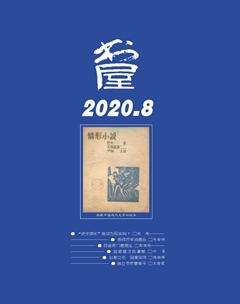以爱之名 泅渡深河
周朝晖
一
我很晚才开始接触远藤周作的作品。因为接触方式很特别,在私人阅读史上可以说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随波逐流自费东渡日本开始漫长的游学生涯。初来乍到,我在埼玉县大宫市(现为大宫区)落脚,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余寒冷峭的春假里,为了积攒学费,我到住所社区一个小型摩托车安全帽工厂打工。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茶歇时段,我在车间休息室里随便翻翻当日的《读卖新闻》时,无意中看到文化版上刊出远藤周作回忆录连载《留学法兰西》(题目大约如此)。当时对我来说,远藤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作家。说陌生,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甚至名字也是到了日本才知道的;说熟悉,是每天晚上必见。九十年代初东芝推出一款文字處理机“哇普罗”(word processing machine),由知名作家轮流当代言人,其中就有远藤周作。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黄金时段NHK新闻播报之后,远藤如期而至,他瘦高个,大额头,黑框眼镜,脸色苍白,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码字如有神助,动作神态极尽夸张搞笑。而且,普通日本人似乎对他也不陌生,我记得“狐狸庵先生”这个与他有关的雅号,也是一个姓仙波的老员工告诉我的。
不过,这个广告并没有激发我去读他的作品的兴趣,只缘无暇顾及。但在工场里就不一样了,因为工作乏味单调,看报纸,尤其是带有故事性的回忆录文字,不但可以消磨时间,还能愉悦心情。顺手拿起报纸浏览,本来纯粹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歇息时间,但目光落在远藤的连载上,就停住了,因为开头的段落把我吸引住了,遥远青春时代的留学生活在作家笔下趣味盎然、跃然纸上:艳阳下南欧普罗旺斯的田园风光,善良淳厚的房东夫妇,美味芳醇的葡萄美酒,恶作剧不断的寄宿生活……这些带着光彩和色泽的文字令我心驰神往,浑然忘了身边骨感的现实。彼时我刚到日本,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自费生,学习、打工没有一样省心,压力如影相随。几个月来,忙碌而艰辛的工读生活使我身心疲惫不堪,简陋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和单调的活计使我感觉麻木。远藤的文章像清风吹入深谷,重新唤起我对美好事物、美好人生的憧憬和向往,顿时眼前一片光明和温馨。
这样,在工场的休息室里连续读了两三篇后,意犹未尽,开工后我悄悄将连载《留学法兰西》的版面单独抽出,按排版折叠成小方块,放在机器旁,边机械地打孔钻眼,一边瞄一眼那美妙的文字,欣赏暗诵,乐在其中,直到有一次被工场长巡视发现后怒呵制止,因为违反劳动安全纪律甚至差点因此丢了工作。我为了能随心所欲读远藤的文章,索性自订《读卖新闻》。每天早上天刚破晓,听到屋外送报人开启信箱投送早报时的声音立即披衣而起,沐浴漱洗后就在书案前盘腿而坐,利用出门上学前的一个小时时间,边吃简单的早餐,边兴致勃勃地诵读远藤的连载回忆录。这段晨读一直持续了近两个月,日式公寓窗外的樱树,从光溜溜的枝条,到出现花蕾,又到含苞欲放,再经过繁华如云似锦最后到残红消退枝叶青青时,连载才结束,这么用心读一个作家的文章,在我的阅读史上前所未有,后再难继。
这些文章成了进一步阅读远藤作品的垫脚石,我开始有意识涉猎远藤的作品,借助《广辞苑》之类的工具书,磕磕绊绊开始读远藤的书。远藤是大作家又非常高产,他的作品很多以廉价而又畅销的文库本出版,社区的小书店都能买到。我从自传、随笔《狐狸庵闲话》、《读了也没用的随笔》等,对他个人的生活与情趣进一步了解后,再接着读他的小说代表作,从《白人》、《沉默》、《海水与毒药》、《哀歌》到《最后的殉道者》……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读了不少远藤的书。
阅读,在我眼前打开了另一个天地,我才知道在我原先自以为熟悉的日本文学中还存在着一个被称为基督教信仰文学的领域,而远藤周作作为这个系谱上最卓越的作家,他的成长道路和文学生涯非常独特,堪称“另类”。
二
远藤周作与基督教有不解之缘,源自早年生活经历的深刻影响。
远藤是东京土著,1923年3月生于首都圈内一个高级白领之家。父亲远藤常久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专业出身的俊彦之才,在安田银行(今富士银行前身)当高管;母亲是上野音乐学校学生,专攻小提琴专业: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日本也可以步入中流精英行列了。远藤周作三岁那一年,父亲调往中国大连的分行任职,举家随其迁移,远藤的童年时代是在中国东北度过的。小时的远藤周作天真活泼,喜欢画画和小动物,但是学习乏善可陈,与他那品学兼优的哥哥正好形成鲜明对比,经常受到父亲的呵斥,幼小的心灵就蒙上了挫败感和自卑感。而给予他巨大影响的是母亲。在远藤看来,母亲身上有一种近乎神性的东西,是爱的化身和使者。母亲天性善良仁慈,对当地保姆也很宽厚亲切。与父亲苛刻轻视相对,母亲对孩子极有耐心爱心,每当远藤周作因成绩不好受到父亲教训打击时,母亲总是鼓励他“不要灰心,你是大器晚成啊”。小学四年级时,远藤周作一篇作文《泥鳅》被大连日系报纸《大连新闻》采用,母亲大为赞赏,预言他长大当作家。她温柔优雅的外表下有一种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对艺术有着求道一般的执着与献身精神。大连的深冬滴水成冰,母亲披着棉袍,立在严寒中,每日雷打不动连续数小时拉琴,指尖流血不止仍不停息,令周作内心受到震动。母亲不但是远藤周作艺术上最早的启蒙老师、文学才华的伯乐,最重要的是他宗教信仰的引路人。这要从早年一场家庭变故说起。
十岁的时候,父亲外遇,家庭气氛急转直下,1933年,父母离异。父亲再婚,母亲带哥哥和他回到日本,投奔在神户的姨妈。为了生活,母亲在当地一所女子学院任音乐教师,周作转入神户市的六甲小学校读书。神户是异国色彩浓郁的城市,作为近代日本最早的贸易商港,西方教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姨妈一家都是天主教徒。婚姻受到挫折的母亲受姨妈的影响,在参加当地教会的宗教活动中找到了心灵归宿,皈依天主教会。1934年的复活节,十二岁的远藤周作和哥哥一起皈依天主教,洗礼名保罗(Paul)。不过幼年入教,对远藤而言还说不上触及灵魂的事件,他后来称这段经历是“母亲给自己穿上的不合身的西装”。长大了觉得不合身,穿在身上别扭,几次想脱掉。他早年的天主教信仰,不是与上帝的契约,而是与母亲的合约,个中包含了悲天悯人的“理解之同情”或“同情之理解”。
上了中学的远藤,对学习不感兴趣,痴迷于读课外书、看电影、嬉笑搞怪恶作剧,不仅中学以接近垫底的成绩毕业,因为连续三次考不上大学,沦为回炉补习的浪人三年。其间,虽然考上上智大学德语系,但因离父母的期待差得太远,只好中途退学,再次准备高考。此前,父亲已经从大连调回东京,在世田谷经堂定居。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远藤兄弟和父亲协商让他到东京和父亲一起居住,一边准备再考。父亲开出的条件要求必须考入旧制帝国大学或大学医学部。远藤周作按照父亲的要求一一投考,结果全部落第,最后只剩一个庆应大学的选项。他估摸以自己的成绩绝对上不了条件苛刻的医学部,就偷偷报了文学专业,居然候补合格。1945年春天,进入庆应大学法国文学科学习。不久父亲得知真相,尤其是看他学了最不中用的專业,勃然大怒,驱逐出门后永远断绝父子关系。失去了依托的远藤周作只能靠自己解决生计,一边上学一边当家教,在学友利光松男家(后任日本航空总经理)寄宿,困窘不堪。在上学期间,远藤周作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评论家、思想家吉满义彦和松并庆训,在他们的熏陶下,耽读法国天主教思想家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和里尔克的著作,并结识了作家龟井胜一郎和堀辰雄。与堀辰雄的交游,是周作人生的转机,按照他的说法,从此告别了“超低空飞行时代”,在文学的天空中展翅翱翔。
在身边一流哲学家和作家的影响下,远藤周作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作家莫里亚克、贝尔纳诺斯等作家的作品,一边勤奋写作。1947年12月,他写的第一篇评论《神与诸神》脱稿,受到著名作家神西清的激赏,并刊发在其主持的《四季》期刊第五号中;不久《天主教作家的问题》一文也被恩师佐藤朔推荐发表在《三田文学》,其后《堀辰雄论》又分三期在《高原》连载。这几家杂志在当时都是深孚众望的文学期刊,短时间如此密集地发表文章,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实属罕见,远藤周作作为新进文学评论家的形象呼之欲出。母亲在他幼年时代的“大器晚成”、“长大当作家”的预言,成为现实。
1950年6月,远藤周作以战后第一批留学生的身份,搭乘客轮赴法国巴黎里昂大学读博,研究现代天主教文学。在里昂大学,他师从著名宗教文学研究学者巴蒂,他一边大量阅读法兰西基督教文学的经典论著和小说,一边为日本国内的刊物撰稿,留学生活充实而浪漫。不过,两年半后远藤健康出了问题,被确诊为肺结核,只能中断博士学习生活回国治病。两年半的留学生活虽然短暂,但对远藤周作的文学生涯来说却意义非凡。其一,他由此确立了从评论家向小说家转型的志向;其二,在法兰西的学习阅历和体验,他坚定了对天主教的信仰。可以说,留学法兰西,奠定了远藤后来成为日本基督教文学先驱的基础。
三
回国后,远藤周作任教会杂志《天主教文摘》主编,除了负责杂志的一些日常事务,业余时间为杂志撰稿,并开始尝试由评论家向小说家转型。此前,现代日本文学在战后的废墟上重新出发,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远藤周作因缘际会,以一系列创作实绩,确立了战后文学“第三代新人”代表的地位,实现了在前评论家身份上“重新出发”的华丽转身。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起点,日本现代文坛出现了新的变化,先后出现了以野间宏、椎名麟三和梅崎春生为代表的第一战后派作家群,以武田泰淳、安部公房、大冈升平和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第二战后派。“第三代新人作家”紧跟其后登上战后文坛,他们是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三浦朱门、小岛信夫、近藤启太郎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同属战后崛起的作家群,却被主流评论界称为“新人”,说明这一代与前两代战后派作家具有本质上区别。最大不同,是将笔墨从对战争的记忆的描述转向当下生活的场景和内心感受,回避政治国家社会重大题材,转入私小说叙事。远藤在回国后的文学转型,首先从私人写实起步。1953年7月,远藤追忆法兰西留学生活的《留法日记》和《在阿尔卑斯山艳阳下》等作品先后发表,其后结集为《法兰西的大学生》一书由早川书房出版,这些作品只是文学转向的铺垫之作,却获得文坛瞩目。
而作为青年小说家,远藤周作出手不凡,一出道即被视为“第三代新人”的代表。1954年11月,在《三田文学》发表《到亚丁去》,遵循的是日本明治文学的私小说笔法,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而翌年发表的小说《白种人》,一举斩获第三十三届“芥川奖”,成了步入第三代新人作家的祭旗之作。继《白种人》之后,远藤周作的文学生涯顺风顺水,渐入佳境,此后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推出一部重量级长篇,作为积蓄能量和休整,佐以随笔幽默小品和历史小说,超级高产,成了拿遍日本国内各种文学奖的专业户,且不止一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国畅销。可以说,在战后灿若星辰的日本作家群体中,远藤周作以一系列作品跻身于当代最优秀作家行列。
远藤周作文学的最大特色,即是以基督教为主题以及蕴含在作品中的人生哲理宗教情怀。基督宗教信仰是远藤文学的内核与灵魂,离开宗教信仰,远藤的文学价值就无从谈起。换而言之,远藤的文学兼具神学与文学的双重价值——关于神性与人性的文学表现与思考。可以说,远藤周作的作品特别是最主要的代表作,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来展开的。这其中,《沉默》与《深河》无疑是表现这个伟大主题的杰作。这两本书远藤生前十分看重,临终一再嘱咐家人,死后将这两部书放入棺椁伴随长眠。
长篇历史小说《沉默》是远藤周作的基督信仰文学的代表作,远藤由此奠定了“二十世纪基督教文学最重要的作家”的地位。几年前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将原作搬上银幕,并在梵蒂冈首映。罗马教皇方济各亲临小教堂观看放映,一举成为世界影坛和基督教领域一大佳话。作品是在十七世纪初期日本江户幕府实行锁国禁教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葡萄牙耶稣会派到日本的教士克里斯多夫·费雷拉神父,在历尽千辛万苦传教二十年后,最终屈服于幕府的残酷刑罚而叛教。青年神父罗德里奥受耶稣教会委派远涉重洋来日本调查此事。他在澳门下船后偷渡日本,潜伏在长崎郊外秘密调查叛教事件,后来因叛徒出卖,被幕府缉拿。为拯救更多无辜的信徒,罗德里奥被迫用脚踩踏刻有耶稣圣象的铜版,当他的脚踩上踏绘时感到一阵剧痛。这时铜版上已经被踩踏得影像模糊的耶稣仿佛在对他说:“踏吧!我知道你脚痛。正因为知道这种痛,我才降生世间背负十字架的。”
这个故事并非虚构架空,而是取材于真实的史实,经过作家直抵肺腑的追索拷问,读来惊心动魄。在文京区茗荷谷,我曾参观幕府时代关押“弁天连”(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和信众)的牢狱“切支丹屋敷”。1643年,遭遇海难漂流到日本九州的意大利传教士朱塞佩·齐亚拉(Giuseppe Chiara),被长崎当局捕获后就曾被关押在这里。后来受不了残酷的身心摧残,齐亚拉被迫放弃信仰,改名冈本三右卫门,在日本娶妻生子,了度残生。此人就是远藤《沉默》中克里斯多夫·费雷拉的原型。远藤也去过位于长崎市当年荷兰传教士集体殉道的遗址,那里伫立着江户时代被杀害的二十六个传教士浮雕,其中有一块《沉默》之碑,用以纪念这部巨作的问世。这部小说于1966年问世,但是准备和酝酿却经历了多年时间。远藤自幼多病,战争期间因体弱侥幸躲过兵役,但因肺结核动过几次大手术,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以此为契机,“开始认真考虑上帝的事了”。1959年周游欧罗巴列国,归来肺结核复发,差点送命,住院两年多,1961年肺部再次出问题而接受手术。生病期间,偶然从朋友带来的报纸上读到关于长崎“踏绘”的历史考据文字,触发了无尽浮想。1963年,远藤病愈出院,多次去长崎实地踏查取材,搜集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沉默》。
四
比起《沉默》,和很多远藤文学粉一样,我更喜欢的是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深河》。一生对自己的创作说长道短的远藤对这部书颇为自许,说它是“迄今为止的自己文学的总决算之作”,“是一生集大成之作……其间,我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全部写完了……就像自己的遗书一样”。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出版于我到日本的第二年,当时我已经读了不少远藤的文库本原著,我有幸目睹远藤生前最具影响力的巨作出版及发行的盛况。我还清晰记得经常光顾的新宿纪伊国屋书店里原本光顾者不多的纯文学专柜前排起长龙争购《深河》的情景。
与《沉默》的背景不同,《深河》讲述的是一个旅途故事,背景是南亚大陆的文明古国印度。但这部充满异国情调的小说讲述的却是日本人的故事,而表现的主题却一以贯之地在《沉默》展示的“人性的救赎”这一主题的延长线上。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腾飞以后的日本人满天飞,没有不去的地方。小说《深河》写的是几个到印度的日本旅行者,所谓深河就是印度教的圣河——恒河,以此作为小说的舞台。但这些人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旅行者,他们“背负着生命中的各种辛酸和伤痕”,在深河畔祈祷。
小说以矶边的故事开篇。矶边是中年公司职员,长期刻板规矩的上班族生活使他形成拘谨冷漠的个性,此前妻子患癌症去世,他才痛感妻子走后留下的巨大虚空。妻子临终前神启般相信死后会转世,留下遗言:“我一定会转世,在世界某处,我们约好,一定要找到我!”尽管矶边不是宗教信徒,不过,抱着对妻子的愧疚和忏悔他决定试试,报名参加印度旅游团,满心期待能在世界某个角落找到转世的妻子。出乎意料的是,与他一同参团的还有一个曾经在妻子卧病期间负责看护的义工成濑美津子。
美津子是一个另类的女人——美丽、浪漫,但又任性,性格冷酷,缺乏爱心,行为乖张,身上有着某种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潜意识里又似乎潜藏着某种不可思议的愿景。她在医院当义工,照顾病人无私奉献,这一切并非源自爱心与慈善,而是出于对爱的某种模拟演习。年轻时,她玩弄过一个名叫大津的男人的真情,挑战过大津的宗教信仰。她参团来印度,是冥冥中受到某种启示,来寻找那个曾经被她无情抛弃而又一刻无法去怀的大津。不可思议的是,在瓦拉纳西城,果然真的与在这里从事神圣工作的大津不期而遇……
大津并非参团人员,但他却是书中的重要存在。大学时代他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成濑美津子企图想将他从神身边拉走,最终又将他抛弃。信仰崩塌的大津开始放浪修行,辗转到法国里昂神学院,试图寻找适合日本人心灵的基督教。他秉持日本人的泛神论,认为“神有几种不同的脸,隐藏在各种宗教里”;神不是“在人以外让人瞻仰的东西,而是在人之中,而且包容人、包容树、也包容花草的大的生命”。这种多元的、泛神论宗教观使他在一神教的欧洲教会中难以容身,晋升神甫也终成泡影。为了践行自己的神学理论和信仰,他毅然来到印度传教,在瓦拉纳西城(Varanasi City),奔走于陋巷与河畔之间,将临终的教徒背到河边沐浴或火葬。后来因为替一个犯禁的客人顶罪,受到暴怒的信者攻击,惨死于河边。
还有几个人物:经营运输业的退伍老兵木口,他要到印度祭奠亡灵,他的战友在二战的缅甸战场上,在极端困境中吃了蜥蜴肉(人肉)而幸存下来。战争结束后,因陷入暗无天日的罪恶意识无力自拔,最终自尽求解脱;喜爱动物并以此为题材的童话家沼田,他坚信是一只鹩哥代替了本该病死的自己,他要前往鹩鸽的故乡印度放生鹩哥……总之,旅行团的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去接触感悟生与死,信仰与永恒。对他们来说,此行与其说是观光之旅,不如说是灵命之旅。书中的“深河”成了测度生命、命运的河流,平稳的河面下隱藏着一个个深不可测的生命之谜:生与死,神与人,信仰与人生等,沉重得令人透不过气,读罢,令人掩卷长叹。
令人击节的是,在《深河》中,远藤在旅途故事的叙述框架下,为人物的外在遭遇与心路历程别出心裁安排了一个底蕴极为丰富的舞台。首先,以印度这个充满宗教文化色彩的古老国度为背景,极富象征意义。印度是世界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是历史上多种宗教,如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的源头。世界各种主要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与印度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印度可以说是多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国家。自古以来在这种宽松多元的宗教观影响下,这个古老的国家散发着浓烈的宗教气息,各种宗教在这里碰撞又彼此和睦共处。
其次,书名所谓“深河”,指的就是故事的背景印度恒河。众所周知,恒河是印度文明的起源圣地,也是印度人的母亲河与生命之河。在小说里,每个背负不同命运、悲酸与罪孽的人在恒河交会,恒河就是测度生命深度之河。
第三,故事的舞台选在恒河之滨的瓦拉纳西城,也是意味深长。瓦拉纳西城坐落于恒河中游左岸,是每个印度教徒一生要朝拜一次的圣地,很多教徒不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这里,据说每天聚集于此的印度教徒上万人,或在寺庙诵经布施,或在恒河里沐浴祈祷;很多信徒都希望死在河里,让尸身漂浮河面,将骨灰撒入河流里,无论贫贱富贵,一经河流洗礼,一切过错罪孽都会得到净化,所有恩怨仇恨都会被消解,所有喜怒哀乐都会被包容在河里,所有信者都会被带向永恒……
远藤周作的宗教文学中,既写了基督的爱与慈悲,写了罪孽与背叛,也写了不同宗教的对立与对话,写了宗教多元主义。从写作时间跨度上看,《深河》与《沉默》相隔近二十年;从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看,《沉默》反映的现实是十七世开始延绵近三百年的幕府锁国时期;《深河》中人物活动的时间则发生在战后经济实现极度繁荣,国家社会发展高歌猛进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写作时间和故事的背景尽管差异很大,但两部作品的主题惊人一致,那就是关于爱,关于信仰和救赎——这或许可以称得上作为基督教文学求道者的远藤周作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吧。
五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得将书页翻回书的开始,那是故事的出发点。扉页上摘录了一首歌:
深深的河流,神啊!
我也想渡过河去,
到集结之地。
远藤将这首《黑人灵歌》置于卷首,可以视为它就是全书的提纲挈领。据说,远藤在写作过程中,听了这首灵歌后受到触发,才决定为小说定名《深河》,在书名旁特地标注英语Deep river的片假名读音“デープリーバ”,就是为了提醒读者,书名较为日语的“深い河”有着更为深广的内涵。
在西方文学语境中,Deep river一词有着极为深刻的宗教内容,指的是摩西率领的以色列人在经过荒野广漠四十年筚路蓝缕的磨砺试炼之后,才横渡过的约旦河。从这一宗教历史出发,河的对岸就是约定之地、集合之地,也就是《旧约·创世记》中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与得到上帝“拥有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应许之地”,是富足和平幸福与安宁的天堂。这个意象被远藤移植到《深河》里,并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隐隐暗示着:深深的恒河,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圣河,是爱与救赎的生命之河、灵修之河,它以宽广的胸怀和悲天悯人的大爱,接纳身在此岸、处于水深火热之現实与灵魂的煎熬中无法自拔的人们,无分别、无功利地度往彼岸圣地。在人心礼崩乐坏宗教纷争冲突此起彼伏的当今,只有爱与慈悲才能屏息一切仇恨和对立,超越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渡过带来灭顶之灾的洪水滔天……
灾难、阻隔、生老病死、爱别离等一切不幸,自远古以来与人类如影相随,也是古今中外文学歌咏不断的主题。《诗经》有云:“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在远藤周作的《深河》里,表述的是一种对阻隔实现超越的宗教文学情怀,颇见异曲同工:“以爱之名,泅渡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