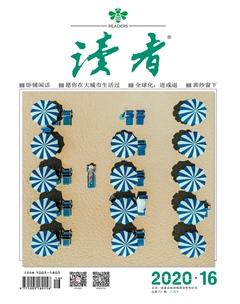旧与老
冯骥才

在京城的一次活动中,我经人介绍结识一名德国女子。她通汉学,尤爱中国的历史人文,对当下备受摧残的古老建筑的痛惜之情,不亚于我们。她说她看过我为抢救津城遗存而主编的《旧城遗韵》,跟着马上问我:“你为什么叫‘旧,不叫‘老?”
这个问题使我一怔。
有时一个问题,会逼着你去想,去自省。我感到这个问题里有值得思辨的东西。一时不及细想。我找到自己当初使用这个“旧”字的缘故,便说:“天津人习惯把那古老的城区叫作旧城,我们就沿用了。”
她听罢,摇摇头,说:“不好,不好。”便扭头而去。这个德国女子直来直去,一点也不客气,却叫我由此认真地深思了关于文化的两个重要的字,就是“旧”与“老”。
一件东西,使用久了,变得黯淡、陈旧、褪去光泽,甚至还会松动、开裂、破损、缺失。我们习惯称之为“旧东西”。按照一种习惯性的潜意识,旧东西是过时的,不受用的,不招人喜欢的。所以旧东西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被扔掉——以旧换新。俗语便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有一种“厌旧”的心理。
这种心理来源于农耕文明。农人们的生活节律是以一年四季为一个周期,所谓春种、夏耕、秋收和冬藏。春天是开头,冬天是结尾。春天里万象更新,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全部孕育在春天的全新事物里。故此,每逢过年,也就是冬去春来之际,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除旧布新。
于是,旧东西必定在铲除之列。这种厌旧心理根深蒂固地潜藏在人们的血液里,便成了长久以来农耕文明在文化上缺乏自珍的深刻缘故。到了今天,自然就成了中华大地“建设性破坏”的無形而广泛的基础。这“建设性破坏”——建设是新,破坏是旧,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顺理成章!
然而,相对于“旧”,“老”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概念。
“旧”是物质性的,而且含有贬义,比如陈旧、破旧,等等;“老”却有非物质的一面。老是一种时间的内容,比如老人、老朋友、老房子。时间是一种历史。所以“老”不含贬义,甚至还含着一种记忆,一种情感,一种割舍不得的具有精神价值的内涵。
比方说某件东西是“旧东西”,似乎就是过时的,需要更新的;若说是“老东西”,那就含有历史的成分,应当考察它,认识它,鉴别它,对于有意味的老东西,更要珍惜。
由此往下说,对于一座城,我们说它是“旧城”还是“老城”,不就全然不一样了吗?

旧城,破破烂烂,危房陋屋,又脏又潮,设施简陋,应当拆去;老城,历史悠久,遗存丰厚,风情别具,应当下力气整治和倍加爱惜。这一切不都与这两个字有关吗?应该说,这两个字代表着两种观念,也是不同时代的文化观。
在宁波,一次关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谈话中,我遇到了阮仪三教授。我对阮教授的人品和学养都十分敬重。谈话间,我提出了一个话题,就是“旧城改造”。
因为现在中国各地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人们是喜欢喊口号的,好像没有口号,就没了主心骨。因此常常由于口号偏差,铸成大错,坏了大事。我依照上述的这些思辨,便说:“现在看来,‘旧城改造中这个‘旧字问题很大。一座城,如果说是旧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就拆掉了事;如果换成‘老字,叫作‘老城就不同了。老城里边有历史,不能轻易大动干戈。当然,法国人是连‘老城也不叫的,他们叫‘古城!”
看来,这个问题在阮仪三教授的脑袋里早有思考。他说:“‘改造这个词儿也不好。因为‘改造这两个字一向都是针对不好的事情。怎么能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不好的东西呢?我认为应当把‘改造也换了。换成‘老城整治,或者干脆就叫作‘古城保护!”
这一席谈话居然把当今中国最流行的一个词“旧城改造”给推翻了。而且换上一个词儿,叫作“老城整治”——或者痛痛快快就叫作“古城保护”了。可别小看这几个字的改动,这里边有个“文明的觉醒”的问题。但这只是书生们的一厢情愿。关键还在城市的管理者们,有谁赞成这样的改动?
(林 一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花巷》一书,陈 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