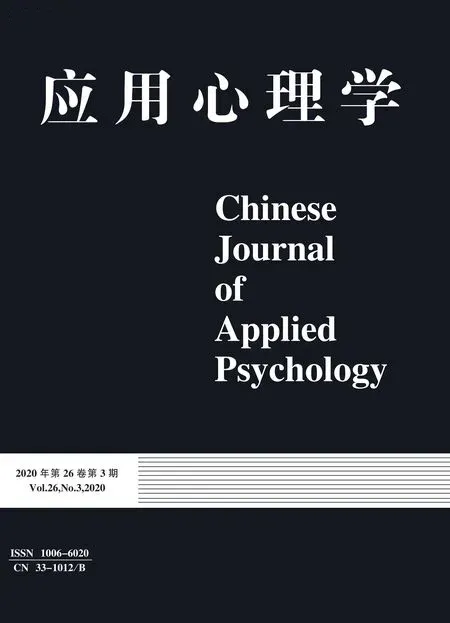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理论与测量方法*
何 铨 沈津如
(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23)
1 引 言
随着老龄化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可能面临着各种被诈骗的风险(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FTC,2018)。根据公安部门2018年统计数据,我国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犯罪案件被破获的就有3000余起,民政部近年也多次发布老年人防骗预警信息。研究发现老年人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受到欺诈的伤害(Cross,2016;Burnes,Henderson,Sheppard,Zhao,& Pillemer,2017),原因是老年人个体决策能力下降(王惠芳,蒋京川,2016)、周围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经济承受能力下降(Andrew & Keefe,2014)。以往关于老年人受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受骗类型以及外在原因分析,也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测量老年人受骗脆弱性(Fraud Vulnerability)(Lichtenberg,Sugarman,Paulson,Ficker,& Rahman,2016)。但有关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缺少统一的测量标准(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Dove,2017)。因此,本文从已有关于老年人受骗及脆弱性研究中总结老年人受骗脆弱性和特征,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分析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比较分析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测量方法,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2 老年人受骗脆弱性和特点
2.1 老年人受骗脆弱性
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指组织或个体不能有效应对风险的表现,不同学科侧重的风险不同,则对脆弱性有不同的定义(Naudé,Santos-Paulino,& Mcgillivray,2009)。在消费领域,脆弱性则强调消费者在营销情境中难以抵御各种诱惑,而做出非理性且影响自身利益决策的行为倾向(Lee & Soberon-Ferrer,1997)。Baker,Gentry和Rittenburg(2005)提出老年人消费脆弱性是由于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心理精神状态和购买经验的综合影响,从而产生具有伤害性的不良消费情境体验。社会学视角则将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看作是老年人在社会关系中缺乏社会判别能力的行为表现(Pinsker & Mcfarland,2010)。Andrew和Keefe(2014)认为老年人受骗脆弱性是个体由于社会状况问题导致在身体、心理或功能上容易遭受损害的程度。心理脆弱性的研究则主要关注老年人受骗的情绪等心理状态问题(Boyle,Lei,Wilson,Keith,Buchman,& Bennett,2012)。在此基础上,Ford,Trott和Simms(2016)提出根据个体的特征和社会环境来界定老年人在受骗过程中遭受身体或心理上伤害的程度,即受骗脆弱性。Dove(2017)则强调受骗脆弱性是老年人在可能欺诈的情境下做出不恰当反应的个体属性和特征。
针对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具体维度,Moschis等(2011)提出可以从认知和行为维度进行解释。认知维度表现为老年人在信息加工和决策规则运用方面的特点(Mears,Reisig,Scaggs,& Holtfreter,2014),行为维度则体现为受骗行为的心理原因(认知年龄、恐惧)和社会学原因(接触模式)(Scheibe,Notthoff,Menkin,Ross,Shadel,Deevy,& Carstensen,2014)。Andrew和Keefe(2014)强调从社会角色转变中考虑诈骗对老年人造成的伤害。Cross(2016)进一步提出老年人受骗脆弱性包含生理、社会和经济维度。生理变化角度认为老年人受骗脆弱性是生理功能衰退导致老年人信息编码和检索所需资源的减少,从而影响信息处理资源的能力(James,Boyle,& Bennett,2014)。社会维度则关注社会支持的程度以及主观的孤独感等。经济维度则更多强调老年人对金融问题判断和经济决策能力(Spreng,Karlawish,& Marson,2016)。
因此,本研究认为,老年人受骗脆弱性是在个体生理、心理特征与外部具有潜在风险环境的共同影响下,老年人对具有诈骗意图信息的不准确感知和无效识别,并做出有损自身福利决策的综合表现。其具体可以通过评估个体特征(生理和心理)、社会支持(社会关系)以及行为特征(经济决策)等方面关键指标来衡量,进而预测老年人被骗的发生率。
2.2 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特点
老年人由于个体认知和健康方面的限制而缺乏应对诈骗的能力(Burnes et al.,2017)。外部环境的变化加剧老年人决策行为的不确定,从而容易被欺骗(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以往研究发现老年人被骗的类型往往集中在医疗、消费、金融等特定情境(Dove,2017)。因此,老年人受骗脆弱性随着老年人个体特征和情境而变化。
医学研究揭示随着老龄化,个体的思维能力和方式都会发生变化(Ngo,2001)。额叶皮层功能受损导致老年人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在下降,轻信误导性信息的行为不断增加(Lachs & Han,2015)。老年人的信任感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提高(Schafer & Koltai,2015),倾向积极的情绪反应,也更容易相信伪善的诈骗者。研究发现老年人受骗脆弱性与性别、教育水平和年龄等变量显著相关(Alves & Wilson,2008;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FTC(2018)报告40岁至69岁之间的老年人受骗比例较高,女性老年人被骗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
老年人受骗脆弱性还与决策情境相关联。在医疗健康领域中,老年人更容易受到语言框架的影响(王惠芳,蒋京川,2016),由于疾病或死亡的威胁而产生的心理情绪增加老年人受骗的风险(Langenderfer & Shimp,2001;Boyle et al.,2012)。老年人无意识成分行为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从而使老年人更易受误导信息影响,犯错率更高(郭秀艳,张敬敏,朱磊,李荆广,2007)。在消费情境中,老年人更多地依赖包装和营销方式来做出判断,难以解读产品实际的信息和特征,从而增加受骗可能性(Ford,Trott,& Simms,2016)。在金融决策情境中,老年人对损失收益的错误感知导致老年人容易受到金融剥削(Schafer & Koltai,2015;Spreng,Karlawish,& Marson,2016)。
3 老年人受骗脆弱性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不同学科对老年人受骗的过程进行了讨论,针对老年受骗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内容主要集中在认知和行为两个方面(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目前研究涉及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理论主要有日常活动理论、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以及说服行为决策模型,从不同视角来解释老年人受骗的原因。
3.1 日常活动理论
作为个体犯罪被害预防的理论——日常活动理论(Routine Activities Theory)提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行为会诱发犯罪行为的发生(DeLiema,2018)。该理论假定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潜在地向不法人士提供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特征。例如,经常对电话推销者作出反应、打开垃圾邮件和在网上购物的消费者,更有可能遭受侵害(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日常活动理论还假设在目标缺乏适当保护或监督时,犯罪活动更有可能发生。当老年人缺乏有效的社会网络支持,增加其对外部或其他信息来源的依赖感,进而面临更大的风险(江明君,张欣之,胡峻梅,2014)。
根据日常活动理论逻辑,相对活跃的社会生活交流和广泛的消费经验使老年人暴露个人行为特征而更容易被骗(Pinsker,Mcfarland,& Stone,2011)。研究发现加入不同的社会团体、在互联网上购物或者使用电话会增加老年人被骗的可能性,因为在此过程中老年人向诈骗者提供了个人信息(Schafer & Koltai,2015)。Bosley,Bellemare和Umwali(2019)认为金字塔骗局就是与生活中的判断和决策相关,采用现场实验发现贴近生活的选择更容易使老年人相信骗局。老年人独居、社交圈缩小、有效资源减少等特点(Ngo,2001),也正是容易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个体特征。老年人在涉及退休决策、使用保险、医疗服务以及家庭中的死亡等事件而又缺乏外界提供的帮助,更容易成为诈骗的目标人选(DeLiema,2018)。
日常活动理论引入情境因素,通过日常活动中的行为更真实地反映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生成机理,为行为测量提供了依据。但是日常活动理论忽视了老年人受骗过程的心理决策机制(Pinsker,Mcfarland,& Stone,2011)。
3.2 社会情绪选择性理论
Carstensen,Fung和Charles(2003)根据行为动机与年龄变化的特征提出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强调个体对未来时间的感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有限,促使人们优先考虑将积极的情感作为社会目标。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时间知觉对社会目标的优先选择和社会同伴的选择偏好有着显著影响,进而可以解释老年人的行为和决策特征,特别是非理性的行为。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强调个体到晚年会将和他人建立紧密的情绪性支持视为首要目标。老年人倾向于尽量减少情绪上的消极经历,更倾向于把情感价值作为人生目标,并积极地记住对高价值诱因的积极情绪反应。Kircanski等(2018)基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对老年人受骗过程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证实高度积极的情绪使老年人产生了更多的风险寻求行为,老年人面对复杂的任务会犯更多错误。同时,在情绪调节引导下,老年人通过与他人交往来实现情绪状态的抚慰,进行有针对性和目标性的社会交往(敖玲敏,吕厚超,黄希庭,2011)。因此,诈骗者利用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与老年人建立强烈的情感联系,得到老年人认同与信任,使得老年人面对诈骗信息时,更关注其中的奖励线索,而忽视其他因素。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从情感需求方面证明老年人容易对他人采取正面评价,让老年人更容易信任他人(敖玲敏,吕厚超,黄希庭,2011)。信任和积极的情绪倾向让老年人面对陌生人的各种信息时,老年人愿意相信,也更容易被骗。但是,该理论过于强调情绪的作用,没有解释老年人生理状态的影响。
3.3 说服行为决策模型
Langenderfer和Shimp(2001)提出诈骗过程是施骗者和被骗者之间信息沟通和态度改变的过程,潜在被骗者的动机与内在状态影响着其对各种信息的评价和认知识别。他们认为本能驱动状态包括恐惧、饥饿、贪婪、性欲望等,强调本能驱动状态将个体的注意力转移到能够满足内心需要活动上,从而增加受骗脆弱性。Dove(2017)在此基础上提出说服行为决策模型(Decision making model of persuasion behavior),强调在可能受骗的情境中应考虑老年人接收信息的决策过程,并从个人需要和特征、生活环境、对信息可信度的解释和说服技巧等维度来说明被骗的原因。
在实际过程中,诈骗者通过唤起老年人的本能驱动状态,将老年人的注意力转移到预设的目标或活动,从而影响决策。Greenspan(2008)从行为的角度解释轻信变量对老年人受骗的影响。在诱导的轻信行为的操纵下,老年人由于情景、认知或所处的情绪状态被诈骗者操纵,难以识别虚假信息导致更容易被骗。Dove(2017)采用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发现说服和冲动可能会影响老年人对欺诈行为的谨慎程度,受骗过程中如高动机积极情绪、信任、易受说服等心理特点,解释老年人被骗局说服。
说服行为决策模型体现了受骗脆弱性的动态过程,解释了诈骗与个人行为和受骗脆弱性的关联,体现了个体易被说服的心理特点。该模型也表明欺诈者利用个体的动机、行为和环境进行针对老年人的诈骗,为老人做出错误决策的问题提供了依据。但是,该模型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实证检验,而且对受骗老年人的个体特征的描述并不明确。
3.4 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行为过程模型
日常活动理论、社会情感选择性理论和说服行为决策模型从不同角度对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进行了理论解释,但是都存在着一定不足(Pinsker,Mcfarland,& Stone,2011;Dove,2017)。目前研究探讨欺诈受害人的影响因素涉及与年龄有关的身体功能下降、认知障碍、情感和动机、信任、心理需求和情境,个体特征能够预测应对受到欺诈的可能性(Ford,Trott,& Simms,2016),现有的欺诈研究以及理论模型并没有说明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在被骗过程中的影响机制(Dove,2017)。针对老年人的认知以及动机态度,需要建立可广泛适用于解释老年人易受欺诈的运行机制。老年人受骗是个体、社会和情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的行为过程,受骗脆弱性模型应建立在老年人行为体系的基础上。因此,本研究从行为决策角度提出一个受骗脆弱性的行为过程模型,构建“个体特征—社会支持—任务情境—受骗脆弱性—受骗”的理论模型(图1),进一步理解涉及多因素多维度的老年人受骗脆弱性。

图1 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行为过程模型
首先,老年人受骗是一个动态的行为决策过程。老年人在任务情境中处理各种潜在风险的信息,需要对特定的信息做出筛选和判断。受骗脆弱性的增加导致老年人的决策出现偏差或失误,进而导致上当受骗。其次,老年人受骗脆弱性受到个体特征(生理和心理)、社会支持、任务情境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的个体特征理解为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同表现,老年人在生理功能上出现器官的衰退,以及精神上的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等),增加老年人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心理,让老年人难以识别和理解风险,直接影响老年人做出决策。但个体能力特征并不是老年人受骗的决定因素。由于社会对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的缺失,增加老年人与陌生人建立情感关系的概率,导致陌生人被信任后,成为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任务情境下,老年人倾向于避免消极的情绪体验,更多关注积极效应。最后,老年人受骗脆弱性可以预测老年人受骗的概率,但是并不是意味着受骗脆弱性程度高的老年人肯定会被骗。整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采用相应的干预措施影响社会支持或任务环境来预防特定的老年人被骗。
4 老年受骗脆弱性测量方法
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评估内容包括了主观评价和客观因素,但目前还没有存在一个公认的受骗脆弱性评估工具的有效标准。基于老年人受骗脆弱性测量内容特征,本文将测量方法归纳为主观性、客观性以及综合性三类测量方法。
4.1 主观性测量方法
目前大部分诈骗研究通过分析受害者的主观陈述,获得涵盖诈骗内容和过程的详细情况以及受害者的基本信息和日常生活方式特点(Lichtenberg et al.,2016)。另外,基于媒体新闻报道或法律案卷资料也可以分析受骗的过程(江明君,张欣之,胡峻梅,2014)。
在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研究中,自我报告法常用的方法是个案调查法,研究者针对某一领域设定系列问题,从而评价个体的特征。该方法既可以评估外显行为,也可以测量个体对环境的感受。Beals等(2015)将老年人的欺诈经历通过自我报告的形式转换成老年人诈骗受害者的全国流行率,建立一个以人口为基础的欺诈预测模型。研究表明老年人自我报告的抑郁症状和缺乏社会需要的需求对欺诈预测具有正相关作用。新闻媒体报道也是一种说明性的文体,有大量的事实材料,对事实的叙述都比较完整。王金水(2017)采取媒体报道的自我报告方法,对来自媒体中关于“老年人被骗”的新闻报道进行定量分析,总体把握老年人被骗舆情报道特征,但是媒体的报道本身可能存在着选择偏差。江明君等(2014)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法对派出所的受骗卷宗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将自我报告式的投诉数据转化为文本报告,总结老年人受害者的被骗的经验和过程。
在主观性测量方法中衡量诈骗的普遍程度来自受害者自我报告的发生率,许多老年人在被问及是否被骗时很有可能未能自我识别为受害者,容易产生错误的诈骗流行率(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自我报告法基于特定的案例,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很难保证,数据不能作为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准确证据。调查没有要求参与者描述他们所经历的欺诈类型,所有变量均为老年人的自我报告,自我报告数据分析方法本身还存在问题,老年人因记忆偏差,或者害怕以及耻辱等感受而导致报告内容不完整不准确,这使自我报告法的稳定性下降(Beals et al.,2015)。主观性测量方法由于是事后的回忆未能准确地反映老年人在具体的任务情境中决策变化的过程(Lichtenberg et al.,2016),而且情境和个体等因素使得结果存在个体差异(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因此,主观性测量方法得出的结论存在偏差,研究仅依据老年人描述的行为特征做出关于是否脆弱性的评估时,难以准确判断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过程变化。
4.2 客观性测量方法
脆弱性指标的客观内容应包含较为准确、符合事实的重要信息,权威性数据的来源更加全面,具有更高的可信度(Naudé,Santos-Paulino,& Mcgillivray,2009)。Andrew和Keefe(2014)依据加拿大健康与老龄化研究和全国人口健康调查的研究对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的二次分析数据,研究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人口学因素与受骗脆弱程度之间的关系,构建脆弱指性指数来衡量受骗脆弱性。Burnes等(2017)采用元分析方法来估计老年人金融欺诈和诈骗状况在美国的流行率,使用州或国家或地区级别的概率抽样并直接从老年人中收集数据。Burnes等在元分析中纳入了12项研究,使用混合模型和个人研究作为老年人金融欺诈和诈骗状况流行率分类的依据,分类分析老年人金融欺诈和诈骗状况。结果表明采用元分析方法描述特定欺诈事件衡量的受害程度明显高于使用单一的自我报告评估方法的研究,为今后研究提供了更为客观的依据。
研究者利用实验室研究揭示老年人心理机制,从情绪、认知以及说服与态度转变等心理学角度出发(郭秀艳等,2007;Bosley,Bellemare,& Umwali,2019),解析老年诈骗受害者上当受骗的过程(Dove,2017)。诈骗者使用的说服策略通常会引起老年人强烈的情绪唤起,Kircanski等(2018)通过实验检验诱导高唤醒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否会增加受骗脆弱性。研究将年龄较大(65-85岁)和较年轻(30-40岁)的成年人被随机分配到高唤醒积极情绪、高唤醒消极情绪或低唤醒三种情绪情境,测量参与者对误导性广告的反应来评估受骗脆弱性。结果显示高唤醒情绪显著增加了参与者报告的购买虚假广告商品的意愿。该研究有助于识别老年人特别容易受到欺骗的情况,为干预老年人受骗脆弱性提供了实验依据。郭秀艳等(2007)通过比较不同年龄被试对最初事件再认的表现,分析老年人易受暗示性的程度。实验结果表明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犯错,更易受误导信息的影响。
临床上的抑郁症状和社会需求表现可以作为心理层面脆弱性的客观依据。Lichtenberg等(2016)从心理层面测量抑郁症状和社会需求等心理受损程度等变量来分析对受骗的影响,通过分析HRS(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跟踪数据发现人口学和心理学特征能够预测新的欺诈案件,如低龄老年人、高学历以及情绪低落等。该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心理脆弱性变量能有效地识别可能受骗的老年人。Boyle等(2012)探索老年人防骗意识的变化与轻度认知障碍以及阿尔茨海默症的关系,对芝加哥市区老年人进行纵向临床病理序列研究。研究使用12项决策能力评估工具,在模拟诈骗环境的情况下,让老年人做出医疗保健决定,并对老年人的认知和决策进行评估。被调查者被问及6个不同难度(简单和复杂)的问题,通过问题评估信息的理解和整合,累计正确回答的项目数来反映老年人受骗的可能性。
老年人受骗脆弱性存在多因素多学科的影响,客观性的测量方法更多的是从一个角度或方面评估脆弱性程度,测量方法但仍未回答更全面的问题,如变量相互之间的影响(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在决策实验中,老年人在涉及分析的任务奖励、惩罚、风险的分类,会出现模糊的不同选择,影响研究结果(DeLiema,2018)。实验研究更多是作为受骗脆弱性的事后衡量标准,缺乏对受骗情境的完全模拟。另外,受骗脆弱性具有多维性和动态性,仅关注静态的衡量标准未能评估复杂和相关的总体结果和水平,需要考虑脆弱性的动态变化(Naudé,Santos-Paulino,& Mcgillivray,2009)。
4.3 综合性测量方法
老年人受骗可能受到如疾病、情绪、社会地位等多变量的共同影响,无论是从主观评价还是从客观因素来评估老年人受骗,都不能全面地评估老年人受骗的概率(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为克服单一测量来解释老年人易受骗的局限性,研究将影响受骗的不同因素整合在一起综合解释老年人受骗脆弱性。
传统的认知评估量表对老年人日常社会功能的预测不足,因此,综合评估量表既涉及主观内容也涵盖客观状况的描述,可以有效诊断老年人潜在有害人际交往的能力受损。Pinsker等(2011)基于原有认知测量标准和老年人的阅读习惯,设计了包含“易受骗性”和“轻信度”的社会脆弱性量表(Social Vulnerability Scale,简称SVS)。SVS作为一种整体的认知评估工具,评估老年人在日常语言中可能被称为“易受骗性”的内容,涵盖的老年人群体更加全面,可以有效应用于患有一系列神经功能障碍以及不同程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进行受骗测量。已有研究表明决策受损和认知能力下降可能是导致老年人受骗的原因(Schafer & Koltai,2015),但缺乏金融工具的测量。Lichtenberg等(2018)制定财务决策评定量表,结果表明决策缺陷与金融风险之间存在联系。研究依据个体在财务决策中的表现,评估金融风险对老年人决策能力和财务能力的影响,以此表明认知功能减退和决策障碍预测潜在的经济诈骗行为。Lichtenberg等(2019)进一步细化研究,补充具体的老年人案例,该研究将以个体经验为依据编制个人财务决策工具,产生临床上有用的风险评分,有助于今后建立与临床相关的评分系统,来评估临床中的老年人受骗脆弱性。Spreng等(2016)强调在社会互动情境中来分析相关决策能力,基于金融受骗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模型提出了经济能力测量(Financial Capacity Instrument,简称FCI)和日常生活决策能力(Assessment of Competency in Everyday Decisions,简称ACED)来预测老年人金融受骗的概率。
老年人受骗测量内容中涵盖多变量多学科,Moschis等(2011)提出了将多个研究方法集成到一个模型中,提出历史事件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简称EHA)模型作为析老年人易受骗的重要分析框架。EHA模型将一个渐进或突然的行为或心理变化表示为一个事件,并将所有事件进行建模以确定突变或渐进的概率。研究人员可以使用EHA模型来研究老年人在事件发生时可能增加的脆弱性,使用几种类型的变量作为协变量(例如其他事件、过程变量、个体和群体特征),同时测试这些变量是否改变个体的受骗脆弱性。Moschis等(2011)建议在生命过程分析形式下研究老龄问题,将稳定的变量与变化的问题相结合,可用于指导今后动态性的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研究。
综合性的测量方法涉及老年欺诈受害者的人口、社会经济、心理和认知特征等多个方面,可以测量更为准确的老年人受骗脆弱性,但综合性方法需要多门学科的知识以及技术。受到严重认知或其他障碍的老年人无法参与调查也不会自我报告受骗情况,从而更加需要分析老年人以往的生活经验等行为事件(Lachs & Han,2015)。
5 研究展望
5.1 拓展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内涵
老年人受骗脆弱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受到年龄、社会孤立和认知障碍等因素影响(Bozzaro,Boldt,& Schweda,2018),受骗脆弱性的不同定义及测量导致不同的实证结果。但目前关于受骗脆弱性都不够明确,没有一个广泛接受的描述解释老年人易受骗。未来研究应继续探究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内涵,并通过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提出一个针对不同类型受骗且广泛适用的老年人受骗脆弱性概念,对受骗脆弱性的实质做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不同文化情境中,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Andrew & Keefe,2014;Burnes et al,2017)。我国老年人容易对权威人士产生信任,老年人相信自称所谓的“医生”以及政府部门等权威信息,更容易陷入诈骗圈套。今后研究可以探究不同文化情境中的老年人受骗脆弱性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例如儒家文化、佛教思想等。同时,未来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内容将出现以下趋势:由现状描述性研究向评价与干预的方向转变;由犯罪学项目向健康干预项目转变,研究内容范围将涉及心理、保健服务、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
5.2 多学科的动态测量
老年人受骗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基于现实情况更加有必要对老年人受骗的流行情况进行有效的评估,为预防老年诈骗提供事实依据。关于老年人受骗的信息,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所开展的测量研究均有一定的结果(Boyle et al.,2012;Lichtenberg et al.,2016;Pinsker,Mcfarland,& Stone,2011)。一般情况下老年人数据来自非代表性的方便样本、投诉人数据库或第三方报告,带有信息偏见(Burnes et al.,2017)。老年人受骗脆弱性受到多个方面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仅使用单一或几种手段对老年人受骗进行测量,评估受骗流行率时并不完整全面(Lichtenberg et al.,2016)。虽然有学者考虑到在受骗过程中同时衡量多个变量对老年人受骗的影响(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但没有考虑脆弱性在受骗环境中可能发生变化。有学者注意到老年人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Dove,2017),通过心理学实验测量情绪与老年人易受骗之间的联系(Kircanski et al.,2018)。不同骗局情境下老年人是否存在不同的决策,哪些情境增加老年人决策受损的可能,还需要研究进行进一步探索。老年人受骗脆弱性具有动态化的特点,今后的研究需要形成与此对应的动态测量方法。此外,在银发经济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下,老年人的消费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更加需要多学科参与来动态测量和分析,确定老年人行为决策过程中关键指标和核心特征,有助于实现多方面测量老年人受骗脆弱性。
5.3 基于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协同干预机制
脆弱性的研究最终目的是能够为公共政策服务(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老年人受骗脆弱性的动态变化以及影响因素,决定了预防老年人受骗需要通过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因素与外部情境、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达到干预效果。未来干预老人受骗的过程可以以个体为中心,家庭、社会、政府依次由内向外衍生建立动态干预模型。个体干预,即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方式影响老年人自身行为决策,并结合老年人所处的社会和其他环境,考察低自制力、个人习惯和生活方式对老年人遭受的其他形式的伤害的影响(Mears,Reisig,Scaggs,& Holtfleter,2014)。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方式影响老年人自身行为决策,并结合老年人所处的社会和其他环境,考察低自制力、个人习惯和生活方式对老年人遭受的其他形式的伤害的影响(Mears,Reisig,Scaggs,& Holtfreter,2014)。家庭干预,直接给老年人家庭提供物质帮助和情感介入,方便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支持、精神慰藉。外部干预则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共同治理和协同。社会构建受骗老年人帮扶型的社会支持,社会团体和自发性社会组织的补充介入,媒体引导人们深入认识老年人被骗问题所折射出来的社会治理问题(Moschis,Mosteller,& Fatt,2011)。政府针对老年消费市场,从老年人的消费行为特征来规范不道德的销售行为,帮助老年人识别诈骗和抵制购买欺诈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