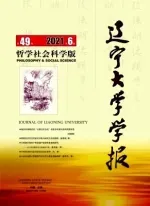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现实与民主根源
曾 森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美国是一个有着漫长民粹主义历史的国家,对于人民权利的伸张和对精英的反抗贯穿于两百多年的美国历史。美国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民粹主义总是与各种不同的政治理念相结合。在社会面临重大转型之时,民粹主义暗潮就会喷涌而出,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可以说,美国历史就是一部民粹主义兴衰史。“作为代议制政治的反映和产物,民粹主义就像装饰图案一样贯穿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1〕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塔格特断言:“没有民粹主义的一些常识,便很难理解美国的政治”〔2〕。同样,美国民粹主义又是如此具有代表性,“没有对美国民粹主义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民粹主义”〔3〕。
一、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与传统
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和精神,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的早期岁月。美国革命奠定了美国的基本政治信条,而这些信条决定了美国的历史道路和政治变迁。这场革命不仅让美国从政治上获得了独立,还释放出了美国人民的力量,奠定了美国民主的基础。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曾说:“革命不仅仅消灭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它还真正重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公众和国家权力,并产生了全新的大众政治和一种新型的民主化的官员。”〔4〕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基本信条,即自由、人人平等和对权力的怀疑,几乎都是在革命时代就建立起来了。美国革命“最为伟大”,“为后来的激情时期提供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模板”〔5〕。虽然存在着一些瑕疵,但在美国政治历史上,或许没有哪部文件会比革命之后所制定的宪法更能代表美国人对民主的追求。这部宪法的序言开宗明义,以“我们人民”的名义昭告天下,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最高理想是人民统治。通过革命和宪法制定,“革命一代的美利坚人绝不仅仅构建了新型的政府,更构建了一整套全新的政治概念体系”〔6〕,其中包括自由、民主和平等。
(一)美国民粹主义的起源:人民党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名副其实的民粹主义运动发生于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兴起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在这种背景下,独立于两大党的、自称代表人民的第三党开始崛起。1892 年,来自南北方的农民联盟建立美国第一个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党”(People’s Party),并制定了奥马哈政纲(Omaha Platform),阐述了该党的政治主张与理念。在被称为“第二次独立宣言”的奥马哈政纲中,人民党怒斥两党精英对立国精神的背叛,号召重建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并制定了货币、交通和土地的三大政纲。凭借着为人民发声的姿态和反建制、反银币的立场,人民党在1892 年的选举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获得一百多万(占总票数8.5%)选民票,这让人民党成为首个取得选举突破的第三党。但是好景不长,人民党在接下来的几年陷入激烈的路线斗争:走温和路线的“融合派”和走激进路线的“中间派”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两派的冲突持续到1896 年的总统大选。在那一年,人民党决定与民主党结盟,并支持该党的候选人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然而,人民党支持的布莱恩在总统大选中惨败,这重创了人民党的政治局外人形象及其在全国的影响力,人民党随之走向衰败。这场一度盛行全国,声势如虹的农民民粹运动也迅速淡出政治舞台。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人民党运动虽然在政治上未能成功,但却第一次向美国历史注入“民粹主义”这一词汇和精神。人民党运动和民粹主义理念对美国造成了持久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开创了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传统。一方面,人民党的奥马哈政纲在很大程度上了吸收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主张,开创了美国左翼民粹主义的传统。这场运动及其余波对于进步时代的政策,如实施对企业垄断的限制、劳动保障以及政治民主化都有促进作用。人民党所倡导的累进税率、国库分库等主张,之后也被两党吸收,并在罗斯福新政中就得到了实施。另一方面,人民党也开创了另一个政治传统:一个夹杂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阴谋论的右翼民粹主义传统。虽然并未明确列入政纲,但人民党也存在着潜在的排外主义和反现代性的政治倾向。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批评了人民党运动中存在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和阴谋论主张,并认为这场运动本质上是思想落后的农民所发动的反现代运动〔7〕。一些人民党人士深信犹太人组成的国际金融家所主导的政策破坏了小型家庭农场,推动了金本位制,是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源。同时,像马里恩·巴特勒(Marion Butler)这样的人民党领袖不时显露出对白人至上主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而这得到了不少人民党普通成员的支持。兼具左右翼色彩的人民党运动开启了民粹主义运动的闸门,为后世的民粹主义运动奠定了人民至上的基调。虽然分属不同的政治光谱,后世的民粹主义者无不效法人民党,尊崇人民的至高无上地位,致力于推动民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二)休伊·朗与乔治·华莱士
在20 世纪,人民党所开创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传统得到了民粹领袖的继承。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贫富差距的悬殊以及政府应对的无力助长了下层阶级的不满和要求财富再分配的主张。这时,一位具有超凡魅力、极具煽动性的民粹政治人物——休伊·朗(Huey Long)横空出世。1928 年,宣称为“小人物”(little man)代言人的休伊·朗,以“每个人都是无冕之王”的口号和反对“金钱权力”的主张,成功当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在就任州长职位之后,朗施行了诸多具有民粹色彩的“劫富济贫”的政策,深受民众欢迎,促使他在1930 年顺利当选参议员。1934 年,朗宣布成立“分享我们的财富”(Share our Wealth)协会,要求限制家庭财富不得超过五百万美元,年收入不超过一百万美元。同时,朗主张将对富人征税所得的收入用于推行免费教育、发放老人养老金和退伍军人补偿金,从而达到每个家庭都有“一处房产、一辆汽车、一个收音机,以及日常家庭用品”〔8〕的理想生活。这种要求再分配的左翼民粹主义虽然最后随着朗的被暗杀而归于沉寂,但却对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推动着美国政治的转型。
三十年之后,随着民权运动所带来的美国国家特性的剧烈转变,一种迥异于休伊·朗的右翼“反动民粹主义”开始兴起。反对民权运动、支持种族隔离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成为这种反动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华莱士的反动民粹主义的政治理念将反种族融合的观点与民粹主义杂糅在一起。华莱士自诩为人民(很大程度上是白人)的代表,把自己塑造成普通人的形象:穿便宜的套装,把头发光滑地梳向后面,坦陈他的偏好是乡村音乐和番茄酱〔9〕。同时,华莱士还对主导美国政治走向和推行种族融合的精英和建制派大力抨击。华莱士的这种反精英的态度常常与反对联邦政府、维护州权的理念结合起来。在华莱士看来,华盛顿的建制派依靠联邦权力推行的种族融合和平权政策是对美国传统的背离和对州权力的肆意践踏。在1950 年代,随着种族议题的凸显及对民主党支持民权运动的不满,华莱士开始从一位支持新政的民主党人士转变为一名高调的反民权运动者。1962 年,凭借着坚定的反种族融合和反联邦政府的政治主张,华莱士当选为阿拉巴马州州长。在就职演说中,华莱士宣称要“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在次年,华莱士尝试阻挡两名黑人学生进入阿拉巴大学就读,这让他名满全国。在1964 年的总统选举中,华莱士在民主党内的总统初选中对在任的总统约翰逊构成了有力的威胁。四年之后,华莱士卷土重来,这次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拿下了13.5%的得票率,并赢得了南方的五个州。
(三)1990 年代的民粹主义
1990 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时之间,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盛行于全世界,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为特点的新世界秩序开始确立。然而,随之而来的经济转型却导致美国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缺乏工会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同时,由于移民政策的宽松,大量来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挤压了美国本土劳工的就业机会。在两大党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美国国内的经济体系经历了重组,大企业和大资本坐享自由贸易的益处,但广大蓝领劳工阶层却因此面临失去工作和薪资下滑的风险。这种发展受益不均滋生了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和对新兴民粹主义力量的支持。
1992 年的总统选举中,两位处在不同政治光谱位置的独立参选人掀起了民粹运动风潮。他们都以政治局外人自诩,力图反对被精英主导的腐败政治。其中之一就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布坎南的竞选充满了草根主义的作风和言辞。他将自己的竞选比喻为“拿着干草叉的农夫”对抗“建制派”、华盛顿的所谓行家和政党领袖的运动〔10〕。在竞选中,布坎南抨击美国大公司与华尔街,并宣称:只要他当上总统,就“不会有更多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让华尔街银行家获益”〔11〕。同时,他还对受到主流政治人物所支持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表示反对。布坎南还是第一位大谈非法移民问题的总统候选人,并承诺重建国家边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移民问题。
布坎南对美国社会变迁的担忧也成为另一位民粹领袖——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竞选主题。在进入政坛之前,佩罗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也是IT 界的传奇人物。虽然坐拥亿万财富,但佩罗一直以政治圈外人自居,并将自己描绘成不支薪的人民公仆,以服务最大的老板——人民。对政治精英的攻击成了佩罗竞选的主轴之一,他将政治精英比喻成“绝缘于人民意志的政治贵族”,并誓言清理华盛顿的“谷仓”〔12〕。因此,佩罗的一大政见就是改造华盛顿的政治,并提出限制政府官员成为说客、强化政治献金管理、改革竞选和投票制度等方案。同时,佩罗巧妙地抓住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崛起,提出使用电脑建立“电子市政厅”(electronic town halls)以及推行电子公投的方式来改造过时政治的主张。在经济政策上,佩罗主张适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以鼓励美国制造的发展,遏制美国工厂和工作机会流失海外。凭借着独立的政治姿态和高超的政治沟通技巧,佩罗在拥有本科学位以上的中产阶级选民中大受支持,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商业领袖。在1992 总统大选中,佩罗获得了史无前例的19%的选民得票率,取得了美国历史上第三党最大的选举胜利。在四年之后的大选中,佩罗再次参加竞选,获得8.4%的选民票。佩罗和布坎南的竞选虽然未取得成功,但他们代表了美国劳工阶层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反抗,这种反抗在2008 年的金融危机重新被唤醒,并成为震撼美国政坛的力量。
二、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左右共奏
(一)后危机时代的民粹主义:茶党与占领华尔街
2008 年秋季,源自华尔街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导致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败坏了美国民主的信誉,动摇了美国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信心,从而激起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民粹反建制运动。茶党(Tea Party)运动的兴起,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作为一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茶党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对奥巴马当选和执政期间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的反弹。奥巴马的黑人身份和其执政时期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对银行和汽车业救助计划,特别是平价医保法遭到了保守派激烈的反对。在这种背景下,茶党借用建国时代的“波士顿茶党”的名称,要求对政府的权力扩张和税收政策进行限制。各式各样的茶党组织都对奥巴马治理下失控的政府支出、高额的税收、对大财团源源不断的财政救助以及政府规模和权力的扩张等愤愤不平。虽然茶党团体之间从未产生过一个共同的政策纲领,但是有些原则性的议题还是取得了各个团体之间的共识。“有限政府,责任财政和自由市场”成为各类茶党组织的共同信条。茶党的一个组织声明其目标在于给全体美国人“更低的税收,更少的政府以及更多的经济自由”〔13〕。一些评论人将茶党的茶(Tea)解释成“征税过多”(Taxed Enough Already)。
凭借着高超的动员能力和对网络的运用,茶党运动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声势浩大,风头一时无二。社会学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威廉森(Vanessa Williamson)统计,在茶党运动处于最高峰的2011 年,茶党团体有多达十六万成员,这还不包括接受茶党理念的数百万人们〔14〕。同时,作为共和党的一个分支,茶党成功地推动了共和党向更加保守主义的方向转变〔15〕。随着茶党运动的势头日涨,茶党分子开始在选举中施加影响力。在2010 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茶党运动的强大动员能力。
2011 年,右翼的茶党运动势头刚过,不满于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华尔街贪婪的左翼人士走上街头,掀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随后蔓延到全美的“占领运动”是对大企业、大银行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反抗。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华尔街银行家的贪婪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导致2008 年金融危机的源头。但是,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 年,当数百万美国人失去房子和工作,为债务所困,为工作而奔波的时候,作为这场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却在大发巨额奖金,这引起了广泛的大众愤怒。更为严重的是,大企业家和大银行家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有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资本所主导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充斥于华盛顿,致力于推动美国政府对富人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取消银行和企业监管,等等。这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政治腐败刺激了美国民众的神经,也让占领者忍无可忍。在一个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网站上,出现了一句简单的口号:“99%决定不再继续容忍金字塔顶端1%的贪婪与腐败”。这个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口号也成为这场运动的最好注脚。
(二)民粹主义高峰:桑德斯和特朗普
茶党和占领华尔街风头刚过,美国就在2016 年迎来民粹主义的高峰。在该年的总统选举中,来自左右两翼的民粹领袖,猛烈抨击美国的建制派和政治精英,不断打破行之有年的政治规则和大众的政治预判,掀起了民粹主义的高潮。
在意识形态的左翼,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民主党的初选中意外地刮起了一阵民粹主义旋风。在2016 年党内初选中,桑德斯虽然以民主党的身份角逐,但却依然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并号召要发动一场“政治革命”(political revolution)。作为长期与政治精英和两大党保持距离的非主流政治人物,桑德斯始终以政治局外人身份自居,其竞选颇具平民主义风格。在政治理念上,桑德斯继承了从人民党、新政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左翼政治传统,其竞选聚焦于美国日益加剧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及经济权力对政治的腐蚀。因此,桑德斯提议,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捍卫中产阶级,必须对富人进行加税。除了经济和社会议题之外,桑德斯还对美国民主本身的衰败忧心忡忡。桑德斯所定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效法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政府反映普通民众的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反映亿万富翁阶层的利益。然而,随着金钱日益渗透美国政治,“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腐败,美国民主的根基已经被削弱”〔16〕。他身体力行,拒绝接受华尔街和大富豪的政治献金,并誓言改变倾向于寡头而非美国大众的竞选融资体制。
凭借民粹主义的竞选风格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桑德斯的竞选获得大量支持。桑德斯对于经济不平等的抨击吸引了大量持相同观点选民的支持。在竞选过程中,桑德斯所到之处,吸引了大量的群众,特别是四十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的支持。凭借着强大的选民基础,桑德斯在民主党的初选中过关斩将,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初选的胜利。不过,作为反叛性的政治人物,桑德斯最终惜败于民主党的老将希拉里·克林顿。尽管最终折戟,但桑德斯所造成的“桑德斯旋风”却撼动了美国政治,迫使希拉里和民主党向左转,也为左翼民粹主义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桑德斯革命虽然失败,但美国最终选择把另一位民粹领袖送进白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意味着民粹主义力量首次进入美国的权力之巅。在从政之前,特朗普曾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主持了一档知名的真人秀节目。在这些商业和娱乐活动中,特朗普显示出自己高调的个人性格、口无遮拦的言语风格和高超的表演能力。这些能力最终在2016 年的竞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促使他攀上总统宝座。
与桑德斯一样,特朗普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人民”,自诩为受到精英遗忘的“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在特朗普的建构下,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被视为是在数十年以来,受到去工业化和全球化冲击,受到东部自由派精英忽视,并被自由派媒体斥为无知大众的中西部普通民众。在其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宣称:“2017 年1 月20 日将作为人民再次成为这个国家主宰者的日子而载入史册。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再也不会被遗忘了。”同样,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反精英和反建制派的倾向。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极力抨击华盛顿的建制派在处理移民和贸易等问题上的“无能”和“腐败”。虽然以共和党的身份参选,但特朗普自称为政治局外人,并不惮于嘲笑共和党的建制派,并宣称要“排干沼泽”(drain the swamp)”,彻底改造美国政治生态。同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表现出对文化和社会精英的强烈不信任。与其他人相比,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来自中西部地区,对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东西海岸主流媒体和大学保持着很深的疏离感的低教育水平群体。出于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在政治沟通手段上,特朗普倾向于绕开传统的主流媒体,而以竞选造势和推特来直接诉诸民众。与其他右翼民粹主义一样,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有时伴随着种族化意象的“他者”而存在。这种民粹主义与排外倾向的本土主义相结合,拒斥那些来自非本共同体的“他者”。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以限制主要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穆斯林涌入为主题,并在执政之后实施了一系列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政策。上任之初,特朗普就陆续推出了禁止主要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入境的“旅游禁令”,强化对来自墨西哥等拉丁裔非法移民的管控,并一直试图在南部的美墨边境建一堵长城以阻遏非法移民的涌入。特朗普的政策主张继承了美国内部存在的排外主义传统,也呼应了全球化时代反移民、反全球主义的时代逆流。如果说桑德斯代表的是人民党所开创的反对大资本和大银行的左翼民粹主义传统,那么特朗普所代表的则是人民党所开创的反对移民和捍卫传统生活方式的传统。
从人民党到特朗普的崛起,民粹主义运动几乎贯穿于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民粹主义构成美国政治的基本底色。与其他地区的民粹运动相比较,美国的民粹主义具有一些独特之处。第一,就发生频率而言,美国民粹主义更具有强烈的间歇性和阵发性的特点。塔格特曾说:“民粹主义是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常常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上的剧变。但它却总是昙花一现,不久便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17〕民粹主义的这种突发性和间歇性在美国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从人民党运动以来,几乎每隔数十年,民粹主义就会以席卷之势突然而至,而又在不久之后归于沉寂。这点迥异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运动。在拉丁美洲,民粹主义势力时隐时现,长期存在。在民粹主义同样盛行的欧洲,虽然其政治影响起伏不定,但民粹主义政党是长期存在的。有些民粹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浮沉数十年之久。第二,美国民粹主义的阵发性与其组织形式不无关系。在欧洲,政党是主导民粹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而在美国,主流政党常常是建制派政治的捍卫者,而小型政党则难以在政坛掀起风浪。自上而下的个人领导和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是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常见组织形式。欧美不同的选举制度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欧洲的议会制度和比例选举制为民粹政党提供了更多生存发展的空间,而美国的多数主义和赢者全拿的选举制度限制了民粹政党进入政治主流。因此,美国的民粹主义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参选人的政治话语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18〕。第三,就意识形态而言,左右民粹主义的共奏塑造着美国的政治版图。正如卡津(Kazin)所说,在美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且往往相互竞争的民粹主义传统:即左翼的和右翼的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的人民理念建构于阶级而非种族和宗教之上,将其斗争矛头指向上层的企业精英及其在政府内的帮凶,斥责他们背叛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而右翼民粹主义的人民概念则带有更强烈的种族意涵,并指责上层精英和下层懒惰的阶级组成了违背中产阶级的联盟。这两种民粹主义传统都源于人民党运动。人民党一方面试图将美国的政治体制从“金钱权力”手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对建构出白人为主的人民意象,保持对外部势力的警惕。前者得到了休伊·朗、占领华尔街和桑德斯继承,成为左翼民粹主义的主旨;后者则对后世华莱士、布坎南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美国民主的悖论与民粹主义信仰
从人民党到特朗普,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构成美国政治一个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阴影。民粹主义的思潮蛰伏于美国政治的边缘和底层,常常在社会面临巨大转型和危急时刻喷涌而出,形成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那么,为何民粹主义总是与美国历史如影随形呢?民粹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一)民主的悖论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漫长的民粹主义传统根源于民主制度的内在悖论。有别于古典时代的希腊直接民主,当代的代议民主政体事实上是一种混合政体,其基本框架来自两种不同的传统:一是由法治、捍卫人权和尊重个人自由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是要求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民主传统。一方面,民主是一套能够维持统治的象征性框架;另一方面,民主代表着人民主权的体现和人民意志的表达。现代民主不但是“人民统治”的回归,也融入了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等理念。卡诺凡将民主的两个面向分别称之为“救赎的”和“务实”的面向:前者是指代表人民主权、平等与自由,人民有同等的机会参与政治理想,后者是指让民主政治得以运行的法治、代议政治、政党竞争、利益团体、周期性的选举等〔19〕。民主政治有着相互矛盾和相互依存的两个面向,即“救赎的”和“务实的”的面向。两者之间所长期存在的鸿沟为民粹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民主的“务实”面向要求建立一套规训冲突和消弭暴力的制度。用普沃斯基的话说,民主可以让人民“要选票而不是子弹”(ballots,not bullets),建立一套“不用相互杀戮来解决冲突”的制度〔20〕。相应的,民主的救赎面向指的是“民意如天”(Vox Populi, Vox Dei)和“民有民治民享”为原则的政府体制。因此,民主的救赎面向要求释放民意的力量,通过政治来达到拯救(salvation)。因此,民主的救赎愿景的内核是人民主权:人民是合法政治权威的唯一来源,当人民能真正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才能达到人类的拯救。民主的务实面向则是将民主视为通过各种规则和惯例来和平解决冲突的机制。民主的务实面向是尊重和依赖制度,而民主的救赎面向事实上具有反制度的冲动,并试图用直接和即时的民意绕开制度的束缚。民主的两个面向是相互冲突和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两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没有救赎面向的实用主义无疑是腐败的,而没有实用面向的政治救赎是难以成功的。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现代民主有赖于人民主权和代议制原则这两大支柱的结合:前者为民主体制提供合法性支撑,后者让现代民主能在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国家中存活〔21〕。因此,现代多元民主就陷入了一种永恒的悖论:民主的运转必须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建立更多的民意输入的政治渠道,但又必须建立一套务实的制度来保障人权,限制民意的肆虐,从而维持政体的稳定。这就为民粹主义思潮的滋生提供了广阔的土壤与空间:一方面,民主的理念为民粹主义提供道德的制高点和理想,“权利归于人民”成为民粹主义最为有力的动员工具。另一方面,民主实践的惨淡在这种伟大民主理想的映照下显得尤为刺眼和难以接受。这就是为何民粹主义总是在民主失灵和失范的地方最有市场,最有力量。事实上,民粹主义是以“民主”的原则来反对(代议)民主。
(二)美国民粹主义的民主根源
这种民主的悖论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根本上说,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植根于美国民主理想和民主实践、美国国家信条与日常政治之间持续存在的、难以调和的冲突。美国政治的根本冲突点在于其崇高的政治信条对几乎所有奉行现实主义的政府制度构成持久而有力的挑战。美国国家信条和政治现实的冲突构成了美国政治斗争的主要来源,也成为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人民统治的国家信条成为后世一代代美国人挑战美国现实政治的标杆。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正当性和强大的政治号召力,根本在于美国信条对美国政治现实提出了难以达到的宏大理想。
长久以来,美国的国家认同都是由一套信念来定义的。欧洲的国族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之上,与此不同的是,美国的国族认同则建立在信条和理念之上。正如亨廷顿所说:“美利坚信条的政治信念一直是民族认同的基础”〔22〕。与其他有着相同种族和共同历史的国家不同,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因此,美国的政治认同并非建立在种族和文化之上。“美利坚信条的政治信念一直是民族认同的基础”〔23〕。其中,对于人民的颂扬和对于平等的追求构成美国信条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美国政治革新的根本动力。
然而,除了理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追求,美国的政治还具有现实和理性的一面。光靠民主理想无法在一个地域广阔、种族多元的国度建立可供运行的民主。对于建国之父来说,现实面向的考虑比理想面向更重要,维持联邦的统一比释放人民意志更加紧迫。同时,有鉴于民主本身所带来的弊端,美国的建国之父建立的是一个复合共和制度:用分权制衡来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用宪政主义来捍卫人民自由,用精英统治来维持政府运行。因此,美国的民主试验开始于一系列原则上的妥协和综合:为了维持联邦的统一,避免南方的反弹,违背“人人生而平等”的奴隶制得到容许;为了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为了解决州和联邦的冲突,分权的联邦制是必要的;为了达致小州与大州的平衡,一个不按人口数量分配议席的参议院建立起来,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两院制。
这种现实主义的制度设计是有必要的,是维持美利坚合众国长治久安的基础。然而,这就是为何美国的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怀旧主义倾向,美国各个时期的民粹主义者的共同诉求是不满当权派背叛美国伟大传统,要求“重夺我们的国家”:人民党怒斥执政者背离了美国伟大的共和传统,并宣称要恢复共和政体,交到人民手里;休伊·朗虽然要求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为理想,但也哀叹美国精神的失落;华莱士抨击华盛顿的自由主义精英用粗暴的方法推行种族融合和平权,以民主的名义呼吁捍卫州权这一建国之父所留下来的传统;佩罗和布坎南则对美国民主制度和传统价值观被大政府和自由主义精英侵蚀感到忧心忡忡。在近期,桑德斯将金钱和不平等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和旧有的完美政治的想象结合起来,特朗普则用煽动性的语言,危言耸听地警告支持者移民和伊斯兰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和生活的威胁,并宣称要“使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因此,对于建国信条的追忆和对于政治现实背离的不满构成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基本论述。然而,不同光谱上的民粹主义思潮对造成美国国家信条与政治现实断裂的原因的认识各有不同。在人民党、休伊·朗、占领华尔街到桑德斯一脉相承的左翼民粹主义的政治话语中,东部商业阶级、银行家和华尔街大亨等经济精英是导致美国民主失范的根源。而从人民党、华莱士、布坎南、茶党到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则将移民、少数族裔认为是危害美国国家特性和民主制度的根源。
这种通过对于美国民主传统的追忆来反抗政治现实的做法使得美国陷入内在的失衡之中,造就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为民粹主义的滋生奠定土壤。第一,对于建国民主理想的憧憬导致了美国人对所有现实的政治权力的本能怀疑态度。正如亨廷顿所说,“美利坚信条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反对政府”〔25〕。怀疑政府、反对权力是美国政治的永恒主题。这种反政府、反权力的政治文化贯穿于美国的历史,普遍受到左派和右派的接受。于是美国独特的联邦主义制度,反权力的政治文化常常以反对华盛顿和联邦政府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美国民粹主义政治话语中,地处联邦中心的华盛顿已经被利益集团、游说分子所绑架,而人民权利则系于各州和草根组织。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反权力和反政府倾向为民粹主义者的动员提供舞台和话语。这种反政府的道德观让美国人对于任何务实主义的制度设计都愤愤不平。民粹主义者很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反政治、反华盛顿的社会气氛。虽然民粹主义者总是自称为“局外人”,但在美国,这种政治宣称的号召力尤为强烈。第二,强烈的民主崇拜和平民主义的社会结构意味着美国社会具有强烈反精英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在美国历史上,反精英情绪遍及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光谱,充斥于美国日常政治话语之中。受到憎恨的精英阶层不但包括盘踞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主导华尔街的经济精英还包括知识精英(intellectual elite)。迥异于其他西方各国,知识精英在美国遭遇到强烈的不信任和怀疑。在美国历史上,对于知识分子、高等教育和媒体的怀疑始终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一些群体之中。霍夫施塔特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1950 年代出版了《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并剖析了反智主义存在的渊源,认为美国人的生活中充斥了反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26〕。在这种反智主义的文化下,民粹主义者可以通过罔顾事实和信口雌黄来获得支持,谋取政治动员。在互联网时代,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的“后真相”更推动了民粹主义的滋生。第三,阴谋论是美国民粹主义者所热衷的政治动员策略。极度夸张、多疑和天启式的阴谋论世界观,总是在美国获得可观的支持〔27〕。通过散布和利用阴谋论,民粹主义者挑动大众对特定精英的反对,营造一种风声鹤唳的政治气氛,从而谋取政治支持和利益。在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者散播和利用了形形色色的阴谋论:人民党对于国际黄金团伙利用各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制造阴谋的想象,对犹太人试图控制美国和全球金融体制的阴谋论焦虑,对共济会阴谋对抗共和政府和背叛国家的警惕,对罗马教会密谋控制美国政治的诋毁以及对国际金融家试图建立全球性统治秩序的虚张声势,等等,在美国历史上都屡见不鲜。在近期,特朗普更是一位编造和散播阴谋论的大师,随着他崛起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阴谋论被编造和散播出来:从奥巴马的出生地事件到科鲁兹父亲参与肯尼迪遇刺案,从宣称911 穆斯林庆祝到渲染墨西哥移民的威胁,阴谋论的制造几乎与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如影随形。霍夫斯塔特认为,“偏执风格是我们(美国)公共生活中一个古老且反复发生的现象,它常与表达怀疑与不满的运动联系在一起”〔28〕。这种偏执的风格造成了美国社会注定陷入一种普遍的不满和愤怒情绪之中,为民粹主义酝酿潜在的星星之火。在社会转型和政治危机出现之时,这种星星之火就会呈燎原之势,成为民粹主义的熊熊大火。
四、结论
揆诸美国两百多年的政治史,民粹主义的运动此起彼伏,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本底色。美国的历史是一部“完善联邦”的奋斗史,也是一部民粹主义的浮沉史。李普塞特将民粹主义视为美国信条的基本原则之一〔29〕。卡津认为,美国政治存在着“民粹主义的信仰”,民粹主义的主题一直贯穿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中〔30〕。民粹主义就像美国政治的伴影,是检验美国民主试验是否达到建国理想的晴雨表。
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衡量,民粹主义运动对美国的民主历程影响如何呢?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对美国历史的认知,更影响到当下美国政治的走向。传统的主流观点赋予民粹主义负面的内涵,将民粹主义视为民主的失范和病态。但是,对美国的民主试验而言,民粹主义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所释放出来的消极能量对美国民主投下了阴影,而某些积极能量则推动了民主的进步。
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运动一样,美国民粹主义的消极面对美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不少负面的影响。民粹主义对于个人领袖的崇拜和对于美国制度的蔑视的确曾经冲击到美国立国之基的代议民主和分权制衡。在1930 年代,人民一度担心,像休伊·朗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如果保持崛起势头,最终登上总统宝座,美国可能会步意大利和魏玛德国的后尘,成为一个个人独裁国家。同时,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可在某种程度上煽动了对少数族裔和外国移民的敌视。在排外主义者看来,美国是一个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为主体的国家,所有不符合这种族文化特性人种和文化都是对美国的威胁。与排外主义结合的民粹主义在美国可谓历史悠久,一脉相承,其敌视对象也随时代而改变:一无所知运动对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人民党对来自中国的劳工,华莱士对非洲裔美国人,特朗普对穆斯林和拉丁美洲的移民,都抱持深深的敌视和排斥。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民粹主义事实上是对美国信条的挑战,也违背了多元化的时代潮流。
另一方面,美国民粹主义运动也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注入了新的政治能量,促进了美国制度的自我更新。其中表现为以下几点:(1)民粹主义运动将那些受到政治精英和建制派排斥的群体和人民动员起来,提升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民粹主义者以“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表自居,在美国历史上的历次民粹主义运动中动员了因大资本而利益受损的来自西部和南部的农民,受困于大萧条底层阶级,恐惧种族融合的南方白人和因去工业化、自动化和自由贸易失去工作和福利的蓝领工人。(2)提出了新的政治议题,推动了美国的一些民主化改革。(2)民粹主义运动凸显了被精英和职业政客所忽视的重大议题。例如,19 世纪后期的美国,大资本和大银行变得越来越强大,美国政治有走向寡头化的倾向。然而,主流的政治势力和人物对此三缄其口,甚至与寡头暗通款曲。独立于两大党的人民党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挑战,并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这推动了美国政治的转型,深化了美国的民主化。(3)美国民粹主义运动推动了国内的民主化改革,为不断僵化的体制注入活力。人民党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却推动了包括企业监管、秘密投票和参议员直选在内的改革。同时,这场运动的余波对进步时代的政策,如实施对企业垄断的限制、劳动保障以及政治民主化都有促进作用。同样,休伊·朗所对不平等的关注也促使罗斯福展开“第二次新政”,建立社会保险法及对富人征税。
虽然存在种种负面影响,但通过扩展政治参与、提出新的政治议题与推动制度化改革,民粹主义事实上是美国政治的一股变革性力量。这种根源于美国信念本身的潜在的变革力量推动美国的制度革新和社会进步,而不会对美国的制度本身构成全面性否定。正如卡津所说,美国各个时期的民粹主义者共享一套价值理念,因此他们可以通过批评和挑战而非全面颠覆来改革现有的制度。“通过民粹主义,美国人可以抗议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而无须彻底否定整个体制”〔31〕。对于以至高无上的民主理想为参照的民粹主义者来说,美国的政治制度远非完美。但是,通过一次次的民粹运动,美国一步一步地建设成一个更完美的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