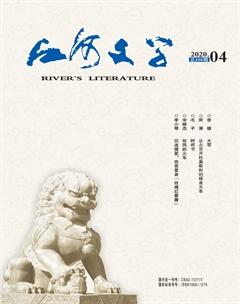体恤之诗(组诗)
毛子
晚安
夜里,穿过空荡荡的街口
看到马路一侧,一个环卫工
放下手中的扫帚,蹲在
绿化隔离带旁
掏出自带的干粮和饮水
悄悄的用餐。
我为我冒失的经过,感到不安。
我放轻脚步,
但还是把一种歉疚留在那里。
我想到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
都像他桔黄背心上,沾着的一小块灰
平凡、琐碎、微小。
穿过几个路灯和它之间的黑暗
我离他越来越远
我的身后,是这座城市,
这个世界,这个夜晚
它们因为一个人,变得柔软。
已经是午夜,该是道晚安的时候
但我不需要这些
因为那个蹲在扫帚旁的人,他身上的那一小块灰
就是这个世界的晚安。
时间书
天空留下来,已经
很多年了。
天空下的山川和流水
也留下来
很多年了。
很多年,一个鲁国的书生
面朝大河,不能自已
很多年,有人走下了幽州台
有人完成了《剩山图》
很多年,只是一瓢、一念、一须
一片汪洋都不见。
很多年,软体生物
遇见了造山运动。
我那类人猿的父亲
开始了直立的行走……
中和反应
牧民的转场,是否适用
两支对抗的球队。
床头的周作人和鲁迅,同样的好。
他们像两把雨刷
刮洗我的视线。
我无法看得更远了
而我的骨灰跑过来,抱紧
我现在的生活。
这是我对你如此紧迫的原由吗
突然明白历代的帝王
为何都想不朽。
哦,阿房宫、金字塔、兵马俑……
在热爱的后遗症中
我把它们再一次堆积
——用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身体
和我们的惊恐
翁牛特旗沙地,给德东
沙漠并不渴望了解,它只
保持它自己。
我们从千里之外赶来,就想看看
拒人千里的东西。
拒绝越来越稀有啊。想想这世界
人们总需要太多,唯独缺少
不需要的能力。
可以没有吗
可以不要吗
可以在他们的正确中
完成不正确吗
如果有一种
和盘托出而又守口如瓶的事物。
眼前的沙漠算一种,我们的寡言
是另外的一种。
小情诗
我怀上了你
无法堕胎。
一个男人
怀上一个女人
无法堕胎。
神说,凡动胎腹者
不可恕。
我并非听神的话
而是怀上了
我的神……
体恤之诗
原谅地图的误差
特别是古代的地图。
原谅大西洋
一直呆在西半球。
我那没有见过世面的母亲
不知道時差为何物。
原谅分子和分母
一辈子都不能平起平坐。
卡在圆周率的小数
永远没有透气的时候。
原谅白天,原谅夜晚。
原谅岁月仅剩下这两个
陪伴我们的
濒危物种……
造就
植物们从不挪动半步,它们是怎样
遍及了世界。
七大洲抛出的问题,能不能
让四大洋去解答。
太大的问题,穿在每一件事物上
都那么的得体。
想想从前的海藻,后来的森林
想想花粉在风中受孕
你我在人山人海中相遇。
这样的造就,这样的奇迹
它们说不清,道不明
却既成事实。
沙漠课
我见到的
最大的
软体动物。
不是陆地上的蛇
也不是海洋里的巨型鱿
而是内蒙古高原西部
库布齐沙漠。
就像亚马逊流域
蛰伏的鳄鱼
用全部的软组织
集聚爆发力。
库布齐,用它的光天化日
告诉你
——一览无余,是另一种白内障
毫无遮拦,是另一种强迫症
而过于炫目的光明,则是
另一种黑暗。
圆
圆从苍穹、果实
和乳房上
找到了自己
它也从炮弹坑、伤口
穷人的空碗中
找到了
残损的部分
涟漪在扩大,那是消失在努力
而泪珠说
——请给圆
找一个最软的居所
所有的弧度都已显现
所有的圆,都抱不住
它的阴影……
夜行记
群峰起伏,仿佛语种之间
伟大的翻译
就这样穿行于峡谷之中
我们谈起了世事经乱
——谈起简体和繁体是一个字
弘一法师和李叔同,是一个人
昨天和明天,使用的是同一天
当谈到这些,天地朗廓,万籁寂静
惟有星河呼啸而来
像临终关怀
数显表
确立一种简洁、精准
而包罗万象的语言。
这是我从一个数学家那里获取的。
万物隐藏它的数显表,行进在
十进位制的大军中
——三围、空气质量、战争规模、贫困线
福乐彩、护舒宝的纯棉度、历史进程、经济指数
离婚率、核当量、无限可分的原子……
我想起民间的唱丧人,在守灵夜唱到:
——“天空好比鸡蛋清,大地才是鸡蛋黄。”
那么,我可以从混沌的世界中
描述一个少女的明亮吗
——这宇宙的第二种光速
这个沉沦世界升起来的
阿基米德浮力
责任编辑:邱红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