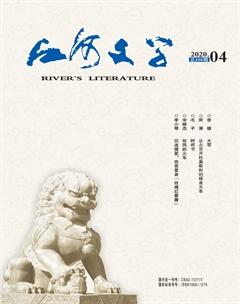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绿皮火车
阿满
如果是一只鹰,会看见一条灰白带子曲曲弯弯伸向天际,墨绿色条虫来了,在广袤高原的脊背上拱动,时而喘息时而停顿,更多时候却是坚定不移地向北、向北——这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
锡林郭勒草原被割开了,列车坠入了无边的厚实。白云像一只只瓷盘倒扣在绿色桌面上,一场盛大的美餐流水席就此展开。许多俄罗斯作家从迷雾中走来,契诃夫推了推鼻子上的眼睛说,为了写《流放地》,他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在泥泞中跋涉,在沼泽里找路,与瘦骨狰狞的野狼相视而立,与神情忧郁的伐木工无声饮酒,而当抵达太平洋西岸韃靼海峡时,他沮丧地说,这是一条世界上最长最不像样的路。他的话传到了一个大胡子男人那里,这个男人叫沙皇尼古拉二世,于是在一八九一年放下了第一条铁轨。接着,俄罗斯人用二十五年的时间,冒严寒顶高温,人拉、肩扛、铁锹铲、鹤嘴锄挖、手推车推,终于像蚂蚁啃骨头一点点修完了这条铁路。
二零一八年,快节奏慢行走是一种奢侈。从北京到莫斯科一共有七千六百九十一公里路程,它纵贯蒙古国南北,穿过俄罗斯联邦的十四个省、三个地区、二个国家和一个自治区。跨越十六条欧亚河流,停靠三十四个站点,经历八个时区和二十多个原住民族居住地。它上高原,入盆地,跨极寒地带,穿越原始森林,走苔原和荒漠,沿途阅尽风格迥异的景致,领略各色人群的文化。哦,如果还能浪漫,就带上一束红玫瑰,用十八岁的心脏,想象与一个英俊的苏联军官相恋,他们有着著名演员裘德·洛那样的面容,深邃的眼睛可以杀死任何一个狙击对手。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行程,那就是有最新奇的体验和最密集的冲击。
我是第二次去俄罗斯,兴奋像潮水一样涌来,因为这次我们要乘坐绿皮火车去,六天五晚行走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原野上。总共有六个女人成行,叶姐,彭姐,我,还有凤、小颖和小莉。
我为行程做准备,首先进入那种氛围,朝书架上一看,耳边就有人在喊,葛利高里——葛利高里。葛利高里是一个哥萨克,他属于一条河,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的顿河像一个精灵穿行于苍茫,也穿行于我们年轻的记忆。有那么一会儿,我陷入了日瓦戈医生的风雪里,当年我是多么喜欢这部书啊,它引导我走向文学的秘境,我爱这不知名状的创作激情。接着,小莉发来了冯骥才老师的《乐神的摇篮》和《俄罗斯双城记》,我读得畅快,也对即将到来的行程热切地期待。
有人说,了解俄罗斯就要了解西伯利亚大铁路。更有人说,俄罗斯得去三次。第一次跟团走,第二次三五成行,第三次一个人慢慢走,进林子住村子,边走边撰写风尘。我已经有了第一次经验,相信第二次会更有收获,在这之前,我要展开身体迎接际遇,直至在自己的秘密通道里雀跃奔跑。
出发了,北京火车站的嘈杂像过电影,推过来搡过去,不一会儿到达车厢。K3次,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这就是我们的车,一律软卧,四人一个车厢。
车轮弹着琴弦伴着人声。很多时候,小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用相机捕捉精彩。我托着腮帮子凝视远方,十分庆幸自己能在画中行。看得意了,祈求下辈子当一条河流,河流是涌动的生命,目标是大海,沿途阅尽斑斓。当岩石不好,不能行走是最大的悲哀。我渴望看见更多的人群美食和另辟蹊径,我爱这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流动生命。
五天六晚最大化的舒适是我这个小团长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开始考察车上方便与否。绿皮火车是旧火车,小时候不知乘坐过多少次,久远的亲切气味涌来了,像奶奶抚摸我的脸颊。开动了,咣当咣当,耳朵里灌满了金属声。过道的地毯很新,走上去软绵绵晃悠悠,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开水炉是烧煤的小锅炉,在两节车厢的当中,洗漱没有热水供应。餐车在最后,中国境内吃中餐,蒙古国境内吃蒙餐,俄罗斯境内吃俄餐。中餐价格过得去,蒙餐俄餐老贵,彭姐带了很多面包和方便面,她安排得很周到。
我问彭姐洗澡怎么办。她说放心会有办法的。我放不了心,四处寻找她讲的那个办法。叶姐也在找,不一会儿回来了,很神秘跟我们说,猜猜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刚才那个列车员说可以给我们提供热水洗澡。乌拉——我们高兴得大叫起来了。
其实是一种经验。列车员教我们把一根大拇指粗的塑料管子接在锅炉笼头上,拉过来,通过壁上一个小洞,水就送到厕所里来了。在面盆里用凉水调一下,就可以洗澡了。
关于餐食我有一点阴影。上次到俄罗斯感觉不太好,面包梆硬,早晨尽是冰凉的东西,口味也不好。但事后证明我担心多余了,这里提前说一下我们的那个导游,他叫谢尔盖,有点像超人,带我们去正规的俄式餐厅,什么烤鸡牛排香肠奶酪沙拉蓝莓汁西柚汁等等,红是红绿是绿,一道道水来一座座山。啊,这才是真正的俄餐,所以我明白了一个真相,即走马观花对了解一个国家的活态远远不够。
火车到达二连浩特站,天已经黑了。这里是国门,有很多事情要办理。最重要的是要换火车轮子。俄罗斯和蒙古国的铁轨比我们国家的铁轨要宽,二连市铁路换轮库是世界最大的换轮库。据说是用起重机将车整列抬起,把原转向架推出,再推进另一轨距的备用转向架。
列车员通知说,火车要在这里停留三个小时,大家下车可以自由安排活动。下来了,一轮月亮悬在头顶,路灯闪耀,一块石碑上刻着“边关”两个字。旁边还有小字:往昔胡马驰骋地,今朝雄关巍然立。二连浩特蒙古语是斑斓之城的意思,那就赶紧到街上去看看。
火车站广场人不多,三三两两有几个孩子在追赶打闹。一群女人坐在石凳上拉呱,手里织着毛衣之类。她们年龄都三十多岁样子,我们问路线的时候,叶姐走过去跟她们搭话了。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问,看出什么来了吗。
我们摇摇头。
候鸟般的人群,她们从南边过来,老公在这边做事。还是写小说的呢,瞧你们那眼力劲儿。叶姐说。
我们伸舌头。是啊,眼睛总是不给力。
朝灯光亮的方向走,街道人多了,原来是夜市到了。既然有时间有心情,何不喝一杯呢。行啊,人生难有几回聚,那就喝一杯。彭姐立马去点菜,烤肉串鸡爪子牛肉片等,外加几瓶啤酒。
我们在街边的椅子坐了下来,菜齐了,畅饮畅快畅怀,我们义薄云天了。真好啊。文学女人有一种真性情,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有思想还接地气,骨子里有血性和爽劲,她们本身就是一部精美的作品。
凤唱蒙古调,悠扬婉转,宽广壮美,有酒味的歌能穿透夜幕和心灵,我们记住这个夜晚了,二连浩特有月亮的夜晚,换轮子出关入关的夜晚,其乐融融的夜晚。
重新回到车上,出关手续和入关手续同时在火车上办理。中国这边比较简单,蒙古那边气氛严肃,三四个威风凛凛的军人上来了,全副武装,两腿叉开,双手背在后面,眼睛直直地盯着,嘴里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喊着,护照。
一个屁股硕大的女军人来了,手里端着一个大硬皮本,打量我,对照了一下,问下一个去了。之后,几个男军人比划着让我们走出包厢,我们出来,他们进去,把下铺板子掀起来,打着电筒东照西照,还用电棒戳戳我们的行李。
这是一种责任。这条铁路线上,曾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抢劫大案。有一个电视剧叫《莫斯科行动》,讲的就是这件事。当时,边关各国警察衔接不严,这边走了那边半天不来,匪徒便乘机实施抢劫犯罪。好在中国警察及时破案,严惩歹徒并整顿了这条铁路的治安,还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警察达成了合作协议,从而确保了这条大动脉的平安和顺畅。
办完手续,火车咳嗽一声缓缓开动了。看到渐渐远去的灯光,这趟行程终于脱离了熟土进入了另一个开始。
从深夜到黎明,我闻不到市井的味道了,从缝隙里钻进来的风,充满了干燥生硬的岩土气息。天大亮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滿目的寂寥苍茫,这就是蒙古国的东戈壁。远看,大漠瀚海,天与地相接,一幅纹丝不动的千年景象。偶尔掠过的几根电线柱子,碗口粗,黑灰泛着白,远看像骆驼背上的几根毛。
过道里开始有人来回走动,谈论的都是做生意的事情。蒙古国最近几年成香饽饽了,快有美国当年西部淘金热的景象了。据说他们地底下有煤炭黄金和天然气以及宝石等,且储量足成色好,结果人们哗啦啦一齐涌来了。
一个尖嘴猴腮颧骨突出的人过去了,红T恤白裤子,脖子上戴着粗粗的金项链,他手里举着手机,叽里呱啦,不知讲的哪国话。一个板寸头的人走过来了,大块头,军绿色的裤子上面很多口袋,手腕上有纹身,还有一只木珠手链。身后跟着一个像举重运动员的男人,估计是保镖。
景色纵深,大片大片的绿色来了,而且越来越浓。草原广阔,马群飞奔,蒙古包星星点点。蒙古国终于润泽起来了,不一会儿,乌兰巴托站到了。《乌兰巴托的夜》是一首流行歌,歌手因它而成名,我们则要下车去看看究竟。
乌兰巴托的冬季长达八个月,此刻,嫩金一样的树叶在枝头上闪闪发光。天空瓦蓝瓦蓝,阳光热情地舔着我们的胳膊。远眺乌兰巴托市容,发现它的规模相当于我们的包头市。据说蒙古一半的人口都集中在这里,成吉思汗的图腾也依旧在。他们的房价跟中国二线城市差不多,堵车也十分严重,物价也贵。
站台上,两个蒙古女孩儿正在聊天。凤走过去,向那两个女孩儿打听卫生间。咦,她懂她们的话。哦,据说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同属于阿尔泰蒙古语系,我估计凤看那两个女孩跟看包头的女孩没有什么区别。
走进候车室,看见了便利店,四下环顾,又发现这里的蒙古文跟我们国家的蒙古文大不一样。哦,他们揉进了很多俄文字母,变成了另一种蒙古文。看来还是中国对蒙古文化的传承最为完整,不过,这或许又是另一种进化的自然态。
窗前,凤的眼睛有点迷蒙,估计人和思想已经分离很远。她是个温暖的人,生活和写作都兼顾得很好。临行前,她到超市给大家买奶茶湿纸巾咸菜等等,包括针线。这种细致为大家带来了不少方便。早晨起来,她给我们泡上一大杯奶茶,接着收拾桌子整理卫生。地毯脏了,她蹲在地上用纸巾擦,一遍又一遍,连缝隙里细末也要擦出来。
我准备把剩下的一点方便面倒掉,凤见了立马阻止说千万别。她像母亲一样看着我把剩下的吃掉,吃完了,教我一句禅语,嗡、其、杂、班、杂——阿、西、比、亚、索、哈。
我问这是什么。凤说,当你吃不下了的时候就念这句话,在脑子里把流浪小猫小狗叫来,让它们把食物吃掉,你这样做了,佛祖就不会怪罪了。
哦。我明白了。从那一刻起,我的脑子里上有了一个紧箍咒,是的,人应该有禁忌。嗡、其、杂、班、杂——阿、西、比、亚、索、哈。尽管拗口,我还是认真学习背诵。记住了,会念了,心情却没能舒坦起来。是啊,现在大家都对方便面皱眉头了,我这个当团长的要想点办法才行。
大家带的东西其实不少,腊鱼酸豆角擂茶豆豉榨菜老干妈奶茶酸奶黑芝麻糊红豆薏米糊……特别是叶姐的旅行袋,简直是个百宝箱,时不时都有好吃的东西拿出来。那就好好调配一下,努力弄出舌尖上的美味来。
火车到达纳乌什基站了。窗外夜色迷蒙,车站的黄色墙壁上,俄国国旗和莫斯科时间的霓虹闪耀。慢慢的,车厢里的温度下降了,从车窗缝隙里钻进来的寒风,像一把把小刀刮得骨头疼。我打了个冷颤,这天怎么由夏天忽然变成了冬天呢。看看手机定位,没有信号,估计已进入了西伯利亚腹地。这时,列车员送毛毯来了,他说西比利亚的夜晚只有冬天,再加一条别感冒了。
尽管有了两条毛毯,夜里还是冷。我只好把两件毛衣全部套上,待迷迷糊糊睡着了,半夜又突然被冻醒了。一摸,原来是毛毯掉在地上了。坐起来,听动静,再看看外面。一钩白月悬挂天际,原野上白茫茫一片,黑色的森林如同坠入了大海的底部。
西伯利亚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冷。夏天都这么冷,难怪说它是冰窟之地。的确,这里冬天可达零下六十度甚至七十度,北半球的两大寒极之地上扬斯克和奥依米亚康都在这里。
列车员说这列火车空调效果不好,到了冬天,从外面看,这火车就是白胡子老爷爷,而里面的车窗缝隙里尽是冰碴子。
下次,你们可以坐满洲里的那趟列车,K19次,条件要好一些。他说。
有没有下一次呢。说不好,有的地方一生只能到一次,有的经历一生也只能有一次。但是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绿皮火车,我希望不是最后一次。
西伯利亚的寒冷是可怕的。过去革命党人被流放在这里,很多人无法坚持最终长眠于此。有关西伯利亚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更多了,普希金的诗,《致西伯利亚囚徒》,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列维坦、伊林内赫的油画等等,都留下了史诗般的精粹。
西伯利亚还是世界最大的战俘营。据说当时光日本战俘就有六十万,其中还有不少女性,但交还战俘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十多万。《西伯利亚战俘营手记》等书有描述。
我感叹西伯利亚之大,也好奇西伯利亚的冷。寒冷极地奥伊米亚康是一个镇子,目前仍有几百个居民生活在那里。奥伊米亚康冬季非常漫长,白天仅有三个小时,这太不合算,人生本来就短,亮光天日还短,那里的人究竟在坚持什么呢。
学了一个新词儿,地盾。意指大陆地壳上相对稳定的区域。西伯利亚是最大的地盾。一块天然的大盾牌,一块世界上最坚硬的骨头。二战时期俄罗斯在这里筑起壁垒,抵御侵略。二零一四年普京启动西伯利亚大铁路现代化改造工程,他说,相信为俄罗斯及其合作伙伴带来更大效益。这是一句高瞻远瞩的话,这个人将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丰碑。
早晨,一大片蓝色把车窗封住了,我猛地坐了起来,揉揉惺忪的眼睛,听到小莉说贝尔加湖到了,快看快看。
一触碰那蓝,哇,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是世界最美丽的湖。湖水如丝,万般柔情却有着最硬金属的光。那种蓝囊括了所有生命的力量,厚重磅礴,深刻绚烂。它的结净,是冰雪的骨髓,它的壮阔,是心的走向。我到过很多的地方,澳洲大洋路的太平洋是美的,但没有这种金屬的光泽。古巴的加勒比海是美的,但没有这种大块棱角的波澜。俄罗斯波罗地海也是美的,但没有这种蔚蓝。这时候,我发现有一种美是无法传递的,想说,难以形容,用手机拍,手机太浅薄。于是我只能哎呀哎呀的叫,这湖,美得唉声叹气了。
得到了一些词条。世界第一深湖、欧亚大陆最大的淡水湖、水资源储量和质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中国古代史书中最早明确记载贝加尔湖地区的为《汉书·苏武传》。清朝在《尼布楚条约》后将这块地区划归俄罗斯。这地儿,古代最早的居民称“肃慎”,是中国满族的祖先。我是满族,与我有关。
又是一个小站到了。有几只狗在站台上咬着玩。旅客下得多上得少,不知什么时候居然有了很多空包厢。他们说,到莫斯科只会剩下四分之一的人。
讲求效率的年代,人们大多会选乘飞机出行。北京到莫斯科的机票价是三千六百多,这趟火车散客票价是五千六百七十四元,团体票是四千五百一十三元,所以选坐火车的人越来越少。然而,两国政府还是依旧重视这条铁路,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投入,相信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这条大动脉会彰显它该有的重要作用。据说,俄罗斯铁路公司准备将一列名叫金鹰号的新列车投入使用,它有点像豪华游轮,每个车厢都有单独的淋浴,还用地板采暖,有等离子电视,还可以到酒吧品尝鸡尾酒和俄罗斯小吃。安全和舒适度匹配了,加上美景相伴,相信选乘火车的人会慢慢多起来。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站到了,列车员招呼我们下去溜达溜达。这一行停车的时间有长有短,长的四个小时,短的十几分钟。一般来讲,停车不在半小时以上列车员不会喊我们下去溜达。溜达就是健步行,火车上呆久了,运动不足会导致便秘,所以要抓紧时间动一动。
从没有看见这么美的太阳,满眼橙黄明净一派华贵。旁边有一座黄色的房子,我们上去打卡拍照,瞬间个个都成了被金框呵护的美女。
小莉穿着吊带背心,运动长裤,两条大长腿怎么摆都是艺术范儿。她上镜,像模特儿,性格率真,除了喜欢帽子,还跟我一样是爱狗一族。
小颖也是风景。一个女人一生都在探索自己的穿戴风格,能够找准并且一辈子坚持下来的,绝对是睿智并且值得钦佩。教科书有很多种,会打扮的算一种。这时候,我看见她正独自地走在阳光里,头发长长,影子长长,韵味长长,不需要文字的光芒。
两个俄罗斯家庭一直在我们附近。他们三十多岁的样子,孩子五六岁、三四岁。出于礼貌,我们会跟他们点点头,笑一笑。他们的孩子很可爱,也很喜欢跑来看我们。到跟前了,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还伸出小手拉我们。但是不知怎的,我们刚跟孩子打招呼,家长就跑过来把孩子拉走了。友好,但不信任。想到五十年代的俄罗斯专家,他们跟我们那么亲密无间,这些人难道不是他们的后代吗。
火车坐久了之后人会犯迷糊。冷不丁大脑出现空白,然后不知今夕何夕,唯有黄昏和早晨轮流穿梭。
西伯利亚的黄昏是金子做的。夏令二十二点,放眼一派金红,大地的角度倾斜了,没有今生来世,只有此刻。壮观神奇的地平线轮廓出现了。一片树林玩变脸游戏,一晃一个面容。再看大地,大地已经变成一块巨大的青布了。金红是一个三角形,蛋黄一样的太阳努力把散发出去的光芒收回来。有一束光很顽皮,掀开了,拉长身子使劲往下探。过一会儿,太阳母亲终于把孩子们拽回去了,大地呈现了灰色的轮廓,几颗星星出来了。
西伯利亚的早晨是银子打造的。凌晨四点多钟,河流就从黑乎乎的大幕里冲撞出来,一路泛着金属色的亮光,唤醒千万条银蛇奔向远方。雾的被子覆盖了原野,黑色的松树林列队出早操,立正,稍息,长长的腿杆历历在目。它们头上戴着白帽子,那是晨曦的礼仪。六点多的时候,树林的缝隙里忽然有金针万箭齐发了。投在河流,河流笑翻了天。投在列车身上,千万条鞭子抽打喊加油。
白桦树来了,一丛丛一片片,飞掠而去,每一棵都有上百年的年轮。
一个小水洼过去了,闪着宝蓝色的光,像女人手上的戒指。它是美中的精灵。
小木屋来了,像一只只小蘑菇,红的顶,白的壁,令人想起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每个女人内心里都有一个白雪公主,一千个女人就有一千个白雪公主,我们要做自己的白雪公主。
俄罗斯油画的青铜色是一个神秘的基调。那些在冬宫夏宫长眠的风景,无论是幽深的人肉丛林,还是呼啸狂澜的大海,唯有它最能唤醒、打动、惊悚、直至震撼心灵。我仰慕这重色,觉得它能把一个凡人变成考古学家。
俄罗斯白色是一种圣色。他们用白色做长袍,隔离人类的邪恶与污浊。可当下从众的心理,很难让我们有洁白的时候。幸好凤教了我禅语,嗡、其、杂、班、杂——阿、西、比、亚、索、哈。
俄罗斯现在没有作协,也不养作家了。我们现在看韩剧看美剧,却很少能看到俄剧,不知道是因为产量低好作品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而我们倒是希望多了解一下现代的俄罗斯。
兴奋让人畅快也让人疲惫。一连四天神经都绷得紧紧,现在有点撑不住了,一出叶卡捷琳堡市我们就打瞌睡了。这时列车员过来通知说,三十分钟后到达欧亚分界处了,要拍照的请提前做好准备。哇,又是一个大景,他这么一说,我们又被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当即又跳起来趴在车窗前了。雨丝飘飘,火车似乎明白我们的心思,开得很慢,路牌一个个来了。1770……1771……欧亚大陆分界碑在路牌1779数值附近,那里距莫斯科1777公里,距北京5927公里,距海参崴7511公里。我们举着手机,睁大眼睛的看着,数着。
欧罗巴与亚细亚的分界,据说是俄国地理学家塔季肖夫提出来的,得到普遍认可。我的想象是把地球拿到桌子上,像切西瓜似的把五大洲切成五瓣。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高加索山脉——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这就是亚欧大陆的分界线。
来了,来了,一个倒立的毛笔尖的白色石碑过来了。它大约高十几米的样子,三个人拉手抱得下。碑上可以看到指向左边的箭头用俄语写着亚洲,下面指向右边的箭头也用俄语写着欧洲。其实,这个塔很不起眼,在西伯利亚渺小得可以忽略。然而它却有文化的力量,幸好没有被我们错过。
弗拉基米尔站是个大站,但是只停了二十六分钟,列车员没喊我们下车,我们只能透过车窗很隔膜的看着它。弗拉基米尔站是整个行程的倒数第二站,据莫斯科只有190公里。它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历史艺术中心,世界闻名的旅游线路“俄罗斯金环”就从境内穿过。最厉害的是这里的白石建筑金门、圣母安息大教堂、德米特里耶夫教堂、涅尔利河口圣母教堂等,都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另外,这里还出名人,大部分是科学家和政坛才俊。
城市面面观。我以为俄罗斯最漂亮的还是在乡村,如苏斯达里小镇。那里有碧绿的草地,雪白的教堂,古老的木雕,紫蓝色的薰衣草,还有在地里作画的农民……我一定要再去那里做一个梦才行。
一声长鸣,莫斯科终于向我们走来了,所有关于它的记忆此刻来了个大汇集。现实的、影像的、書本的、想象的。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下午一点五十八分,我们终于准点抵达了这趟列车的终点,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火车站。
远远地,一个高大的光头的莫斯科人朝我们走来了。
责任编辑:肖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