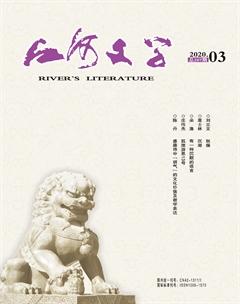日行乌江
赵永康
仲春一个周末,我和朋友约好一同沿乌江去沿河。清早,我们来到思南港,登上去潮砥的机动木船,机器刚发动,朋友突然因事不能去了,我只好一人前行。
船舱里有十几个人,为了清静,我走到船尾遮篷的甲板上,船两边是空的,探头可看前后江水,左右可观两岸风景,随着螺旋桨在船尾翻滚出雪白的泡漩,船调过头,船身直指下游。
船逆风而行。我扶着栏杆,侧头后看,视线从思南山城的码头慢慢上升,直到一幅美丽的江滨小城图画慢慢显现又慢慢消失,木船开始进入薄薄的江雾。
这是一段舒缓的江面。江水清澈透明,不时有一条鱼蹦出江面。岸边是一条沿江小路,三三两两的行人,有的背着背篓,有的领着孩童。前方出现一块鹅卵石的沙坝,沙坝上面是一个村寨,一只木船停在沙坝边,廖廖几人从船上走下去,另几个人等着上船。我们的船刚要行过沙坝边一只船的位置,只见船夫斜撑着篙竿,大声呼叫要去潮砥的快点,他的声音在我身边柴油机突突的声音中显得极具洪亮和张力。
江边一块绿茸茸的草地来了。三两头黄牛水牛低头啃草,悠闲地甩着尾巴,两个小孩离草地较远,蹲在江边的沙地上,像用手玩着细沙,又像在沙地画着什么,他们完全没有把放牛当成一回事,牛怎么自由地吃草,他们就怎样自由地玩着。几只黑色的水鸟从江面飞来,正要飞过我们船顶,又突然拐出一个弧线向岸边飞去。沿着飞鸟栖落的方向看去,一个个窑洞并列在江岸,有的残破不堪,有的长出萋萋的草,过去窑堂映红的江水,窑田蒸腾的水汽和砖瓦出窑装船运载的热闹情形已成为乌江的历史被人们记忆。
江面的雾气已经散尽,阳光照着碧蓝的江水,被江风吹得凉嗖嗖的身体也顿感温和起来。江面时宽时窄,机器在顺流中始终保持突突突的音律,我没有感觉船速有什么变化,也没有感觉山水太大的区别,于是找了一块木板坐下来,点上香烟,驱除一点小小的枯燥。
两岸山势开始高峻起来,江水流速明显加快。半山一树粉白色的樱桃花,在一间木屋外的树荫中像礼花灿然开放。我举起摄像机,随船速调整着画面,静静地看着取景框里移动的景物。江岸,一条石级小路,在画面中越来越近,我翘动手腕,对着它,缓缓向上,去连接树荫,连接樱桃花,连接青瓦吊脚楼。船突突行进着,我正欲放下摄像机,正要回放刚才看到的村舍和樱桃花,突然前面几墩巨大的乱石卧于江边,它们像峡口堆积的黑云。而船过峡口,置身其境,带给自己的感觉又仿如遭遇黑云里的闪电。望着它们,可以想象数十年或者数百年前的某一天,巨大的山体滑坡,该是怎样惊心动魄的场面。
驶出峡谷,眼前是大片开阔的水域,德江的潮砥到了。几只舶船靠在码头,宽宽的右岸堆满大大小小和不同形状颜色的卵石。阳光下,石的世界精彩奇异,它们历经磨难,从上游奔闯而来,埋于沙土,又从江边的沙土被挖掘出来,聚在一起,接受收藏家的问鼎,接受外商的青睐,再沿乌江入长江,去作客繁华都市。
因潮砥没有客船去沿河,我转乘客车到德江长堡乡与和平乡交界的白果砣已是下午两点,同样没有客船,只好搭乘一家私人运载水泥的机动铁船。
船出白果砣,两岸山势陡峭。河床很窄,江水相比之前,流速明显加快。站在船尾的甲板上,仰头看两岸山顶,脖颈酸软,脑袋有些许晕舷。船在峡谷的江中行驶,与一枚树叶颠簸在浪涛上没有两样。十公里,二十公里,两岸遮天蔽日,看不见一点村舍,看不见一点生灵,只有波浪不停地拍打船身,也只有波浪不停地撞击两岸岩壁和礁石。无数的石壁和礁石被水浪嘶咬,形成万千气象的石纹石痕,它们或成波纹,或成蜂穴,或成石刀、石凿、石钻,岩壁有多远,急流就多长,江涛就多响。正是年年岁岁的江水,一路大抒情,一路大构思,一路大运笔,才使两岸临江的岩壁上留下无限隽永的写意和翻江狂草。
船上只有驾长,机械师和我。我在甲板上摄录了一阵险山险水,走向船的前舱,不看便罢,一看让我毛骨悚然。船的吃水线已经够着舷沿,击水浪花时而扑进舱里,如此情形,稍遇一点紧急状态,船将如一扁梭标斜刺江底。我水性很差,心里暗想,即使用尽全部体力,也会难逃厄运。于是我迅速地返回到船尾的甲板上,看好一块能够急救的木板,它虽然短而窄,但它至少要比一根稻草强许多倍。机舱和船尾的甲板仅一壁之隔,机械师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他从舱里出来,来到我的身边,我紧张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一些,与他在甲板上聊了起来。他和前面驾长共同买了这艘船,载运德江水泥到沿河县城,一年四季,生意很好。他谈话的意思是只要乌江水泥生产不断,只要有沿河县城的发展和已经开工建设的乌江沙砣电站,乌江航道就是一条水上黄金运输线。當我谈到他们船的货载和自己的担忧时,他笑了一下说放心,已是家常便饭了,不会有事。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顿觉踏实了许多。
我们在甲板上坐了下来,交谈无所顾忌。或许是他长年在船上孤独的缘故,有一个人陪他说话,他格外高兴。他说船在装货卸货时,没事就坐在船上钓鱼,说着,说着,他就叫我看桶里一条约两斤重的鱼。因太阳晒热了水桶,他见鱼快翻肚了,于是取下壁上挂着的砧板和菜刀开始破鱼。船上破一条鱼有的是时间,他慢条斯理,一边说话,一边去鳞、剖肚,接着扔下吊桶,打一桶江水洗一次鱼,从洗鱼到冲净甲板,打了五六桶水,然后又将鱼切成小块,酌上食盐装好,以便回家时带上,整个过程像在完成一件工艺品的制作。船上没有开火的炊具和食物,但鱼竿、鱼食、砧板、菜刀、食盐都是为排遣寂寞和改善生活长期准备的。
不知不觉,船到了新滩。江面突然留下一个坎,水声怒吼,江流湍急,船身纵浪,水花卷上甲板,好不惊险!折身一看,半山建有一间砖房,原来是绞关站。由于现在航行在江上的船只都有足够的马力克服江水的冲击,现在这个绞关站已经废弃,但是矗立在半岩上绞得吱吱作响的孤独和寂寞,却永远刻在了走江汉子的心里,永远留在了乌江航运史的深处。
天色渐晚,峡谷的江上,突突的机器声,异常清脆。昂首山崖上的岩洞,那里藏着千年悬棺,虽无缘目睹洞中的秘密,也无能考证它的科学价值,但在快速行船的江上,仅仰首一瞥,我的内心便充满了一种对生命的理解和敬畏。顺流而下,依然是窄窄的河道,我递给机械师一支烟,听他讲述一些江上的传说,一些走江汉的爱情、婚姻以及生活的艰辛、快活和不幸。他不时用手朝崖壁上指了指说,那是古纤道,是用凿子凿出来的纤道。我睁大眼睛,视线沿着纤道移动,看到它,我想到了蚕,想到一个个纤夫蠕动蚕一样的身体在纤道里奋力前爬,想到了他们赤身裸体的雄性美和力的释放,也隐约听见了他们一声声苍劲而哀婉的船歌。
前面有灯光闪烁,穿过沙砣电站坝址,驶过江心洲,灯火辉煌的地方,那该是沿河了。江水舒缓起来,宽宽的江面倒映无数灯火。面对一天乌江的行程,她的婉约、剑气、苍凉、冷峻、温柔等多重性格,不停地诗意着我的感受,“我以一粒沙一颗石子的身份/以一枚落叶一棵草根的身份/以一块遗弃的舢板一弯晓月的身份/来到你的身边/聆听千年的梦呓/猜度没有破解的哑谜”。
船靠码头,握别两位师傅。登上岸,望着静静的江水,我留下心中的诺言:乌江,我们相约明天。
责任编辑:肖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