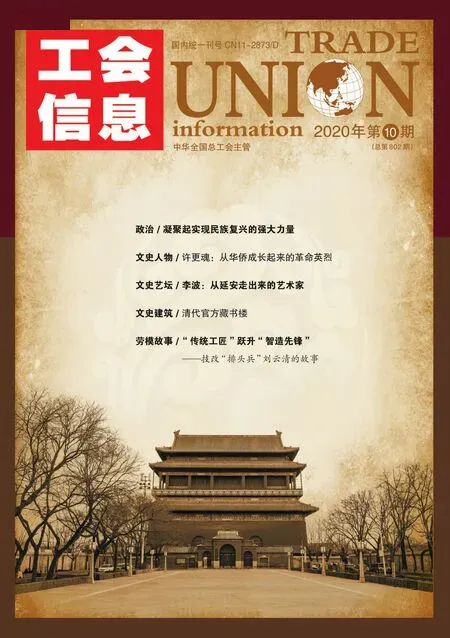李波:从延安走出来的艺术家
◆文/冯晓蔚
李波,原名任秀英,河北曲阳人,1930年,李波全家随着逃荒的人群逃到了山西太原。曾任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团演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后勤部俱乐部干事、代主任。1940年入党。1942年入延安鲁艺学习。后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演员、华北文工团戏剧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音协理事,全国妇联执委。是第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延安时期,因创作和演出《兄妹开荒》而出名。演过话剧、歌剧、秧歌剧,如《生产大歌舞》等。独唱的主要歌曲有《翻身道情》《新疆好》《走西口》《劳军歌》《刘志丹》《茉莉花》《闹元宵》等。参加演出新歌剧《白毛女》,主演《兰花花》《王贵与李香香》等歌剧。1949年获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歌唱比赛二等奖。
在延安鲁艺参加秧歌运动
1941年底,经组织批准,李波到延安鲁艺去学习,成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第五期正式生。
当时鲁艺的教学,还是按正规艺术学院课程进行的。但物质条件很差,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艺术大学,既没有教室,也没有桌椅板凳,各系上课就在院子里,上大课在操场上,同学们席地而坐,把两条腿拱起来记笔记。戏剧系也上声乐课,每周上一堂课,李波的声乐老师是叶风,教的是西洋发声法。每天就在一个破窑洞里,那儿放着一架声不全的破手风琴,就靠着它练起声来。两个月下来后,老师对她的进步提出了肯定。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我国文艺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只注重关门提高,不深入实际,脱离群众,重洋轻中,轻视民族传统,对于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没有明确的认识等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了精辟的论述。
5月2日,在延安的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约请80多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宾”,要召开一次别开生面的文艺座谈会,构想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李波有幸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上,李波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向工农兵,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陕北的民间艺术很丰富,要到群众中去采集,去挖掘,要向群众学习,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提出了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向民间艺术学习……还说现在群众要的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必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鲁艺所作的报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为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服务,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

1943年春节,延安鲁艺秧歌队在边区政府门前表演《歌唱南泥湾》。

文化沟广场上,演出秧歌的火爆场面。
1943年新年时,鲁艺俱乐部组织了秧歌队、推小车、跑旱船等。一天黑板上写着:李波、王大化同志表演“打花鼓”。李波感到很意外,因为大化同志在当时已经是鲁艺的知名演员,而李波是个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是从部队到鲁艺的“土包子”,一双草鞋穿了很久也不破,同志们都笑她是“背着脚走路的”。
王大化当时在实验剧团,平时他俩连话也没有说过,现在突然让他们在一块儿搞节目,真不可想象。李波正不知该怎么办时,大化却主动来找她了,他亲切地问李波:“你看见黑板上写着让我们搞打花鼓吗?”
李波紧张地说:“看见了……我不行。”
王大化笑着问:“过去你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
“扭秧歌,说快板,演双簧……”
又问:“会唱凤阳花鼓吗?”
“那都是旧词,不能唱。”
于是大化就带着李波到音乐系,找到安波,安波听说来意后,就把已写好的一首用民歌《打黄羊》填的新歌唱给他俩听。因为这个歌的内容是拥军的,形式又要求打花鼓,于是给它起名叫“拥军花鼓”。王大化拿了一面小锣,李波背了一个小鼓,就这样开始了排练。
在排练过程中,李波曾经产生了一些顾虑,这个顾虑的不是形式,而是唱法。过去在战地和部队,都是用大本腔(真声)唱歌,到鲁艺后从没有见人家用这种嗓子唱歌,都是用西洋发声法唱,可是李波跟老师学的西洋发声法,一时还用不上,更不用说表达感情了,特别是在音乐系同学们面前,李波确实有点害怕。王大化却一再鼓励,并说:“你什么也别管,大胆唱就行。只要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惯就行。”
就这样在王大化的鼓励下,李波完成了《拥军花鼓》的排练。各系向民间艺术学习的节目都准备好了,大家都集合在操场上开始了预演。领导看了很高兴地说:这是鲁艺的“新气象”。领导不但肯定了成绩,还让大家到校外去演出,首先演给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群众看。于是大家打起了锣鼓,扭出了学校,在老乡的打麦场上,面对围成圈的观众,表演起来,老乡们看了节目非常高兴,说《拥军花鼓》唱得清楚,听着亲切。
于是大家又扭出桥儿沟,到机关,到部队,到杨家岭、王家坪、枣园、西北局、党校、联政等等各处去扭。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群众、干部、战士、领导们的热烈欢迎,扭转了鲁艺当时脱离实际,关门提高的倾向。
l943年元旦这天,李波和大化按照民间秧歌的样式化妆,一个拿了把小花鼓,一个拿了面小铜锣,同“鲁艺”秧歌队伴演的《赶旱船》《赶毛驴》《推小车》等节目一起,一扭一扭地奔向桥儿沟街头,又赶往延安南门外新市场演唱: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呀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大家就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面前扭起了大秧歌,一会儿“龙摆尾”,一会儿“剪子股”, 各种花样,越扭越欢,扭到“卷白菜心”时,达到了高潮。也就在这时,起了大风。四周黄土飞扬,演员都成了黄土包,毛泽东的脸上、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只是兴奋地哈哈大笑。演员们见毛泽东快乐地笑着,演出的热情更高,扭的秧歌更快了!
毛泽东主席观看演出后高兴地说:“你们这样做就对了,群众欢迎你们,我们也欢迎你们!”
周恩来副主席看了演出后,对王大化说:“马门教授(大化在话剧《马门教授》中曾扮演教授)头上也扎了这么多小辫子(当时大化演《拥军花鼓》时的打扮)?这可是个很大的变化呀!群众是欢迎这个变化的……”接着又说:“向民间艺术学习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些旧形式还需要改造,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一变。”
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秧歌队成了一支工农兵学商大联合抗日的、健康的秧歌队,老百姓都亲切地称秧歌队为“鲁艺家的秧歌队”。后来延安的秧歌一直扭到了各个解放区。
创作演出《兄妹开荒》
1942年,侵华日军将60%以上的兵力集中到中国敌后战场,对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扫荡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和胡宗南又集中全部精锐部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层层封锁,扬言要把边区的军民困死、饿死。革命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自力更生,渡过难关的号召,边区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于渡过了艰难时期。1943年春,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开始大反攻,秧歌队结合庆祝红军胜利,在春节期间组织了第二次秧歌表演。
1943年春节前,鲁艺领导让王大化和李波,并让路由来协助,三人自编、自演、自导一个小节目,题材自己去找。大家在《解放报》上看到一篇反映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的事迹,感到这个题材和当时的生产自救运动结合得很紧,就决定选做创作题材。
在创作中大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更没有什么形式约束,思想特别活跃。一开始就七嘴八舌地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段、我一段,结构起来。觉得这儿用唱好,就唱;觉得这儿用说好,就说。一个不到20 钟的小节目,有说有唱,有舞,还有快板。因为节目是包干,演员只有王大化和李波两个人,也只能按两个人来安排情节和人物关系。决定王大化演哥哥,李波演妹妹,开始是哥哥落后,妹妹积极。经过多次讨论,才改为兄妹都是积极的,这样更符合当时边区青年实际情况。形式上,仍采取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步,加上情节故事,还是在锣鼓声中扭着上场,但要加上生活的舞蹈和步法,感到这样既热闹,又能表现开荒的乐观情绪。下场时,妹妹挑担,哥哥扛锄,扭着“龙摆尾”下去。

1943年2月5日,延安各界两万多军民聚会,举行春节联欢活动。鲁艺教师王大化(右)、学员李波(左)表演了秧歌剧《兄妹开荒》。

《兄妹开荒》表演者:王大化(左)、学员李波(右)。
三人把结构、对话、轮廓搞出来后,就由路由去编词。剧编好了,起个什么名字呢?由于主题内容是开荒,那就叫什么人开荒吧。延安的男孩子通常都叫什么娃啦,小啦,疙瘩啦……就给男主角取名叫“小二”,由王大化扮演,于是小二也跟着姓了王,这样剧名就叫《王小二开荒》。音乐仍去找安波来写。
安波在写第一曲时,很不顺利,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几次试唱都感到民歌味不够浓,就再改。周扬院长对这个小节目很关心,每次试唱他都听。白天李波和王大化一块儿设计位置和动作,晚上就一块儿到安波屋里去。安波不顾疲劳地在一盏小油灯前苦思冥想,大化和李波一边一个趴在他肩上(因为灯光太远了看不见),他写一遍,他俩唱一遍。不行,又改,如此反复多次修改,终于完成了创作任务。审查节目的那天,李波犯了偏头疼,她带病上场,表演了这场戏,没有想到审查后领导非常高兴地通过了,并认为比《拥军花鼓》提高了一大步。
《兄妹开荒》秧歌剧,描写陕甘宁边区一家兄妹二人响应边区政府开荒生产的号召,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争当劳动英雄的故事。该剧虽采用旧的秧歌形式,但摒弃了旧秧歌中常有的丑角以及男女调情的成分,代之以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农民特有的诙谐交织在一起,使一出剧情十分简单的小戏演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剧中唱道:
图7为气流出口与垂直方向成30°雾滴运动轨迹。当气流出口方向与对自然风相逆时,在其出风口产生水平向前的气流速度,可减小雾滴向喷头下风向飘移的速度,从而增大了雾滴沉积的可能性,减小雾滴飘移量,产生的下风区域较大,涡流速度较小,进一步减少了雾滴的飘移潜能和向上卷吸潜能,从而有助于降低雾滴的飘移量。随着气流出口与垂直方向夹角的增大,辅助气流对自然风流场的影响范围迁移出雾滴运动范围之外,从而使得辅助气流减少飘移的效果降低。
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
叫得太阳红又红;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呀懒虫。
扛起锄头上呀么上山岗,
山呀么山岗上,
好呀么好风光,
我站得高来看得远来么咿呀嘿,
咱们的边区到如今成了一个好呀地方。
哪哈咿呀嘿嘿呃嘿,哪哈咿呀嘿!
经过艰苦创作和排演,《兄妹开荒》就要正式出演了。那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服装道具,也没有制作费,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如妹妹的衣服是李波自己缝补的,担子是王大化屋里的一根顶门棍(延安风大,他住小平房,晚上不顶门,就会被风吹开),担子两头拴上两根背包绳子,一头是平时打水的旧水罐,一头是个旧篮子。碗、筷是向伙房借的,锄头是自己用木头做的。陕北老乡喜欢在腰里系一条紫红色的粗羊毛围巾,大化就向老乡借了一条系在腰里。化装品是带颜色的土制成的,当然,擦在脸上很不舒服。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更没有扩音器,一大早从桥儿沟出发,走过飞机场,穿过延水,每走到一处,锣鼓一敲,全体演员就都扭起大秧歌。扭完就演唱小节目,在万人以上的广场上,全凭自己的嗓子把歌声送到观众耳朵里。
记得有一次,演员们在文化沟的青年体育场演出时,操场一面是个大山坡,虽然当时天气还冷,但坡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观众,其他三面也坐满了八路军的指战员和头上扎着白羊肚子手巾、手持红缨枪的自卫军,真是人山人海,连篮球架子上都是人。看到这种壮观的场面,演员们的心里非常激动,大家情绪饱满,感情充沛地表演着每一个节目。老乡们看完戏高兴地说:“把我们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
散场后,老乡们碰上熟人互相转告,但不说看的是《王小二开荒》,而是亲切地说看了《兄妹开荒》。于是后来《兄妹开荒》便代替了原来的剧名,在群众中传开了。
1943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去劳军,兼为当地老乡演出,借此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个分区去。在这段时间里,演员们经常是一清早化好装就出发,一天要赶三四场,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吃饭。那时正是春天,西北的风沙特别大,刮起黄土来,眼睛都睁不开。大家常常第一场还是有眉有眼的,到第二个地方,就成了黄土包脸了。演唱时,风沙刮满嘴,大家只好咽下沙土继续唱。老百姓也在满是尘土的广场上看演出。一场演完后,又动身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时总有许多的老百姓跟着剧组走,常常是剧组走几处,他们也跟着看几场,还有的人一大早从家里带着干粮跟着跑,有的人对节目已经非常熟悉了,于是一边看一边仔细地向新来的观众介绍情况,说哪个节目好看,现在的戏该怎么样了,该谁出场了,下边该演什么了,好像他们自己也是这个秧歌队的成员一样。
一次在南泥湾演出《兄妹开荒》,当扮演哥哥的大化和扮演妹妹的李波分别拿起锄头和挑饭的扁担,要开展劳动竞赛,最后唱起“向劳动英雄们看齐”的时候,战士们和演员们的心顿时沸腾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数以千计的锄头高高举起,漫山遍野响起“向劳动英雄们看齐”的歌声。那叩人心弦的场景,简直无法用文字和语言来形容。
1943年2月9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五,鲁艺宣传队带着秧歌剧《兄妹开荒》,到杨家岭、文化沟和枣园等地扭秧歌拜年,在枣园表演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同志等中央领导看完演出后,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毛主席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周恩来同志参加完延安整风后,高兴地把延安秧歌带到重庆,在周公馆过道、《新华日报》社场地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草坪上多次演出,使祖国大西南的群众大开眼界。郭沫若先生不禁开怀放歌:“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1943年4月5日出版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社论中肯定春节演出初步实践工农兵方向的成就,赞扬《兄妹开荒》是个“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
演出歌剧《白毛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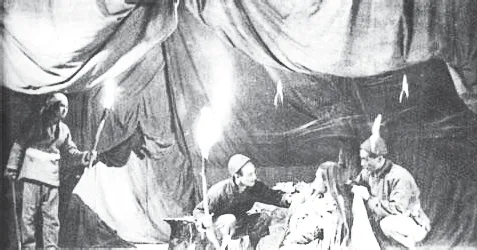
1 9 4 5年,延安鲁艺在延安演出《白毛女》。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剧照。
1943年《兄妹开荒》演出告一段落,演员们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但在这期间,大家的创作并未间断,涌现出很多反映现实生活的秧歌剧,也涌现出一些像 《牛永贵负伤》和《周子山》等多场次的秧歌剧。
1944年冬,中央号召要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摸索和创作出一个我们民族的新歌剧,以迎接即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项任务提出后,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文学、戏剧、音乐各个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寻找题材。大家对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线带来的“白毛仙姑”的故事颇感兴趣。故事最初流行于河北阜宁一带,叙述一个被地主迫害的农村少女只身逃进深山,在山洞中坚持生活多年,因缺少阳光与食盐,全身毛发变白,又因偷取庙中供品,被附近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在八路军的搭救下,获得了解放。这一带有传奇性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包含着“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思想,有典型的教育意义。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周扬院长的主持下,集体讨论了剧本的构思、人物设计和场次。然后,分工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瞿维等作曲,王大化担任执行导演。剧本定名为《白毛女》。该剧剧情复杂,人物众多,加之又是一个新的尝试,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在歌剧《白毛女》中,李波扮演了地主婆黄母。过去她没有演过这种角色,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大地主是什么样,这对李波来说是个难题。但在革命大家庭里,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同志们都热情地帮助她分析角色,提供材料,这样使她回忆起自己见过的资本家、工头、房东老太婆这类人物对工人、对待小丫环的种种凶恶的手段。在导演的耐心启发下,李波完成了《白毛女》的排练。演出后得到了好评,同行说李波演绝了,还说她是“活黄母”。该剧在延安连续演出了30多场,场场爆满。每次演出,台下没个不落泪的,不少观众从第一幕开始擦眼泪,直至看到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这部歌剧是我国第一部深刻反映劳动人民命运和斗争的新歌剧,为后来歌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它的演出,产生强烈的政治效果。
l945年5月,《白毛女》开始公演。首场演出的地点是延安中央党校会堂,观众是出席党的“七大”的全体代表。当时,会堂内挤得满荡荡的,八路军129师386旅的陈赓旅长就被挤在门口站着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全部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后台,接见了李波等创作人员和全体演员,对《白毛女》给予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指示:这个戏是非常合时宜的;艺术上是成功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