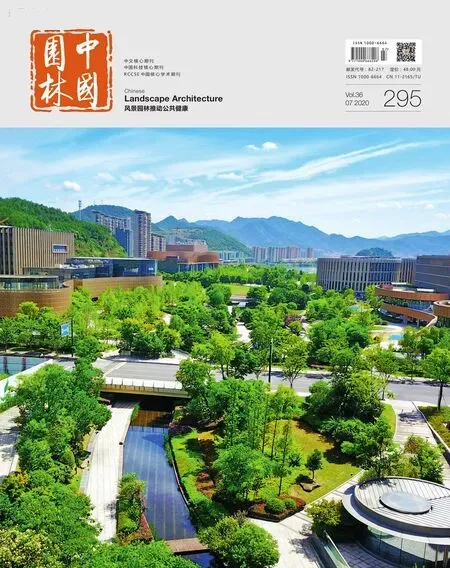日本枯山水嬗变过程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
熊 川
邓 舸
金荷仙*
李 胜
枯山水庭园(以下简称“枯山水”)能在咫尺之地创造无限空间,其营造的意境与13世纪流入日本的禅宗在精神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者遂产生紧密联系。就目前中国居住区内风景园林的营造现状来看,对日本枯山水进行大规模仿建已然成为一种时尚。枯山水背后的禅宗理念虽备受客户青睐,但这种一味追求形式及所谓“禅宗精神”的现象背后,是对枯山水园林文化的片面之解,对枯山水形成过程尚不明晰便进入意境营建阶段,有“拿来”之态势。因此,全面梳理与归纳日本枯山水的演变历程,不仅有利于认清其园林文化的本质,更能为枯山水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一定思路。
中外学者关于枯山水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于枯山水背后禅宗精神及理念的论述,强调禅宗对枯山水的影响[1-4];其二,对日本某一枯山水造园意匠进行分析,解读其设计手法或背后的历史文化[5-7];其三,关于枯山水现代继承与创新的解析[8]。而有关枯山水造型演变过程的论述却颇为不足,进士五十八在“日本庭园山水河原者造型论”一文中,强调山水河原者(以下简称“河原者”)于镰仓、室町时代的造园实践对枯山水造型的影响,否定“宗教→ 造型”的观点[9]76。河原者对枯山水的影响多限于室町时代后期[10-13],而有关日本镰仓以前枯山水的研究则较为不足。由此,通过归纳总结枯山水嬗变过程并厘清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影响因素,对枯山水后续研究及其中国化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 日本枯山水嬗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日本《造园用语辞典》将枯山水定义为:“日本特有的庭园样式之一,在平庭内以置石为主喻山,以白砂喻水。[14]”经文献典籍查阅可知,13世纪兴起的禅宗在特殊时代背景下赋予枯山水浓郁的禅意色彩,并作为禅师参禅的重要工具一直沿用至今[15]。枯山水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其形式和内涵随时代更迭而不断演化和升华[16](表1)。

图1 园城寺阏伽井屋[18]18

图2 大汤町环状列石[18]15
1.1 日本古代“写景式”枯山水的形成与发展
枯山水造型可溯至日本远古时代。六国史之首《日本书纪》中记载:“高皇产灵尊敕令曰:‘吾将树立天津神篱及天津磐境,为吾孙奉斋。’[17]”自然界的巨石被认为是神灵驻留之地,遂以盘座祭祀神灵,其他如古坟、水边祭祀等悼念先人或崇拜神灵的活动中均涉及砂、石的组合置放[18]16(图1)。奈良时期的《古事记》中记载砂庭可作为倾听神托的空间,在神社附近铺设白砂成为传统①(图2)。
平安时代,日本从中国引入小乘佛教,净土园林随之产生,成为后世枯山水之载体。据《李部王记》《三代实录》等书记载,日本嵯峨天皇十二皇子源融(822—895)生平好筑庭园,在京都宇治和嵯峨分别建有平等院与栖霞观②。但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修建了贺茂川河畔的河原院,院内模仿陆奥国景致而造的盐屋对日本缩微式景观影响甚远[19]。此后,于各地用堆山叠石以表现自然山川的尝试层出不穷,如京都毛越寺、高阳院等[20],用“筑山”“穿池”以模拟自然的筑景手法可视为后世枯山水之源流。
平安时代后期,《作庭记》(又名《前栽秘抄》或《山水抄》)中出现了枯山水最早的文字记载:“于无塘无水处,设石组,谓之枯山水。[21]”与古籍《尺素往来》中记载相类似的是,“野行”“山行”等表现山体的造型仅构成庭园的某一空间,并强调园林中部分野筋及山畔的自然写实样式。《作庭记》受中国道教思想影响至深,园中构成海洋的洲滨、荒矶等均可体现对道教仙境的追求与再现[22]。
1.2 镰仓时代“筑山写意式”枯山水的形成与发展
镰仓时代,枯山水因政治、禅宗等因素被赋予禅意色彩,其造型的改变与僧侣假山之趣味颇具联系,其中的“拟山”“缩地之术”等称谓则与中国神仙蓬莱思想不可分割。
1.2.1 镰仓时代枯山水被赋予“禅意”的时代背景
1)政治因素。
写意枯山水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因素。镰仓时期,武士崛地而起,明庵荣西随后提出“兴禅”指令并颁布《兴禅护国论》,权力者通过建置寺社、招募僧人,极力发展禅宗并使之世俗化[9]79。禅宗在与日本神道思想交融的过程中强化了“绝对的无”即“空”的精神理念,与武士“死的觉悟”高度吻合,因而备受武士青睐。残缺之景如枯山水更能创造佗寂与纯粹之境,以展示内心悲悯情怀并强调“出世”的生命观。因而武士于这个时期兴造园之风,武士阶层作为枯山水的挚爱者,亦是禅宗的拥护者,枯山水遂与禅宗之间产生微妙的耦合关系。
2)设计师因素。
镰仓期间,举国兴禅之风也使得禅僧备受武士宠幸,禅僧地位得到提升。而庭园设计者如梦窗疏石、雪村友梅以及修建仁和寺的石立僧等,均为当时的作庭家。由于梦窗禅学功底深厚,其设计的西芳寺楞伽窟石组富有禅意一说,为武士与统治阶级所钟爱。由此,镰仓期间众禅师时兴造园也是赋予枯山水禅意的重要因素。
1.2.2 镰仓时代“筑山写意式”枯山水造型形成因素分析
“枯山水”一词继《作庭记》《尺素往来》之后并未出现在任何文献中,直至江户时代末期,喜多村信节的随笔《嬉游笑览》中才再次出现“枯山水”的文字记载[23]。但室町至江户时代流行的《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筑山山水传》,以及《房屋杂考》等绝大多数古籍中并未出现“枯山水”文字样式。而诸如西芳寺、大仙院、龙安寺等枯庭在江户时代以前的文献中更多是用“假(仮)山”一词予以记载[24]。尤其是与镰仓期间僧侣相关的诗赋与古籍中,“假山”作为“枯山水”“石山”等词的统一描述极为普遍(表2)。

表1 日本枯山水造型嬗变过程
镰仓时代,从相关诗歌典籍中可知僧侣庭园置石背后有着极为浓厚的假山之爱好(表2)。据《(故大德正法国师)古岳大和尚道行记》中记载,大德寺大仙院创建者古岳宗亘有云:“禅余栽珍树,移怪石,以作山水趣者,犹如灵山和尚(1295—1369),古今圣人皆为之。[25]”表明僧侣假山趣味历史源远流长,“假山”作为庭园石景的统一称谓,于镰仓期间广为流行。
镰仓时代的僧侣假山造园之趣极可能源自中国。《古事类苑》中记载:“茂陵富人袁广汉,筑石为山,高十余丈,假山之始也。”而《庭训往来注》《平家物语》等古籍中则是用“枯泉水”的汉字记载假山庭园[26]。说明假山筑园之手法可能源自中国并在镰仓时代尤为盛行。由此,“假山水”→“枯山水”的发展图式极有可能成立。不仅如此,在众僧人的诗赋中,如别源圆旨的《东归集》以及虎关师炼的《府亭假山》中,均出现“拟山”“缩地之术”等词,但该造型思想仍是基于中国《后汉书》《神仙传》等书中传递的神仙起源思想[27]。因而,镰仓时期在神仙思想支配下的僧侣假山趣味与禅学之境应时、应势而合,是“筑山写意式”枯山水造型应运而生的主要原因。

图3 《潇湘八景图卷》屏风局部(引自《日本美术》)

图4 龙安寺石庭[5]
1.3 室町时代“平庭写意式”枯山水的形成与发展
室町时代,平庭写意式枯山水形成并独立于寺社之中,该造型受宋代山水画、军事,以及河原者介入造园等因素影响至深。
1.3.1 宋代山水画的影响
宋代山水画“边角半边”的院体图式不仅契合日本民众偏爱空寂幽玄的内在情致[28],也与自古以来僧侣的假山趣味不谋而合,因而引入日本之初就大受追捧。室町时代,古籍《君台观左右帐记》中记载了足利氏家族收藏有牧溪、玉涧、马远等宋代画家的山水画③[29]。在《筑山庭造传》的“叠石法”“山水远近法”等内容中,就有以画论的远近法和构图法进行筑园的记载④。因而平庭写意式枯山水或许出自于画技高超的禅僧之手,如在南宋《潇湘八景》山水画的影响下,相阿弥对龙安寺枯庭的设计(图3、4),以及他在大德寺屏风遗留的山水画与大仙院远近虚实构图法的相似性[30](图5~8),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山水画对平庭写意式枯山水发展的影响。

表2 与僧侣假山趣味相关的诗赋与古籍
1.3.2 军事与自然环境因素之影响
室町时代平庭写意式枯山水造型的形成与军事战略据点及其选址环境密不可分。《无象和尚行状记》最早记载了京都临济禅宗之五山,这些寺院在选址上具有明显的战略意图[33]。禅寺因需收集军事情报多设于战略要地、交通要冲或制高点[34],因而庭园布局往往因山就势。由于制高点处,即京都盆地中部地势较高,地表水系极为匮乏,且琵琶湖开渠引水前京都尤为缺水,所以“无水禅庭”多布设于此[35]。不仅如此,历时12年的应仁之乱,使京都经济尽显颓废之势,原有的池庭无法建造[36],而京都盛产白川砂以及白川石、加茂川水石等石材,这些因素均为砂石组合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1.3.3 河原者造园过程中将盆景艺术融入枯山水
室町时期平庭写意式枯山水的形成与河原者介入造园关系密切。该时期的《荫凉轩日录》一书中记载有善阿弥(河原者)及其集团具有土木、建筑、造园等方面的卓越技能⑤。身份卑贱的河原者凭借高超的园艺技术获取丰厚待遇并巩固整个集团的地位。由于寺社中的盆景主要是以善阿弥为首的河原者参与维护管理,河原者介入造园过程中受盆景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枯山水与盆景在造型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37]。且室町时代河原者多以《植树排石择吉凶选月日之书》为造园依据,书中传递的风水理论与盆景艺术颇有联系,进而影响至庭园造景,如五台山地形影响下的龙安寺石组布局[38]。

图5 《潇湘八景图》局部[31]

图6 大仙院东庭[18]5

图7 大仙院东庭以南[32]55

图8 大仙院南庭[32]198
1.4 日本近现代写景式与写意式枯山水园林并存发展
明治时代,传统枯山水受欧美园林影响而停滞不前。直至昭和时代,造园学者永见健一在《造园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由“林泉回游型”“筑山型”“茶庭”构成的日本庭园系谱[39]。但枯山水仅附属于“筑山型”一类,并未受到重视。之后,《京都美术庭园大观》登载了重森三铃的“京都庭园一览”调查报告,其中将京都庭园分为“枯山水系”“池泉系”“综合系”三系[40],该报告表明京都庭园的主流是枯山水,由此,枯山水才被人们重新审视与认识。战后的日本为展示其民族精神的优越性,众学者如铃木大拙开始用禅宗界定日本民族精神中“和谐”的一面,继镰仓时代后再次将禅宗融入枯山水文化中,并推广至世界[41],使枯山水富有禅意一说受到西方造园界的追捧与喜爱。日本民族结合时代,将写景式与写意式枯山水相互融糅、创新发展,其造型与内涵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
2 从日本枯山水演变历程谈中国“枯山水”的发展与创新
2.1 中国枯山水发展现状
日本园林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影响着中国园林,尤以枯山水为甚。枯山水由于小巧、精致等特点为设计师及其客户所热衷,而“禅意”一说更为之笼罩一层神秘的色彩,在中国本土进行盲目增建已呈现流行化趋势。纵观众多中国已建成的“枯山水”,从设计选材、空间尺度和造型特征上看大多是日本枯山水后期样式即“平庭写意式”枯山水[42-43]。石与砂的浑然组合再经“禅意”理念的包装,成为一种新兴的潮流所在。在中国,枯山水背后的“禅意”理念似乎超越其样式本身,但无论是禅意理念抑或是造型本身,仍旧难以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与接受[44-45]。枯山水在中国如何进行演变与创新才能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值得反思且亟待解决。
2.2 基于日本枯山水变迁过程谈中国枯山水的发展与创新
2.2.1 明确枯山水在中国园林中的文化定位
日本枯山水演变过程中受中国假山、宋画、盆景等文化艺术影响,在最初的磐座、砂石立柱等造型基础上不断深化与革新,才形成最终的形态样式。外来文化的补充与完善作用必须建立在本国文化延续性的基础之上,才能符合大众根深蒂固的审美趣味与艺术鉴赏力。而中国现阶段只是将平庭写意式枯山水照搬至园林中,而未找准其最佳定位,因此显得格格不入。结合日本枯山水发展历程,中国“枯山水”在后期的发展中,可将日本枯山水具有的艺术特性融入中国园林,如在枯山水园林中创造可进入游赏的观景布局方式,强调中国园林动态游赏性与枯山水静态观赏性的对比。这样,既能将枯山水合理地融入中国园林,也有利于2种园林文化的渗透与交融。
2.2.2 注重日本枯山水文化的普及
园林发展与创新要建立在大众对园林文化的理解与认知之上。日本枯山水由构成庭院的一角到独立于寺社中,再由寺社转向整个社会,这一过程涉及大众对枯山水文化转变的认同与肯定,大众的审美偏好会影响并促进风景园林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枯山水在中国不能只是为少数人服务,应该面向社会并向大众普及枯山水文化知识,包括日本枯山水演变过程、日本枯山水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以及日本枯山水的鉴赏与审美方式等。设计师应依据大众的感知和反馈对枯山水进行改进和完善,这对中国枯山水的发展和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2.2.3 中国枯山水设计应结合场地与自然特征
日本枯山水在借鉴中国文化后,最终样式仍具有中国假山、宋画等艺术观赏性;日本枯山水受佛寺神社面积大小限制,在庭园中主要起装饰性作用。基于上述特征,中国枯山水应结合场地面积,同时顺应自然而发展。在建筑中庭内,可利用枯山水精致、简洁等特征创造静谧、素雅的空间氛围。在面积较大的室外环境中,可创造以中国园林为主体、借鉴枯山水造园手法的复合式景观,即以卵石为底,再于周边种植各类湿生植物,利用雨水创造干枯景观与水生景观于一体的多样性生态景观,这样既能营造庭园艺术性效果,也符合生态景观建设需求。
3 结语
日本枯山水完成了从古代的自然写实到镰仓、室町时代的写意表达,不断地脱离自然的原生性而向着更高维度的精神内涵进行演替和完善,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善于将外来文化恰如其分地嫁接、融入至枯山水中,使其成为日本庭园的标志性存在。直至今日,枯山水形式及内涵仍在不断地丰富与提升,并影响着西方极简主义思潮乃至整个世界[46]。鉴于日本枯山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枯山水”应摒弃对日本枯山水造园元素、形态的一味模仿,继承唐宋时期影响日本造园的精神遗产,未来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及特定的自然环境进行演变与创新。
致谢:感谢东京农业大学服部勉教授提供日本相关论文与部分参考文献资料;感谢浙江农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陈高敏帮助查找文中所引用的部分日语文献资料。
注释:
① 日本古代在祭祀神灵时,需要专门的祭师(史称“さにわ”,原有“清庭”之意)来传达神灵旨意。“祭师”一词也喻指神灵所指定的洁净场所(如砂庭)。《古事记》的“仲哀天皇”一章中记载了大臣武内宿弥在砂庭得到神灵的旨意,其后神灵进入神功皇后体内并传达了神谕。
② 《李部王记》:“平等院原为源融在宇治的别墅,其后并号为宇治院。”而栖霞观(现清凉寺)则为日本第56代天皇清和天皇在寻求佛道的过程中曾经休憩的地方,该史迹于《三代实录》(卷38)中有所记载。
③ 日本在16世纪前期,足利氏家族收藏有牧溪、梁楷、马远、夏珪,以及玉涧等宋代画家的山水画,如牧溪的《猿鹤图》《观音图》、夏珪的《风雨山水图》等,这在《君台观左右帐记》(能阿弥、相阿弥合著)一书中有详细记载。
④ 《筑山庭造传》中记载有“平野之事”“庭坪地形之事”“二神石之事”等造园之手法,其中在“立石阴阳之事”“山水远近之事”“叠石之事”中就有以画筑园的论述。
⑤ “河原者”为日本中世纪受歧视民众的称呼,又可称为“非人”“散所”等,常居于河滩等不收征税之地。由于身份卑贱,主要从事屠宰、清洁、筑园等工作。室町时代古籍《荫凉轩日录》中记载“山水河原者”有土木、筑园等方面的卓越技能,并且山水河原者也有集团所属及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