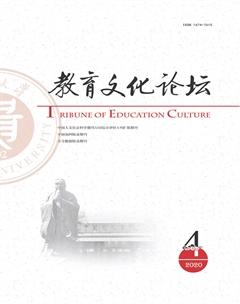苗族社会文化传承中的教育学探讨
杨珂 吴小花
摘 要:在教育人类学视野下,文化传承与教育学所探讨的实为同一话题。以往对苗族社会中传承问题的研究大多注重其表面特征,而对这种特征的形成过程缺少追索。本文以盖赖苗寨的传承现状和当下的传承特点及传承人的亲身体验为案例,追问这种特点的形成根源。在探究中发现,苗族传承机制是苗族社会各要素的有机联接,且在联接中呈现出传承智慧,对当下的学校教育具有深刻启示。
关键词:文化传承;教育人类学;盖赖苗族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0)04-0039-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0.04.006
Abstract:I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edagogy are actually the same topic. In the past, most researches on the inheritance of Miao society focused on its 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s, lacking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ases of current status of inheritance of Gailai Miao Village as well as the current inherit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heritors,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 of this characteristic. In the investig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Miao inheritance mechanism is an organic conne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Miao society, and the inheritance wisdom is presented in the connection, which has a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o the current 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cultural inheritance;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Miao ethnic groups in Gailai
功能學派认为,无文字社会是通过口头传承来教育民众[1],这就说明无文字社会中的口头传承与当下教育所实现的功能是相同的,两者所探讨的就是同一话题。有学者将苗族的古歌传承方式划分为家族传承、拜师传承、社会传承三种方式[2]。但这种划分方式无法道尽苗族社会中古歌传承的复杂形态,例如家族传承与拜师传承两类之间可能有所交叉。就盖赖的经验来说,可能是家族血缘促成了师徒关系的结成,师徒传承就是建立在家族的血统机缘上。而社会传承也与家族紧密相关。苗族人的集会大多以家族为单位,能够在公众场合中接受传承的也多为家族中人,他们比血缘之外的人获得了更多的传承机会。此种分类能够概括苗族社会的传承外在形态,但却无法从中获得更多教育学上的启示。要想从教育学上来探讨,就需要在外在传承特征上更加精细深入地考察。
一、文化传承中的教育视角探讨
谈及教育,我们不得不从其最根本的定义开始探讨,而这定义的内涵可表述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文化传承[3]。不可否认,在当下的话语系统中,人类社会的教育定义是处在不断狭隘化的历程中,教育从文化传袭这个本质中不断缩小,在其广泛的定义上附加上了很多要素,故此教育定义便具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教育指为教育的专业化提供手段。要探讨传承中的教育问题,就必须先从定义上来切入。人们对教育的定义已经包含了关于教育内容及任务的最核心洞见。如此,便有必要从广义的教育定义开始。“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4]可见,从群体视角来看,教育所传授的内容包括两点,就是增进外在的生存技能及影响内在的精神世界;而从学习者个人来说,教育就是个人获得知识和见解的过程,个人的观点或技艺由此得到提高。因此,广义的教育定义则可以在更广泛的范畴内来探讨教育,让不同群体的教育智慧能进入教育领域的视野,从而为狭义的教育提供借鉴。而在多元文化下探讨教育问题,且追溯教育的广义定义,恰好是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基础。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文化传承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濡化过程,也就是指一个共同体的社会文化在其成员中的纵向交接过程。按照人类学的多元论观点,不同群体因为其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群体特征而具有不同的纵向交接方式。因此,深入不同的群体中获得其文化的传承特点是教育人类学的研究目标之一。而教育人类学的这种任务预设,就来自文化的传承是教育的本质这个前提。文化的延续和存在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如果没有每一个文化群体长期累积而成的教育机制,该群体的文化很难展示它的活力和历史长度。如此说来,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文化是通过一个群体所形成的特定教育方式传达给下一代,而下一代根据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对文化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创造新的文化,这便是某个群体的教育实质。
从教育人类学的这个预设引申开去,对于一个文化群体而言,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是文化创新的首要基础[5]。人们只有以本群体中固定的教育方式来进行族内的文化续接,才能在续接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从而不会被不断发生变迁的社会价值所抛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传承和广义上的教育就是同义的,两者无论是从目的还是手段上几乎就是一致的。
基于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有助于揭示长期被教育研究界忽视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互动、他们各自的态度、情感和生活体验及其对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影响”[6],本文旨在人类学观察和访谈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作为教育者的传授者和作为被教育者的传承者的情感与体验,从中获得当地人在文化传承中所呈现出来的教育特点,继而深入探究这种特点的形成原因。
二、盖赖村及其文化传承现状
在探讨一个群体文化传承中的教育问题之时,必须将这一问题置于其社会文化背景中才得以阐释[7],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本文的探讨区域——盖赖村的当下状况进行介绍。盖赖村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东南部,是该县久负盛名的苗族村寨。盖赖村离县城17公里,从县城到达村里,必须沿着都柳江沿岸的蜿蜒公路前往。可以说,地理位置的僻静,使得盖赖人的交际圈子局限于周围的苗族村寨、水族村寨中,有限的交际圈让盖赖的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播,并使得外界的其他价值观难以进入村内,传统文化传承得以很好保存。
盖赖村苗语称为“Khat hlas”,也就是富裕的客人之意,盖赖就是苗语发音的音译。可见,盖赖人天生就热爱自己的家乡,这种热爱对文化的传承起了决定性作用。
盖赖村下辖五个自然寨,分别是党柳、杨家中寨、杨家下寨、李家寨和地翁。这五个自然寨为血亲家族聚居而成,其中杨家中寨和下寨是杨家聚居地,而李家寨则是李家人的居住区域,地翁为刘家人所居。五寨不同姓氏之间可以互相结亲,村内的通婚率颇高。由此,五寨之间既有寻求生存时的团结凝聚需求,也在家族间产生文化上的竞争。由此而来的,就是五寨之间在生计生产上互相协助,亦有文化的禁忌,从而出现自然寨内或家族为传承边界的重要特征。但五寨之间又长期毗邻而居,加上姻亲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出现了突破家族的关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同辈朋友”关系。“同辈朋友”是指年龄相仿的、按照当地的分类大致为平辈的朋友关系。这些同辈人的交往不局限于家族内,只要是谈得来的同龄人之间都可结成这种关系。同輩朋友可以结成跨越家族的文化传承团体,是家族间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盖赖村之所以成为三都县名声颇显的村寨,在于寨子内保存良好的苗族传统文化体系。其中,吊脚楼工艺、蜡染技艺、芦笙文化体系、古歌等口头知识体系均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保存。如果以单项的技艺来看,盖赖也许并不是那一带苗族寨子中最为突出的,但如此多的传统文化事项在盖赖这个特定的空间中都得以保存,其完整的资源优势便体现出来了。按照教育的定义,本文也将盖赖的文化传承划分为技艺传承和影响其精神、品德的口头古歌类传承。
盖赖村当下传承最为完好的要数吊脚楼技艺。吊脚楼是盖赖人的传统建筑形式,苗语称为“zaid leb”,也就是楼宅的意思。鉴于盖赖山高坡陡的地理环境,盖赖村内的宅基都是在陡峭的山体上硬生生开凿出来的,面积狭小且外临陡坡。这种宅基决定了盖赖人想要修建房子只能采取吊脚方式,吊脚方式是能在有限的宅基上建筑出宽阔木楼的唯一选择,吊脚技艺也成为盖赖木匠必须掌握的本领。地势决定了吊脚楼成为不可遗失的技艺,因此,这是盖赖目前传承状态最好的传统技艺。根据寨子年长的木匠统计,寨内能独立主持吊脚楼修建的木匠至少有50人,这个传承人数与其他项目比较起来算是颇为庞大了。
如果说吊脚楼技艺是男性专司,那么蜡染技艺就是依靠女性来传承的。在盖赖“白领苗”支系中,蜡染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是女性的盛装,主要是盛装中的上衣的肩领及衣袖部分和整条下裙;二是作为家居装饰用,诸如女性常用的布包,家里常用的布帕;三是作为仪式场合用品,盖赖老人去世之时需要一张绘有特定符号的床单,作为老人的陪葬之物,据说这是逝者获得祖先认可的凭证。这些实际的功用,使得盖赖的蜡染技艺得以继承延续,而这项技艺的实施者大多都是家中的女性。
除了技艺之外,盖赖村的口头知识体系承担着盖赖人日常知识储备、交际礼仪、道德修养、行为约束等诸多方面的教育。即便是生活技艺的传承,也是在口头传承体系中才能找到其来源。可以说,口头知识体系承载了盖赖苗族人世代生活的经验智慧,它以神话、神辞、传说、古歌等名义进行传承,是他们关乎宇宙来源、祖先根源、生产技巧等知识的传递。其中,古歌这种口头传承方式最为常用,占据了口头知识体系的绝对比例。古歌下又有多种歌类分类,是一个适合于不同年龄阶段进行传唱的庞大体系。
三、盖赖文化的传承特点
从上文对盖赖村的介绍可知,盖赖村目前的传承项目主要是技艺的传承和口头歌类传承,这两种传承具有浓郁的当地特点。
1.以血缘的远近为主要传承依据,并以此为纽带衍生到姻亲之间的传承
在这个传承方式下,盖赖村形成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亲缘相交叠的传承样态。盖赖作为一个自然行政村,下辖五个自然寨,这五个自然寨就是不同姓氏的家族聚居形成的。正是因为当地人的传承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因此,每个自然寨皆有自己更擅长的技艺。盖赖村杨家上寨和杨家中寨为杨氏一族聚居之地,寨内最为擅长的便是吊脚楼手艺,这门手艺在盖赖主要由杨姓家族的男人们来传承。现在杨家尚能用木工工具做木工的年长木匠是76岁的杨公,他的手艺自其父亲那里传承而来,到他的孙子已经传了四代。作为杨家木工行当的领衔者,他亲自传授的徒弟为他的两个儿子、他的亲侄子、一个女婿、两个孙子。从杨公的传授情况来看,传授者和传承者之间主要为直系血亲关系和由直系血亲衍生的姻亲关系。当然,杨家寨内的其他木匠也有一些人偶尔上门求教,这些人是距离较远的血亲。
从杨公的传承关系可以看出,盖赖苗族的传承是以血缘为基本准则,血缘关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教授内容的广度。苗族人是以父系血缘为聚居条件的,在条件许可下,血缘的远近决定了地理位置的远近,而这两个距离决定了师徒之间的交往密度,密切的交往当然为传承创造了条件。同样是吊脚楼工艺的教授与传承,直系亲属间的传递内容明显更为宽广更成体系,所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而关系较远的旁系亲属只能在师傅闲暇之时进行零星技巧的传授。
2.对口头传承体系进行分类,按照不同年龄阶段进行不同内容的传承
除了以亲缘和地缘为传承依据的血亲传承特性外,盖赖村中的传承还呈现出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传承不同内容的传承机制。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苗族人的个人交往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即婚前的个人交往和婚后的家庭交往。如果说婚后家庭间的交往是以家庭、家族为界限的,那么婚前的个人交往就是以年龄为界限的,而婚前的青少年时期是苗族人学习各种技能的最佳时期。苗族社会青年男女长到四五岁就会逐步摆脱纯粹的家庭内部交往,逐渐在自己的活动区域内寻找可以一起玩耍的朋友,形成自己的同辈朋友圈,是为“同辈人”。苗族村寨的同辈人是指年龄差距在五岁以内的同龄伙伴,这个同辈人之间的交往不仅突破了家族的限制,甚至突破了村寨的限制。苗族的传承除了家庭、家族的启蒙外,同辈人之间的互相监督与影响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苗族人的家外传承就从同辈人的结团传承开始。
以盖赖村中唯一的汉族家族石家为例。石家目前的古歌传承人石老人,姑且称为石老,从他的学歌经历就可以窥视盖赖在传承过程中按照年龄进行不同內容传承的教育智慧。石姓老人是盖赖村中最有名的歌师之一,他的传承经历代表了同辈人结团传承的典型。石姓是盖赖村中为数不多的汉族人,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家的祖辈要娶亲都是远到临县去找汉族人家结亲,可见他们与寨内苗族人还是有隔阂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平等政策的不断深入,石姓汉族与寨内苗族开始频繁交往。在这种交往中,作为少数石姓人,必须要学习苗族人交往规则才能获得认同。石姓汉族人不仅学会了说苗语,保证了与苗族人无障碍的交流,同时还迎娶苗族姑娘,与苗族人结成较为稳定的姻亲关系。然而,盖赖姻亲之间的交往主要以酒席的交往为主,而酒席上的交往便以古歌为基础。于是,学习苗族古歌就成为当时石姓家族与苗族人进一步交往的重要任务。
石老出生之时正是石姓汉族与寨内苗族人建立密切关系之时,他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结交苗族小伙伴,与他们一起玩耍学习。由于家中老人并不擅唱苗族古歌,石老的苗族古歌都是与同辈的苗族小伙伴一起结团学习而来。盖赖苗歌按照功用和歌唱场合的不同主要分为花歌和酒歌,花歌就是年轻人谈恋爱所唱的歌,而酒歌就是某户人家或者某个家族招待来客之时在酒席上所唱的古歌。花歌一般短小而精悍,一般可以单独歌唱。花歌虽然不乏历代所传承下来的经典唱词,但大多数人学成之后便可以根据当下语境进行创作。盖赖人学习苗歌一般从学习花歌开始。花歌的内容是教授青年男女恋爱时的礼仪的,具有歌唱禁忌,有家中长辈幼小、异性兄妹在场之时不唱。这种歌唱禁忌形成了花歌必须是同性同辈人结团学习的模式。石老就是在同辈人结团学习的模式下顺利打破苗汉之间的界限,学会了苗族花歌,与苗族姑娘恋爱结亲。
3.“打平伙”聚餐式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
盖赖苗族人将他们在学习技艺、古歌之时的聚餐称为“打平伙”。“打平伙”是当地对聚餐的别称,具体形式是大家约定时间和地点,每人从家中拿出自家酒肉,大家聚在一起喝酒交谈。盖赖苗族在世代的传承经验中,将传承的现场营造成一个快乐场域,学习者与教授者都是在寓教于乐中完成自己的传承任务。无论是学习哪一种技艺,盖赖人都很少举行严格的拜师仪式,所以,传授者与学习者之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徒关系,这为学习过程中的轻松氛围提供了基础。
从上文可知,在盖赖的口传古歌学习中,按照学习主体年龄,大致可分为少年同辈人的花歌学习和成家后同辈人的酒歌学习。这两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虽然内容不同,但学习方式一致,就是不约而同地把学歌当成是同辈人之间的聚会,他们的学习是在伴随着玩笑和打趣中进行的。
少年同辈人学习花歌之时大多年纪在8至15岁之间,这些青少年去学花歌之时,或从家里带一个糍粑,或从家里带碗甜酒,有些人甚至带几把黄豆。甜酒和糍粑可煮甜酒粑,黄豆可以炒来当零嘴。可以说,花歌的学习夹杂着快乐的食物分享,这对青少年来说是一种稀奇又难得的体验。而刚刚成家生子的同辈人群中,结婚就意味着具有了在家族所举办的酒席中接待客人的资格了,酒席接待能力的强弱主要是以是否会唱酒歌为主要标准。因此,结婚生子的同辈人,在歌师家除了学习酒歌,也学习酒桌上的礼仪,包括酒量的锻炼和敬酒、挡酒等各种经典理由。于是,结婚生子的同辈人要去歌师家学歌之时,大多是从家中带上米酒或者下酒菜前往,他们的酒歌学习是在聚餐式的歌来歌往中进行的,使得他们在模拟酒桌的情境中能更快地将所学运用到实践中去。
从以上两组不同的学习方式可以看出,尽管青少年同辈人和婚后同辈人所学习的内容不同,但却都将学习视为是同龄人之间愉快的聚餐行为,这种做法保证了他们是在快乐中学习的。可以看出,盖赖苗族人不把学习当作一件殚精竭虑的苦差事,而是当成一次愉快的同龄人之间的聚会。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聚餐式的学习并未降低学习效率,相反,他们的学习进度颇快,几千行的古歌一般人不到一个月就能学会,而记性好的只要歌师叙述一遍就可以记下,这除了苗族古歌中特有的记忆方式外,也得益于学习者是在快乐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为有效学习提供了保证。
盖赖村刘姓老人在描述他与自己的同辈人学习花歌时的感受说:“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寨子内的小学上学,由于不会唱歌经常被同校的女同学笑话。我们同辈人约起去学花歌的时候,我现在就只记得能吃到很多平时都舍不得吃的东西,才正式去学几个晚上就差不多学会了。”而学习酒歌的时候,石老也表示自己学歌的过程是很快乐的,都是同辈的兄弟及媳妇,大家喝喝酒、聊聊天,歌就在玩笑的话题中学成了。从他们的学习经历可知,大多数人将学歌当成了农闲生活中的一件乐事。
4.传承即运用,口头传授与实际运用相辅相成
无论是口头古歌的传承还是技艺的传承,盖赖苗族人都坚持口头教授与及时的实践运用。古歌传承之所以按照年龄进行不同内容的传承,就在于不同的年龄段所需要唱的歌类不同。青少年正是恋爱时节,需要学会花歌才有与姑娘谈恋爱的资本。而学习酒歌更是如此,学习场域就是运用场域的模拟,待歌师的口头教授完成之时,学习者就已经学会了酒歌的真正运用。可以说,看起来以口头传承为基础的古歌传承,其实也是讲求实践运用的,按照年龄进行不同内容的传授更是为古歌的现场运用提供了条件。
技艺的传承更是以口传为第一步骤,以实践为第一准则。在询问杨家寨族人吊脚楼技艺传承人过程中,每当问到他们跟师傅学了多久才学成的时候,他们都一致回答师傅只是稍微说说,其余的都是自己学成的。在后来的多次问询中才发现,他们所谓的跟师傅学习是指师傅的口传部分,即师傅通过口授的方式将自己的技巧、心得告知徒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吊脚楼技艺的传承过程中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其他都是在实践中完成技艺传承的。吊脚楼技艺的传承步骤,一般第一步是师傅向徒弟讲述以下内容:工具的种类及用途,修建吊脚楼主持木匠的个人修为,建立吊脚楼过程中的日子择吉、仪式主持,等等。这个口授的过程大概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而其他时间都是徒弟自己的实践操作。
杨氏家族中第三代木匠杨江(化名)的学习过程,呈现出吊脚楼技艺传承中的口头传授与实践运用相结合的特质。杨江的祖辈、父辈都是传承吊脚楼技艺的木匠,正是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喜欢做木工。在尚未拿动工具的放牛娃时代,他放牛闲暇就已经开始用山上的树枝搭建吊脚楼模型。而到了十来岁能使用工具的时候,他父亲开始有意传授他诸如裁切、镶嵌木板的诀窍,但这些口授都是在正式的实践现场中进行的,这种点滴式的口头传授融入长年累月的实践中就显得微乎其微,以至于很多木匠在被訪问之初都否定自己被师傅教导的过程。
蜡染的传承更是口传与实践同步进行的典范。由于蜡染布在盖赖村中具有地位超然的用途,大多女性从小就要学习这一技艺。在盖赖村的三个自然寨中,李家寨李氏家族的女性以善于画蜡和染布著称。李氏家族的女性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随母亲、姐姐学习画蜡,一般到出嫁之时已经是做腊料、画蜡、脱蜡和蓝靛染的能手了。李二莴(化名)的蜡染学习经历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她是家中幼女,母亲就是李氏家族中的画蜡能手,她的几个姐姐均得母亲真传,特别是大姐更是一众姐妹中最为出色的,她就是在大姐的指导下学习蜡染的。李二莴说,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姐姐们一边画蜡一边唱蜡染古歌的场景,古歌中讲述了苗族人画蜡的来源、染布的季节等。在这些古歌声中,李二莴关于蜡染的知识积淀已经完成。待到拿稳蜡刀时,姐姐便从握刀、沾蜡、着力开始传授,讲毕就直接让她在蜡布上实践。从握蜡刀那天开始,她的蜡染技巧主要是通过真正的实践来提高,佐以口头上的诀窍传授。
从杨江和李二莴的学艺经历可看出,即便是动手实践为基础的技艺传承,也是需要口头传授作为基础,技艺的实践是建立在对该技艺所属的文化体系的理解基础上。盖赖苗族与其他大多数地区的苗族一样,传统技艺的技巧都是以古歌的形式进行程式化传承,这使得其技艺的基础理论都是以诗歌体的古歌来记载,其学习的第一步就必须依赖于口头的传授方式,待对这种技艺有所理解之后,才进入实践性的系统学习。同时,即便是口传古歌的学习,也是在口授的基础上尽力地创造实践条件,诸如酒歌学习过程中对于酒桌交往的模拟等。
四、盖赖传承中的教育学启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定义认为,教育是为学习而进行设计的有组织的、持续的交流。从这个定义中可以提取出四个因素,那就是交流、学习、组织、持续的时间[8]。按照这四个要素来说,盖赖苗族的传统技艺及口头古歌传承是完全符合教育定义的。当然,盖赖苗族的传承与该定义之间又稍有差异——学习所进行的设计并非当下学校教育中的教学计划及教师教案,而是以当地的生计方式、农时应用、习俗习惯为基础,制订出适合当地人学习的方式,并且以信仰、禁忌等为外在约束力,同时以世代沿袭的方式固定下来——也根据不同的时代进行适时调整,形成符合当地农时及习俗的传承“设计”,这些设计可以给当下的教育学以诸多启示。
盖赖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传承为学习提供了便利,因为举族而居的定居规则造就的血缘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理距离的远近,这为学习者的就近学习提供了更为良好的条件,学习者不仅可以在心中有惑之时及时求教;同时因为教授者较为熟悉学习者的个人品性,更利于因材施教。
盖赖苗族以禁忌、社会评价等多种方式将苗族口传体系知识划分为不同类别,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者提供了适合其年龄阶段学习的内容,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同辈人学习的机制。这种机制在不经意间提供了由浅入深的学习途径,同时由于同辈人平时关系亲密,在学习过程中为学习者之间的友谊养成提供了条件,他们互相鼓励却又互相竞争,更有利于学习。更为重要的是,苗族人有辈分之间的相处礼仪禁忌,同辈人学习使得学习者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学习效果更佳。
盖赖苗族人“打平伙”式的聚餐方式为学习场景确定了欢乐的情感基调,在他们的心目中,学习并不是一项辛苦任务,而是一件人间乐事。学习花歌的青少年可以在学习中吃上自己平时吃不到的零食,学习酒歌的成人能喝上自己平时舍不得喝的酒。但聚餐式的学习并不仅仅只是建立一种快乐氛围,同时也是所学习知识实践场景的模拟,如酒歌学习过程中聚餐场合就是对真正酒席上的场景模拟,为学习者的学习即运用提供了条件。可见,盖赖苗族的传承习性是在自身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除了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固有形态外,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深究这种形态形成背后的各种关系的联接:如若不是苗族本身固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乐于歌舞的民族性格、春耕夏种的生计方式,这种传承形态也不会由此形成。由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传承的机制,更要关注其形成过程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不同要素的联接中寻找到其所内含的教育智慧,以对当下的学校教育有所启示。
当然,盖赖现在的诸多传承项目也与其他苗寨一样,遭遇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除了尚能产生经济效益的诸如吊脚楼手艺外,其他传承项目大多濒临失传,传统的传承机制也停止了运转。持进化论的学者认为,当社会组织从简单到复杂时,口头传承则从繁复走向简单[1]。按照这种推理,苗族的社会组织无疑是呈现复杂化趋向的,但在寻找出越发简单有效的传承方式之前,如何让原有的传承机制与当下价值融合且继续发挥效用,才是当务之急。参考文献:
[1] 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 口头传承研究方法纵谈[J]. 民族文学研究, 2000(B12):3-17.
[2] 罗丹阳.苗族古歌传承的田野民族志[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3] 南文渊.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4):92-96.
[4] 董纯才.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1.
[5] 杨叔子. 民族文化教育自主创新道路[J]. 中国高教研究, 2006(10):5-9.
[6] 滕星,巴战龙.从书斋到田野——谈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范式[J].西北师大学报,2005(1):19-22.
[7] 滕星.书斋与田野——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方法与技术[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1):14-21.
[8] 王卫华.教育的定义方式及评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9(3):11-16.
(责任编辑: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