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响乐,缺失之下的尴尬
景作人
近日,我将所存唱片拿出一一听赏。这次我着重听了交响乐方面的作品,如贝多芬、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马勒、柏辽兹的交响曲,以及李斯特、理查·施特劳斯、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诗等。在重温了这些经典作品后,我的头脑中忽然闪现出一些对中国交响乐创作的看法。
坦率地讲,对于中国的交响乐创作我一直很关心,但若叫我敞开心扉来讲,我只能说是有些失望,因为有很多遗憾存于心中。我认为,中国的交响乐创作至今仍然有着很大的缺失,由此而呈现出的状况是颇为尴尬的。
缺乏抽象思维和逻辑布局
深入了解交响乐的人都知道,交响乐是具有严密逻辑性和多重思维的艺术,它表面上依靠管弦乐发声,但内在还有着“聚核”式的表现空间。而这种表现空间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交响乐最根本的魅力所在。
在古希腊,交响乐(Symphony)是“合音”“和谐”的意思,指的是两个音在一起和谐地结合。然而,交响乐的真正含义并非仅仅如此,因为“合音”与“和谐”仅仅是表层的意思,而与这种表层意思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隐隐存在着的立体层面(即“聚核”空间)。音乐家们在创作交响乐时都十分看重这一特性。他们总是在把握形式(逻辑性)的同时,尽量挖掘交响乐中这种“聚核”式的隐形空间,借以达到用音乐表达深刻哲理性的目的。

要想挖掘出交响乐中“聚核”空间,充分表现作品的思想内涵,作曲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抽象思维的方法,才能达到深入、深邃、深刻的艺术效果。贝多芬、勃拉姆斯、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的交响乐,无不存在着抽象思维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在以套曲形式为结构的交响曲中)。他们常常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隐喻性的思路展开乐段,从而使作品的交响性得到多维式的立体呈现。
纵观中国的交响乐创作(尤其是近现代作品),其中最缺乏的就是抽象思維的运用,甚至很多作曲家的头脑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亦没有对这方面的清醒认识。这种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是对交响乐形式的极大误解,亦是作曲家在创作中难以提升艺术质量和艺术高度的根源。
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多为交响诗或交响音画,很少有包含统一思想在内的、采用套曲形式写成的交响曲,且大多数都是平面化、表现化的标题曲目(命题作品),其中有着太多的具象思维和浅层意义。换句话说,这些作品都是一些应时性的、缺乏深刻想象力且带有表现性质的、由管弦乐演奏的乐曲(有的甚至就是编配式的歌曲化作品)。这样的“交响乐”,尽管有着贴近大众的某些优势,但从本质上说,实在是一种“披着交响乐外衣”的俗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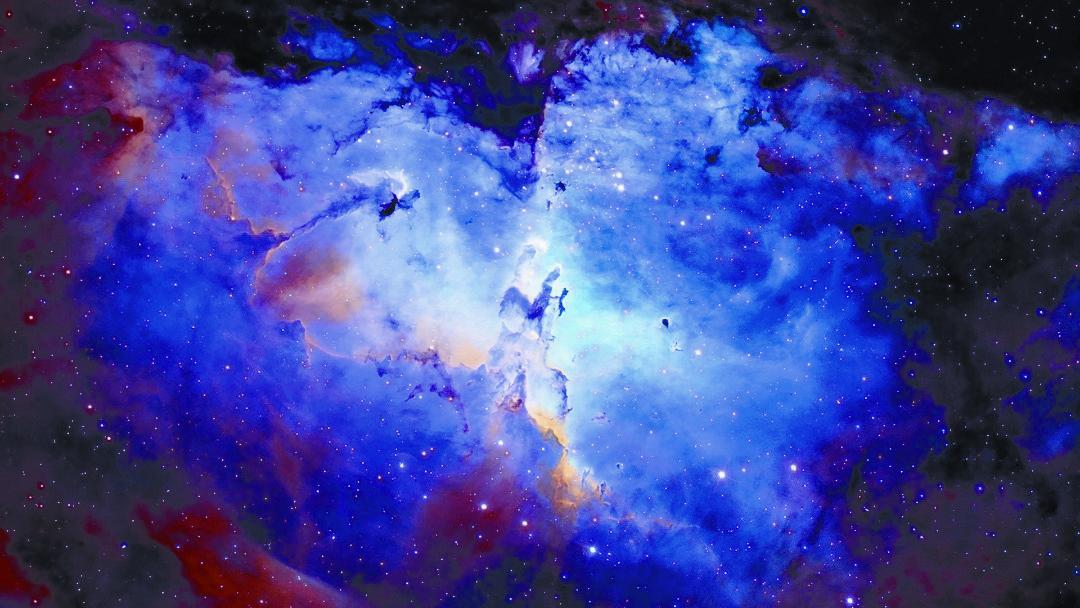
因此,要想彻底改变这种面貌,作曲家就一定要学会如何运用抽象思维来加强交响性中的“聚核”特征,使音乐在这种特征的包容下,与作曲家的内在心声达成默契的融合并展开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将“哲理性”和“统一性”的交响乐本质尽现出来。
此外,中国的交响乐创作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品中缺乏缜密的逻辑布局。很多作品随意性过强,听起来思想不统一、主题不集中、发展不合理,有一盘散沙的感觉。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创作才能的低下与基本功的欠缺是主要原因,当然也有着盲目跟风所产生的浮躁因素。有些作曲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作曲家),传统曲式学还没有掌握好,就急于搞创新、搞花样、搞现代派的东西,致使创作上不严谨、不规范、不均衡,作品失去了交响乐形式所依赖的逻辑布局。也有的作曲家受才能所限,他们本身并不具备写作交响乐的能力,但限于形势所迫或者其他原因,硬着头皮投入创作,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创作技法的盲目与缺失
众所周知,交响乐艺术在欧洲发展了数百年,其创作技法经过几代的传承,如今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翻看世界音乐史,无论是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还是印象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都有着各时期代表性的交响乐杰作,例如巴赫时期的管弦乐组曲(未形成奏鸣曲式),贝多芬时期的套曲交响曲,柏辽兹、李斯特时期的标题交响曲及单乐章交响诗,马勒时期的巨型交响曲,德彪西时期的印象主义交响曲等。这些交响乐作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变迁,不仅将思想内涵及“聚核”空间带到了极致,同时也将技术的发展更新换代并将其推向了高峰。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世界交响乐艺术整体蜕化的必然过程。
中国的交响乐艺术从二十世纪初自西方引入后,至今已有了百年以上的历史,它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交响乐艺术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在老一辈作曲家中(如马思聪、陈培勋、丁善德、朱践耳、罗忠镕、徐振民、杜鸣心、吕其明、王振亚、郭祖荣等)曾涌现过一批颇有价值的作品。后来,“文革”使我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停滞了下来,致使老一辈作曲家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直到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气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开始大量涌入,这使得当时一批颇有才华的年轻作曲家受益匪浅,周龙、陈怡、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何训田等(大部分后来留学于国外)都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的创作带有新的观念、新的技术和新的水平,才华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当然,这同样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和影响。当时,在二十世纪诸多现代音乐技法来势汹涌的情况下,传统技法掌握和经验积累尚不成熟的中国作曲界一时陷入了一种跟风的潮流中。而对于年轻一代的作曲学子来说,跟风潮流使他们在创作上产生了一定的盲目性,由此一些不正常的连锁现象开始频繁出现,从而导致了交响乐创作上根基的缺失与技法的泛滥。
近年来,我经常关注一些年轻作曲家的交响乐创作,发现他们的很多作品是传统不像传统,现代不像现代,是一些“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的描红之作。还有的作品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贴上了“先锋”的标签,为的是借助某些现代派的“云山雾罩”来掩盖自身的贫乏。有的年轻作曲家学马勒,一部交响乐写六七个乐章,又加合唱又加钢琴的,形式上搞得轰轰烈烈,内容上却没有丝毫创意,作品结构乱、质量差,旋律难听、技术糟糕,整体十分浅薄、平淡。
还有的年轻作曲家学十二音体系,学无调性,却学了个“似是而非”。浏览过他们的作品后你会感觉到,满谱面的变化音符和复杂节奏都是一些为了避免调性出现而进行的蹩脚游戏,毫无深刻的音乐内涵可言,亦没有任何艺术上的实际意义和想象空间。



当然,目前很多人对西方现代音乐存有一种偏执的理解,总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标新立异的“怪物”,甚至觉得它们是颓废的、无思想的、无逻辑的混乱音响。然而事实证明,二十世纪的很多现代音乐都是有规律、有发展脉络、有理论依托和表现功能的。近日我也听了一些现代作品,如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艾夫斯、萨蒂、潘德雷茨基等人的作品。我发现他们采用的很多技法都有着合理的用意,无论是抽象表现力还是具象表现力,其效果都是十分明显的。
比如斯特拉文斯基,他的不协和与多调性基本上是建立在“原始主义”基础上的。晚年的序列音乐比较怪异,虽是无调性,但与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并不完全相同。他的《春之祭》最为典型,为了表现远古时代的野蛮、离奇和恐惧,作品中运用了大量不协和和弦,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始节奏。这些都是为了扩大音乐张力、提高生动表现效果而使用的手法。
再如艾夫斯,他的多调性与复节奏(包括微分音),同样是为了追求奇异的效果。在对待新音响的探索方面,艾夫斯所做的很多尝试都是颇有成效的。他的创作形式多样,风格怪异,很多作品带有朴素的现实民族感,例如他的《第二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
最典型的是潘德雷茨基,我听了他的《第三交响曲》和《广岛受难者的挽歌》(为五十二件弦乐器而作)。这两部作品非常现代,有着很多前卫化的技术,风格上也相当得玄妙。然而,它的表现力与震撼效果却非常惊人。《第三交响曲》是潘德雷茨基在创作上走向新时代的代表作,它有着哲理化的抽象思维,技术上将现代手法与古典精神做了“穿越”式的嫁接。而《广岛受难者的挽歌》则是一首表现性极强的作品,有着具体音乐的特点。为了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广岛惨景以及受难的人们企盼和平的心声,音乐中运用了音块、音簌、微分音等现代技法,还发掘了很多弦乐器的“极限”发声,取得了恐怖、凄厉和惊骇的效果。
以上是这些大师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对于这些作品,我听后的感觉是相当信服的。我觉得,他们运用的各种现代派技法,基本上都是有的放矢的心灵创作(当然也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人)。在我的理解中,这些作曲家,不管是什么流派、风格、主义,其音乐创作的目的都是明确的。就像勋伯格,他的十二音体系尽管深奥艰涩,但并不完全是虚无缥渺的音响游戏,关键是要看他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作品是要表现什么内容。例如他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朗诵、男声合唱与乐队),其内容是表现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与残杀。在这部作品中,十二音体系的无调性特征得到了尽情发挥,它所采用的不协和、尖锐刺耳及怪异音列,将当时残暴与恐惧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也许就是无调性音乐具有的最恰当的表现效果。
反观我国一些青年作曲家近年来所写的作品,可以说将现代派技法滥用到了无可附加的程度。他们几乎样样都敢“招呼”,什么十二音无调性、音色音乐、具体音乐、偶然音乐等,“十八般武艺”齐上阵。然而要论这些作品中的音乐效果和音乐内涵,或者是更加高超的音乐意境和音乐特色,却是什么都没有。无奈之后所剩下的,只有“东施效颦”般的拙劣和“邯郸学步”式的可笑。
我曾经听过一些名牌音乐学院毕业生的作品(获奖的),说实话,那些作品令我非常失望。当时我就纳闷,这些青年作曲家究竟在想什么、追求什么、表现什么?作品玄乎、干涩,其中除了变化音的堆砌就是不协和的泛滥,除了标新立异就是空洞乏味。音乐上毫无内涵,技术上也都是一些无意义、无道理、无效果、无规律的杂乱拼凑,既没有传统技法的扎实和严谨,也没有现代技法的精准与超然,完全是一片不知所云的“音响堆积场”。
民族风格的误判与错位
众所周知,在交响乐创作上,民族性的体现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它往往是一部作品风格、个性、特点最终汇集的基础点。如果一部交响乐中没有民族性,那它就不可能是一部成功的、有价值的作品,这一点在历代作曲家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然而,交响乐创作中如何体现民族性?民族性与思想性、技术性如何结合?这种结合又如何升华到艺术理性的高度?这是一个非常深奧的连锁问题,同时也是在实践中必须经历的艰难之举。
纵观世界音乐史,在历代大师的交响乐精品中,民族性都是作为“乐魂”来体现的,它们是音乐的本质,是融合在音乐内核之中的以“基因”模式存在的细胞(民族素材作为动机变化、赋格发展来展开)。换句话说。这些作品中的民族性都是与音乐内容合为一体的,它们同时也是与作曲家内心乐思融合相依的组成部分。

反观很多中国作曲家的交响乐,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民族性往往是被当作“标签”来使用的,且没有任何真实的意义。为了达到所谓的“鲜明”目的,这些作品常常只对作品做一番民族化的“外装修”,并没有将民族性基因深入到音乐“细胞”之中,更没有与音乐内核的发展融为一体。还有很多作品甚至就是将一首民歌配配器,拆卸出一些民族素材做做转调的处理罢了。更有甚者,其作品干脆就是地方民歌的大连奏,根本谈不上统一乐思、主导动机、抽象思维、变化发展等交响手法。这种创作,实际上是对交响乐民族化的一种严重误判,而由此所产生的错位意识,则实为我国交响乐创作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
因此,要想在交响乐创作中体现出真正的民族性,我们的作曲家就必须将民族音乐素材(旋律、节奏、韵味特点)融会在自己的血液中,继而从创作思维开始就能够牢牢地抓住民族性的根本,而非仅仅做一些表面化的“一张皮”处理,或者是偷懒,走一种“搭便车”式的简易捷径。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亲历体会以及对中国交响乐创作的看法。我在此提出,目的是供我国年轻一代作曲家参考,并为他们的创作提出专业发展方面的诚恳建议,而非刻意挑剔与指责,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理解我的用意。
学无止境,任重道远。通过这段时间在家系统欣赏世界交响乐经典,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我国交响乐创作与世界高水平之间的差距。现实证明,缺失得越多,尴尬就越明显,而若想减轻这些尴尬,就必须努力弥补存在的缺失。但愿我们新一代的作曲家们能够继续努力、不断实践,在学习经典、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知耻而后勇,早日提升专业水平,继而创作出被世界公认的优秀交响乐作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