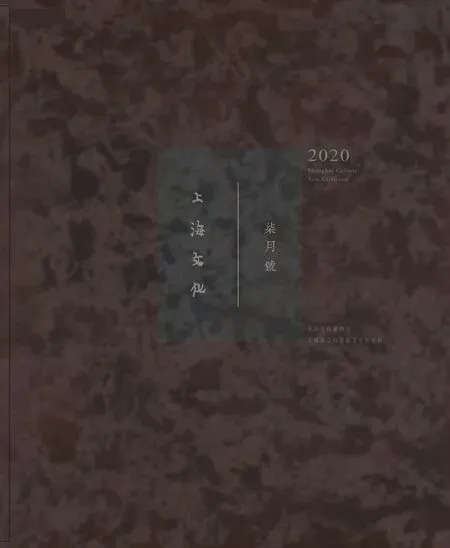“锯齿”思维,或悬崖上“蹦极”夏宇诗歌论
陈仲义
夏宇是台湾诗坛的超级女巫,另类得有些神秘。她身兼多职:诗人、词家、编辑,客串综艺节目、翻译、设计。她的流行歌词拥有数十万粉丝,透彻犀利,却难得在舞台露脸,她的现代诗作极具争歧,却长年匿迹于热烈的研讨之外。她行迹飘忽,在自己开发的天地,我行我素,悠游自得,每隔一段时期总会抛出个怪怪的风信球,引发一阵海啸。
在有限视野内,本人阅读到陈柏伶博士论文,探源 “歧路花园”的秘密路径,用fusion(混合融汇熔接),连带fuzzy(含混模糊糊涂)、 fuckable(可亵渎的)来诠释夏宇的诗写逻辑,颇具说服力。正是这种混融逻辑的展开(破音乐性、被翻译性、拟一次性),消解了诗的边界,让这位超主义诗人,用诗反省诗、质疑文字独大的体制,动员与调配广义符号群参与(从线条、色块、图案、噪音,一直到虚拟混声、造型设计、装置艺术、行动展演)。挑拨意义的疆界、离间诗意的典型,藉此重审各式诗艺的守成与合成。她奉持Copy创造 Original理念,让一首诗的完成过程,每一个组成零件,全部违反我们的习以为常,推翻我们的理所当然。她用极大化的特写和聚焦,让所有的局部与环节,变得既巨大又陌生,怪异又可疑。①
笔者同时还注意到,夏宇在《备忘录》里,收藏了一把非同寻常的《锯子》:
我贴身于黑暗中/继续对一种锯齿状的真理的思考//我从事思考/锯齿状的/譬如一个打开的罐头/我对于罐头的思考如下:/罐头的开启依赖/一种锯齿状的真理//我思考,但是我睡着了/睡眠是一种古老的活动/比文明/比诗更老/我端坐苦思良久/决心不去抗拒它//我思考睡眠/当我/像一把锯子一样的醒过来//我思考锯子
反复四次提到:我贴身于黑暗中,对一种锯齿状的真理的思考;我从事思考锯齿状的真理;像一把锯子一样醒来;我思考锯子。物理意义上的锯齿,是开启罐头、截取木料、剖析年轮、比试刀刃的利器,精神上的锯齿,犀利、尖刻、锋芒毕露,直抵历史、社会、现实的阴郁处。夏宇用她特有的锯齿——嘲讽、挖苦、讥刺、吊诡,来回拉锯着人世间百态。许多坚硬的事物,经不起她的咄咄逼人,尖锐旋进,纷纷解体;笔触下的存在洞穴,露出了些许光线。夏宇既是诗坛古怪的“拾荒者”,又是狡黠的“施魔者”。她兴致勃勃捕捉日常的番茄、啤酒、胶带、指甲刀,把它们与诗之外的细菌、鸽粪、痔疮、溃疡一起排练成踢踏舞;她在恋情、婚姻、厌烦、无聊的困境窒息中,凿开缝隙,争取一点新鲜的呼吸。她从泛爱窥伺萎琐,从趣味嗅出“高雅”,从俗化并入粗鄙,以反向、“非诗”的思维自制得意的容器,盛装个人的尖刻体认,分餐现代与后现代的生活哲学与人生况味。
拿艰涩最重的《腹语术》为例,她提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人间地狱,所有人与物都发生巨大变形:被撕开的、像邮票有着毛毛边锯齿状的小孩(《小孩Ⅰ》);带着不同计数、凌空悬挂、面容平静的“温度计人”(《与动物密谈Ⅰ》);无以计数的座位无以计数的人坐着在看同一部反面电影(《与动物密谈Ⅲ》);集体失踪的小孩化妆成野狗,张望回不去的家(《小孩Ⅱ》);阉掉猪们、油炸所有睾丸、沾点葱花吃了的“接生者”(《颓废末帝国》);用一种完全不懂的伊尔米弟索语,为人性中还未被污染的部分送出深刻表达《(伊尔米弟索语)》;九口人的毛巾,一直挂在同一根木条上等待腐烂变黑(《与动物密谈Ⅱ》);天使们拥有全套的潜水装备,而我们走失唯一的那只羊(《非常缓慢而甜蜜的死》)。现实与超现实颠倒,现代与古典“倒挂”(《咏田园》),“寓言”与“蓝调”合奏,独角兽与马戏班巡回。幽灵们的研讨会,野兽派的乳房,荒诞意识与怪诞手法, “文不对题”的思路,匪夷所思的幻象、臆想,充满癫狂。估计没有多少人能进入这样怪异的文本,也很难适应她的“幽浮文法”“锯齿思绪”:截断、离散、隐没、突兀、插入、闪跳,造成一定程度的接受阻碍。当然,她还不失提供另一种比较晴朗的两人世界,典型如《十四首十四行》。但该诗也完全弃置传统的线性写法,所以才会有陈柏伶的四种解读方法,再次证明夏宇思维的稀奇古怪。第一种解读是将零散的碎片追补成三次分手的线索与场景,最后终结于剩下的“房间”在读这段“错误的翻译”。第二种解读是采撷十四首诗中十四个主意象,借助意象串联起爱与爱欲的象征花环。第三种解读是通过声音与节奏(看见的声音、重复的声音、恫吓的声音、混乱的声音,及消音、扩音、韵味、回声、转韵、叠字等)完成对意味的捕获。第四种解读是通过第二首回忆的核、第四首回忆的壳,第十四首伪装的根的分析去探索主题意识。当然,不止于四种解读方式,还可以从原型、心理、比较、结构、风格、技术等角度进入。但,文本能够承受如此繁多的X光照、显微镜、解剖刀,至少证明创作者拥有硕大的风暴头脑、诡秘的思路,否则怎么受得了一系列的切片、活检、开腔与缝合呢?
左半脑的“锯齿”思维,右半脑的fusion逻辑,造就夏宇在“反诗”与“非诗”的边缘穿山越岭,跑完大半程跨界的马拉松,看起来还一脸轻松,十分自信。“锯齿”的袪魅与“混融”的返魅,无疑是后现代一个有效的书写范式。而游戏性是它的最大硬件。
一 不按规则的游戏
游戏的宽泛定义可来自康德无目的、无功利的审美活动,来自席勒的“寓教于乐”,也来自王国维的广阔襟怀与视野,“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②。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入赫伊津哈的细密观察:“在诗性短语的转变、某一主题的发展、某种情绪的表达里面,总有游戏成分在运作。笑、愚、风趣、诙谐、玩、滑稽等术语,都分担着属于游戏的特征。”③虽然游戏是艺术的源头之一、本质之一,或是雏形,但长期以来游戏性总是蒙上一层阴影,经常被玩物丧志、感官享乐、奢华无聊捆绑在一起,连带“坐庄”。其实,应该将游戏本身的天性与受众因过度沉溺而造成不幸的负面区别开来。
夏宇多年旅居法国,深受法国前卫艺术运动的影响,包括塞尚的“移动视点”、重复涂抹的上色方式,杜尚的“反艺术”“纯形式”,以及达利(西班牙)的超级变形,马格利特(比利时)的“波普”,都曾鼓舞她向实验极地大举进军。在先锋精神刺激下,夏宇撕开道德的厚面具,回归游戏的本真。她首先拿自己的《腹语术》开刀,毫不吝啬地放血,楞是对一行行现成的字、词剪裁,然后拼贴到另一本照相簿上,取名《摩擦·无以名状》。COPY、切割、镶嵌,她用摩擦的方式完成第二本诗集的互文性。她希望受众读到原文本的浆糊+毛边+手汗+褶皱的组合,而不是原作可能产生的新意。这种彻底决绝文本的意图明显带有很大的嬉戏成分,或者说,嬉戏本身也包含一定的互文性。拆卸与拼贴,“不求意义,但求愉悦,不求理解,唯求戏逐。就阅读心理而言,是一种自得、自信的表现,就创作者而言,何尝不是抒发后的愉悦、游戏时的满足”④。
游戏性继续扩散到夏宇诗集设计时的各种把玩,比如制造前后版本的巨大差异,字体多变、字号突兀、间距犬牙、用纸参差,未经裁切的书页、赛璐璐片的印制、油墨的深浅、首字位的出轨,等等,都让人联想玩童时期的不定性、好动症,忽而搭建皇宫,转眼间一脚踢翻,旋即骑木马去了。最早是《连连看》初露端倪,应是华语世界第一首引逗读者的互动诗。借用小学生国语测试题,随意选取几组毫无关联的字词,鼓励受众玩把选择的过瘾。十六个词组或字,分居不同位置,在此范围内,可找出最佳搭配。结果十分诱人:没有任何强制、规约,充满随机、任意,即使不动脑筋,完整答题也可收获六十四种结果,与其说它尝试突围文字的霸权主义,毋宁说是争取一次无需签证的自由出入境。笔者试做一下,小结出有三种连结状态可供咀嚼:一种是得体的、有张力的连结组合,如“自由鼓”、“磁铁方法”;二种是勉为其难的连结组合,如“铅字五楼”、“手电筒磁铁”;三种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一塌糊涂的连结组合,如“著无邪的”、“著挖”。在这样的游戏里,林耀德说它“是一首没有中心主题的诗,传统意义的主题消失瓦解了,只剩下是容读者自行设定的各种可能和猜臆”⑤。其实,还很难说得上是诗,只能说,一个文本存在各种可能和猜臆,证明它的无限空间和自由度,完全挤兑了原本文字的独占企图,那些所谓的“文字霸权论”,在非诗的前提下,委实被夏宇戏耍了一把。
比《连连看》胜出一筹的是《简单的意外》,它至少遵循诗的基本守则,在诗的基础上留出空白,让读者在填空中继续一番诗的踌躇。书写者的主体性互文,“变质”为与受众分享,给出诸多可能空间,这是诗歌游戏性的首批告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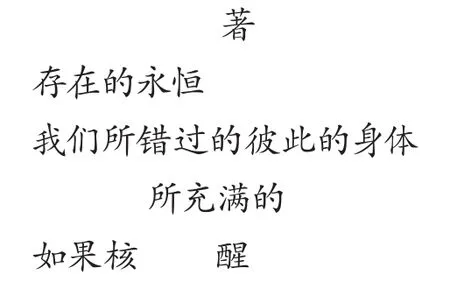
《腹语术》的压轴之作是十四首十四行诗。整体结构布局统一,单篇作品也整饰精到。有趣的是,我们的顽童似嫌过于按部就班,突发奇想,居然把每一首诗的第一句抽取出来,连缀为全新的第十五首,成为流淌血缘关系的“连体婴”,或然?必然?巧合?妙的是,全诗每个句子,仿佛是母体子宫伸出的十四条脐带,既带有母亲旅途的基因,又隐含着新生儿自身的温度与心跳:
Ⅰ时间如水银落地 Ⅱ在另一个可能的过去 Ⅲ她们所全部了然的睡眠和死亡 Ⅳ在命定的时刻出现隙缝 Ⅴ一些一些地迟疑地稀释着的我 Ⅵ在港口最后一次零星出现 Ⅶ在墙上留下一个句子 Ⅷ你几乎总是我最无辜的喷泉 Ⅸ我确实在培养着新的困境 Ⅹ让我把你寄在行李保管处 Ⅺ当倾斜的倾斜重复的重复 Ⅻ所有爱过的人坐在那里大声合唱而他说6点钟在酒馆旁边等我 XIV我的死亡们对生存的局部误译
不管是无意抽取或刻意安排,该诗大抵可以成立,这正是现代诗巨大弹性与张力的优势体现。看成互文、复制、镶嵌、拼贴的混合物未尝不可,也属于高级的嬉戏产物。这让我们想起洛夫曾结集四十五首出版的“隐题诗”,它是形式美学范围内新型诗种。标题是一句诗或多句诗,每个字都隐藏在诗内,形成整体有机结构。如《危崖上蹲有一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鹰》,从标题十七个字延伸为全诗十七行,每行起首字皆按标题字的顺序分别嵌入诗中,全然不觉牵强。夏宇的作法恰是洛夫隐题诗的逆行版——倒过来,从十四篇诗中提取第一句组合另一首诗作,在在是异曲同工。异曲同工,既可比较两者在相反方向的诗写难度,又可比较双方游戏心理的权重。
《被动》则是另一种“声乐”游戏。通过m zgs——5种声母发音——纯粹的能指滑动来抵御所指的过分压制。如何用文字或诗语表现能指发出的声音,通常要动员大量的修辞,以突破听觉与视觉间的鸿沟,通感的做法是架在两者之间的上乘桥梁。韩愈《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琵琶行》、李贺《李平箜篌引》是这方面的绝唱。与建立在音形义统一基础上的古代“音乐诗”不同,现代诗为突出能指的声音作用,往往进行独立抽取、单列:或者让声音走在意义的前面,或者让意涵自行剥离出声音的行列。
她说/m//必须很久很久不说话/才发得出来/这非常低的/m//她说m//然后不动/不想动//那音节不动一丝涟漪/在养着青苔/绿灰的湖//她说/m//然后她说/n/就是不动//有人唤她/像水滴在蜡上/她在蜡里//被蜡封住的湖/湖底轻轻晃动/而不动//的果冻/她的被动//在音槽里/结成冰/z///如果有人在她的胸脯或耳后/用力呵暖/她就会解冻/掉落//像一枚松果/我们就听到/g//先是被吹动的那层汗毛/有点缩紧/然后起来/膨胀/而弯曲/而极想被打开被/穿透/那被动//无限稠密而可以/收缩/用最少的呼吸/她说/s///不转头/亦不张望//想降低/再继续降低
即便有自然形象的生动陪衬(涟漪、养着青苔、绿灰的湖 ),物象的翩翩起舞(水滴在蜡上、冰封、果冻、掉落松果),再配备连贯准确的动作(晃动、吹动、呵暖、缩紧、打开、转头、张望,)声音在声带上的生理运动轨迹依旧十分动听。不必去挖掘能指滑动背后可能潜藏的意涵,能指经由沿途花团锦簇的迎来送往,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赏心悦“耳”。充分提升耳朵“聆听”的分辨率,乃不失现代诗一个重要职责。表面上看,是唇齿喉与声带配合的摩擦振动,实质上可归结于出自生命的内在声音。原因是诗人通过自己的体验,调动周遭的自然意象、贴身物象、本能的生理动作,合成了一次成功的“元音联唱”,也完成了一次心得意会的游戏。这也让我们想起杨黎早年成名之作“扑克”,在无限空旷的撒哈拉沙漠,打出“响当当”的三张红桃K;稍后,又在《红灯亮了》,用八次灯熄与灯灭,完成了一次“无声”声音对于有声意义的领先。但是,夏宇在声音的形象化方面显然胜出一筹。夏宇对声音形式的追求还体现在《一个好的开始》,全诗用十一个动词“燉”豆腐,但也仅仅是强调燉豆腐,别无他意,如此而已。而《嚇啦啦啦》究竟还带点意思,在也许永远不可能遇见的命定中,毋宁做出一种高亢热烈的“诀别”仪式,七次循环式的《嚇啦啦啦》,为友情的谢幕不惜大嚷大叫。
夏宇承认过自己很贪玩,每本诗集都各有其玩法,虽然客观上总是带给诗坛不小的震荡,但其实诗人只为自己而写,她的游戏是为了证明生命与诗的无限可能,而这正是她所说的“用一种填字游戏的方式写诗但保证触及高贵严肃的旨意”。相信游戏对夏宇的意义不只是单纯引发快感的游戏,而更倾向一种自我的追寻,一种因为对诗的热爱,而以诗来证实自我存在的方式。⑥诗与游戏是古代文明世袭下来的一个亲密无间的文化团体,极端地说,诗可以写成游戏谜语,谜语可以变成诗的胚芽。诗和游戏之间的亲和不只是外在的,许多互通的成分明显存在于创造性想象本身的结构中。游戏——谜语——诗,作为某种同源性脉络,当解析的钥匙在直通或曲折的锁孔萦回不已,受到艰涩的阻挡,我们一方面受挫于磨钝的“锯齿”,另一方面,也更乐意投靠她的神秘感。
二 互文,带“假面”的互文
互文性是“锯齿”思维或fusion 逻辑的得力软件。互文性意味着文本间相互的交织、指涉,使得后文本在影响、克服与超脱中带有明显的断裂和不确定。始作俑者巴赫金曾把它看作众多声音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因而产生小说的“复调”与“狂欢”。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探讨诗人六个心理阶段,受制于曲解和误读——完成和对立——突破和撕裂——魔鬼附身——自我净化——死者回归,也充满后代与先驱的继承与超越关系。热奈特于1982年发表《隐迹稿本》,总结互文性五个类型:①互文性(含引语、典故及抄袭)。②准文本性(含序、跋、插图、护封上文字)。③元文本性(指与“评论”的关系)。 ④超文本性(指现文本与前文本“嫁接”关系。⑤统文性(指与读者关系)。如果就此考察夏宇,我们会看到一个后现代的互文大师,如何通过引语、复制、移植、灌水、转嫁、误读等一个个“假面”道具,成功举办一场场诗与非诗的舞会。就整体而言,《摩擦·无以名状》是《腹语术》全方位的COPY、仿制。就单篇而言,比较相似度较高的文本,绝对不少于四十篇。
夏宇接受万胥亭访问时表示:“这是一个大量引号的时代,我们随时可能被装在引号里,头上脚下各一个上引号和下引号,不着天,不着地,飘着、荡着,被命定,被解释,被象征,被指涉、介中,被后设,乱箭穿心,声嘶力竭。”⑦夏宇顺其道推其行,在数量与质量上蔚成风潮,文献、史料、典故、寓言、神话,甚至公告、文书、招贴,都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直接引用”是互文性最明显的表征。在《姜嫄》诗作中,她伸手拿来诗经《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 ”五行诗句,作为不同寻常的起兴;在《印刷术》里,她直接引用史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三行诗句;《开罐器》同样征用美国现代舞蹈大师邓肯的原话,直指情爱关系;《我所亲爱的》,全面移栽《旧约·雅歌》第三章,不忌过度复制他人的风险而乐此不疲;《听写》则复制了《楞严经》的典故。如果说直接引用,是文本的临时补给站,起到辅助、强化、论证的功用。超文本的引用,则具有派生与转换的“生育能力”,它通常用戏拟手段——没有直接拿来底文而是仿作——对典律与教科书范文进行反讽式模拟,经由扭曲、误读的途径,升级了新文本的意义。如《也是情妇》是对郑愁予名篇《情妇》的“翻转”,对男性权力中心话语的一次“修正比”。《南瓜载我来的》,领取灰姑娘、睡美人的材质,通过否定美好愿景,来否定传统的王子公主、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圆满结局的书写模式。《上邪》故意用文不对题的写法,让古老的海枯石烂的爱情诗言志,变成当下一场旷日持久、莫可名状的战争。还有《安那其(男性的苦恋)》,以咏叹调性,融化台语老歌《港都夜雨》,表达对失意男性的同情。而处于偏僻位置的准文本,是充分利用“户外工具”——插图、封面、封底、勒口以及序跋的额外加工发挥余热。如《Salsa》隔页纸的彩插;《备忘录》的四格漫画和无题诗;《逆毛抚摸》的自序;《腹语术》的跋,总是通过多渠道的补充、交代、说明,提升原文本的价值。
《粉红色噪音》则另辟蹊径,在翻译界面上玩起全新的互文游戏,与往常不同,是三明治”式的互文。第一回合是取材于英文为主的一封封垃圾邮件,和网格上捡来的句子,将两者混搭成“原作”;第二回合是将原文本丢给翻译软件,进行平行性直译;第三回合是根据译文的语境或调整或修改,设法分行断句仿制成诗的形式。因机器直译,导致不少生疏、僵硬、差错。有趣的是,这些“歪打正着”的误谬,众声喧哗的排列,反倒有可能孕育“嫁接的奇葩”。至少在夏宇的心目与理念中,这样的噪音,不必进行什么主题集结,只消受个人喜欢的句子,收割异质化的成果便算做大功告成。在前卫批评家眼里,译文更像是原文的一面哈哈镜,其背后,隐藏着超越现存意指,发掘新表意的可能。同时留下一个悖论:它是一本“透明”的书,但却晦涩得令人沮丧。它的晦涩正来自它的透明,直白的翻译产生相反的结果。它最终表明,所有的翻译都是误译,所有的翻译也都是原创。⑧平心而论,有的互文性译文十分可人,与人工没有什么区别,如:This is a document(这是一个愚笨的文件),It is meaningless drivel(它是无意义的蠢话)。有的则充满机械生手,难获认同:I' ll take a trip to the drugstore and slowly browse through the aisles for oodles,(我将采取行程对药房和慢慢地将浏览通过走道为好吃的东西);Like facial masks and hair repair stuff(像面部屏蔽和头发维修服务东西)。女诗人全然不顾软件带来的硬伤,兴味盎然地结集推出,想必是秉持随机感兴的二度创造:诗意未必大量保存,但只要作者与读者共享其中——烦恼与愉悦的过程,本身也就是一种幸福的完成。
有别于机器同步,翻译改写是夏宇另一种互文利器。对法国诗人、女学者Judith Gautier在《白玉诗书》翻译的六首中国古诗,她如法炮制进行大幅度的“翻砂改造”,彰显出弥合差异的努力与更新。没错,“她故意戴着模仿的面具,执意要谋杀诗和翻译,但是我却为她的不以为意感到非常得意,我以为那无疑是一种展示,而且是一种矛盾的展示:因为实际上夏宇是用模仿背叛了模仿、以面具背叛了面具,她用极端阴暗而危险的手段锋芒毕露地重新发明了诗和翻译。”⑨
以上种种,尚属小打小闹,《失踪的象》与《降灵会Ⅲ》才是互文中的最大客户。前者取材于王弼《周易·明象》的底本,对准靶心“象”字,用其他十六种动物、植物与物品的造型“象”进行逐一置换,造成文字与影像合谋、古象与今象“交接”。置换的结果,伟大的经典名篇“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变成了“言者所以明猫,得龟而忘言,蛇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恐龙”,夏宇完全颠覆了传统文字意义上“意、象、言”三者关系,闯出一条让人目瞪口呆的跨界路线。
《降灵会Ⅲ》比跨界还跨界,其机心,对准整个汉语语系。

降灵会是幽灵们泡茶聊天的会所,前Ⅰ、Ⅱ首皆统一采用吾国母语,讨论厌烦话题,到了第Ⅲ首,忽而采用一种全新的自我杜撰的语符,除幽灵们,八十七个“汉字”,绝对没有人能读懂听懂。虽然它留存不少汉语形态的偏旁部首基因,但与万年积淀的音义无关,无异于“星外密码”。显然,夏宇的野心是企图用符号的巨大变形(同时隐含变意),来体现母语运作仍拥有无限自由。这样的异想天开在实践上自然无法通过,但充满创意的诗想是值得肯定的。比起前头“失踪的大象”,它的互文性削弱了许多,仅仅依靠微弱的“象形”互相致意而已。这也让我们想起十年之后徐冰的《天书》(1991),他以汉字为型,拉丁文为体,自创四千多个“伪汉字”(是夏宇的五十倍),还采用宋版活字印刷制作几十米长卷。同样包括作者在内无人能读出任何内容来。同类型的互文合力,共同表达了对现存文字的遗憾和挑战——改变“一统天下”的格局,力争最大化的自由书写空间。
“划掉诗”则是夏宇与新生代“厮混”后又一互文成果。她在“现在诗”第九期征稿启事”中,鼓吹“披着羊皮的”:对于众人文本,可采取“非版权法”的暴力刑罚——删除、删除、再删除,即随便对着一份纸媒:报纸、杂志、广告、指南、说明书、节目单、处方、简历……随便捡一页阅读,精心划掉你不要的句子。“最后留下五个或六个句子,甚至二个三个,它们彼此心领神会,自行运转,变成一首诗。”⑩笔者在现代诗写作教学课堂,曾将这一互文性的减法引入,深受学生欢迎。普遍认为,超级瘦身,可以学会如何在泛诗化语料堆中直取诗之核心;快速剪裁萃取,可以练习如何在非诗中收割隐匿诗意。相信互文性的“大棚”和互文性肥沃的土壤,还会不断地培育出新品种。
三 “锯齿”思维术
如果再把锯子的理念用到诗的修辞,我们发现,那些“幽浮文法”、“逆毛抚摸”、“窃窃腹语”、“溜冰鞋”单刀,都可归入雪亮的牙齿。在游戏的迷宫前,夏宇既集结大量的传统修辞:双关、谐音、黏连、通感、示现……,又加固现代与后现代的隐喻、博议、后设、误推、拼贴、镶嵌……,连同未及冠名的,形成语法怪异、目迷五色、佻达戏谑、文意暧昧的演出。除了前面有所涉猎外,下面再胪列数例,藉此窥视她一星半点的花样。
偏离常规语法与构词法。
就是
只是
这样,很
短
仿佛
爱情
——《爱情》
“杜撰”式畸联。
患失忆症的人坐在海边听到了
而唤起的第一个记忆是一些防痨邮票
——《百叶窗》
叫人顿生疑窦的是,固然失忆症与肺痨是属跨科的两种病,在病的基础上可建立牢靠的联想,问题是病与邮票,全世界有没有一种基于防治痨病而发行的邮票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要归咎于无中生有的杜撰,想当然的发挥?幸亏有前病“失忆症”的“接头”,使得后句在错愕中不致完全轰然倒塌。突发奇想的词句在夏宇笔下,真是如泉奔涌,陡峭、突兀、劈立,给长期平庸爬行的修辞抽上一阵锯齿形鞭子。类似的还有 “在段落这个令人愉快的礼拜式”(《我不知道它的发生我来是这么舒适》)。“净重是骨骼/毛重是戏”(《蛀牙记》),“永恒的喷泉狂想如蛆”(《她们所全部了然的睡眠与死亡》),等等。
她决然锯断长链条句式,故意将四组虚词(范围副词“就是”“只是”,指示代词“这样”,程度副词“很”)以碎片方式作为“垫片”塞入诗中。表面上付出累赘的代价,暗里却收获整体语调短促、气促、急促的意味,吻合爱情结束后的空洞空荡感。试想前代诗人如洛夫辈,是绝不会出现这种离散句式的,无论如何会视那三行累赘如眼中砂子,立马清退。可是女诗人不但挽留,且变化花招:“如是/玻璃/玻璃地/遇到/在苍白的青春反光中/性命本体与生活”(《插图》),名词玻璃在这里转品为形容词化,使得主格在遇到动词前有一个短暂的华彩。
突兀性暗喻或远取譬
舌尖上
一只蟹
——《阅读》
远取譬是在遥遥相隔的事物间寻找同一性,在出乎意料中获取惊愕的效果,其杀伤力造成的震撼可以万吨级计。突如其来,将甲壳类动物——八肢二鳌植入柔嫩的舌尖,造成视觉上强烈的反差。在标题笼罩下,牵引出味蕾与蟹肉构成的丰沛的阅读滋味,一种异常突兀的陌生化张力油然而生。可类比:“我写过很多次钢琴/也从来没有像过一头象”(《梦见波依斯》)。
时空的灵敏转化
晚一点是薄荷
再晚一点是黄昏
——《铜》
诗歌是各种事物“交换”频次最高的文体,有如城市社区间穿街走巷的运载工具,而时空转化是其间特别繁忙的小中巴。“晚一点”作为时间的弹性刻度,对应于它的事物,一般有两种选择。1,时间的截止或延宕,总之在时间的维度上做足文章。2,不在时间上打主意,而是向空间方面转化。第一句“晚一点是薄荷”——选择了时间与饮品的关联,显然也是一种畸联:相隔千万公里的两种属性在瞬间胶合,迫使晚来的“时间”(还可以承载他人他物)带点薄荷的气息与味道。第二句是属于正常不过的时间常态,但因了具体的时间点黄昏,使得时间获得结实而实在的存在感,由于两句——难易适中、张弛有度的配合,尤显奇特而自然,自然会获得较高的满意度。可对照:“经过一千年和/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哈欠”(《南瓜载我来的》)。
偏爱能指的演奏。
1当她这样弹着钢琴的时候恰恰恰/2他已经到了远方的城市了恰恰/3那个笼罩在雾里的港湾恰恰恰/是如此意外地/4见证了德性的极限恰恰/承诺和誓言如花瓶破裂/5的那一天恰恰恰/目光斜斜/在黄昏的窗口/6游荡的心彼此窥探恰恰/7他在上面冷淡地摆动恰恰恰/8以延长所谓时间恰恰/我的震荡教徒/她甜蜜地说/9她喜欢这个游戏恰恰恰/10她喜欢极了恰恰
——《某些双人舞》
夏宇偏爱声音修辞,该诗采用双关修辞格,是在一定语言环境中,借助词义或同音,使语句焕发出双重意义,从而制造言此意彼的效果。古代诗歌的双关俯拾皆是,但因篇幅关系,总是跳不出双层栅栏。夏宇的《双人舞》,踩着象声词“恰恰”的步点,至少跳出了四层跨栏,实属罕见。第1个恰恰恰,作为引入剧目的情景导语,没有实质性含义,但略微传递出妻子打发日子的单调心绪。第2-4个恰恰,押韵似的回应了妻子的寂寞“声响”,多一个了字的结束“前缀”和多一个恰字的“定音”,明显带有丈夫摆脱束缚与顿感轻松的情调。第5个恰恰恰,巧妙地转嫁于花瓶的破裂声,暗示婚姻的不堪一击。第6个恰恰,显然是针对窗口、街头的游猎、邂逅,彼此窥探的心跳。第7个恰恰代表交欢的生理节奏。第8个恰恰代表冷淡敷衍、开始不耐烦的心理节奏。第9个恰恰恰表达了对方的高度愉悦。第10个恰恰再次进行了强化。应该毫不犹豫地说,在百年新诗史上,象声词拖动了这么多意涵的能指诗,授牌夏宇为头号大力士名副其实,它为传统双关修辞的现代作为,提供了绝佳范本。不过,笔者有点小小遗憾:如果结尾再来一两个“恰恰”呢,回应开场的引语,在结构上岂不更加完美?笔者自作聪明,设想来个续貂,比如“此刻,他真想给妻子挂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阵恰恰、恰恰、恰恰恰”。
对于艺术,夏宇是一个“跳来跳去的人”,难得安分。对于语词,更恨不得每天都能刷新:“在狂喜最薄最薄的边上”(《继续讨论厌烦》);“我们甚至不能像”(《而他说六点钟在酒馆旁边等我》);“第一个吻淡绿如梗”(《在墙上留下一个句子》);“市集里倾翻的香料/用十匹骡马交换一个厮混的黄昏”(《一些一些地迟疑地稀释着的我》)。甚或,还不时制造些“病句”:“在这样的下午/这是譬如的第6次方”(《耳鸣》)。
诚然“诗的魅力在于它的歧义性”⑪,歧义,也属于犬牙交错的“锯齿”。但歧义的汜滥会造成堰塞,不可掉以轻心,以多人谈论的《拥抱》为例:
风是黑暗
门缝是睡
冷淡和懂是雨
突然是看见
混淆叫做房间
漏像海岸线
身体是流沙诗是冰块
猫轻微但水鸟是时间
裙的海滩
虚线的火焰
寓言消灭括号深陷
斑点的感官感官
你是雾
我是酒馆
作为压轴之作,在夏宇心中肯定分量不小,但由于艰涩,解读者或者干脆以感觉取代诠释,或者以笼统的语焉不详大而化之。要读“懂”此作,笔者以为当先做二度“还原”。第一度还原,是将全称判断的八个系动词“是”暂时“搁置”,夏宇一直喜欢采用此种句式“××是××”、“我是××”(在解冻时期的七八年间也盛行这样的句式:A=B),其实太过宽泛,反而可能成为短板;万用胶囊,委实可以装入太多东西:“风是黑暗,门缝是睡”,依序不是可以变成——“风是光明/门缝是醒”、“风是狐臭/门缝是香”、“风是蜂蜜/门缝是嗡蝇”……无穷无尽演绎下去,全诗就被“是”的管道带到歧义汜滥的大海。与其如此,不如先删除“祸首”,让所有的意象先无条件幷置于屏幕上。第二度还原,是将各自独立的意象进行一番梳理,有序成一个个桥墩,在标题的指示下,完成一段《拥抱》的桥梁。通达桥梁的“拥抱”,当然可以有多种方案。比如纵向轴列:一连串的外在的意象与内在心理流程投影在一起,合成一种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感官节目。笔者则比较倾向于横向轴列的联通,毛遂自荐,再顺手写下该诗的“迻译”:拥抱在黑暗的风中,拥抱在睡眠与梦的缝隙间,拥抱在冷淡与懵懂的交织里,有时会突然醒悟,亲密的拥抱或许是一种混淆?拥抱的身体如下陷的流沙,溶解诗的冰块;镶嵌在浪花里的裙裾,点燃断续的火焰,但都难以抵御时间的悄悄流逝,没有什么寓言也没有什么后设,有瑕疵(缺陷)的拥抱,或许只是感官与感官碰触,一边是挥之不去的迷雾,一边是欲望骚动的酒馆。当然,笔者的“迻译”,只是“懂”的一种,还有多种多样的“懂”,等着你去打开。
如果说《拥抱》像钢丝上舞蹈,精致考究,那么《耳鸣》就是在峭壁上攀援。一阵阵呼啸的山风,我们听到什么呢?是作者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轻微耳背,甚或我们已接近耳聋?
我们称之为夏天的/这些椅子其实/是不同的岛我们/停下来找东西/解开悬挂/交换倒数/骰子就变成线索/瓶子就变成船螺/鞋子就开始/是一个邮轮/我就驶过你的港/你就坐在箱子上写字/耳朵的手风琴地窖里有神秘共鸣/头发已经慢慢留长了/钟用海擦得很干净/我们都会打勾/在这样的下午/这是譬如的第6次方/你喊我的名字/遗失三颗钮扣
找不到基本架构和内在逻辑,截断式闪跳,看不见有什么出口,除了一句神来之笔“耳朵的手风琴地窖里有神秘共鸣”极为传神切题,余下笔者实在不敢恭维。或许我们可以从拉康的理论找到答案,夏宇的诗正体现了这样一种后现代的“维持沟壑的伦理”:即不直接抵达意义,或者说,通过将意义不断地延宕,维持欲望的持续动力。在夏宇的诗里,一方面有着语词不断推进的欲望运动,另一方面这种欲望又持续地在断裂的语句构成中遭受阻隔。⑫晦涩的阻隔,跳闸式的短路的阻隔,是迄今人们对夏宇最大的微词。而质量的参差也是夏宇的一个问题。
四十年来,夏宇穿上她自我设定的“蹦极”服,一直站在诗与非诗的悬崖,站在101顶楼。她乜斜常规地弹跳、腾跃,醉心于花样百出的自选动作。接近死亡的大前冲,跳出心脏的后滚翻。嵯峨间飞旋,嶙峋里穿梭。嬉戏的姿态,Salsa的舞步,以生命与自由为代价,有巧智到“甜蜜的复仇”精度,也制作不知所云的“耳鸣”。永远的涉险、实验、探索,永远的乐此不彼,花样翻新。调皮、捣蛋,童心未泯的嘴角,总是挂满狡黠的坏笑。顽劣不化的恶作剧,跃跃欲试的好奇,打破疆界,魔术师的布袋塞满快感美学,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衔接处,玩出了一座多面向的、甚至带胡子的蒙娜丽莎。
在夏宇的后面,紧跟着叶觅觅、刘亮延、雨果……一大群新新代“玩手”,夏宇式的“积木”,是延续着展开更大的体量,还是接近变异后的拐点呢?
❶ 陈柏伶:《先射,再划上圈:夏宇诗的三个形式问题》,博士论文,台湾清华大学,2013年。
❷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一百二十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❸ (荷)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❹ 萧萧:《后现代新诗美学》,台湾尔雅出版社2012年版,第65-68页。
❺ 林耀德:《在速度中崩析诗想的锯齿——论夏宇的诗作》,《文艺月刊》第205期,1986年7月。
❻ 李淑君:《低限马戏——夏宇诗的游戏策略》,硕士论文,彰化师范大学2009年。
❼ 万胥亭与夏宇《笔谈》,《腹语术》自行印刷1991年版,第114页。
❽ 奚密:《噪音诗学的追求:从胡适到夏宇》,《长沙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❾ 同【1】。
❿ 具体参见夏宇:《披着羊皮的诗——现在诗第9期征稿启事》,台北心灵工作坊2009年12月,第205页。
⓫ 详见龙协涛:《读者反应理论》,(台)扬智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8-61页。
⓬ 杨小滨:《欲望与绝爽》,(台)麦田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