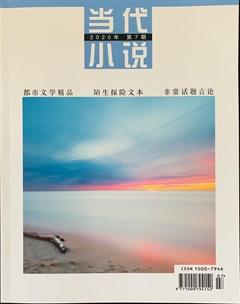二姑弥留之际
柏祥伟
1
我怀揣一盒叫做杜冷丁的针剂去了二姑家。这是一种不常见的药物,我是拿着二姑的病历,找了一个熟识的人开了那张红色字体的处方笺。我从取药窗口里接过那盒针剂,窗口里的那个年轻医生对我挤出一些莫名的笑。
那天风和日丽。二姑家的院子里盛满了明亮的阳光,几只鸡在低头啄食,羊默默地嚼着干草。二姑家的门框上,春联已经褪掉了喜庆的颜色,翘着边角儿随风微微颤动。小丽倚在门口等我,眼神就像门前的土路一样平直呆板。
她说:“哥,拿来了?”
我把那盒杜冷丁掏出来,小丽的手哆嗦了一下,她接过去攥在手里说:“你进屋来吧,俺妈正念叨你呢。”
我说:“你先回屋吧,我在外面待会儿。”
表妹进屋了,我听到木门吱的一声涩响。我对着刺目的阳光猛吸一口气。院子里静无声息,少倾,屋里传出丝丝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医生在用微型锯片割掉针剂的脖颈。就像刀子划在皮肤上。我对着村街呆了片刻,便骑车折回城里。阳光和风扑在我脸上,我回家后通体大汗。
2
三天以后的早上,小丽打来电话,语气惊喜:俺妈今天情绪很好,早上吃了一碗面条,我给她洗了脸,梳了头。这会儿正在晒太阳呢。她老是念叨你,如果你不忙的话,就来看看吧。
我当然想看到二姑高兴的样子。该有半年多了,小丽的语气从来没有这么轻快过。这个十九岁的少女,已经被我二姑的病折磨得憔悴不堪。半个多小时后,我骑车来到二姑家里,果然看见二姑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小丽脸上带着浅浅的欣慰,围着她说笑着,二姑除了脸色苍白,神情和正常人没什么异样。二姑看见我,就叫着我的乳名说:“明,二姑好了,我什么病都没有了。”
我靠近二姑的椅子坐下:“二姑,你本来就是小毛病,这不就好利索了嘛。”
二姑说:“多亏你前天拿来的好药,打一针就好了,我浑身一点也不疼了。”
二姑不停地说笑,好像要把这半年来没说的话全说出来。一会儿说过几天就骑车去邻村里赶集。一会儿说晚上割肉包韭菜水饺,让我吃了饭再走。二姑说了一会儿话,对着太阳偏头眯了眯眼,忽然扑哧笑了一声,转脸问我:“我这一段日子,是不是疼极了就大叫啊?你听见我叫没有?
我说:“没有,我没听见呢。”
二姑面露羞愧:“我知道,我叫了,我叫得很响。”
我扭头问小丽:“我二姑叫过疼吗?”
小丽笑吟吟地看着我:“没有,我没听见。”
二姑看看我,又看看小丽,自言自语似的说:“我叫了啊,肯定是叫了,难道你们没听见?”
我不知道该再对二姑说什么。这可能是二姑人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了。那支杜冷丁像一块抹布,暂时堵住了二姑的嗓门。这个正午的时光里,二姑正在享受着这样残忍的幸福。我低头对着地面呆了会儿,抬脸看见二姑半个身子歪在一边,她似乎是睡着了。一只手搁在椅子的扶手上,另一只手搭在肚子上。
其实二姑已经七天没有大小便了,医生告诉我:可怕的肿瘤在她的肚子里膨胀着,正在悄悄地挤扁她的膀胱。我正发呆,二姑忽然睁开眼,对我说了一句莫名的话:明,你不知道吧?我的嗓门很大。小时候,我在咱老家里的村子里,一起和小伙伴们做游戏,数我喊得最响呢。二姑看我一脸迷惑,又说:“真的呢,你爸爸知道我的嗓门大,你不信回家问问他。”
二姑努力直起身子,她的眼神对着不远处的砖墙。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眼光穿透了砖墙,看到了她五十年以前的童年。
听着二姑虚弱的声音,我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副画面:干净而凉爽的夜晚,圆盘似的月亮挂在树梢。月光如水,淡淡的青草香气缓缓流淌。七八个孩子在我老家的石桥旁边,麻雀一样叽喳乱叫。有清脆的蛙鸣从远处的池塘传来,点点萤火虫闪烁缭绕。孩子们的欢叫使得月光荡漾起伏。
他们在玩一种叫做丢手绢的游戏。一个扎着朝天辫的小女孩跳起来,她甩着一块花色繁杂的手绢,开始绕着围坐成一圈的小伙伴转圈。她边转边唱:
“丢啊丢手绢,丢到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
小女孩的嗓音像玉米粒儿一样清爽干脆。围坐着的孩子们扭头对她嘻哈乱笑。止不住的笑声时常打断她的歌声,也使得她的脚步踉跄。她一圈又一圈地跑着唱着,最后也忍不住跟着伙伴们笑起来,她边笑边唱,终于把手绢丢在一个小男孩身后。那个小男孩马上跳起来追上了她,伸手抓住了小女孩的朝天辫。小女孩爆出“啊”的一声尖叫,整个夜晚也跟着尖叫了。
二姑出神地盯着远处的砖墙,声音羞涩:“那个小男孩叫马三,我每次把手绢丢给他,都被他撵上来抓住我,我的尖嗓门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二姑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漾出一股奇异的光亮。我被她的眼神感染着,二姑在这一刻确实是快乐起来了。作为一个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亲人,我应该让二姑得到她向往的快乐,能让二姑痛苦的叫喊变成快乐的叫喊,应该是我尽力所作的事情吧。
我说:“二姑,这个游戏真不错,当时你一定很快乐。”
二姑看着我笑了起来。小丽和我在旁边跟着笑。我转脸看了看不远处的姑父,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无声地笑着,好像面对大片即将收割的麦田一样开心。
3
那天下午,我在二姑家吃完了韭菜馅的水饺。回到城里后,天色已近黄昏。客厅里没有开灯,父亲坐在沙发里,模糊成一团黑影。我能感觉到父亲的眼神一直盯着地面。从他的眼神到地面不过两米的距离,却又似乎很长,长过了父亲大半个人生。
二姑是我父亲唯一的妹妹。从我二姑查出癌症晚期那天,父亲一夜之间就变得苍老了。刚开始时,父亲自己折磨自己。后来就是二姑折磨父亲了。二姑的疼痛总在半夜里发作,表妹被二姑疼痛的叫喊嚇得没有主张,就一次次地在半夜打电话:“舅,我妈又叫疼了。舅,我妈又叫你了。”
每次父亲和我赶到二姑家里时,二姑又在疲惫中睡着了。也许疼痛就像潮水,时有起落。父亲坐在床边,看着他的妹妹,往往总在天明时候,二姑醒来第一句话就说:“哥,你来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呢。”
一个多小时后,我和马三踏上了回城的路。马三骑了一辆老式自行车,他蹬得不快,松弛的链条叮铛作响。我跟在他身后,顺着他的车辙左右摇摆。我看到马三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刮了胡子的嘴巴显出粗粝的乌青色。我俩拐过一片杨树林,老家就被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了。我回头看了看,整个村庄被大片的树木遮掩了,只有几柱炊烟从村子中央缓缓升腾,安详而又温暖。老家的样子在我心里定格了这样一幅画面。
翻过一段不算太陡的坡路,我听到马三轻微的喘息。他的车子发出疲惫的吱呀声。我惭愧地说:“三叔,我真觉得过意不去,让你受累了。”
“不说这些客气话了。我给你说说你二姑的事吧。你二姑叫起来的声音有多尖啊,在咱们踅庄村里是出了名的。咱村里像我一般年纪的人,应该都记得吧。”中午的阳光从身后照过来,我和马三骑车的影子贴在路面,看上去就像纸一样单薄。马三迎风咳嗽了一声,眯眼看着前方,他的声音很低,随着车轮碾压着路面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一样潮湿:
咱村里搞运动的那一年,我十五岁。你二姑比我小两岁,她应该是十三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不知怎么一夜之间,你爷爷就从支部书记打成了右派。被红卫兵拉到村西打麦场上临时搭起来的高台上批斗他。当时全村里人都去了,我也跟着人群去看热闹。我沿着贴满大字报的大街朝村外跑,听得传来阵阵叫喊声,叫喊声越来越近,等走进打麦场,发现围满了村子的男女老少。你爷爷站在高台上,他低着头,倒剪着双手,头皮在阳光里闪闪发亮。他一动不动,保持着睡觉的姿势。
一个戴着红袖章的男人揪住了你爷爷的头,使劲儿摁着,似乎不解气,又举起手朝他的脖子砍了几下。接着打麦场上沸腾起来,喊叫声一阵高过一阵。我听清了人们高喊的是打倒你爷爷。这时我发现你二姑也挤进来了。她钻进人群,挤到高台下面,举起胳膊高声喊:打倒俺大大!你二姑的话音未落,所有的人也跟着喊:打倒俺大大!
人群喊完这句话后,忽然就一下子停顿下来,会场上寂静无声。你二姑对着你爷爷咯咯笑了两声,她笑得很好看,两根朝天辫翘翘着,花瓣一样的笑脸。你爷爷抬起脸,也咧着嘴巴笑了。接着全村的人才反应过来,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那场面一下子就乱了。
马三说,这是当时流传很久的一个笑话。你可能不知道,大大是咱们乡下的方言,就是爹的意思。村里人跟着你二姑喊“打到俺大大”的时候。我也跟着喊了。我刚喊完就捂住了嘴巴。接着那个戴着红袖章的男人从高台上跳下来,揪住了你二姑的辫子,一巴掌打在你二姑脸上。你二姑嗷的一声尖叫,接着就哭了。
“那人干嘛要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呢?”我好奇又气愤地问马三:“那人现在还活着吗?”
“那个年代,很多人都疯了。后来那人卖血当路费,去了北京天安门,后来就一直没有音讯。”
我叹口气:“希望他还活得好好的。”
马三扭头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前面是又一段漫长的上坡路,马三胯下的自行车发出了艰涩的吱呀声。他粗重的喘息声也随风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扭头看见他糙黑的脸上冒出了汗水。
我说:“马叔,您累了吧?”
马三摇摇头,绷着嘴唇,怔怔地看着我,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大声对我说:“大侄子,我不能瞒你,当年那场批斗会,打了你二姑一巴掌的那个男人……他是我的爹。”
我一下子便呆住了。我怔怔地看着马三。马三哭着说:“我恨他,我恨我那个狗日的爹,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死活……”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蹬起车子,一阵风刮过来,扬起的灰尘迷住了我的眼。
5
村街上没有多少人走动。阳光静静地漂浮在头顶上,整个村子像是蒙上了一层油画里的模糊色彩。我的脑袋昏沉沉的,好在马三的自行车链条叮铛作响,还在时刻提醒我。拐过这条贯穿东西的街道,就能看见我二姑的家了。她在等着我,等着给她这个出其不意的惊喜,在她弥留人世之际,让她和童年伙伴重温一场开心尖叫的游戏。
我騎车在前面领路,马三跟随其后。他开始沉默了,一句话也没说。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绷着嘴巴,脸上溢出了细碎的汗珠儿。拐入二姑家的那条胡同时。我指着二姑家的绿漆大门说:“看,到我二姑家了。”
进了院子,我看见姑父正坐在门前的小椅子上抽烟。他转脸看见我和马三进来,就起身迎过来:
“是马三兄弟吧?”姑父打量着马三,却又是转脸问我的口气。
“还记得嘛,我们见过面,你老多了。”马三伸出手,两个人说了几句话,姑父让马三进屋里坐,一边忙着给马三递烟,一边对我说:“小丽知道你们快来了,去街上买菜了。”
我说:“二姑睡下了?”
姑父朝卧室了看了一眼说:“睡了一个上午啦,现在还没醒来呢。”
二姑躺在卧室的床上,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我过去关上了门。刚坐下,小丽就回来了。她的脚步很轻,手里提着一些青菜和肉食。她对马三点点头,叫了一声舅,就折身端了茶具去门外洗刷。马三的眼神跟着小丽追出去,随即转向墙上相框里的照片。
“这个闺女,和你二姑小时候一模一样。”马三说。
我忽然觉得烦躁不安。对门外的小丽说:“不要沏茶了,给我们煮面条吃吧,三叔怕是饿了。”
小丽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厨房。片刻,我听到厨房里响起切菜的声音,点火的声音。我头晕得厉害了。厨房里飘出植物油和熟鸡蛋的香气,我起身进了厨房,看到小丽正往两个碗里盛面条。面条上盖着些菜叶,摊着一个荷包蛋。
姑父忙着张罗饭桌。我和马三对坐下来,挑起面条塞进嘴里,表妹煮的面条还不错,很有筋道,满嘴里都是花生油味儿。马三像是真饿了,他把面条塞满了嘴巴,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我姑父起身推门走进卧室,他探身看了看二姑,接着就折身关上了门。
6
阳光从外面斜照过来,贴在卧室门上的“福”字映出了陈旧的光亮。马三吃完了第二碗面条,脸上显出了汗水。他放下筷子的时候,又夹了一个辣椒塞进嘴里。一只苍蝇围着马三的空碗转了一圈,又飞走了。
马三说:“天真热了,你看,都有苍蝇了。”
坐在一旁的姑父砸吧了一下嘴巴,接过马三的话说:“是啊,快入夏了吧。”
马三扭头和姑父聊了起来,他们先是说了一些关于老家的闲话,马三又把话题转到今年麦子的收成上,他很羡慕这个村里的土地一马平川,全是水浇田,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说到这个话题,马三忽然提高嗓门说:
“以前吃不上饭的时候,俺们那些穷山村的大闺女都愿意嫁到这些平原村子里。哪怕是找个眼瞎腿瘸的男人也乐意。”
马三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说到“俺们那些穷山村”的时候,冲我夸张地抬了抬嘴巴。我愣怔了一下,才明白他的表情是说我和他是一个村里的,虽然我从未在老家生活过,但是我祖辈还是老家的人。我不乐意马三这么自我贬低自己。虽然他表面是夸这个村子地产丰富,但是认为他的话里有话。应该是暗指我二姑从老家嫁到这个平原村子里,嫁给了我姑父这个男人。
姑父却像是没有听出马三的话音,反而对马三显出了看似优越感的笑。他的手在衣兜里摸索了着,掏出一盒大鸡牌烟卷。烟盒的封口似乎很紧,姑父摸索了老大会儿,还是没拆开。他把烟盒递给我说:“明,你帮我拆开吧。”
我接过烟,拆开了烟盒封口的塑料封条,撕开了封口上的锡纸,再次递给姑父。不料姑父接过烟,手指哆嗦着抽出一支烟,抬手递给我。
“明,你抽一支烟。”
姑父这个动作让我吃惊,平时他知道我不吸烟。为什么还要让我抽烟呢?他的动作拘谨,表情谨慎,好像我是一个初次登门造访的客人。我不明白姑父此时忽然怎么对我这么客气。
我避开了姑父手里的那支烟。姑父却对我跟进了一步,他的眼神瞬间变得怯弱起来,嘴巴哆嗦着低声说:“明,我对不起你姑,她这辈子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福,我不是人,我还打过她……”
我忽然觉得心如刀割。我叫了一声姑父:“过去的事了,别再提了。”
姑父带着哭声说:“明,你打我一巴掌,替你二姑解解气吧。”
我想不到姑父会突然对我做出这般言行,面对这个长辈的内疚和忏悔,我手足无措,显得窘迫不安。內心除了百般纠结,竟然在瞬间也有了一些说不出的释然。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把求助的眼神转向坐在一旁愣怔的马三。马三显然也听清了姑父言语里的端倪,他起身搓着手走过来,满脸堆笑对我姑父道:
“哎呀,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别放心上啦,夫妻俩一辈子过日子,谁还没个脸红吵嘴的时候呐。”
马三这么一说,姑父好像变得委屈似的,两眼冒泪,转朝马三走过去,把那支烟递给马三,哽咽着说:“三哥,你也清楚,以前过穷日子的时候,闹心,难啊。”
姑父哽咽的话显然引起了马三的心里共鸣。他接过姑父的那支烟,叼在嘴巴上,却又拽着姑父朝门外走。姑父被他拽得趔趄着出了房门。我跟着他们走出房门,马三扭头对我说:“我让你姑父带我去麦地里看看,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我对马三点点头,看着他们并肩走出了大门。午后的阳光落在他们后背上,使得他们走路的样子有些模糊。下午天空晴朗无云,风也开始停歇了。今天晚上的月亮应该又圆又亮,是一个适合做游戏的好天气。我掏出手机,拨通了父亲的号码。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