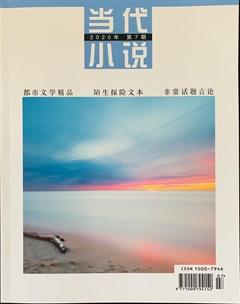泡市场的姥姥
于海波
好容易找到位置停下车,便直奔小市场。远远看到市场口北面马路牙子上,姥姥正和一个穿制服的城管争执,赶紧跑过去。城管见到我松了口气,说姑娘看好你家老太太,拉着我没用,这里不能摆摊儿,文明城市正验收呢。
市场不就是用来摆摊的?姥姥质问着,一脸的不服气。
跟您说了几十遍啦,这里是市场外面,不是市场里。
我马上赔了笑脸,对不起啊,我们马上收拾走。您看她那些东西能不能还给我们,不值钱。
都拉走啦,你去局里交完罚款就能领。
那好。我转身拽住姥姥意欲伸出的手,城管大叔急忙走人。姥姥直跺脚,你把他放走了我向谁要?不去交,找你三舅。哎呀姥姥,这点小事还值得我三舅出马?就别给他添乱啦!您放心,罚不了多少的。我再三保证,老太太这才消停。
也不知平时老太太都怎么搞定的,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的电动三轮从一排密密挨挨的车子里推出来。姥姥骑上走了,灰白的头发被风吹起,纯棉的套头衫被汗湿透紧贴在背上。
交完罚款领东西的时候,办案的小青年看着我笑,说就这点东西还够罚款的钱?我说肯定不够啊,可是必须得要,这都是我姥姥的宝贝,你不给她弄回去她会心疼得不吃不睡。你姥姥多大年龄了还出来摆摊?他看了眼我的宝马730,又说你们少加次油都够她生活半年的。老太太八十四啦,就喜欢这个你有啥办法?她自己的钱都能买辆这样的车了。我也牢骚着,大热天的弄一身臭汗不说,孩子中午放学还得回家吃饭呢,这都耽误了。小青年似信非信地看着我,不信的成份更多。这样的眼神我見得太多了,搁我我也不信。
牢骚更多的肯定不是我,是我那几个舅舅和舅妈,特别是三舅。沿海地区近二百万人口的县级市里一个分量不算轻的干部,自己八十多的老娘街头摆摊卖针卖线袢马扎,叫人家怎么说?上一次她老人家不交管理费,管理市场的要把她的摊子给扔了,姥姥拽住不撒手,被那人推了一把。老太太一屁股墩地上,接着就动不了了——腰椎错了位。三舅正开着会,接了电话火急地赶来,所幸老太太没啥大事,找大夫正了骨歇了几天就又照旧出摊了。三舅说娘你能不能不去摆这个摊?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还跟人打架,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姥姥说你当你的官,我卖我的东西,嫌丢人就当不认识我。三舅说那你卖东西就得守规矩交费用。姥姥火了,我这么大年纪国家都给发补贴了,还交管理费?我就不交!三舅脸憋得一会儿青一会儿紫,一句话说不出来拂袖而去,晚上打发舅妈给姥姥送来了五万块钱。姥姥钱收下,摊照摆,只是把摊子挪到市场外面来了——不在市场里面,看谁还要管理费。所以今天这事儿姥姥便不好再跟舅舅们说,只给我打电话。
路过王嫂饺子馆顺便买了两份饺子,一份给姥姥——她指定不做饭,一份带回家。果然,姥姥在客厅里坐着等我,没有动火的迹象。看我送回来的东西,高兴了;又看见饺子,更高兴了,都是她爱的。夸我办事利索,不像那些人,光知道啰嗦。我知道那些人是指舅舅们和表弟们。我说姥姥你先吃了饺子再去查点你的宝贝啊,人家没有稀罕的,保证少不了。她答应着,别看她答应的好,我打赌她一准儿是先查点完再吃饭,即便那是她最爱的饺子。
我太了解姥姥啦!从上小学直到初中毕业,我一直住在姥姥家里,姥姥的脾气我最摸,当然姥姥也最疼我。当年我和强子谈恋爱,全家上上下下没一个同意的,强子家里穷,又没有正式工作,谁也看不上眼。我俩好了好几年,爸妈也不松口。我去求姥姥,姥姥跟我妈说给俩孩子办喜事儿吧,你不张罗我张罗。谁年轻不穷?俩孩子愿意就行。在姥姥的支持下,我俩才体体面面结成了婚。强子的物流公司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没有资金,是姥姥一下子给了我二十万,十八年前的二十万是啥概念?现在生意做大了,强子买了宝马给我,他自己却开一辆旧帕萨特。
说起来,我打心眼里佩服姥姥。姥姥从不在家长里短上纠结,她的精力都用在干活挣钱上。她有经商天赋,政策一松动就开始做小买卖:一大早去赶集,随便包下一堆什么东西,蹲集上慢慢卖,一上午能挣个三元五块的;半夜起身去临县背回来一些干的海产品,第二天在集上也能换个好价钱;自家地边地角种上高粱,秋天收了高粱能养人也能养鸡,高粱秸钉成盖顶又可以换钱……在姥姥眼里,处处都有商机,啥啥都有用。姥姥的小买卖不起眼,却供出了村里仅有的几个大学生——舅舅们上大学的上大学,考中专的考中专。他们继承了姥姥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精神,发展得都很好:大舅是一家国企的老总,三舅仕途顺畅,二舅四舅经商。姥姥是人前显贵,人后也收获了舅舅们丰厚的回报,但她一直没停下手头的小生意。对此姥爷对姥姥意见很大,嫌她不收拾家,不好好做饭。
前些年姥爷去世,舅舅们把姥姥搬到城里,她谁也不跟,执意自己住。一开始姥姥度日如年,念叨着说跟坐监牢大狱没啥两样,除了吃就是喝,不是废人一个?不过没几天她就发现了新的商机:城里的小市场卖吃的穿的多,就是没有卖针啊线啊扣子的,也没有给马扎换带子的。姥姥收拾收拾摊儿就摆上了,你想啊,谁家不得买个针线缝点啥?谁家不掉扣子?谁家不坐马扎?马扎上的带子磨坏了,马扎架子还好好的,重新买个得几块钱,袢个带子才块儿八毛,买卖有的做唻。刚开始,舅舅舅妈们都极力反对姥姥去摆这个摊,后来也就随她了,因为谁也掰不弯她。姥姥说我闲着干啥,等死?那死得更快。我去市场就高兴,有人说话,有事干,还能挣钱,多好!
第二天一早姥姥又打电话来,吓我一跳,以为城管那里短针少线了,却是让我去接姨姥姥,说姨姥姥要来住些日子。姨姥姥是姥姥的亲妹妹,比姥姥小十岁,每年总要来姥姥家住几回。姥姥和这唯一的妹妹脾气不投,但是时间长了姨姥姥不来她又想,可能是因为姨姥姥是姥姥拉扯大的,对姨姥姥,姥姥总有当娘的意思。其实我不愿意她来,净耽误我出摊儿。要扣电话了姥姥又补了这样一句。
姨姥姥住在乡下,一路上风光明媚。五月的阳光不是很烈但非常明亮,空气里有一股暖熏熏的香,即将变黄的麦田整整齐齐,树木却早就成了荫,只等夏日来临。万物清朗,看得我心旷神怡,心想难怪姥姥一直不愿意往城里搬,乡下多敞亮。
姨姥姥早收拾停当端坐着等我。和又矮又黑又干巴的姥姥不同,姨姥姥年轻时是个美人儿,老了也好看,双眼皮儿平平展展地斜上去,皮色依然白净。只是眉眼间总有一股子哀怨,让人心里揪着——姨姥姥爱哭,不为啥事就抹起了眼泪,用姥姥的话说你姨姥姥的眼泪——现成。
姨姥姥见我换了车,问是什么牌子。我说宝马,她大喜,说我老了老了还坐上宝马了。我只笑,去给她开车门。她坐好了,却撑住车门不让关,探出头来使了劲向胡同口正要走过去的一个胖大嫂打招呼,胖大嫂闻声驻足,大娘这是要去住姐姐家吗?是啊,这不也坐坐宝马。这就是宝马?胖大嫂便紧走过来前前后后打量起我的车,嘴里不停地嘖啧着。好歹胖大嫂赞叹停了,姨姥姥的头和手才收了回去。
姥姥没在家,刘姐来开的门。刘姐是大舅妈找的钟点工,本来说好一天来一次,除了洗衣服打扫卫生还做顿饭。姥姥不让,说我可不想家里多个外人。对于姥姥来说,自由高于一切,她不喜欢多出个牵挂。刘姐就改为一周来一次,若姨姥姥来住,刘姐就天天来。
你姥姥又出摊去了。姨姥姥语气里很不满,说有福不享,非得找罪受。我忙着泡茶,说这个点儿也快回来了。姥姥的课程表我清楚,天刚亮起来赶早市,九点左右回家吃饭,饭罢还去小市场,中午一点左右再回家。姥姥的饭是最简单的,能吃就好,并不在意内容。大多是子女们给早准备下的包子饺子,拿出来微波炉热一热,外加一袋牛奶。下午姥姥在家歇着,收拾她的货,数她的钱。她把一毛一元的纸票伸开,压在我上初中时用的大辞典下,压平整后用皮筋一摞一摞绑好,藏在衣橱里面的大塑料袋子里。等攒满一袋子,就让我拿去存上;存够一个整数,便放在强子的公司里,强子给她最高的利息。据我所知,整理那些钱是姥姥最享受的事儿,那时候的姥姥,小眼睛是咪咪笑着的。
果不出所料,姥姥很快就回来了,见了姨姥姥解释说昨天有个老头儿让她给袢马扎,还没袢完就叫城管给收了去,她跟那人说好今天去拿,老头果然去了。做人得讲信用,她说。
我说姥姥你还在那个地方啊?再让城管收了去,可就要不回来了。姥姥说九点半之前他们不去,昨天我贪干活忘了看表。姥姥一边说,一边冲我眨眼睛,露出狡黠的神情。嗨,您这老太太,敢和城管藏猫猫!姥姥大笑起来,很得意的样子,又说:“那个老头儿今年才七十六,就老得走路都不顺溜了,看着我给他袢马扎,说老姐姐,真不忍心让你给我干这力气活——我看他还没有我力气大。”
“我说姐,都八十多的人啦,这熟麦子的天,在家里歇着享个清福吧。”姨姥姥一边说一边递给姥姥扇子。
哎,姥姥看着姨姥姥突然想起什么,她小姨,要收麦子了,你不在家帮衬着点儿?我就是特意找这个空儿来的。姨姥姥端起茶,看我和姥姥都等着听下文,得意起来:不把我当回事,好,等着用人的时候就知道了。你这人,真是……姥姥语气里有责备。真是啥?姨姥姥不高兴姥姥的态度。心眼不正当呗!姥姥这一句话可把姨姥姥惹恼了:你不是我亲姐姐,从来都不向着我。看姨姥姥的眼泪马上又要涌出来,我赶紧借口回家做饭开溜。
其实不光姥姥不喜欢姨姥姥,我们也不喜欢,特别是刘姐。姨姥姥在,不是嫌刘姐的饭做得咸了淡了,就是吩咐刘姐做这做那,谱子摆得很足。刚开始时把内衣裤扔给刘姐洗,刘姐说这不在她的服务范围之内,姨姥姥就恼了,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后来看姥姥都自己洗,她也就作罢,但是每次来都会把刘姐支使得团团转。
姨姥姥在这里,姥姥连着几天没去出摊儿,憋得直上火。星期天我带孩子去水上公园玩,顺道也接上她们老姐妹俩出去散散心。一进门却发现气氛不对,姥姥紧着一张脸,姨姥姥又在抹眼泪。见我来,姥姥起身穿衣服,姨姥姥却不动,向我哭诉:我跟你姥姥说说体己话,她倒过来说我的不是。我扭头看姥姥,姥姥不接话,连说快走快走,别让孩子们等时间长了。
公园里人很多,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姥姥背着手东瞧西瞅,兴致好得很。姨姥姥不怎么看风景,也不怎么看人,扇着手绢说大热天的出来干啥。姥姥悄悄跟我说,你姨姥姥一会儿不抱怨也不行,谁也打发不着她。我说姨姥姥来住几天你将就她一下,别惹她眼泪叭嚓的,一边疼她,一边还招她不高兴。
“我忍不住,”姥姥把手里孩子玩的气球使劲甩一下,“嫌儿媳早晨不等她就吃饭,我说你早晨睡到东南晌,人家还能不吃饭了?给留锅里就不错了。嫌儿媳妇中午不做饭,人家打工,那么远的路,出去就是一天,你自己做点吃不行?也不是干不动。嫌儿媳妇给她娘买排骨,我说人家养大了闺女吃个排骨也不过分;嫌儿子家不是自己家,干啥都得看儿媳的脸,我说你有老屋,搬去自己住多自由……她就恼了。”说完姥姥双手摊开,一脸无辜的样子。
我哈哈大笑,姥姥啊,有几个老太太能像您这样。姥姥摇头,嘿,我就不明白,自己腿好胳膊好的,非要去跟人家掺和,还专门挑人家的不是,你说这不是自己找难过?
真是一母生百般,姨姥姥和姥姥完全不一样,难怪两个人总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姨姥姥在树荫下冲我招手,说天太热,不如去逛商场。孩子们一听都不愿意,姥姥也反对,商场里有啥好逛的,又不买啥。姨姥姥说我想去买件夏衣裳。姥姥说我不是给了你好几件么?那都是新的,我没穿。小姨姥姥说我想买件像样点的。姥姥说那些衣裳都是媳妇们给买的,哪件不像样?姥姥说得不错,舅妈们给姥姥买的衣服没有便宜的,可惜姥姥基本不穿,嫌贵嫌不结实,还经常拿了衣服去退,或者换两件便宜的,弄得舅妈们哭笑不得。姨姥姥犹犹疑疑地说,你那些颜色都暗了,我想要件鲜亮点的。再说了,让外甥媳妇们看着光穿你的衣裳,也不好……
我想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打发孩子们去看电影,然后陪俩老太太去逛商场,于是皆大欢喜。
姨姥姥很快试了件暗绿底子亮红花的衫子,售货员小姐舌灿莲花,一连声地说好。姥姥说姑娘多少钱啊?不贵,八百八的打八折,再给您去个零头,七百。这还不贵?姥姥转身就走,姨姥姥也开始往下脱。售货员赶紧拉住姨姥姥说这可是真丝的,您这么富态,正配这件衣裳呢,有的人穿上也不好看。她冲姥姥的背影微微摆了一下头,姨姥姥就会心地笑了。小姑娘继续鼓动,您这么大年纪,年轻时没的穿,现在就应该穿好点的,儿女们脸上也有光彩不是?我们轻易不打折,您正好赶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啦。姨姥姥要迈开的脚就停下来,看着我,我连忙喊姥姥,姥姥说一件夏衣裳这么贵,也舍得。姨姥姥说我活了一辈子就不能穿件好衣裳?姥姥又说穿这么娇贵的衣裳去哪里?天天去赴宴?在家可不行:太阳一晒就掉色,炕席一划就勾丝。姨姥姥不再说话,盯着姥姥的两只眼睛汪了满满的泪。我赶忙说姨姥姥看上就买吧,姑娘开单子。姥姥说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我说我有,姥姥就没再言语。
事后姥姥塞钱给我,我说算了。姥姥说拿着,她花我的是应该,花你的算什么。又叹一口气说,手里没几个大子儿还那么能花,一辈子也改不了浮华的性。
姥姥本来应该是有条件浮华的。她出身于大城市里的富商之家,战乱时家里进了土匪,父母被枪杀,她和四岁的妹妹被藏在柴房里幸免于难。姐妹俩没了依靠,去投奔乡下的姑姑。姑姑留她们在家住了一年,就把姥姥许给了比她大十三岁的姥爷做填房,当然是带着妹妹嫁过去的。后来姥姥接二连三生了六个孩子,“浮华”这个词在她眼里基本上与十恶不赦相当。
为了这件衣裳,姥姥还是和姨姥姥吵翻了。
姨姥姥每次来,舅舅们都会请一顿饭,这次是小舅请客。姨姥姥穿了真丝的衫子,更加富丽端庄,坐在豪华酒店的大圆桌后特别应景,加上一大家子人敬酒夹菜,姨姥姥切切实实风光了整个晚上。
姨姥姥高兴多喝了几杯,到了家意犹未尽,在镜子前端详自己,边照边说贵有贵的道理,就是上档次。姥姥带着调笑的口吻说,穿这么贵的衣裳,也不觉烧得慌!不料姨姥姥黑了脸说,你看了那么多大光景,见了那么多大世面,我穿这么件子衣裳又怎么了?就算是“烧”,也轮不到我!
姥姥闻言竟然也变了脸,老姐妹俩大一声小一句地顶了起来,而且越顶越激烈,我怎么劝都劝不住,直至姨姥姥放声大哭,一迭声让我送她回家。
送下姨姥姥回来,见姥姥缩在沙发里发呆,话也不说。在我的记忆里,从未见她如此颓丧过。我安慰她,说姨姥姥就这性子,加上多了喝幾杯,您别往心里去。姥姥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我不该惹乎她。你姨姥姥要强爱浮华,自己又不想踏实出力,嫁了个男人没本事,儿女也不出息,她心里总憋屈得慌,性子越来越娇气,容不下话。不过这里还有别的。姥姥接着跟我说起了那些陈年往事,我才明白为什么一向容忍的姥姥这次火大了。
姥姥有个大哥,我应该叫舅姥爷的,早年去了海外,一直没有音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有了联系,后来小舅陪姥姥去看望过他。当时姨姥姥也想去,她对大舅姥爷没有印象,只不过想见见世面,但是考虑到路费,就打消了念头,说以后有的是机会。那时姥姥手头还不宽裕,没给她出这份钱,也说以后再去。没想到的是大舅姥爷日子过得紧巴,退休金少,没有积蓄,大舅姥姥还有病卧床,家里雇了个帮佣,经济上很吃紧,对姥姥和小舅并不怎样热情。姥姥回来后将状况如实告诉了姨姥姥,说不宜再去。姨姥姥却似信非信,觉得姥姥不知道叨了大舅姥爷多少光,心里便系上了疙瘩,姥姥一惹着她,嘴里就冒风凉话。
姥姥又说,其实你姨姥姥也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当年我带着她离家的时候,抓了我娘的几件绸子衣裳塞包袱里。你姨姥姥爱臭美,稍微大点就偷着穿上身,到街上显摆。这还了得,咱家出身高啊,这一显摆不等于对外人说明了吗?我吓得狠了狠心把那几件衣裳全烧了。她大哭了一场,我说等以后条件允许了给你买更好的,她说买什么样的也不是那回事,她稀罕那些衣裳,是因为想娘,衣裳里有娘身上的味。这话锥心,我一辈子心疼她!姥姥越说越动情,我怕她太难过,想安慰几句,却找不到适当的话说。
所幸,第二天姥姥照常出摊了。
我知道过不上多长时间,她又得叫我去接姨姥姥,姨姥姥还是会欢天喜地地来。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