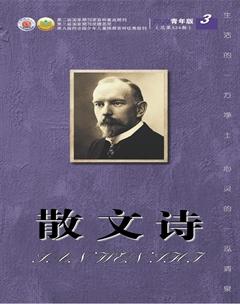九州志异
马硕
用黄沙筑起城墙的国度,宿命般归于尘土;亡于清醒的伪装,也亡于真实的遗忘。
——题记
一很久以前,这里曾铺满了草木和鲜花,铺满了野生。
很久以前——也许,是在历史存在以前,甚至在神话和传说口耳相传以前,在土壤上还存有植被的某个时代;又也许,只属于另一个子虚的世界;再或许,只是醉倒在晚灯下的痴人,流着涎水的无趣的梦。
——庙堂里清醒的匍匐,是否比醉倒后的呕吐,更接近真实?
二沙漠。
河流从东海疲累至此。至此而止。
卷了边的漠北,藏宝图上一贫如洗。
裸露的河道里,长出半截干瘦的白色头骨,希望从蜥蜴尾爬出。爬向来路。爬向深处。但爬不出沙海。
年久的孤魂,沿记忆里的直线,一圈一圈,行走成圆。像无数个昨夜那样。
太阳呼出滚烫的风,路过黑夜,被月光冷却,抚平足印和哭泣,变成天地间一气温柔的呼吸……
又一次地,吹进少年梦里。
三博物馆。
这里满是历史——不同朝代丢失的器物,遗弃的神话,记忆真实而模糊。很多过去的时间被关押在此。昏暗的灯光下排成的长蛇,在时域的磁场里弯曲前行。
风声与哭泣缠住年轻的脚步。
他站在那里,望向他,望向他空洞的双眼;那双眼也正望向自己。相见,终于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生。
戈壁滩的刺槐,长久地站立。几乎忘了背后的推搡和叫嚷。
一“啊,真是块保存完整的头骨!”
身后男人的呢喃,没有让他反感。
声波鼓动了耳膜,他什么都没有听到。
他只看到眼窝,深陷出光滑的网形,窟窿的深处,黑暗里被刻上零,和无穷。无穷的零。一如无止境的大漠,生长着的无止境的希望,和同样的灭亡。
深处,谁依然在一圈一圈地行走、行走…
沙漠没有留下飞鸟的影子,也不曾留下任何的脚印。
少年看到远处的沙漠,热烈地连着自己脚下,连向更远处的沙漠。
四 九州。
这世间英雄太多,人们厌倦了追赶着马车,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投去鲜花。
比起英雄,眼下更让人动容的,是死去的英雄——
被洪水淹没的禹,就那么沉了下去;他们站在岸边,看着禹就那么沉了下去。
女娲爬进了地壳深处的洞穴,走投无路的共T死在了不周山脚下,连尸首也无人掩埋。
东海南海再没有青色白色的龙高高跃起。
屠龙一技终于成了千古笑柄。
云被晚霞焚尽血肉,海面上浮着灰烬。在海岸的最高处,阿喀琉斯树立巨大的骨架——
“真美啊。”
布告和悬赏,屠尽了蛟龙野兽,也屠尽了英雄。
他们树立起画着图腾的旗帜,然后推倒。于是他们终于不再追逐英雄的马车,也不必向看不到的上方投去鲜花。现在他们弯曲膝盖,正跪拜着向登基的夏王行礼;然后商王;然后周王……
劫后余生的金乌,褪下了恐惧的战栗,抖落人间焦黑的脊背与颈椎,如已裂开肢解的土地。
红色的弓,白色的箭,早已被饥饿的拾荒者们劈成柴火,燃了三天三夜;紫青色的烟气,凝成一根僵直的食指,升上天空,被月光轻易挥散。
断了的食指,已不再渴望被簇拥成英雄——或者竞从未想成为英雄。
那晚的月光冷清,冷清而锋利,他瑟缩着被切割成风里的深谷,胸膛上布满大地裸露的疤痕。世上无药可医,唯一的仙丹已被红线另一端的她囫囵吞下。
月色人间,隔着千分之四光年。
第十万零三天。
“羿卒,羿卒!”他们高喊着,一如既往地带着滑稽的哭腔,像禹死时那样高喊着。假意或真心。
人群熟练地号啕大哭。
但这次,更多人沉默。
沉默被突如其来的叫骂声撕开。一瘸一拐的斗篷,被马车撞倒在地。旁边的妇人和孩子惊叫,急急忙忙跑来搀扶。
爬起身,他刻意别过臉去,藏起残损的手掌。在他摔落的阴翳的右眼中,同时烧着九个太阳。
五城市。
这是一片龟裂的焦土,四处是焦黑的木头和无力奔跑的野兽,烙在巨大岩石身上的文字滚烫而陌生。他伸出手,灼辣的砂粒沾在手掌上,再往前,往前……天边燃烧的巨鸟,突然嘶鸣着俯冲而来。
少年惊慌地收回手。
不见了断流的河水,干渴的世界消失、重启。眼前透明的方框里,洁白的头骨缝隙裂开,发出绿莹莹的火光。他大声喊叫,在楼宇间逃亡。沉重的石门关上了出路。偌大的博物馆里,空无一人。
凝固的空气。
凝固的恐惧。
窗外夜幕如铁。半透明的窗外,城市灯火熄灭,寂寞无声。月亮遥远地望向他,眼角是星星的泪痣。
少年感到右手的食指,正在激烈而冰冷的寂寞里燃烧。
六祠堂。
最可恶而可悲的是,那双手属于医者,也正是凶手。
他们的崇拜与信仰,赋予永生的荣光;而亲手将其扯下神坛,赋予永生的折磨的,亦是他们。
对于英雄而言,被辱没或遗忘,是比死亡更彻底的消灭。
一正如此刻,面对祠堂里煮烂骨头的老妇人、赌博的男人们和踩着牌位偷吃贡品的孩子。无法去爱,他恨自己竞无法生恨。
异兽臣服脚下,却一再折辱于手无寸铁的凡人。
离开吧?
离开吧….
离开吧。
月光在身后跟随,安静,温柔;舔舐着残损的手指,和失落十万里的灵魂。
七展厅。
灯光轰然亮起的瞬间,刺痛让他睁不开双眼。
寒冷。
冷得像冬天的凌晨,冻僵的老佣人靠在黑暗的火炉旁,焰火熄灭了。
空白的牛皮纸在他面前兀白翻页,他似乎没有看到,又也许和眼前的头骨熟识已久。
“好久不见,朋友。”
八异域。
儿孙们挥舞着锄头,垦在绿洲,垦在沙地,垦在父辈们闭眼安歇的土壤上。
于百姓的墓坑之下掘出,这是王的金矿。
而一旁是熊熊燃烧着古书的废墟,文字被煎熬成一只只满身泥垢的乌鸦,从坑洞里嘶哑地惊叫着飞出。
他路过,看到古老法典里失落了远古的梦魇,从后人记忆的墓葬群里涌出,传染。
拖着疲累,他走向在阴凉下琴瑟声中的王。
“停下。”
“为何?”
“地下有妖孽。”
“地下有黄金。”
“妖祸人间,金银何用?”
“铸神祷神,佑我楼兰。”
“荒唐!”
王站起身,挥手喝退逼近的刀戟。
“我知道。”歪斜的皇冠下,露出斑白的发丝,下面是同样斑白的胡须。
“我都知道……”王起身时皇袍摆动,隐隐现出补丁与破败的棉絮, “在你之前也曾有人来过这里。一个老人。他像你一样,抛弃了姓名;远行了很久,从同一个地方——华夏,或神州。你两手空空,而他一路背着鼎……他带来了沉重的铁器,礼,带来了琴瑟,带来了春秋。他说,他爱并信奉的一切都已经死去,而他竭力所否定的一切却都将再度复活。他希望在这里——史书最偏僻的角落——留下一颗种子。”
他看向王,王正看着远处弓着腰的子民,他们的影子和身体拼接成扭曲的符号,印在远古的岩壁。
“但,如你所见。他可以拯救任何一个人,但终究无法救赎年代。你也一样。无论如何,春秋之后,就到了战国。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命运。 你走吧——羿。”
九墓地。
宽大的岩石里,平躺着王;更宽大的沙层里,蜷缩着民。
沙漠深处的宫殿里纷扰依旧,甚至更加吵闹;但无人琴瑟,传出的只有满世界的锣鼓和唢呐。
他看见奴隶们将鼎推下去,侧翻在王的棺椁旁。巨大的哀乐将尸体毛发震动,悲伤栩栩如生。
无数的积郁和叹息,墓碑上没有刻下一个字。
沙海之风如昨,带着昨日王的最后一道御令——“白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绞!”
最后留在他眼里的,是王悲戚的神色,还有最后的轻语:
“即使这里有一个人记得,或质疑或唾弃,楼兰都有存在的意義。我无法回答一个没有疑问的句子。注定无法拯救任何一个不怀有期待的灵魂,即使神明如你……我也一样。”
十楼兰。
他一世一世地死去,连同历史;一代一代地活着,独自一人。
从父辈,到子孙。他们只是朝而往暮而归,无数次挥动锄头,无数次弯腰直立,在一片无望的沙漠里寻找黄金。遵循谁的旨意,以为生活就是意义本身。
每个人都从不停止言语,无人带有语气。
于是,这里消失了。
一连消失都是乏味的陈述句。
锄头和刀戟,连同岩壁上的文字,都破碎成一把沙。
神州还是大漠,华夏抑或蛮夷;虚境里真实的疯狂和庸陋……原来路过的无数人间,不过路过了无数相似的楼兰。沉默的沙尘无处不在,失落的古国从未消亡。
只要置身其中,沙海之外,还是沙海。
他终于明白为何他们穷尽平生也无法走出这里。看不到透明锁链的人们,该如何逃离如世界一般宽广的囚笼。
十一橱窗里的白色头骨沐浴在绿色荧光里,阴森而亲切。
“你将每一世的记忆留存于我,只带着月光行走人间。你,找到了吗?”
少年眼神闪亮,数十万年的山海巨变,沧海桑田,无数朝代的人世沉浮,在一息之间奔涌而来。
沉默。熟悉的沉默。
褶皱与褐斑悄无声息地爬上少年脸颊。光亮苍老下去,熄灭在同样的寂寞里。谁在半边黑暗里,永远追逐另一半光芒。
十二公元某年某日的寻人启事:
某少年走失。
穿着斗篷的流浪汉被从酒馆轰出,从马路上被汽车轰赶到路边,终于醉倒在晚灯下,流着涎水,做了个无趣的梦。
人们从他身边躲过去,或是弯腰,随手扔下硬币和怜悯。
呼出的白汽粘在睫毛上,冻成冰霜。
“哈,今晚没有月亮……”
缠在右手食指的肮脏布条,包裹着的风尘依然滚烫——正如已经在爆裂中,兀白燃烧了四十多亿年的太阳。
十三很久以后,这里铺满了水泥和钢铁,铺满了野生。
谁又在沿着梦里的直线前行,把未卜的前路,踏成后人的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