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经验,乡土世界的未来性
吴晓东
在五四以降的中国文学史中,如果说关于城市的故事是相对贫瘠的土地,那么关于乡土的叙述则是一方沃土。从鲁迅的《故乡》开始,文学家们就似乎更善于讲述乡村故事。新文学值得大书一笔的最初成就即是乡土小说,新时期以来堪称最早被经典化的创作也是寻根文学。而与此相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乡土领域也一向为学者们精耕细作,在老一辈文学研究者那里,关于乡土的著述也更容易取得实绩。在这一学术领域,想获致新的研究角度、视野和方法似乎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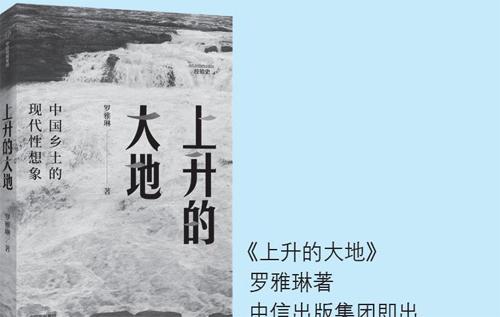
因此罗雅琳的新著《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选择以乡土为研究对象,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也因此,在隶属于九○后一代青年学人的雅琳眼中,乡土中国会呈现出何种与前辈不同的图像、视域甚至可能性远景,就令我陡升一种阅读期待,同时也不免有一丝狐疑,担心的是新人类们的乡土经验是否足够丰厚,是否会令自己的乡土研究成为无本之木?
当我拿到《上升的大地》这部书稿之后首先翻阅的是注释和参考书目,当我看到雅琳在与相关前研究进行着充分对话的时候,开始感到放心进而感到欣慰:雅琳的研究并非是从天而降的无源之水,其实是在汲取前辈们的丰沛的滋养的基础上起步的。正如她在书中所交代的那样:“我突然意识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这一命题其实暗藏着与三位我十分敬重的前辈学者提出的著名命题进行对话的可能,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从他们提出的著名命题中延伸出来的一点心得。”前辈的研究中已经先期预设了一些为雅琳引路的“‘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之理论指向”。而雅琳所谓的这三位前辈的几种著述也因此超乎一般意义上的参考书目,呈现出与她自身的研究更为相关的关键性视野。其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构成的就是雅琳与前研究进行对话的基础范式之一,也意味著费孝通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呈现的乡土研究图景,至今仍有统摄性意义。
如果用一两句话概括百年中国文学,不妨说乡土和都市的故事构成的是二十世纪具有总体性的大叙事。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格局中,乡土和都市的对峙构成了极其重要的图景。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乡土与都市这两极的冲突与互动,这种互动性与二十世纪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是从古老的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转型的时期,正是这种转型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一个贯穿性的母题,甚至也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而在两极的互动格局中,更具有主导性的是乡土世界。乡土性不仅仅体现在广大农村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许多内陆城市也曾经一度生存在乡土文化的延长线上,从而导致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乡土文化的主导模式。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所谓“东方的巴黎”的同时,北京却仍被看作传统农业文明的故乡,一座“扩大了的乡土城”。正因如此,费孝通在社会学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开宗明义地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不仅仅指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的乡土面积的国度,也不仅仅指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据国民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同时也意指乡土生活形态的广延性和覆盖性。乡土性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以及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是基本的乃至全局性的,甚或影响到了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审美认知模式。譬如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就是一部内涵乡村和都市对比格局的电影,也是一部美感分裂的电影。之所以分裂,正是因为影片描述上海都市情境的前半部分相对逊色,而到了后半部分把外景地移到一个荒凉的海岛上,电影叙事便一下子流畅了起来,也造成电影前后两个部分风格的不统一,暴露出张艺谋与大都会之间的隔膜。而同为第五代导演的陈凯歌拍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表现西北黄土高原的《黄土地》以及知青插队生涯的《孩子王》。你会发现是乡土情结构成了这些影片的灵魂与底蕴,而乡村对第五代电影人也正意味着支撑其艺术感受力和美感经验的深厚的故土。

理解了中国的这种乡土性,也就多少理解了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中,乡土研究一直是显学。但也因此,一些约定俗成的进而僵化机械的研究模式渐渐生成。雅琳的新著中所表现出的学术自觉首先就落实在对乡土研究领域既有范式的反思:
在讨论乡村与城市时,我发现自己总遭遇一个难解的问题。有几种常见的思路是需要批判的,一种是“城市高于乡村”的文化等级观念,以及随之延伸出来的、认定乡村的问题只有靠现代化和城市化才能解决的发展主义思路,另一种则是将乡村视为神秘和原始的浪漫主义思路。但在此之外,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乡村与城市之间实际上的落后?我们固然需要将乡村与城市的不同理解为一种多元化的“差别”而非以城市为单一标准的“差距”,但过分强调乡村的特殊性和自足性,以至于希望它停留于某种理想中的样态(不论这种“理想”是充满人伦之美的“乡土中国”还是风景如画的原始边地),是否让我们陷入了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在城乡问题上的“欺诈”?
在城乡问题上的所谓“欺诈”说并非危言耸听,雅琳援引的是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的说法:如果认为“社会的发展进程应当停留在现在这个相对的优势和劣势状态,不再变化,那就是一种欺诈”。中国乡土经验在整个二十世纪直至二十一世纪的持续嬗变,其实早已提供了进行差别化描述的可能性,而研究者引入一种变量的动态叙事格局,则是还原乡土中国既有图景的丰富性的必由之路。雅琳的新著首先考量的正是突破已有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模式,在此基础上尝试贡献新的视野,其中一个核心的论述线索是在乡土与都市之间建构一种新的整体性。以往的研究总有一种将乡土与都市、乡土与世界进行二元化区隔的倾向,而雅琳的研究试图揭示的是,从现代伊始,中国的乡村就已经与都市和世界胶结在一起,二者的边缘以及分界线从来就不是那么明晰的。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市和乡土其实更是不可分割:都市里吃的东西,大都是从乡村运来的;在都市打拼的人,父母可能都还在乡土生活。每年春节至为壮观的被称为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候鸟般迁徙的人口流动,也大都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返奔波。中国的乡土和都市因此呈现出的是一种彼此参照性,一种交互嵌入或者互相依存的关系。
罗雅琳新著的另一个线索是把乡土与现代性的维度更具新意地连接起来,因而真正展示出乡土视域的开放性以及未来性。其中雅琳念兹在兹的一个核心向度即是“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对接:
在我们意识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的“乡土中国”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让“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连接起来,一种既是“乡土”的又是“现代”的想象如何可能?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农村人对于定居城市、成为“城市人”的渴望—一种发自乡土的,却向往着“现代”的渴望?这是否只是农村人失去了“主体性”的体现?要知道,正是这种渴望使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成为长销多年的经典励志书籍。

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被学院派文学史家普遍忽视甚至漠视的时候,雅琳独具慧眼地发掘到的恰是在《平凡的世界》中寄寓着农村人在都市化的渴望中所蕴含的一种集体政治无意识,一种历史“主体性”,一种对于现代性的世纪向往。雅琳的新著由此就揭示出中国的乡土世界始终内含着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即是“现代性”。如果说以往的研究者更为关注的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乡土固有的传统生活形态、价值体系、古旧的文化美感正无可挽回地在一点点丧失,以及伴随着丧失而来的怅惘的挽歌情怀,那么,雅琳对我们习见的挽歌意绪和怀旧心态的恰如其分的警惕,更透露出属于她自己的独有的研究志向。
这就谈到了雅琳借助尼采的经典论述所捕捉到的“崇高”的范畴,借助对“崇高”的阐释,本书生成的是堪称别致的美学意味,也升华了雅琳的乡土叙事中的一些独异的面向。与以往研究界所热衷的那些相对稳定的乡土研究对象不同,雅琳更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具有边缘性的对象,而正是在诸如斯诺、冼星海、光未然、路遥以及刘慈欣所链接成的这个似乎有些另类的人物线索中,雅琳挖掘了通向崇高美学的可能性:“他们都试图讲述人即使在极度落后的环境中也有通往崇高的可能。这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叙述。”而本书标题—“上升的大地”,这个带有崇高感的意象也是对尼采的创造性挪用,雅琳重视的是来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名言:“超人是大地的意义。”无论是对超人的激赏,还是对崇高的诉求,都使雅琳的研究显得别有怀抱。

但我更欣赏的是雅琳对这个“上升的大地”的范畴所持有的更繁复的反思性态度:“我又突然想起另一种‘上升的大地—《格列佛游记》中的飞岛‘勒皮他。飞岛是斯威夫特对于那些不接地气的知识人的反讽,我如此关注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中那些最令人振奋的形象,是否也是一种飞岛上的视角?因此,‘上升的大地既是我对‘乡土中国的奇情狂想,也将成为我对自己的一次反讽,一种警醒。”对于一个有着反思的自觉性的学人来说,这种自我反讽和警醒的姿态是更值得读者欣赏的态度。反讽和警醒也把一种非确定判断加诸雅琳自己的研究论域之中,使乡土视界更具复杂性和可能性。“崇高”也因此不仅仅是一种美学判断,而是一种蕴含了自我反思性的价值立场和经验预设。
雅琳的新著也赋予了“经验”范畴以新的内涵,并试图尝试一种“经验史”的写作形态。在雅琳的理解中,经验史既是方法论,也进一步化为自己的写作形态:
“经验史”意味着,我们所关注的种种貌似宏大的问题,其实应当去日常的零碎经验中寻求答案。“经验”的范围既包括文学经验与音乐经验,也包括情感经验与生活经验。“经验”之所以成“史”,是因为“经验”并非只与一时一地相关,若我们将目光放得更为长远,将会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验”或许关怀着类似的问题。借助“经验史”的视野,我们希望可以从看似独立的文学、艺术、情感、生活案例中找到一种解释问题的可能方法,展望一种充满希望的历史远景。如果说流行的“后现代”学术是以“经验”解构大叙事、大框架的话,那么,“经验史”的态度是“建构”,是对以片段通往整全的可能性探寻。

所谓的“经验史”,意味着间接的经验和审美化的体验也足以为研究者可能并没有亲身经历的乡土世界,提供着感性学和认识论层面的双重积累。由此,雅琳发掘了“想象”在重构乡土叙事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是重新发掘了“文学性”的重要性:“这本小册子的核心是想象。”本书的每一章,都可以说是以灌注了想象力的“形象”为关键词,因此本书最后的落脚点居然是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就很可以理解了:“在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幻想作品中,不是卡尔·施米特笔下象征着现代力量的海洋,或者‘天空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火与‘气,而是‘大地和有着‘大地性的中国形象成了最重要的主题。”刘慈欣的科幻并非“星辰大海”的高蹈的科幻,而是“落地”的,或者说属于“大地”的科幻。中国传统的乡土主题就是这样飞升到了想象力的世界,或者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幻想的世界终于落地生根。
在一般人眼中,乡土世界是与诸如脚踏实地、泥土现实主义、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一些名词、俗语联系在一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即是把天空的形象摒弃在想象之外。乡土似乎容不得想象和虚构,这恰恰预示了既有乡土研究最欠缺的维度,可能正是“想象”。而雅琳却把“想象”视为自己的乡土研究的核心图景和视野。当雅琳的研究最后触及的是刘慈欣的科幻作品时,或许把想象的维度提升到一个极致的高度。至少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为乡土中国赋予了新的幻想性的维度。譬如在《乡村教师》中,刘慈欣把最贫瘠的西北农村与宇宙中神级的文明扭结在一起,科幻的想象力为乡土视景增添的是新的文明论视野。而想象和科幻的空间也借此为我们熟悉的乡土赋予了陌生的面向,生发了新的文明生机,这就是雅琳建构的属于未来的乡土视野。
雅琳新著的题目中“上升的大地”这一具有本质直观特征的概括本身,就是对新的乡土图景和乡土研究的未来性的塑形,是形象化和想象化的提炼。雅琳的新著由此告诉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中国百年乡土经验的重塑,也正是挖掘乡土新的活力和可能性,进而展示乡土世界的未来性的一个奥德赛一般的卓绝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