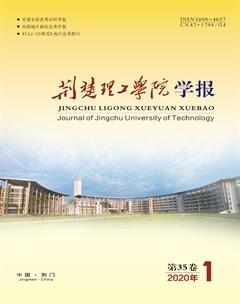对“夫妻共有股权”制度的思考

摘要:以夫妻共有财产出资设立公司,而将股权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情形十分常见。当登记在册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而径自处分股权时,其效力如何不无疑问,由此引发了无数纠纷。我国公司法中无共有股权制度,夫妻共有股权实为伪命题,登记在册的一方对股权的处分为有权处分。股权仅仅是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夫妻共有范围仅限于股权的财产价值。当股东一方对股权的处分损害了非股东配偶的权益时,非股东配偶可以根据一般侵权、恶意串通规则寻求救济,亦可请求分割夫妻共有财产予以求偿。
关键词:共有股权;有权处分;共有范围;一般侵权;恶意串通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D9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20)01-0062-06
一、问题缘起
(一)案情概要
郎某与李某二人为夫妻。婚后,李某于1996年、2004年先后向信源公司出资20万元、58万元,占股10.71%。该公司的另一股东为李某的弟弟李坚忠。2013年3月15日,李某与李坚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持有的信源公司的股权以78万元转让给李坚忠,转让款于今日付清。2013年4月12日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而李坚忠并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2013年8月15日,李某起诉离婚。
2014年3月12日郎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一、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非日常生活代理的范畴,一方所实施的处分行为为无权处分。而受让人作为出让人的弟弟,主观上不具有善意,同时转让价格较低以及受让人未支付相应价款,无法善意取得股权。另外,转让行为发生在李某与郎某离婚诉讼前夕,李某有转移财产的嫌疑,遂判决《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笔者认为,此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如何。
(二)理论及实践争议
根据《婚姻法》第17条规定,婚姻存续期间投资于公司而产生的股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我国公司法上无共有股权制度之供给,仅夫妻共有财产股权的分割存在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指引,而有关夫妻共有财产之股权的行使(表决权、收益权等)、处分均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夫妻一方对共有财产之股权的处分行为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主张为无权处分,其理由为:股权处分不属于家事代理的范畴,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的规定,应当为无权处分行为。同时他们还认为,应区分相对人主观上为善意还是恶意,该共有关系不得对抗善意的相对人[1]。也有学者认为,登记在册的一方对股权的处分为有权处分,另一方的意思在所不问[2]。
实践中,争议则主要聚焦在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夫妻一方股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笔者以“夫妻共有财产、股权、转让”为一组关键词在“无讼”上检索2017年至今的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民事裁判文书,并筛选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股权转让”的裁判文书,仅得到48篇(1)。为补充案例,笔者又以“夫妻、股权、处分、转让”为一组关键词在“无讼”上检索中级法院以上的案例,选取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婚姻家庭纠纷”“侵权纠纷”的案例,共58篇(2),经整理后共得到49个有效案例,其中确认合同效力案件有36例。在这36例确认合同效力案件中(3),法院最后认定合同有效的占大多数,共22例,占比61.11%;而判决合同无效的有14例,占比38.89%。
从裁判理由看,笔者发现,在合同有效的案件中,法院几乎认为夫妻一方的处分行为为有权处分,进而根据合同法第52条认定合同有效,仅有3例(4)认为一方的处分为无权处分。而在无效的案件中,法院则主要结合股权转让对价、对价支付情况、受让人主观状况等综合认定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而行为处分的效力——“无权处分”仅作为补充论证合同效力的工具。具体数据见表1。也许法官并不纠结于一方的股权处分行为为无权处分抑或有权处分,法官对股权处分行为的定性往往取決于在个案中是否能够实现公平正义,此即裁判后果主义[3]。裁判后果主义本身并无可厚非,法律推理本就是在先有了初步结果下寻找理由,并在结果与理由之间来回逡巡的活动。裁判结果的正当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而裁判文书的充分说理是保障其正当的基础。裁判文书的充分说理是法官的职责所在,无充分裁判理由的文书其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公信力均将遭受质疑[4]。因此,对夫或妻一方处分共有财产股权的行为之定性仍然存在重要意义。
二、股东资格认定
对股权的处分属于股东的基本权利。因此,判断股权处分行为之效力的先决问题是确定股东资格的归属。股东资格的确认一直存在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争议[5]。范健[6]认为,股东资格认定应以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为指导,严格贯彻形式主义认定原则,胡晓静[7]亦持此观点。而虞政平[8]则认为应从出资或认购、章程签署、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方面综合认定。张双根[9]认为应以股东名册为中心认定股东资格。笔者认为,股东资格的认定应当以形式要件——即股东的工商登记为主要依据。而实质要件如是否实际出资、出资财产的性质等基本上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仅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依据。对此,笔者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一)股东资格认定形式主义的体现
1.对《公司法》第32条的理解
根据《公司法》第32条(5)第三款的规定,股东的工商登记有着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法条的用语为“第三人”而非“善意第三人”,即立法者赋予了股东的工商登记具有绝对的对抗效力,无论相对人的主观为善意还是恶意,登记在册的人即为股东(6)。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第32条第三款所指的第三人应当理解为善意第三人(7)。笔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理解。1993年,我国公司法出台,此后历经五次修正,在第三次即2005年修正时加入该款规定并保留至今。“第三人”一语之前无“善意”这一限定词并非立法者的疏漏,而是有意为之。可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证据多而复杂,如投资协议、公司章程、出资证明、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股东参与股东会的一系列痕迹等[10]。当多种证据所证明之事实不一致时,股东资格的认定将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立法者注意到,商事行为更加注重效率以及外观主义,有意赋予股东工商登记的绝对对抗效力,以解决此困境。此外,《民法总则》为民商事一般法,第65条所确立的“登记事项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规定为一般原则,《公司法》中对股东登记的效力所作出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根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这一理论基础,在商事审判中,股东登记效力的判断仍然应当依照《公司法》第32条第三款之规定予以处理,即登记在工商名册中的一方为股东。
2.对共有财产股权分割及股权代持规则的理解
工商登记作为股东资格认定依据的立场并非仅体现在《公司法》第32条第三款之中。《婚姻法解释二》第16条(8)中关于夫妻共有财产股权之分割的规定以及《公司法解释三》中有关代持股的规定均体现了股东资格判定的形式主义原则。《婚姻法解释二》第16条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股权的分割用语为“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以及“转让”。从中可以直接得出,未登记在册的一方并非公司的股东,不享有股东资格。在股权共有财产分割中,若其想要成为公司的股东,须作为股东的一方愿意出让股权。同时,为了保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其还须履行特定的对外转让手续——经过半数股东的同意。进而可探知,出资财产的性质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以共同财产出资所形成的股权并非共有股权,非股东配偶不得干涉股东权利的行使。
另外,在股权代持关系中,《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倾向的立场为名义股东即为真正的股东[11]。实际投资人并非公司之股东,其仅可根据股权代持协议享有相应权益。若实际投资人想要显名而成为股东,需要履行特定的程序。此外,根据该解释第26条之规定,名义股东负有在未履行出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义务。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所负之法定义务[12],该补充赔偿义务的主体也应当归属于股东。不可否认,该条款体现了商法外观主义原则,但同时也暗含了名义股东即登记在册的人实际上就是公司的股东。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主义即外观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两者一脉相承。
(二)股东资格认定实质条件例外适用
通常情形下,是否出资、出资财产的性质等实质条件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判断。2013年公司注册资本改为认缴制后,是否实际出资并不是股东身份取得的必要条件。对此,我们可以从《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的规定中得出该结论。该条款规定,即使股东未实际出资,其仍然具有股东资格,除非全体股东在催缴未果后以股东会的形式将其除名并通知至其本人。在特定情形下,是否实际出资可以作为股东资格的判定之依据,具体表现为《公司法解释三》第22条股权归属争议、23条出资后请求公司登记等的情形。有学者认为该司法解释第22条(9)表明了是否出资是股东资格认定的必要条件[5]。有必要指出的是,该规定实际上进一步肯定了股东资格判定的形式主义原则。该条规定请求确认股权一方负有证明其已出资或已认缴出资,或证明其已经合法继受股权的义务,实际上表明了该解释持“推定登记在册的人为股东,未登记在册的人不是股东,除非有充分證据证明足以推翻”的态度。在单纯的股东、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情境下,应当以实质条件,即出资或认缴出资等作为认定依据。股东与其他人(包括股东)之间的纠纷等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以实质条件为股东资格认定基础时,则应主要以形式要件作为股东资格判定的依据。
出资财产之性质并不影响股东资格认定这一结论可以从《公司法解释三》第7条之规定中得出。该条规定,即使出资人对出资财产并不拥有处分权,出资行为仍可能具有效力,进而取得股东资格。在共有财产处分中,部分共有人对财产的处分为无权处分。部分共有人以共有财产出资形成的股权当然属于该出资的共有人,并不会因其性质而认定该出资所换取的股权属于全部共有人所共有。对此在夫妻共有之外的意定共有中更容易理解。此外,即使出资财产为夫妻所共有,其所换取的股权仍非共有股权。对此前文已述及,在此不予赘述。此外,根据前述条款的规定,即使出资财产是为犯罪所得,该出资仍然有效,出资人仍然享有股权。
三、共有财产处分规则排除适用之缘由
(一)夫妻共有范围之明晰
夫妻共有财产出资而形成的股权并非夫妻共有股权,这仅仅是夫妻共有财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股权是一种集合性的权利,其不但拥有财产属性,还有着一定的管理性属性,如表决权、知情权等。当其作为夫妻共有财产时,共有力所及的范围如何?有学者认为,作为夫妻共有财产的股权并非是夫妻共有股权,共有力所及之范围仅限于股权的财产价值[13];有学者认为,可主张共有的仅能是股权中体现出财产性的自益性权利,不具有财产属性的共益权非共有力所及之范围[14-15];还有学者认为,共有力所及之范围及于股权的全部内容[16]。
笔者认为,将共有力所及范围界定为股权的财产价值更为合理。若共有力及于股权的其他范畴,则另一方实质上成为了公司的股东,违背了《公司法》中股东资格认定的规则。股权是一种新的、集合性权利,不同于物权、债权,其不仅仅具有财产属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其人身性主要体现在股东身份,或称股东资格上,只有拥有股东身份之人才可以行使诸如表决权等具体股东权利。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股权和知识产权有一定的相似性。如著作权之中的署名权只能由具有作者身份的一方行使。股权之财产性与人身性结合的方式与知识产权不尽相同[17]。股权的人身性不如知识产权那样可以天然地完全分离,股权的人身性通常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但是,该差异并非本质差异,其并不影响股权参照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根据《婚姻法》第17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共有财产所及范围为“知识产权的收益”,而非知识产权本身。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一方可独立行使有关权利,另一方并非权利人,仅在特定情况下对知识产权的收益享有请求权。值得注意的是,对应到股权,于此之“知识产权的收益”应当理解为“股权的价值”,而非“股权的收益”。知识产权的价值计量不够明晰,只有其财产权利实际行使时,其价值才能够确定下来。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12条(10)规定,共有范围为知识产权事实上已经取得或者已确定能够取得的财产性收益。而股权的价值较为明晰,通常以相应的出资额、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者权益额或公司价值估值为基础。因此,笔者认为,类推适用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将共有力所及范围界定为股权的价值更为合理。
(二)民事规范向商事规范的让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而产生的股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其处分似乎应当按照一般共有原则以及《婚姻法》及相应司法解释之规定予以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股权及股权转让的一般规定见于公司法之中而非民法之中,股权属于公司法创设的财产,股权转让属于商事行为。《物权法》《婚姻法》以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对夫妻共有财产处分作出的一般性规定。公司法是商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价值取向与民法不同。民法追求对真实意思的保护,而公司法更加注重效率,关注对公司利益、交易安全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公司法应理解为特别法,依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这一理论基础,在处理夫妻共有财产之股权时,应当遵循公司法的规定。即仅登记在册的一方为股东,其有权处分其名下的股权。而未登记在册的一方不具有该公司的股东资格,无权参与股权处分的意思形成及表示。
四、非股东配偶的救济路径分析
实践中,作为股东的一方独自处分共有财产股权的情形十分常见。而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夫妻一方转让共有财产股权主要存在请求确认合同效力(无效、可撤销、未生效)、侵权以及夫妻共有财产分割(包括离婚时请求分割股权转让款或请求处分方少分得、不分得共有财产)三种救济方式。笔者根据前文的检索结果(49例)分析发现,确认合同效力是最主要的救济方式,有36例,占比73.47%;而侵权(5例,占比10.20%)以及共有财产分割(8例(11),占比16.33%)救济方式出现频率较低。
然而,在前述有权处分之语境下,非股东配偶便无法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为依据请求确认合同效力(12),其权益应当如何寻求救济呢?笔者认为,应当区分股权转让的对价是否合理以确定是否给予以及给予何种救济。当股权转让对价合理时,夫妻共有财产的形式由股权转变为货币,其利益并未受到损害,无需救济,也不得据此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13)。当股东一方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损害了另一方的财产利益时,另一方可选择分割共同财产、一般侵权规则、恶意串通以获得救济。若非股东配偶既不愿意分割共有财产也不愿意离婚,则可以选择侵权或恶意串通的救济方式。共有财产分割(或离婚时请求股权处分方少分得、不分得共有财产)的救济方式在婚姻法及解释中有明确的规定,没有太大争议。因此,笔者将在下文仅论述一般侵权与恶意串通。
(一)一般侵权规则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其保护范围,即人身、财产权益。虽然另一方并非股权共有人,但其对该股权仍然享有财产利益。当该利益受到他人的侵害时,可以根据一般的侵权条款获得救济。对于侵权的构成要件,非股东配偶需要着重证明“过错”以及“损害结果”的存在。换而言之,即主要的证明责任在于证明股权转让之对价不合理。考虑到非股东配偶不参与公司的任何事物,在信息掌握方面其處于弱势地位,有学者主张对股东方课以向非股东配偶提供公司经营状况等义务[18]。笔者认为,实践中正常的股权交易居多,若对股东方课以以上义务,将影响交易的效率,对非股东配偶提供事后救济即可。对此,在诉讼之中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对股权进行重新估价的申请。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在共有财产制下,并不存在夫妻之间的侵权救济制度。有学者根据《婚姻法》第46条之规定,认为夫妻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以离婚为前提[19]。需要指出的是,侵权责任法是侵权领域的基本法,而在婚姻法律制度中并不存在夫或妻一方不得向对方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婚姻法第46条应理解为释明性规范。而根据《婚姻法》第47条以及《婚姻法解释三》第4条的规定,法律承认夫妻之间财产侵权损害的存在,并愿意为之提供救济。此外,在夫妻财产共有制下,并非不存在个人财产,夫妻侵权损害赔偿具备可行性。当一方侵害另一方的个人权益时,则应当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赔偿责任。当一方侵害了另一方共有权益时,首先应当对该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共有财产处分致另一方的损害应当由侵害方的个人财产支付。
虽然,在笔者所检索到的有效案例中,侵权救济仅有5例,并非主要的救济方式。但令人振奋的是,其中4例均获得了支持。这表明不少法官已经认识到股权的特殊性,“夫妻共有股权”是为伪命题,并且愿意在侵权责任法上为非股东方配偶提供救济,扩张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夫妻共有股权”这一伪命题有望破除。
(二)恶意串通规则
根据《合同法》第52条以及《民法总则》第154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无效。恶意串通规则一直以来存在较多的诟病。理论界对恶意串通的地位及构成要件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实践中对恶意串通的适用也不一致[20]。《民法总则》出台后,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逐渐明晰,形成了主观恶意与客观损害相结合的认定标准。我们通常说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民法亦应当如此。合同无效在民法中属于类似刑罚的制度,应当谨慎适用。因此,民法总则与合同法明确限定了合同无效的特定情境。此外,民诉法律规定恶意串通的证明应当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进一步限制了恶意串通致合同无效规则的适用。有学者认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并不必然无效,其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仅适用于对特定债权的保护[21]。笔者对此持相同观点。并非所有的损害都可以通过金钱赔偿获得充分的弥补。在金钱赔偿无法有效救济的情况下,该债权则可以理解为特定债权,通过合同无效给予受害方更充分的救济。
根据法条的描述可知,在恶意串通中,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主要在于证明合同双方主观的恶意与串通行为,以及客观的损害结果。恶意串通的主观状态是一种复杂的内心状态,往往不可获知且难以证明,实践中通常以法律或事实推定的方式予以认定[22]。在本文的情境下,股权出让方的恶意以及损害结果的存在通常以股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正常价格而推定。然而恶意串通的证明难点在于“串通”的证明。串通不能仅仅是知情,还需要有合谋的意思存在。在本文的情境下,通常以受让方知晓出让方的夫妻关系、股权转让对价的不合理以及长期未支付合同对价等综合认定。由此可以发现,侵权与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相似,但两者均有其独特的价值。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较为严格,当无法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时,便可以通过侵权的一般规则请求股东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侵权的救济方式以损害赔偿为主,虽然也存在恢复原状等责任承担方式,但在仅能够证明股权出让方存在恶意的情况下很难得到支持。而恶意串通的结果是合同无效,可以将股权恢复到转让前的状态,给予非股东配偶多元的救济。
五、结论及展望
当股权作为夫妻共有财产的客体时,夫妻共有力所及的范围并非股权,而是股权的财产价值。股东一方拥有独立、完整的股权,可以独立、自由地处分其股权;非股东配偶不享有股权项下任何股东权利,包括股权处分权。当股东一方不合理处分股权损害了非股东配偶的财产权益时,其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则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股东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能够证明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时,受害方还可以根据恶意串通规则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我国的法律规范未提供共有股权这一制度,域外的共有股权制度适用的主要情形为法定股权共有以及意定股权共有。具体在我国表现为因夫妻关系、继承等而共有,以及股权代持。夫妻共同财产股权可依本文的路径予以解决,其他法定的股权共有情形也可以参照此路径予以解除。至于股权代持问题,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相应的解决路径。股权共有制度以解决的问题似乎均可以在现有制度下得到妥善的解决,股权共有制度似乎并无存在之必要。
注释:
(1) 无讼案例网,https://www.itslaw.com/bj,笔者访问于2019年12月25日。
(2) 无讼案例网,https://www.itslaw.com/bj,笔者访问于2020年3月23日。
(3) 在此,笔者仅讨论“合同效力”的案件,其他案件将留在后文讨论。
(4) 参见(2018)粤01民终10525号、(2019)赣11民终1203号、(2017)湘11民终465号民事判决书。
(5) 《公司法》第32条的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6) 冒名股东为司法解释所创设的唯一例外。下文所称的“绝对对抗效力”与此同义。
(7)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条,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及其适用。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11/id/4638096.shtml
(8)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9) 2014年《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修正后,前第23条变更为现在的第22条。
(10) 《婚姻法解释二》第12条:婚姻法第17条第三项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
(11) 共有财产分割案件中,当事人主要的请求为(平均)分割股权转让款,而请求处分方少分或不分得财产的案件仅2例,或许是因个案因素所导致,如转让价格公允等。
(12) 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据此,即便认定为无权处分,股权转让的合同也应当有效。
(13)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的规定,婚姻存续期间仅可在有限条件下请求分割共同财产,而合理对价转让股权的行为不在此之列。
参考文献:
[1] 李如霞.夫妻共有股权转让问题探讨[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5):43-48.
[2] 吉明.夫妻一方擅自转让共有股权的效力问题[J].知识经济,2013(4):18-19.
[3] 雷磊.反思司法裁判中的后果考量[J].法学家,2019(4):17-32,192.
[4] 孙海龙,高伟.裁判文书及其公信力现状调查和改革路径研究[J].法律适用,2007(5):35-40.
[5] 贺辉,梁晓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股权转让的效力[J].人民司法(案例),2017(35):68-73.
[6] 范健.论股东资格认定的判断标准[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6(2):66-73.
[7] 胡晓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思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20(3):144-150.
[8] 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J].法律适用,2003(8):69-72.
[9] 张双根.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以股东名册制度的建构为中心[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5):65-82.
[10] 甘培忠,周淳.隐名出资纠纷司法审裁若干问题探讨[J].法律适用,2013(5):18-24.
[11] 周游.股权利益分离机制下隐名出资问题之再阐释[J].北方法学,2015,9(1):152-160.
[12] 李志刚,李后龙,叶林,等.认缴资本制语境下的股权转让与出资责任[J].人民司法(应用),2017(13):105-111.
[13] 杨青,郭颖.离婚案件股权分割的法律分析[J].求索,2005(12):105-107.
[14] 王建东,毛亚敏.离婚诉讼之公司股权分割问题探讨——兼论“《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16条之完善[J].法学,2007(5):136-141.
[15] 叶名怡,张伟.离婚案件中三类特殊共有财产分割探析[J].法学杂志,2009,30(11):59-62.
[16] 王彬,周海博.夫妻共有股权分割制度探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3(1):87-90.
[17] 梁开银.论公司股权之共有权[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28(2):140-148.
[18] 杨青,郭颖.离婚案件股权分割的法律分析[J].求索,2005(12):105-107.
[19] 陈群峰.夫妻侵权之责任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158-162.
[20] 朱广新.恶意串通行为无效规定的体系地位与规范构造[J].法学,2018(7):131-142.
[21] 茅少伟.论恶意串通[J].中外法学,2017,29(1):143-170.
[22] 张平华.恶意串通法律规范的合理性[J].中国法学,2017(4):207-226.
[责任编辑:王妍]
收稿日期:2020-01-10
作者简介:段淑婷(1997-),女,四川达州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事法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