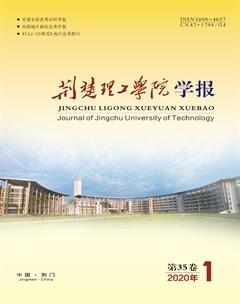十九世纪下半叶西人眼中的台湾城镇印象
卞梁 连晨曦
摘要:晚清台湾城镇因其自身特点及各异的市政建设轨迹,呈现出不同的城镇风貌。西方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台后,将当时台湾的城镇风貌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在西方世界面前。由于视角不同,投射出相异的台湾城镇印象,并与传统中文涉台游记方志的“我者”形象有所差异,勾勒出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他者”视野下的台湾城镇形象。对相关史料进行甄别梳理,并从生活地域、个人背景、在台事由等方面寻迹西人描述差异的群体性原因。这不仅为在学理上重构真实台湾印象提供来自西方的“他者”视角,且在现实层面对映现客观真实的台湾城镇面貌大有裨益,对今日台湾古迹保护、城市原貌修复亦助益颇多。
关键词:近代西人;台湾城镇;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势能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20)01-0009-07
近代西人来台后,大多数选择进城居住生活。这不仅因城市有着相对更为舒适的住宿条件和更好的卫生条件,亦因山区条件及治安较差、其人身财产安全难以保障。如马偕所言:“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喜欢聚居在一起,所以就会聚集住在城镇和都市。在台湾,为了安全起见,大家更会聚居在一起。”[1]105也因如此,西人对近代台湾城镇记录颇多,且不同地区的城镇面貌多有不同:台湾北部河流众多、港口林立,因此,以淡水、艋舺为代表的北部港口城镇大多船舶连片、商贸繁华,是当时台湾的商业重地。台湾中部地区扼南北之要,历史悠久,因此,以鹿港、台湾府为代表的中部城镇成为当时全台的政治中心,并形成朴素庄重、有序协调的城镇风格。台湾南部地区环境秀美、风光旖旎,这使得以打狗为代表的南部城镇群犹如花园丛立,成为自然与人文融合的典型。归纳西人眼中的台湾城镇印象不仅能从“他者”视角对近代台湾有更切实客觀的体悟,且能对当前台湾地区城镇修复及古迹保留提供借鉴参照。
目前学界对近代台湾城镇的研究较为零散。大陆方面开展的台湾城镇研究较少:徐晓望[2]将其置于闽台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台湾南部城镇发展与福州有着经济、人员往来等方面的联系;纪立芳等[3]则从专业的建筑学角度对台湾城市中的寺庙进行描述。台湾学界的研究则更为多元:李佑安[4]考据台南府城的建城历史;郭文华[5]从台北在1887年至1895年的近代化建设入手,来反推台北建城的规律及动因;陈广文[6]从台北建筑的拆除角度阐释城市在“新陈代谢”中的动态平衡;游志文[7]从地名的研究视角探寻北部淡水诸城的建设历程。虽然近年来学界对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研究愈发重视,但其研究多趋向于对个别城市发展历史的梳理及城市建筑风格的探讨,以纵向考察研究为主,但将台湾不同城市置于同一历史阶段进行横向比较、梳理、归纳的研究几趋空白,对近代西方人的台湾城镇印象的考察与归纳方面亦有所欠缺。本研究按地理位置,将台湾城镇大致分为北部、中部和南部进行分述。在选取区域内较为典型的,西人记载描述较多的城镇进行剖析的同时,概括这一地区的城镇特点,并结合时情宏观概括西人对台湾城镇的印象。文章侧重于1865年至1895年这三十年,但不局限于这一时段,原因在于,随着1860年代一系列保障西人在华财产和生命权益的条约的签署,越来越多的西人来到台湾。密集、深入的西人在台活动展现出以往中西交往中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虽然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使台湾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折,西人在台话语权迅速丧失,但近代西人所构建的“台湾印象”已然成型。这使得获得较为完整的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他者”视野下的台湾城镇形象成为可能。
一、大气包容、商贸发达的北部城镇
台湾北部雨量丰沛,气候温润,河流众多。因此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港口型商业城市圈,是当时台湾商品经济的中心地带。在近代西人眼中,淡水、艋舺、基隆显然是当时台北港口城镇的代表。马偕牧师曾对台湾北部城镇分布进行过大体的介绍:“北台湾的三个大城市分别是人口约有四万五千人的艋舺、三万五千人的竹堑,以及约三万人的大稻埕。”[1]105而当时的中港、锡口、新埔、三结仔街、猫里等地常住人口亦超一万人。可以说在整个台湾北部,城市、乡镇和农村和谐共生发展着。
淡水位于台湾西海岸,是台湾与大陆及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埠。因优越的地理环境及开放的文化氛围,淡水成为诸多西人登台的首选地点,马偕甚至将淡水作为长老教会在台活动的总部,并竭力推动当地近代化过程的开展。西人对当地风貌的记载存留颇多。如英国人必麒麟如此描述:“一条从峡谷流出的小河,缓缓地注入淡水港内。淡水是一个前途似锦的港埠,它的港湾较易进入,便于贸易的往来。但停泊场是由浮沙所构成,地基并不稳固。淡水市镇位于其西南方的一座双峰山和淡水山脉之间,前者高约一千七百尺,后者高约二千八百尺,并延伸进入内地。”[8]57美国人史帝瑞从淡水来台,他为闪避淡水河口的沙洲,沿着河流往上行驶一英里,也因此欣赏到独特的景色:“河流两边是陡峭的火山丘陵,上面长满了杂草和芦苇。北方山脚下,汉人城镇沿着河岸群聚而建,上面的山坡则长满了榕树及各式树木。有一片石头矮墙沿着山脊而建,许多老旧生锈的中国大砲透过石缝,凝视着远方的海面。”[9]33史帝瑞还拜访了英商陶德在淡水开办的宝顺洋行,对在台西方商人所从事的台茶贸易有更深的了解:“当我们下锚停泊时,就有一股浓郁的茶香从岸边的低矮建筑物传来。我们在隔天早上前去拜访,原来这里是宝顺洋行用来制作及储放茶叶的地方。部分建筑作为仓库之用,里面的箱子装着从茶农处买来的茶叶。另一处则有汉人忙着制造包装茶叶用的铅盒和木箱,以便送到世界各地去。在制作箱子的过程中,绘图占了很大的比重。”[9]34当时,淡水不仅是台湾北部重要的港口,也是全台湾茶叶贸易的中心,此地不仅运茶贩茶,也种植茶叶:“淡水山里种植大量的茶叶。茶叶的品质虽然称不上顶级,但发展的潜力颇大。当时,在陶德先生的努力经营下,此地生产的台湾乌龙茶在市场上颇具声誉。”[8]58
在淡水,荷兰人所建的红毛城无疑对近代西人最具吸引力。必麒麟曾对这种位于淡水河右岸的古老荷兰城堡进行细致描绘:“这座城堡有一部分区域被挪用为领事馆。关于它的历史,我找不到任何欧洲人的记录,而它本身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目前城堡的保存情形虽好,但潮湿又无人居住,甚至有闹鬼的传说。这座城堡已成为淡水港的地标。”[8]57史帝瑞则更关注红毛城的历史:“在两三百英尺高的山坡上,有一栋方形的碉堡,顶端生长了一颗榕树,上面飘扬着英国国旗。原来那是荷兰古堡的要塞,因为墙壁厚实,内部空间很小,并采用拱状支撑的建筑方式,所以它能够经受当地气候的侵蚀,在此耸立达两百五十年之久。这座要塞的外观有些破损,现在充当英国领事的住所和办公室。”[9]33
基隆位于淡水东北,是当时全台最大的港口,承担着与淡水相似的运输任务,但略有不同,淡水以货物的进出口为主,基隆则以资源物质的运输为主:“此地原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后被荷兰人占领,直至荷兰人被迫撤离台湾为止。这附近的风景远比西部沿岸优美,港口位于宽阔的海湾岸上,在富贵角和鼻头角之间,二角相距二十二里。海湾里距港口两里处,高耸着一座黑色岩礁,名为基隆屿。”[8]58基隆有着丰富的煤矿储量,有“煤港”之称,因此很早便受到西方列强的觊觎与掠夺:“基隆是一个大煤矿区。矿场位于欧洲人称为‘煤港的海湾里面。以往煤矿都是按照汉人的方法横向开采,并大量出口烟煤。后来欧洲的企业采用现代的方法,以机器采矿,生产量大幅提升,使得满清当局终于注意到这片隐藏在台湾北部矿田中的重大财源。目前这个地区有两条铁路,使得矿产的运送更为便利。”[8]59
而在史温侯来台时,基隆的煤矿开采业已日趋成熟。籍由英国“刚强号”驶入基隆并下锚,史温侯“随着轮机长许乐勘察港区附近煤矿,发现当地人仍用原始的方式采运煤炭,水平的矿穴点着油碟照明”,他看见某处“五个几乎全裸的矿工手持鹤嘴锄挖煤,将挖出的煤炭装在可容一担的长方形竹筐中,置于方块上,拖过滴水、泥泞的坑道,再背到市场贩售”[10]。基隆煤的特点是沥青含量较高,燃烧太快。史温侯认为这“不利蒸汽轮船,尤其不利须长途征战的蒸汽动力炮船,恐怕无法维持三四天的航程”。因此,他建议将基隆的煤与威尔士的煤混合使用,以弥补基隆煤的不足[11]148。
西人对基隆民众生活的关注度似乎并没有其他城市那样高,这或许是因当地重商气氛较浓,对西人较为淡漠所致。如马偕对基隆便无好感可言,当他第一次前往基隆,发现“那里的人们对我们的仇视最深。有很多人跟在我们后面辱骂并向我们丢石子……在基隆,我们在一间很大间的庙宇的石阶上唱了一、二首诗,庙口和路边很快的都挤满了人,他们都是拜神明的人,所以都很生气。”[1]134这不仅能反映出当时基隆社会对西方势力的排斥,也体现出当时西方人对传统中国城市的歧视与偏见。
作为当时台湾北部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艋舺自然受到西人的格外关注。同时,艋舺的建城史也是汉人积极开拓的艰难岁月的历史展现。艋舺低洼潮湿,饮用的水略带咸味,不甚卫生,因此艋舺居民不得不修建沟渠,引山泉入城,确保城市的供水稳定。他们凿开一个十六码长、八尺宽、深度达十四尺的隧道,并将溪水引至水道里……导水管是三边的,用厚木板钉在一起,周围另钉有木头。水管里涂着石灰泥,所以不透水。导水管深度约五尺,宽达八尺,还有四十七支拐杖一般的支柱。”[8]58
除此之外,西人还对新店、竹堑等地进行了考察记录,但多轻略描述。如马偕对新店繁荣的描述是为了说明教会势力在台北地区的兴盛:“新店是个人口集中且繁荣的小镇,位于离淡水约十八里远往内陆去的山脚下……现在的新店教堂是北台湾建得最好、风景也最美的教堂之一,教堂的位置是在镇端一处高起的地方,它的石砌尖塔从好几里外就可明显的看到,教堂周围以石墙围起来。教堂正门前方数十码,有新店溪围绕流过,溪和教堂之间铺满了由洪水冲下并被溪水洗得圆圆的鹅卵石。”[1]144他也描绘过竹堑地区的相关情况:“竹堑,这个住有四万个居民并有城墙围着的都市,是我在1872年刚抵达淡水后的次个星期第一次沿着西海岸南下时所拜访的地方。从竹堑往山区去约十里处,有个称为月眉的客家村,我们是由数个到竹堑市参加礼拜的客家人带到这里的。”[1]1461874年北上淡水途中,史帝瑞也经过竹堑,可能是因为行程匆忙,这座城市并未给他留下太多印象,仅是“我们经过了好几个村落,以及四周有城墙的竹堑,当中大多数居民都是客家人。当晚,我们在一个山丘上的小乡村过夜。”[9]100
总之,西人对台湾北部城镇的描述较为清晰详细,且多以港口城市為主。这一方面是因当地自然气候相较中南部更为宜居,以此成为诸西人暂居之处。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台湾北部港口众多,经济较为发达,对外贸易产业较为发达,给西人来台提供了较好平台所致。台湾北部星罗棋布又互相连结的城市群无疑成为台湾近代化转型的重要保障之一。
二、沉稳庄重、井然有序的中部城镇
台湾府是当时台湾中南部第一大城市,虽然规模不及北部诸市,却在一段时期内作为台湾地区的政治重心而存在。因此,以台湾府为代表的中部城镇群自然成为全台庄重有序的代表。英国驻台官员史温侯曾前往台湾府拜谒当时的道台孔昭慈、台湾知府洪毓琛及知县王衢,因此得以清晰呈现近代台湾府官衙的景象及官员办事流程。
首先是当时台湾府的概况:“(台湾府)为了连接安平港,开辟了五条水道连接大西门外,由南到北有安海港、南河港、南势港、佛头港、新港墘……港中有绿意盎然、开满赏心悦目紫宣花的漂亮羊蔓草堤岸边的浅水道。”[11]151必麒麟也评价“台湾府是个典型的汉人城市,和中国各地的城市比较起来相差无几。府城的气候相当干燥,晴朗而舒爽,只是偶尔会刮起强风,空气中布满尘沙,把屋子弄脏,使旅人感到扫兴。”[8]57
而从面海的西城门进城后,史帝瑞则目睹了更为真实的台湾府街道景象。西街是整座城的主干道:“这条街道向东延伸,据说原来是荷兰人所盖的马路。街道两边非常热闹,各种商店林立,各色人等来来往往。苦力们打着赤膊,肩上以扁担挑着重担快走,一路上哼哼哈哈叫行人让路。阔气的商人身穿长袍,为了生意来回奔走。中国官员则坐在轿子上面,由四到六个苦力抬着,前方还有一位警备吆喝着行人回避。”[9]43必麒麟眼中的西街则有所不同:“越过城墙朝海面望去,可看见一大片城郊,商市就在那里,这片地区就像所有汉人的城镇一样,吵杂、贫穷又污秽……府城唯一的大街上,拥有数家可观的店铺,这是从西门通往道台衙门的重要街道。”[8]54两者论述迥然相异的原因,便是立场的不同:史帝瑞作为一名旅行者,单纯地以记录与欣赏为目的,描写相对客观;必麒麟彼时则因南部船难及樟脑事件而与台湾官府处于对立状态,自然无心欣赏,甚至对其地多有贬低,以发泄自身的不满情绪。
对于打狗的自然风物,必麒麟重点介绍了猴山:“这是一座古老而庞大的珊瑚岩山,山上有一些奇异的洞穴和缝隙,塞满了贝壳和鱼骨。由山顶望去,景色壮丽。走过一个小海湾,便见一池硫磺泉,若沿着海岬蜿蜒而上的小径前进,爬过峭壁后,眼前立即呈现出一片辉煌的美景,使你顿生不虚此行之感……再往里走,出现一片肥沃的平原,种植着翠绿的稻子和纤细的甘蔗,还有一丛丛的翠竹点缀其间,偶遇一个小村庄,从远处看来,景致如诗如画。最远的边界是一条低矮的山脉,在晴朗的日子,特别是日出时分,遥望东边,可看见山上紫色的熹微——真是一幅神圣的图画。”[8]52
可见,当时台湾南部除打狗外的大部分地区虽然有着优厚的地理条件,但受制于多方因素而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开发。在这其中,南部先住民的半开化状态是影响南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诚然,清政府对先住民(2)有着刻意的野蛮化与妖魔化,如陈龙廷先生认为,在书写策略上,“文明与非文明”是帝国中心与边缘论述,并呈现出“同心圆式的族群关系”:由天子为中心出发,外层扩散出去,分别为文人官僚、黎民、熟番、生番。这种阶序关系,实际上就是以“人与非人”的二元论为核心发展而来的[17]。如《台湾府志》将原住民归于原始人之列:“番人无姓氏,不知岁月,惟凭草木,听鸟音,以节耕种。无祖先祭祀,亦不自记其庚甲,父母而外,无伯叔、甥舅之称。”[18]
但在客观上,由于历史、语言及地域环境的不同,南部先住民确实对汉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偏见,甚至常以暴力相待,因此变成了这样的南台湾:“1870与1880年代的台湾南端,是东亚地区最荒凉而难以进入的地区。不过,此时此景的结束,只是整个大历史剧码进展中的一部分而已。至少有三项主要剧码,由世界各地主要邦都所参与的一连串事件中,彼此交缠在此。”[19]
四、余论
综上所述,近代西人所呈现的台湾城镇风貌,根据地域不同而存在着诸多差异。北部城镇因便利的贸易交通环境,成为当时台湾对大陆及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当时台湾主要进口纺织品、建材、陶瓷、漆器、纸张、草席等,出口自产的麻、靛蓝、花生、樟脑、鹿皮、藤、咸鱼等物产,其中尤以茶、糖、樟脑为主业,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因此也是当时各大洋行驻台总部所在地。同时,台北诸城镇也是赴台西人的首选之地,因此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一旦北部遭受打击,旅台西人的生活质量会受到直接影响,如法军对台封锁期间,陶德感慨“可怜的外商仍在望梅止渴……希望法国当局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无辜的洋老百姓,至少让大家过个快乐的圣诞节总可以吧?”[20]中部城镇因台湾府的存在而颇具活力,亦因此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但却因产业单一及频受先住民骚扰而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当时台湾各港口因淤塞而迅速衰落:“鹿港口门淤浅,商舟不前,道光四年采舆论,请开五条港利商船。”[21]同时先住民与汉人的冲突时有发生,“猎首”行为时有发生,这无疑对台中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南部打狗地区的情势则较为复杂。自辟为通商口岸后,打狗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因“鹿耳、鲲身悉被沙淤,”“海舶到台,即泊凤山县之旗后口”[22],甚至一度成为与淡水齐平的南部货物集散地,形成了南北两大市场体系,也成为日后台北、高雄两大都会区的雏形。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岛内经济北移的大趋势,使得打狗迅速衰落,至1893年,淡水的贸易总额已是打狗的2.5倍[23]。因此,打狗在西人看来,难免呈现颓败衰落之相。
值得注意的是,西人身份的不同会引发对台湾城市的不同阐述。如台湾府在史帝瑞、史温侯、必麒麟等具有官方背景的西人眼中显得破败不堪,但在1877年赴台协助在台中地区进行石油开采工作的美国雇员简时(A.P.Karns)和洛克(R.D.Locke)看来,台湾府却是个风景旖旎、物产丰饶的地方:“台湾府城人口约5万,住在高25尺、厚12尺、周围6哩长的城墙内,城墙够宽、上可跑马。气候十分暖和,阴凉处介于华氏75度到80度之间,人们整年可睡在户外。当地农产品很多,有凤梨、橘子、柚子、香蕉、梨、甘薯、甘蔗、花生,以及烟草等。整体而言,这是个美丽的地方。”[24]究其缘由,似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多数长期接受西方学院派教育的西人,均会将在台工作生活的不利归结于台湾及台湾居民,进而对台湾城镇产生厌恶之感。如他们认为官府在处理事务时有失公允,“二峰庄那件事让官府办,是因为有英国领事逼他;兄弟去入呈都不听。”[25]因此,台湾府城亦呈现衰败破旧之景。而被高薪聘请,待遇优厚的美国雇员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愤懑情绪,因此对城镇的描述自然更为客观现实。另一方面,西方优越论及西方中心主义让西人固执地认为台湾文化在总体上远低于西方文明,因此,近代赴台西人一直对当时台湾的各类事物持否定和轻视的态度,台湾的城镇自不例外。这可以说是所有近代赴台西人的通病,难以剔除。
当然,西人“他者”视野下的台湾城市形象,在客观上对复原和呈现旧时台湾诸城的历史面貌大有裨益,尤其是其对淡水红毛城、台南热兰遮城、高雄旗后山风貌等的描述,值得深入挖掘、比较。而中西历史印象所呈现出的差异,亦值得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析与思考。
注释:
(1)对于热兰遮城墙上的字迹,史帝瑞与必麒麟在“Febowed”一词的释读拼写上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因城墙年久失修,“F”之轮廓不清晰,导致必麒麟将其看成“G”。
(2) 目前台湾地区以“原住民”称之,但国际通行语义中的“原住民”带有较强烈的独立意涵(见联合国原住民工作组会议文件,E/CN.4/Sub.2/AC.4/1996/2),本文遵照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有关规定,以“先住民”称之。
参考文献:
[1] 马偕.福尔摩沙纪事——马偕台湾回忆录[M].林晚生,译.郑仰恩,校注.台北:前卫出版社,2007.
[2] 徐晓望.晚清福州与北台湾的城市化建设[J].福建论壇,2016(10):187-192.
[3] 纪立芳,朱光亚.试论台湾地区与江南地区晚清寺庙建筑装饰异同及工艺传承[J].建筑与文化,2009(12):109-111.
[4] 李佑安.晚清台南府城空间纹理保存现况之研究[D].台南:成功大学,2013.
[5] 郭文华.台湾洋务科技初探(1887—1895)——从台湾铁路、台北机器局与基隆煤矿出发的初步讨论[J].新史学,1996(2):99-138.
[6] 陈广文.台北府城兴筑与拆除之研究[D].新北:淡江大学,2009.
[7] 游志文.地名演变与转型争议——以淡水河流域为例[D].台北:台北教育大学,2017.
[8] 必麒麟.历险福尔摩沙:回忆在满大人、海盗与“猎头番”间的激荡岁月[M].陈逸君,译述.台北:前卫出版社,2010:57.
[9] Steere J B.福尔摩沙及其住民:19世纪美国博物学家的台湾调查笔记[M].林弘宜,译.李壬癸,校注.台北:前卫出版社,2009.
[10] 陈政三.翱翔福尔摩沙:英国外交官郇和晚清台湾纪行[M].台北:五南出版社,2008:42.
[11] Robert Swinhoe.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J].Journal of the North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59,1(2).
[12] 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D].台北:台湾大学,1993.
[13] 临时台湾旧惯委员会.调查经济资料报告(下册)[M].东京:三秀舍,1905:174.
[14] 荒井贤太郎.台湾经济事情视察复命书[M].东京:大藏理财局,1899:63-65.
[15] 翁如珊.清末台湾洋货的进口与消费[D].台南:成功大学,2011.
[16] 林满红.茶、糖、樟脑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M].台北:联经书店,1997:2.
[17] 陈龙廷.帝国观点下的文学想像——清代台湾原住民的妖魔化书写[J].台湾文献,2004(4):233.
[18] 陈碧笙.台湾府志校注[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56.
[19] 杜德桥.1880年代南台湾的原住民族:南岬灯塔驻守员乔治·泰勒撰述文集[M].谢世忠,刘瑞超,译.台北:顺益博物馆,2010:1.
[20] 德约翰.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战争台湾外记[M].陈政三,译.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84.
[21] 曹士桂.宦海日记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23.
[22] 丁绍仪.东瀛识略[M].台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5.
[23]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M].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264.
[24] 陈政三.美国油匠在台湾——1877-78年苗栗出矿坑采油纪行[M].台北:台湾书房,2012:16.
[25] 台灣教会公报社.台湾教会公报全览[M].台南:教会公报出版社,1885:40.
[责任编辑:王妍]
基金项目: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黄檗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中日黄檗文化传播与交流研究(2019HBKF00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清台湾近代化转型与社会变迁研究(19CZS037)
作者简介:卞梁(1989-),男,浙江杭州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闽台关系研究;连晨曦(1988-),男,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黄檗文化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亚太区域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