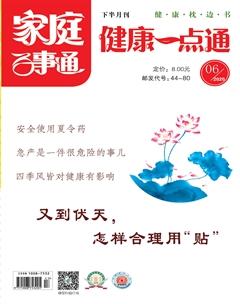且吃几粒糖醋蒜
周芳
小时候,我的胃口格外浅,尤其是对蒜味无法接受。每次吃饭,见到有肉便两眼发光,若看到佐味的一粒粒白胖的蒜头,则要挑出来。后来,我年岁渐长,口味也杂了许多,竟对蒜有了嗜好。蒜苗、蒜薹,再到蒜头,都会出现在我的餐桌上,糖醋蒜更是四季佐粥佳品。
糖醋蒜是母亲的拿手小菜。曾经有个笑话,母亲家里装修,我请一位朋友来帮忙。事毕,父母给工钱,朋友死活不收,父母很是犯难。结工时,朋友望着桌上一碟吃剩的糖醋蒜,不好意思地说:“这糖醋蒜闻着太香了,是你们自己泡的吗?”母亲说:“是啊!”“老人家,要不你就给点糖醋蒜吧,我就爱吃这个。”母亲乐坏了,这可是对她手艺的最高赞赏。她赶忙到厨房里连坛子都端出来:“都拿去,都拿去,明年新蒜上市,我再给你泡一坛。”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还剩下的大半坛糖醋蒜被朋友一个星期就吃完了。
后来母亲真惦记着这事。第二年新蒜上市,她早早就去买了一个别致的泡菜坛子——美食配美器是她的厨房信条之一,这次送人更要郑重地践行。
打理新蒜时,只留里面一层完整的蒜衣,蒜底部的须根要修掉,蒜梗留约一厘米长,尽量保持一头蒜的完整性。散成一瓣瓣的蒜,容易吸取过多的糖醋汁,吃起来就不脆了。
新蒜洗净后一定要沥干水,撒上鹽,每天来回颠几次,保证均匀腌入味。腌几天后,将上好的红糖、醋和酱油按比例和水熬开,冷却,倒入装蒜的坛中,密封,一个月后就可食用了。
糖醋蒜在北方最常见,汪曾祺先生在北京时,曾请当地人吃“藠头”,结果他们多用不信任的眼光瞅半天,乃至入口也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有糖蒜好啊!”
我不喜欢糖蒜的北式做法。且不说糖蒜是由白糖泡制,色感上也比醋泡过的淡了许多。母亲做的糖醋蒜每每开坛,一股浓郁的蒜香味直扑鼻翼,蒜头经过时间的涵养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剥开赤红的蒜衣,里面的蒜瓣也红得深沉,醋酸恰好地中和了蒜的辛辣味,入口脆爽,咸甜适中,直让人吃了一粒又想一粒。在我家,糖醋蒜不但是佐粥佳品,正餐时也常配上一小碟,一两粒入口,正好解了油腻,助了消化,成了我这个食肉者的救星。
每年暮春,新蒜上市,母亲做糖醋蒜是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彼时,窗外光影婆娑,室内蒜香袅袅。母亲做的一坛坛糖醋蒜被我们抱回家,来年,又一个个空坛子被我们送回来。日子,在一抱一送里流淌;光阴,在一来一去间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