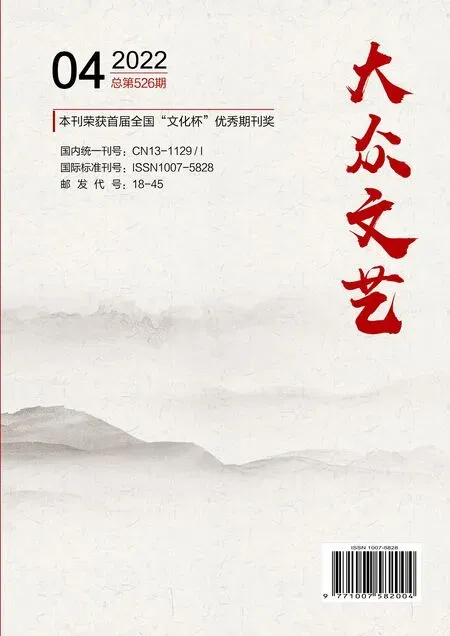试论19世纪末西方对中国音乐的研究
——从阿里嗣的《中国音乐》谈起
(中公教育 100000)
J·A·范·阿里嗣(Jules A.van Aalst,1858~1914后),比利时人,是一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活跃于中国的传教士,也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他的《中国音乐》由上海总务司出版,发表于1884年。这本书被重印多次,是继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之后第二本系统性地介绍中国音乐的外国出版物,也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外国人了解中国音乐的主要途径,其影响甚至可以说高于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
《清末》一文以评介为主,主要介绍了《中国音乐》中的著者态度、古代音乐、总论、律制、记谱法、调式、半音音阶、声乐、和声、雅乐、俗乐、乐器、结论等内容,并对阿里嗣关于中国音乐的错误理解进行勘误。
一、阿里嗣与《中国音乐》
19世纪,物理、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类学科都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与完善,并对随后诞生的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民族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哲学根源是当时自然科学成就带来的世界观革命。”《中国音乐》成书于1884年,民族音乐学派尚处于萌芽时期,“以古典进化论为代表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为它在音乐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为了寻找和印证进化的规律,众多的学者开始对非欧洲诸民族,尤其是自然民族的文化进行了广泛、详尽的调查研究。”阿里嗣的《中国音乐》正是受此浪潮的影响写作而成的。
阿里嗣特别注重中西对比,以期将中国音乐文化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他在序中强调:“在此我将努力指出西方和中国的音乐之间的对比或相似性,以最无聊的方式呈现其中艰深的理论。揭示此前从未发表的关于中国音乐的细节,并简短的叙述它。”在行文过程中,阿里嗣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将中国音乐置于落后地位,但这本书也确实是建立在阿里嗣对当时中国音乐有着较为完整的、系统性的认知上的,具备足够的参考价值。
二、书中的其他错漏之处
1.《中国音乐》在其“关于中国音乐”(On Chinese Music)一章中的引用串行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应该是出自《论语》而非《庄子》。而上一个注释的“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应是出自《庄子》而非《苑洛志乐》。注释中的“乐无诗非乐也”一句才出自《苑洛志乐》。
2.十二律后五律的计算数字出现差错(见《中国音乐》中律吕相生图),大吕的长度应为蕤宾管的三分之二。夷则的长度应该为前管的三分之四。夹钟的长度应该为前管长度的三分之二。无射的长度应该是前管的三分之四。应钟的长度应噶为前管长度的三分之二。阿里嗣在最后五官将二和四完全写反了。
3.阿里嗣在描述元明清音阶发展的时候忽视了其他乐种的音阶,因此所述之音阶发展脉络并不正确。
4.在“音符变更记号”(Signs of Alteration of Notes)一章里,阿里嗣在将五声与外国名称对应时,把羽音对应的音搞错了,应该是下中音而非下属音。
三、《中国音乐》的研究特点——阿里嗣关于中国音乐的取向上的两面性
阿里嗣在《中国音乐》序的第一句便写道:“中国是一个与我们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它以一种独有的语言,独有的制度、习俗和礼仪而闻名。”这一句中的两个“peculiar”,《林文》将其翻译为“怪异的”,但是结合后文,笔者认为,将其翻译为“独有的”之意更为妥当。因为,从后文来看,阿里嗣虽然确实受到了文化进化论观念的影响:但在他每次描述中国音乐时,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阿里嗣一直在尝试采用更为中立的语气,尽可能客观地对中国社会音乐体系进行介绍与分析,尝试寻找中国音乐与其他中国文化概念的关联。
因此,笔者认为,处于进化论学派与比较音乐学学派两派之交的阿里嗣,其著作带有两面性的特点——他的文中同时具有进化论与比较音乐学两派的研究态度与理论特点,一方面,阿里嗣一直在尝试理解并分析中国音乐本身的概念、体系及其内部联系,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多个方面,尝试建立较为完整的音乐文化模型;另一方面,阿里嗣又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进行对比,将西方音乐的大小调体系、十二平均律列为“先进”文化的参照物,开始搜寻起中国音乐落后的原因来。从前后两者间的冲突中不难看出当时西方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者们在研究中的彷徨与抉择。
关于其比较音乐学特性的一面:这一点,可以从阿里嗣的中文引文中寻求解答,阿里嗣在其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文原文文献,并尝试向西方人转译、解释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的概念,以此寻找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乐记》中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和“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声和,声和故天地之和”两句,被阿里译为“音乐,据《乐记》记载,音乐由人心出发,心灵的和谐产生气息的和谐,气息的和谐产生的声音,而这声音则成为天地之间和谐的象征。”并在后文基于自己的理解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由此可见,阿里嗣的确是在尝试,在西方人可以理解的基础上,更明确的描述关于东方音乐文化的信息。
四、与钱德明《中国古今音乐考》的对比分析
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字若瑟,法国人。他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位大汉学家。他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成书于1776年,出版于1779年,是第一本系统性地介绍中国音乐的外国出版物。
《中国古今音乐考》与《中国音乐》这两本可以说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音乐的主要途径。两者前后间隔一百年,从同样的起点出发,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1.共同点
(1)主体内容
两者的主要内容都涉及到音乐理论与乐器。其中,关于音乐理论的部分,都涉及到了律学、记谱法、音乐美学思想、调式理论,并且都讨论到了和声的概念;而关于乐器的部分,都涉及到了乐器形制、演奏法以及分类法。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民族音乐学诞生之前的跨文化音乐研究中,学者们就已经有意识地整理归纳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特殊审美观念、独有音乐概念、调式理论等,这可以说为之后比较音乐学学派兴起打下了很好的理论框架。
(2)乐器分类法
两者都采用了八音对自己著述中的乐器进行分类。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参考了李光地的《古乐经传》,深受其中雅乐概念的影响。但阿里嗣经常参考类书中的资料,而类书自宋代开始,在对乐器整理分类时大多会按照演奏方法进行排序。阿里嗣在研究过程中,不可能看不出乐器的这种排列规律,却依旧选择用八音来进行分类,这种行为难免让人有些疑惑。这恐怕是因为阿里嗣认为相比于没有明确标准的演奏方法分类法,使用带有明文规定的八音分类法会更严谨。
2.差异
(1)两者在时代背景上的差异
《中国古今音乐考》和《中国音乐》,分别成书于鸦片战争之前和之后各约五十年的时间点,清政府经历了一个相当大的转折——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从平等转为弱势。这对文化方面来说同样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仅从西方人的研究专著来看,同样是中国音乐研究,研究态度却发生了转变,从《中国古今音乐考》中那种平等、尊重甚至可以说推崇,到《中国音乐》中那种经过简单比较便开始划分先进落后的草率。当然,其中也有可能是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西方文明经过一系列的蜕变与革新,变得更为自信。
(2)两者关于和声观念的差异
《中国古今音乐考》中认为:“假如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人是否早就具有了关于和声的概念,我敢十分肯定地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通晓和声学的民族,他们最广泛的吸取了这门科学的精华。那么又有人要问他们是如何吸取这门科学的精华的,我这样回答,他们的和声学是包括在一个总括万物的‘和弦’中的,它存在于物质力量之间、精神力量之间、政治力量之间,存在于构成其宗教信仰与政府机构的一切无形的事物之间。所谓声音的科学只不过是对于这一总括万物的和弦的展现形式”1,而在《中国音乐》中则认为:“中国音乐没有像我们那样的和声、和弦观念、对位法等等。它只是通过同时出发弦乐器如琴、瑟、琵琶的两根弦,使不同的音同时发声而已(四度、五度或者八度)。”2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音乐》中同样提到过和谐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和谐的本质存乎于天地人之间。”3但阿里嗣却并没有将之引入到和声的观念中。这一方面说明,当时西方大小调体系臻于完善,西方人的和声观念随之定型,除非阿里嗣阅读过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否则他很难向这个方面考虑;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当时文化进化论学派那种线性发展理论对研究者们的影响,他们当时将所有文明的发展前途归结于西方文明本身,因此,在接触新概念的时候都会与自己文化的相似概念先行比对一番,寻找其中的差异或者说所谓“缺陷”。
(3)两者关于结论的差异
钱德明关于中国音乐的结论可以总结为: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古老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艺术体系,这一体系与其他古文明存在或多或少相同之处,并沿袭至今。而阿里嗣关于中国音乐的结论则可以简略为:音律不准、乐器粗糙、旋律单调、没有大小调。仅从结论来看,似乎后者像进化论学派的观点,而前者则像是比较音乐学学派的观点。由此可见,西方学者们一直在通过调整视角、革新观念以促成其学术视野的拓展,就如同这两本专著一样。钱德明有时会将中国音乐看的过于神秘,反而有些迷失了方向,如其关于律吕的诞生,律吕与八卦的关系等;到了阿里嗣,虽然文化进化论使其将中国音乐视为一种落后的文化,但在其关于中国音乐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很多细节方面,阿里嗣的论述更为大胆,反而比钱德明更为具体、明确,如其关于律吕起源的论述,关于祭孔典礼的记录等等。
五、结语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很深切地感受到了跨文化研究的难处,英文的一词多义使笔者多次怀疑自己的理解是否有误,很多时候即使翻遍上下文也依然难以确定阿里嗣的真正态度,只好选一个相对中性的意思先行略过。但是,这也提醒了笔者做研究时的“融入”之难,即使如钱德明、阿里嗣那样的汉学家,在研究中国音乐时亦有各自的盲点:阿里嗣与“新法密率”失之交臂,钱德明则将理论与实践割裂——“新法秘律”一经创立便被束之高阁。若从当代民族音乐学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来看,他们都可算是自己时代的专家:阿里嗣在论述音律起源时,一方面他可以很好的将伶伦制律的相关引文很好的转译;而在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及时跳出当前的文化圈子,从外围角度切入,对律制的起源进行一系列的考证与分析,这种类似于“局内人”与“局外人”视角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钱德明与阿里斯的论述中还有很多,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著作仍然存在很多的盲点与缺憾。这也告诉我们,在研究中,我们不应该仅满足于现有的理论体系与框架,而是应该不断地寻求突破,进行理论创新,尽可能地去排除现有研究中的盲点、缺漏,寻求新的突破。
注释:
1.【法】钱德明著,叶灯译《中国古今音乐考》(续完),载《艺苑)(音乐版),1997年第3期, 第53-63页.
2.见Chinese Music,原文为:“The Chinese have nothing like our harmony,taken in the sense of chords,counterpoint.etc..The only collection of different,but simultaneous sounds recognised by them is that produced by playing two strings (at a distance of a fourth,a fifth,or an octave) together on the ch’in,the se,or the guitar.”见附录:《中国音乐》中本文所涉及部分的中英对照翻译,关于律吕.
3.见Chinese Music,原文为:“t is,say the Chinese,the essence of the harmony existing between heaven,earth,and man”见附录:《中国音乐》中本文所涉及部分的中英对照翻译,关于中国音乐.
——读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