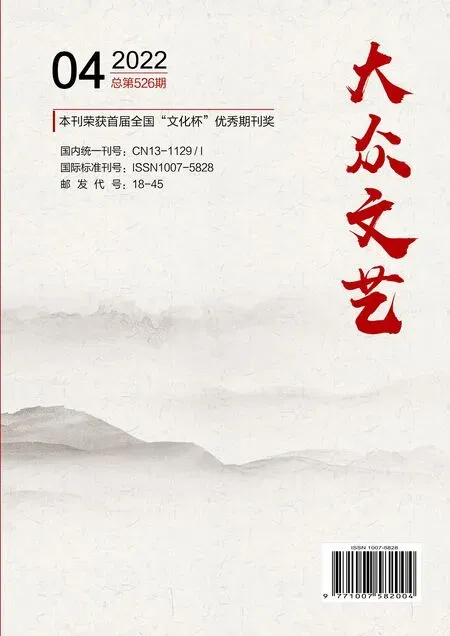绝望的抗争
——简析严歌苓小说中生存至上的女性价值观
(北京市东城区职工大学 100061)
旅美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素来以刻画女性形象见长。她的小说大都关注下层女性的疾苦,女性形象也以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居多,然而恰恰是小人物的世界才最能反映出人世间的疾苦,才能在最真实的生活之中映照出历史的真善美来。小人物的世界,没有贵族式的花前月下,笙箫互答;更没有历史人物的轰轰烈烈,光彩照人;更多的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哀嚎,以及对苦闷绝望生活的悲鸣。总的来看,严歌苓的小说中,女性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活着,或者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这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生存价值观。千百年来,中国的普通百姓早已熟悉了这样的生存价值观,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余华笔下的徐富贵,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底层生存者,他们朴素的愿望也仅仅是活着。与鲁迅、余华等人不同,严歌苓刻画出的是女版的阿Q、闰土和徐富贵,只不过她的书写带有着强烈的女性观照意识。但如果按照女权主义的标准来评论严歌苓的作品,又不太合适,因为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并没有强烈地追求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也没有大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她们只是蜷缩在世间的某一角落,努力地、认真地活着。
一、无知中无我地生存
无知中无我地生存,是严歌苓小说中一类女主人公形象的生存状态。这类女性,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也没有清晰的道德原则,要么在一种本能的驱使下去生活,要么在外力的拉动下被动地生活。这样的女性形象在严歌苓早期以文革为题材的作品中比较常见。
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就刻画了一位被政治强力改造的女性形象。“陶小童是文艺女兵,她有着自我的意识,喜欢写日记,特别是喜欢把朦胧的爱情写到日记里。但是在部队的生活里,她的日记被偷看了后,她就迎来了一系列生活问题,大家好像把她当成了另类,并且各方领导都来教育她,特别是团支书更是对她开展了严肃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谓的教育无非是让她放弃自我,树立集体之上的思想,正如约瑟夫·海勒所写的《二十二条军规》一样荒诞,个体的人承受着来自集体冠冕堂皇的压迫,却只有顺从。出于对政治的无知与妥协,陶小童最终通过艰难地改造成了一个积极的政治模范时,她才发现别人都是把那一套当作政治口号来宣传而已,事实上大家并没有那样去做,而她自己也在完成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失去了她喜欢的男人徐北方。就这样,陶小童在单纯的无知中,被高压的政治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符号。
在小说《天浴》中,“文秀作为一个知青刚被下放好牧场的时候,她十分珍爱自己的身子,但是,后来她为了回城过上更好的生活,居然盲信一位供销员的话,用自己的身子打开回城的门路。小说中的文秀显然是一个懵懂的姑娘,她并不能认清社会的真实面孔,凭着自己的身体资本进行无谓地牺牲,可悲的是她的牺牲换来的缺是回城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最后在绝望中死去。”小说《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是个十分典型的无知无我的存在。“小点儿没有什么文化,还曾经在文革中杀过人,出逃之后,她可以为了一顿饭与任何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她还为了获得姑父的照顾与姑父乱伦,她的蒙昧与淫邪可见一斑。”但是从小点儿的生活环境来看,不难理解,她的行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自己过得更好,哪怕是在道德上承受污点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她能做出那个时代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来。也是为了生存,小点儿放弃了自我,过上了无知无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她开始喜欢上那个骑兵连长的时候,她才认识到自己的灵魂早就污秽不堪了,最后作者借一把大火,让小点儿实现了人生灵魂的救赎。
二、自知中自我地生存
严歌苓的小说不仅描写了一群无知少女堕入无我深渊的悲剧故事,也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类坚强不屈的女性形象,她们可以超越世俗的限制,拥有完整的人格,对自己的生活有着明确的目标,并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大潮中,始终坚定自我,凭借一种对自我内心良知的把握,坚定地守住了自我的精神高地。她们虽然也面临着生存的考验,却凭借着她们高超的生活智慧,对残酷的现实生活给予有力的回击。她们是严歌苓笔下最有力量的女性。
小说《第九个寡妇》就塑造了一个王葡萄的形象。“王葡萄敢于忠实自己内心的想法,她不能像蔡琥珀那样可以牺牲自己的丈夫而救活一个八路军,而是很率真地选择了救自己的丈夫,这是对人性最忠诚的敬意,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政治压力,荣誉鼓励,就改变自己的心志。其次,王葡萄还敢于向不公正的政治行动发起抗议,她在得知公公孙怀清并没有死的时候,主动救助公公,并把公公藏在红薯窖里长达二十年之久。期间她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但是都被她巧妙地躲过去了。就算改革开放之后,她也为躲避计划生育的妇女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她一根筋地挑战着所有不合人性的政治运动,所要遵循的就是中国传统遗传下的民间潜规则。”再次,王葡萄在性的态度上也是开放的,她的开放并不代表她是淫荡的,她正视自己的生理需求,在性的伴侣上也有自己的选择,所以她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并不是一个道德完人,相反她是一个道德上有污点的人,这一点是与她所处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评论家张勇认为,“在王葡萄的身上体现了一定的现代性”,她超前的思想观念影响着她的生活,也给那个缺乏人性美的时代注入了一股暖流。
《小姨多鹤》中朱小环也属于有自知自我的女性形象。作者在这部作品里讲述了一个机智灵活的女性,“朱小环不能生育,张家就买来了多鹤作为儿媳,为张家传宗接代。朱小环并没有对此耿耿于怀,相反她放下个人恩怨,帮助丈夫和多鹤度过危险,对丈夫和多鹤生下的孩子也视如己出。”从她的身上显示出的是女性无限的包容性,朱小环也尊重传统,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尽管在别人眼中,她的行为似乎有点荒诞和不可思议,但是朱小环的所有行动都是在追求基本的人权,那就是活着,“凑合”活下去。她知道自己生活的不幸,在不幸中她并不是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她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相夫教子,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姐妹。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一家人过上和谐稳定的生活。正是在这个信仰中,朱小环在自知中,不改本色地努力生存着。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对待爱情的态度,也说明了田苏菲是一个有着自己明确爱情观的人,并有着坚定的信念。这样的女性活得很美,美在她们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在坚守中保持自我。“田苏菲在文工团里遇到了两个男人,一个是有钱有势的首长都汉,一个是政治干事欧阳萸,但是田苏菲就是喜欢欧阳萸,为了跟欧阳萸走到最后,她经受住了各种考验。首先是来自父母以及周围同事的压力,父母主张要她嫁给都汉,但是被她果断拒绝了。其次是欧阳萸生病,田苏菲不离不弃,悉心照顾。甚至是欧阳萸移情别恋,她都能忍受,并始终对欧阳萸投入高度的关怀,直到欧阳萸受到政治批判时,所有的跟随都离开了他,此时唯独有田苏菲始终如一地坚守在他身边,最后欧阳萸方才大梦初醒,被身边这个女性的定力所感动,与田苏菲共度余生。”这么疯狂的恋爱,正如史诗一般,波澜壮阔。田苏菲驾驶的恋爱之舟,由于她目的明确,内心坚定,最后成功到达了目的地。
在这类女性的形象中,无论她们的性格的好坏,品行的优劣。她们的身上都有着生活磨砺的痕迹,之所以她们没有被生存的不幸所击垮,是因为她们能在不幸中发现自己的生命本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一旦发现自己的生命本性的时候,就能始终如一的坚守,最终在平淡艰苦的生活中,打磨出了一个极富生命魅力的个体形象。当她们按照自己的生命本性所生活的时候,尽管会显得有点荒诞,但是总有一股强大的人性魅力,正是这股人性魅力才让她们身边的人受到感召,从而激发人们对她们进行应有的保护,让她们的所有坚守都有收获。可以说说这一类的女性形象是严歌苓笔下最幸运的人。
三、有知中超我地生存
在有知中超我地生存,指的是有一类女性,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存追求,但是经过努力却始终实现不了。最后在无奈中坦然面对,甚至是甘愿承受生活带来的各种不幸。这类女性形象往往被评论家们称为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和牺牲精神,甚至称其为地母精神,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类女性身上的悲剧色彩更为浓厚,她们所秉持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恰恰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另一种变形。这样的牺牲是对人性的自我放弃,在自我麻痹,并不是评论家们常说的“神性”。
小说《扶桑》中的扶桑是一个华人妓女。进入到美国这个异域国家,扶桑没有生存下去的技能,她唯一的资本就是自己的身体,为了生存下去,她只能被迫用自己的身体去做交易。这是一个底层女性堕落的开始,并没有人愿意靠卖笑度日。作为一个妓女,扶桑是一个弱势群体,她不能在任何交易中表现出反感来,在一种无奈的压迫下,扶桑最终坦然接受了所有施加在她身上的虐待和侮辱。“扶桑习惯了坐在格笼般的窗子里等待生意,习惯了赤裸着身子被人叫卖,在这些活动中,她表现的没有任何担忧和恐惧,相反,她总是露出心甘情愿的笑容。甚至当她被一群反华暴徒强暴时,她也不反抗,”“一律地包容,就像礁石包容汹涌的海浪一样。”人们往往习惯把扶桑神化了,却没有在这种神化的光环背后读出她绝望的内心世界。因此,可能就有人得出结论说,她的笑容是经常挂在脸上的,有人可能会说她是笑对生活。这般言论似乎有点言过了。扶桑的不反抗,是因为她没有反抗的能力,要她拿什么去反抗呢?放弃了生存吗?显然不是这样。只有默默地容忍才能维持生存,眼看着这种容忍即将成为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扶桑的内心是一种绝望,也正是这种绝望才让她表现得什么都无所谓了,反正都得忍受,甘心认命地忍受总要好过屈辱地忍受。这样的生存价值观是不值得提倡的,鲁迅曾经把阿Q写进小说,批判的就是这种精神鸦片,扶桑的精神胜利甚至连阿Q的精神胜利法都比不上,至少阿Q还知道在精神上反抗,而扶桑已经把自己反抗的意识掐灭了。
在严歌苓小说中,这类女性形象还出现在了《陆犯焉识》、《小顾艳情》等多部作品中。《陆犯焉识》中的冯婉喻和《小顾艳情》中的小顾都因为爱,做出了足够的容忍与牺牲。冯婉喻为了救出陆焉识,委身于戴同志,实际上是一种性交易。小顾为了救杨麦也出卖了自己的身子。这是生活在底层社会中,女性最无助的行为。她们没有权利,没有金钱,惟一有的就是自己的身体。但是与金钱权利相比,出卖身体是最让人感到耻辱的,也是最不明智的。这一点可以从冯婉喻和小顾的悲惨结局中得到印证。
经过对几部作品中此类女主人公的身份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她们的行为不代表她们是地母,相反,凸显的是她们的绝望与无助,这是一群最值得同情的女性。
四、小结
严歌苓的小说,反映不同时代的女性生活状态。在时代大潮的洗涤下,为了生存下去或者是更好地生存下去是严歌苓小说中女性的共识。严歌苓试图用一种神性来升华她笔下的女性,即一种无私奉献的地母精神。但是这终究是一种徒劳,真正的生活让那些地母都沦为了悲剧的主角。因此,唯有保持真正完整的人性,才是疗救女性的有效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