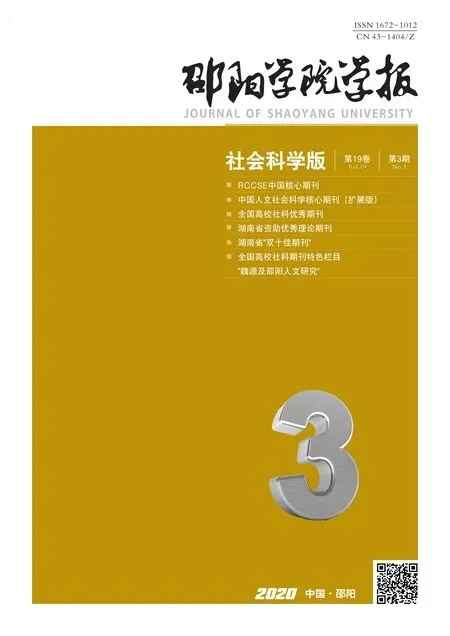南宋武冈军的政治与社会之考察
——以牟巘《陵阳集》为中心
唐春生, 杨 薇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宋时的武冈县,地处荆湖南路的西南。徽宗崇宁五年(1106),朝廷以其“疆境阔,户口繁”,由县改设为军,目的是为了控御武冈周边的少数民族,即所谓“控制溪洞,弹压诸蛮”。同时,将绥宁、临冈二县归武冈军统辖。绍兴二十五年(1155),又新设新宁县,也并入武冈军。后废临冈。所以,武冈军辖县三:武冈县(军治所在地)、绥宁县、新宁县[1]2163-2165,辖境包括现在的武冈市、洞口县、城步县、绥宁县,以及邵阳、隆回、通道三县的一部分。
《陵阳集》的作者是蜀地井研人牟巘(1227—1311)。其父牟子才在成都落入元军之手后,“尽室东下”[2]12355。淳祐七年(1247),牟子才因言事忤宰相郑清之而退居吴兴寓第,他“以直道事理宗,为时名臣”,与其往来的,都是“一时人望”[3]879。
牟巘的仕履,文献记载极为有限。《宋元学案》称其“以父荫累历浙东提刑、大理少卿”[4]2689。《全元文》卷三三二称其官至大理少卿、浙东提刑[5]491。《全宋诗》卷三五一○则称其“以父荫入仕,曾为浙东提刑。理宗朝,累官大理少卿,以忤贾似道去官”[6]41915。以上文献均没有提及其知武冈军。《全宋文》卷八二二二称其曾知武冈军,又为浙东提刑;历大理正、侍右郎中,累官朝奉大夫、大理少卿[7]173。据牟巘《陵阳集》,他确曾做过武冈的知军。《陵阳集》提到的他在知军任上的年份有“丁卯岁(咸淳三年,1267)”[5]519(1)本文所引牟氏诗文,是从牟巘《陵阳集》析出、收入《全宋诗》《全元文》《全宋词》的作品。“戊辰(咸淳四年,1268)”[5]497“己巳秋”(咸淳五年,1269)”[6]41971“咸淳八年(1272)”[5]499。武冈籍蒙元史学家、内蒙古大学教授周清澍先生认为牟巘在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就到武冈来了。他之前的武冈知军是景定三年(1262)六月的赵希迈和景定末年(1264)至咸淳二年(1266)的蜀中同乡杨巽,牟氏大约在度宗咸淳三年(1267)至八年(1272)在武冈知军任上[8](2)周先生对赵氏知武冈军的具体年代失考。据《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都梁志》,赵希迈是景定三年(1262)六月十八日赴任武冈知军的。。牟巘在武冈工作、生活了大约十年,时间并不短。离开武冈后,他就任的应是浙东提刑,当为咸淳九年(1273)后,之后又再任大理少卿(3)李之亮据《宋诗纪事》卷七六:“官至大理少卿。宋亡,时献之(即牟巘)已退,不任事。”系其任大理少卿的时间为咸淳九年(1273)。见氏著《宋代京朝官通考》(5),巴蜀书社,2003年,第246页。。据戴表元贺牟氏七十而作于元大德三年(1299)的《陵阳牟氏寿席诗序》称,“自还会稽使者节,食贫茹辛,卧苕溪上二十余年”[9]153,可见其于度宗朝末期还曾被朝廷用为会稽郡守。当时因时局艰危,他可能没有赴任。
由上考述可见,牟巘一生为官时间最长、也最有可能见其治理能力的是在武冈知军任上。学界对牟巘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唯陈彦池的华东师大硕士学位论文《牟巘〈陵阳集〉研究》,该文主要从牟氏交游、诗文角度入手,但几乎没有涉及其在武冈军上的事[10]。乡贤周清澍教授作有《从牟巘〈陵阳集〉看南宋地方官》[8],对牟氏在武冈为官的情形考订甚详。笔者拟在此基础上再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不堪重负:大礼与圣节之银钱
牟巘在其文集中提到的圣节有乾会节、寿崇节:乾会节,是度宗皇帝的生日(四月初九日),寿崇节是谢太后的生日(四月初八日)。这两个节日,由于只隔一天,两节叠加,很是隆重。林希逸《潮州开元寺法堂记》提到了咸淳五年(1269)潮州人庆贺乾会节、寿崇节的场面:“乾会、寿崇节礼行,郡之簪缨缁黄咸集,驺隶纵横,肩袂交午,喧声如虚市。”[11]22元人佚名氏《三朝野史》:“四月初八日,谢太后寿崇节,初九日,度宗乾会节。贾似道命司封郎中黄蜕作致语,中有一联云:‘圣母神子,万寿无疆,亦万寿无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满朝缙绅皆喜之。”[12]469在行在杭州,咸淳元年(1265)四月的乾会节、寿崇节曾“免征临安官私房僦地钱”和“免在京征商三月”[13]894,其目的是为了增添喜庆祥和的气氛。
举国同庆的圣节(帝王、皇后生日)和大的典礼(如明堂大礼),按例是要进贡的。高宗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中书舍人王居正说:“生辰及大礼进奉,乃是臣子用致区区倾祝飨上之诚,初非朝廷取于百姓之物。”[14]1549但在实际财政生活中却走样变形。在潮州,天申节(高宗生日)进奉银、大礼年分银,一度也是“白科民户以足其数,既不支与本钱,其交收糜费且半于正数”[15]2682。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九月,赦文曰:“诸路监司并二广州郡,合发进奉圣节及大礼银绢,在法合以系省钱收买。今闻诸处科抑民间买纳,委是违戾。”[16]7942也就是说“进奉圣节及大礼银绢”原本应由地方留用的钱物(系省钱)来承担,但最终却演变成向百姓的“科抑(定额摊派)”。
武冈给外来主政者的印象是“山广田稀,小歉即赈贷”[15]2286“山城如斗大”[17]2142。曾任武冈军通判的李刘说:“盖一岁止万石之租,而四郊无百金之子。”[18]157财政不能自给,缺额有一半要靠永州、邵州补给,可有时这两州并不能如数调拨。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武冈军知军的汪义和上书朝廷,请求将邵、永二州配拨给武冈的财物充作武冈缴付朝廷的赋税,武冈应缴的赋税则留作自用,将缴纳赋税的皮球踢给了永、邵二州,所幸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在他的努力下,武冈的财计始“日益充衍”[19]391-392(4)李刘《通判到任谢参政启》也说武冈“岁租仰于永、邵”,详《全宋文》,第317册,第157页。。
尽管财政状况不佳,当圣节、大礼来临时,武冈自然也要奉礼庆贺。知武冈军的牟巘作有庆贺二表,也献了寿礼,其《乾会节进银状》称准备了“上件银品”[5]495。虽说武冈军所辖除武冈县外,还有绥宁、新宁等地,但经济中心只是武冈一县。南宋时期,县级财政艰难,县令至有“日坐汤火涂炭而每不聊生”之说[16]8368。武冈军财政上所依赖的治所武冈县财力本身有限,加上要平定“妖寇”,“调发官军民兵”,致“为费不赀”[5]498。在三、四月青黄不接之际,武冈军要完成进贡任务,这无疑是一沉重的负担,牟巘《创大礼例库申省状》[5]498说:
本军每遇大礼,例进奉银二千二百十一两一钱四分,随纲别进奉银三百八十四两五钱二分五厘。所有价钱,系照指挥截拨,及刬刷杂色窠名应副外,尚且不敷。旧来弊例,或敷之质库墟户,或敷之军县吏胥,甚至有告讦献助之名。本非得已,而吏胥缘奸,重贻民害。质库墟户之往往停闭,以避科买。市井萧然,日甚一日。
这大礼是有指标的(指挥截拨):例进奉银加上别进奉银共计二千六百余两。征收正税之外的“刬刷杂色窠名”这类杂税,武冈军就已经很困难;再摊上大礼,武冈军财力更是雪上加霜,只好摊派:“敷之质库墟户,或敷之军县吏胥”,对象有当铺、商户乃至胥吏,就连“告讦献助”这样丑陋的手段也曾用过。
武冈的经济状况,或许从武冈知军李知新理宗绍定五年(1232)所作的《武冈州创置社仓省札》[15]2286-2287可见一斑:
本军自宝庆三年,有知军吕朝散劝谕到在城上户,每年蓄积米二千石,至三四月青黄不交之际,即以市价斟酌量行裁减出粜。……照得本军上户绝少,劝到积米之家,多者止数石,少者至五七斗,事出勉强,颇为费力。兼其间多有田产退落、户头死亡之家,官司即有名籍,卒难消豁。是以两年之间,人户多有以此陈词者,知新只得与之斟量减免,是以今岁所存,止有一千四百来石。知新又劝谕令其自相推陈产业增进之家,填补元额,终无肯相纠举者。兼当来吕知军创始之初,官司先谕备米七百石为之倡率,自后因循即不曾有此米。知新到任之后,自绍定四年撙节浮费,至今年六月前后共籴米三千石。
此记录了武冈军社仓的粮食来源,宝庆三年(1227)的吕姓知军劝谕上等户筹措。但是军内上等户极为有限,即便是所谓的上等户,所筹得的也只是“多者止数石,少者至五七斗”。同时,由于出现“田产退落、户头死亡”的新情况,至李知新做知军时只得由每年原定蓄积额的二千石减至一千四百石。这亏缺的六百石,知军李知新的办法之一是劝谕上等户“自相推陈产业增进之家”,彼此互揭家产的多寡,然而“终无肯相纠举者”。这一做法或是牟巘上文提及的“告讦献助”。
牟巘《创大礼例库申省状》[5]498-499又说:
某曩岁抵军,询知此病应词诉,并不许告讦献助,而他未能区处也。……某不敢以一镪一粒科扰百姓,自行那融,应办皆出于常年调度之外,郡计愈见单窘。无可措画,遂痛行樽节浮费及供给等钱,铢积寸累,计见钱一万贯者,创置大礼银纲贴助解库,一坐月收微息,专一桩管,不许移动。如遇大礼年分,收买两项进奉银两,除久例截拨刬刷钱外,将本军三年所积息钱支出,添助上件银两价钱。咸淳八年,明堂大礼为始,大约可增钱六千四百余贯者。
据《宋会要》称大礼银是三年一次[16]6627,这一点与牟巘所说如遇大礼年,“将本军三年所积息钱支出,添助上件银两价钱”,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这段文字可见宋地方财政的捉襟见肘。牟巘筹措大礼时,在他做知军之初,只是革除了“告讦献助”这一做法,其他也无力袪除。与他的前任李知新一样,牟巘也采取节流的办法,“樽节浮费及供给等钱”,计得钱一万贯,并将这笔钱存入当铺(解库)。所得的微薄利息,不许挪用。牟巘说,这样就能“稍革科配、献助等弊,田闾之间,生意初回”[5]499,可见大礼所费对武冈民生影响之巨。大礼库,属武冈军资库之一种,得受监司的点检[20]61。牟巘的申省状,正说明当时军县一级的财政权在中央,节流开源建大礼例库还得向朝廷申报。
与牟巘设法轻减民众负担的种种努力形成对比的是武冈军某些官员的贪得无厌、敛财自肥。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知武冈军李若朴,被人指为“贪污刻剥”被罢免[21]3313。《宋会要》对在武冈任过职的贪墨官员有过记述:光宗绍熙三年(1192)八月十三日,武冈军签判薛大圭因“其凌上忽下,贪财妄取”而被罢免[16]5007。宁宗庆元六年(1200)五月三十日,新知武冈军赵公砬也因为“志趣贪污”而被罢免。时人云:“今武冈小垒,岂堪诛求!”[16]5045嘉定八年(1215)八月,新知武冈军丁大同因“痴騃贪黩,资历亦未应格”被罢免[16]5075。嘉定十二年(1219)正月二十九日,知武冈军林拱因侍御史李楠称“其居官则流毒郡邑,在家则贻害乡闾”而被罢免[16]5083。如以知军来看,18年之内有三任知军因贪渎不法而被罢免,他们对当地政治生态的破坏之严重可想而知。
二、武冈:极边之地(5)“极边之地”,出自武冈知军赵善谷之口。详《宋史》卷494《蛮夷传二》。的设寨置县
武冈军地理位置重要,“西通融桂,北控沅靖,南连全永,家与溪洞相联”[5]497。其境内蛮猺众多,有“溪峒七百八十余所”[22]14191-14192。两宋时期,武冈军境内的少数民族不遵王度,频生变乱。与蛮猺相邻的武冈军境内的汉人,为了逃避南宋统治者的“征敛百出”,选择抵抗的方式便是“客依蛮峒,听其繇役”,其结果是“官失其税,蛮獠日强”[22]14187。真德秀说:“武冈为郡,本蛮猺故地,风俗愚悍,不知逆顺。”[23]3复杂的民族关系,致自北宋以来,就变乱连连。仁宗嘉祐三年(1058)六月,邵州武冈杨昌透造反,宋廷派潘夙权任荆湖北路转运使,驻军赀木寨,统兵平叛,攻下了蛮夷团峒九十余处[24]4514,“并以所领十余州永输租赋”[25]341。仁宗朝,德州人刘禹权知邵州武冈县,其时“溪洞蛮蜂出,烧民积聚”,赖刘氏“晓以祸福”得以平定[26]498。哲宗元祐四年(1089),关峡、城步、真良等团峒作乱,宋廷派兵进讨,酋首杨晟进等四十三人投降[16]9893。宣和年间,也发生了武冈洞獠仇杀之事[27]479。
南宋时,武冈军境内的少数民族变乱仍不绝于史籍。绍兴九年(1139),武冈洞首阳三天反叛,“势摇荆湖”,朝廷用谢祖信知武冈军,“遂擒三天,破其巢穴”[28]2424。对武冈军地方政权危害最大的是杨再兴的叛乱:持续时间长,从南宋初直至绍兴二十四年(1154),才彻底荡平。史载:自高宗建炎年间开始,“湖南猺人杨再兴父子占夺民田,且招叛亡添寨栅,意欲作过。”[29]374绍兴四年(1134)十月,因“杨再兴连年作乱”,湖南安抚司遣统制官吴锡率部征讨,“大破贼徒,获再兴之二孙,得良民被掠者甚众”[14]1525。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直秘阁、知潭州刘昉称“武冈军猺人杨再兴父子,自建炎中侵占省地几二十年”。获朝廷准允,他成功地招降了杨再兴,杨氏归“还省地及民田共六十余亩”[28]2913。绍兴二十四年(1154)三月,杨再兴因“抄掠不已”[21]3154,且“寇武冈、全、永、邵数州”,朝廷遣大军生擒之[30]4899。至此,多年来影响武冈军及周边地区社会秩序安定的势力终于被根除。
此后,武冈军虽然再没发生像杨再兴那么有影响的变乱,但影响溪峒之地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孝宗乾道八年(1172)夏秋之交,武冈“猺人”“凭恃溪谷,创立楼橹”[31]285。孝宗淳熙初,“有武冈军客人郭三逃入洞中,诱引小夷姚明教据有一洞田产,不遵王度”[32]42。
武冈军不仅要应对本土“猺人”的变乱,还要防范来自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威胁。光宗绍熙三年(1192),与武冈军接壤的辰州(治所在今沅陵县)境内的溆浦县少数民数造反。知军汪义和大修武备,且让乱贼自首,起事的少数民族最终没有入境武冈[19]391-392。杨再兴作乱时,甚至有从其他地方过来的力量参与其中,像“四方亡命”与“游手不逞”这两类人,以及“强盗之贷命者”,通过全州、永州东安、静江府兴安县及邵州其他方渗透入杨再兴所控制的势力范围[16]9899-9900。
杨再兴乱后,为了更好地管控“猺人”,绍兴二十五年(1155)四月,宋廷在武冈军水头江北岸新设一县,“以新宁为名,拨扶阳、恭和、宣义、零阳四乡隶之”。同年四月十一日,诏令武冈军于旧治复置绥宁县[16]9397。
除新设县份外,宋廷还在要道隘口设寨控扼。牟巘《武冈置靖安寨申省状》:“旧来节次,于要害去处置立堡寨,控扼防把,无虑十五六,而后徭省各安。”[5]497《明一统志》卷六三《宝庆府》:“宋十五寨,俱在邵阳县。宋初,蛮寇钞掠邵阳,命将讨平,置十五寨守之,管土丁、弩手。其寨曰武冈、真田、白沙、水竹、界冈、三堂、罗尾、盆溪、塘儿、古限、查木、新兴、安定、三门、硖口。今遗址俱存。”[27]347所记寨堡的数量与牟巘的说法是一致的。不过,宋元时期所修史籍与以上说法有所不同,只是将武冈军说成了邵阳县,这是由于明代行政区划调整的缘故,十五寨其时已改隶邵阳县了。部分寨堡情况见表1。
武阳、关峡二寨的设立,是北宋熙宁年间开梅山的结果。在章惇与湖南提举常平仓蔡奕筹划下,对“猺人”采取“使为土民,口授其田,略为贷助,使业其生,建邑置吏,使知有政”的办法,“招怀邵之武冈峒蛮三百余族,户数万,岁输米以万计”,设武阳、关峡二寨[33]249。城步、白沙二寨也应是因应开梅山这一历史背景下设立的。
南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后,原有的寨子或存或废,又新增了一部分。据《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武冈军计有十寨,即三门、石查、真良、岳溪、临口、关峡、黄石、新宁(绍兴二十五年,即1155年升为县)、绥宁、永和。同时的永州有三寨,宝庆三寨、郴州五寨、道州四寨、全州四寨。荆湖南路共二十九寨,武冈军就占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五[34]4793-4794,也可见宋廷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力的进一步加强。
每个寨子的兵力有多少人呢?据《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九之二十四,至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武阳寨有兵三百人,有人建议朝廷将这三百人平分在武阳、岳溪、绥宁三个寨子上,各以一百人为限额。从下文所引牟巘的奏状看,一百人的员额,应是标配。官府采纳了这一建议。
上文牟巘提到武冈军境内所设的十五六个寨堡收到了“徭省各安”的效果。军治所在地的武冈县虽“无溪洞”(无少数民族),但由于县境广阔,统治力有所不及的地方并不安分,牟巘主张也应设寨。其《武冈置靖安寨申省状》[5]497-498又说:
武冈一邑,虽地无溪洞,而紫阳乡都分最阔,去军县且二百余里。其俗顽犷,又与永邵接境,往往恶少之所出没,乃无巡寨以为弹压。戊辰(咸淳四年,1268)妖寇相梃啸聚,无所控制,几至猖獗。本军随宜招捕,仰赖圣朝威德,随得弭宁。……某虽侥幸替去,然不敢不为此邦长久之虑。昨差官相度下育渡,乃紫阳乡要害之地。遂行创立寨屋三十余间,及寨官衙守等,皆是本军自行措办,一毫不以扰民,并已齐备了毕。今来欲以靖安寨为名,招刺寨军一百人,驻扎防守。见将标钉到,已断妖贼周千四等及其余妖徒,田产尽行籍入本寨,充养军之费。或尚支用不敷,在本军随时那融,应付其契。勘得本官旧有武阳寨监押一员,并同管辖一员,阙官岁久,欲乞公朝敷奏,将上件二阙省罢,特置知靖安寨兼巡检一员,专任武冈县紫阳、长溪两乡防把之责。
据浙江诸暨出土的《宋武冈县令杨应元墓志铭》:“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喻,又不可以武胁。招乡之以众向者,与之言道:‘爰素宽误,兹蠢蠢挟妖澒洞,令去即安。’”“婆婆鬼”翻然悔艾,按堵如故。“绣使张公性之、黉堂杨公巽、牟公巘、监州公孙止,列剡于朝。”[35]
《宝庆府志》卷一○三《金石一》“宋乔奣诗刻”也记载了理宗咸淳四年牟巘等人平定“猺人”叛乱一事,文称:道州人何扬祖题诗:“石室何年霹雳开,曾听绣斧凯歌回。讵知二百余年后,复有旌旗笳鼓来。”末题云:“咸淳戊辰(即咸淳四年,1268)夏五月,猺叛。六月,舂陵何扬祖偕棘阳芮大椿、侯城庞翔,奉郡侯牟(即牟巘)招捕。九月,师次白仓,游乔奣。”[36]1547,1558
牟巘提到的紫阳乡,今属隆回、邵阳县二地。妖寇周千四等人,应是所谓的“婆婆鬼”。从上引三则材料来看,咸淳四年(1268)五六月间发生的“猺人”叛乱,当知军牟巘率兵进讨时,是通过派人劝说,以招降手段平定变乱的,但过程并不轻松,因为事变一直延续到了九月。为杜绝后患,牟巘才请求在紫阳乡设立靖安寨,以达紫阳和长溪两乡长治久安之目的。设寨堡的经费主要是通过没收周千四等人的财产获得。拟招收寨兵一百人,委任知寨官和巡检一员,这些都是地方无力解决的,所以他只好向朝廷上奏状。
三、祈神求雨与武冈军的地方信仰
在以农为本的帝制中国,关心农事成为地方官员重要的政治生活之一。牟巘知武冈军时,像大多数官员一样在劝农日也劝农,作有《劭农日漫成》,他兴奋地说道:“且喜畦秧三日雨,莫愁花信几番风。”[6]41948不幸的是,咸淳五年(1269)的六七月间,武冈军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牟氏又遇上了新挑战。有人请其为画梅题诗,他说“今年四野赤如赭,安有吟情到此花”[6]41972,心情不佳,无心作诗。牟巘还作有七言绝句七首,诗题很长:《己巳秋七月,不雨,人心焦然。乃戊午斋宿,致城隍、清源、渠渡、龙君、鳌山五神于州宅以祷。始至,雨洗尘。自是间微雨,辄随止。旱气转深,苗且就槁,要神弗获。某忧惧不知所出。越癸亥日亭午,率郡僚吏申祷于庭,未移顷,雨大挚,旄穉呼舞,皆曰神之赐也。某既拜贶,又明日以神归,念无为神报者,乃作送神之诗七章,以侈神功,且又以祈焉》[6]41971,诗题大意是:咸淳五年(1269)七月,大旱无雨,人们焦虑不堪。七月十四(戊午)日,牟巘便祈求城隍、清源、渠渡、龙君、鳌山五神降雨,但只是下了点微雨,丝毫无助于旱情的缓解。眼瞅着稻苗将枯,又于癸亥(十九)日率领同僚祭神,没想到下了大雨。老人小孩高兴得手舞足蹈。作者便写了这一组诗以送神。兹摘录二首以见其时大旱的情景:
休休早稻已焦卷,晩稻揺风更可怜。枯尽百源无一滴,老龙何处卷云眠。
几度看云眼欲穿,不应气数总关天。去年兵又今年旱,守也于民自寡缘。

牟巘通过祭神祈雨以抗旱魔。牟巘所祭的城隍、清源、渠渡、龙君、鳌山五神,都有神力可致雨。城隍,“宋以来其祀遍天下”[37]406,本是城市的保护神,但也有致雨的神效。太宗雍熙二年(985)临海县“自春徂夏,烁石流金,离离旱苗,燋灼殆尽”。知县王子舆率同僚祷曰:“幸雨如绳注,则庙必鼎新。”数天后果然下了大雨。王氏也兑现了诺言,重建了城隍庙[38]186-187。再如哲宗朝的元祐五年(1090),东莞曾“一月不雨”,县令李岩祈祷于城隍庙,大雨“如期而应”[39]196。南宋时,行在临安的城隍庙,“丰凶水旱”,“祈而必应”[40]182。牟巘敬祭武冈的城隍庙,当然也希望其能带来甘霖。
渠渡庙供奉的是武冈“土神”。祠庙原在天尊岭上,据传百姓祠祭畏其高峻,神灵遂从人愿移至山脚。其神奇在宋人叶梦鼎的《渠渡庙记》有详细的记载:
景定癸亥(四年,1263),郡守赵希迈属岁旱,遣武冈令林昂、孙鼎舁神至郡城以祷,赵迎之北阙,意颇懈,神怒掷圭,且舁之弗胜。赵悔谢,雨乃随至。景定甲子(五年,1264)四月,郡守姚岩下车初,梦有渠秀才者来。次日,吏告谒神祠。姚曰:“畴昔之梦渠秀才者,此也。”于是亟往谒焉。祠旁有溪水,冲胁庭中,有树将仆,姚曰:“水冲则风水不便,树仆则庙貌不安,神如有灵,去其树,移其江!”言讫而退。是夕,大风雷雨,若有人马金鼓之声,逮晓,已决江水,左流而迂绕于祠之东侧,拔庭树置垣外数十步,祠宇寸瓦无恙。
渠渡庙“旱潦祷即应”,景定四年(1263)化解了武冈的旱情;景定五年(1264),又随人愿“去树移江”[41]337。因此,宋时封其神为灵济侯[27]346。
牟巘提到的龙君神庙,即昭潭庙。《明一统志》卷六三《宝庆府》:“昭潭庙,在武冈州城南五里古山之麓,祀昭潭龙神。”[27]346《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八《宝庆府》称古山“上有瀑布,下有深潭,相传龙潜其中”[42]426。鳌山神祠,据周清澍先生考述,神为李姓,秦时已显灵异,民间有传说他去修过长城[8]。所以牟巘说:“惟鳌山祠最古。”[5]758徽宗政和元年(1111)三月被朝廷赐庙额“敦济”,政和六年(1116)四月又封为广应侯[16]1041。其地位的一步步提高,当与其神力灵验有关。大约具有“旱祷即应”的神力,至《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八《宝庆府》就明确说城内的鳌山庙“俯瞰渠水,下有龙湫”[42]426。
从牟巘所祭的五神来看,以上四神是武冈原本就有的,说明本地神庙的影响力在时人的宗教生活中的地位之高。但牟氏所祭的也有一外来神,即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据宋人周虎《清源妙道真君庙记》,所祭祀的是隋代赵昱,此人随李珏隐居于成都附近的青城山,“隋炀帝奇其才,起为嘉州牧”。犍为有龙害民,赵昱“出奇策以除,郡人神之”。隋末不知所终。“江水泛溢,防断不补,蜀人见王(即赵昱)青雾中乘白马超波而过,水患遂平。民德之,建庙灌口,以昭其异。唐太宗时,上不豫,祷于王,疾遂瘳,诏封神通大将军。明皇幸蜀,护跸有灵,加封赤城王。”真宗时,因有功于张咏平蜀,改封清源妙道真君[43]379-380。《梦梁录》卷一四:“二郎神即清源妙道真君”[40]188,将经历多在蜀地的赵昱与二郎神(秦蜀守李冰次子)牵扯在一起,可能与其被“建庙灌口”有关。清人钱大昕也指出清源庙就是“俗称的二郎神”[44]477。这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信仰在南宋绍兴年间已扩散至杭州。其神力除“平疫疠,弭盗贼”外,还可“降丰年,除水旱”[43]379-380。牟巘《祭二郎祝文》称二郎神(清源妙道真君)可“使蜀人有灌溉之利,而无干旱之忧”,他自然希望“神而移其惠于蜀者,用惠我千里”,武冈军因而能“大沛甘泽,俾有丰岁”[5]757。
牟巘加以祠祭的二郎神与梓潼神、射洪神,被称为蜀中三大神;对后面两神,牟巘《陵阳集》中也有祭祀之文。此外,《陵阳集》中还有祭祀蜀侯蚕丛之祝文。钱大昕称蜀地三大神“皆盛于宋时”[44]477,所以武冈军有此信仰并不奇怪。周清澍先生认为这可能与牟巘为蜀人的身份有关[8]。扩散至武冈军的蜀地信仰,可能不是牟巘一人努力的结果。在牟巘之前,蜀人杨巽景定五年至咸淳二年(1264—1266)出任知军,牟巘为知军时,同样是蜀人的公孙止出任其副手——通判[8]。又据《跋杜隐君墓铭》,牟氏知武冈军时,还有一杜姓眉山人为李曹掾[5]599。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在宋代,当士人出任某一地方的主官时,其里籍相同的老乡有可能前来投奔并为其属下。杨、牟、公孙、杜氏四人极有可能都推动过蜀中信仰在地化(武冈军)的工作。
牟巘担心旱情失控会生乱:“苗且槁死,人心皇皇”[5]756,“不得食,民将流亡”[5]757。饥馑有可能导致强人行劫掠等一系列社会不安定的问题。宁宗嘉泰三年(1203)正月,曾任湖南安抚使的赵彦励就说过湖南九郡与溪洞相接,如果有“饥馑”,可能会发生民变[16]9901。问题还不限于此,如果衣食有虞,甚至有可能激起兵乱。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嘉定十七年(1224)(6)真德秀是嘉定十七年(1224)九月初九日,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兼知潭州(今长沙),主政湖南的,当年秋天就赴临安为直学士院。这次军变,就发生在1224年的9月至10月初。,武冈军禁军蒋宗“借为众之名”倡乱,军卒“以为我辈衣粮得免减刻”,“一呼之间,从者千计,诸营为空”[23]3。倡乱之日,劫掠百姓三十余家[45]268。不惟城内,城外二十里的民户家财也遭劫掠,“打荡屋宇,一番惊扰”[45]399。这种兵乱历史,作为知军的牟巘不会不了解。我们知道,宋代州军的经费支出,主要是官吏军兵的廪禄,其中尤以军俸军饷负担为重[20]54。当因旱灾招致出现饥荒而难以支付军俸军饷的严重后果,就不只是民变那么简单了,军卒也可能会闹事。此其一。其二,在灾害来临时,往往也是民间宗教力量最为活跃之时。真德秀曾说湘人有“巫觋兴妖”、尚鬼的习俗[23]36-37,妆扮成超自然、具有特殊力量的巫妖,有可能对政治与社会秩序构成危害。高宗绍兴前期在洞庭湖作乱的钟相就是邵阳人,其“善咒水治病,好作神语,人呼为钟颠,又称钟老爷”[46]1411,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上文所说的准备谋逆的妖寇人称“婆婆鬼”,其所借助的应是巫术。巫师、巫术的活动主要是围绕祠神信仰展开的[47]10,崇祀祠神很有可能被人所利用。光宗时,武冈配隶王文彬等六人就想利用“坊市祠神之会相挻为变”,幸赖知军洪秘“捕尽得之,以尸诸市”,才没有酿成大乱[48]112。作为知军,牟巘的祈神求雨,当然是官府对民生困境高度重视的表现,但也可能是他想把祭祀之事向着官府掌控的方向引导,变民间私祀为官民共祀,从而实现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武冈的地方信仰,除上面提及的外,还有一些祠庙。安远庙,是纪念一个叫刘锡的人,他死于熙宁二年(1069)征讨叛乱者的王事中,被封为上将军,人们“立庙祀之”。淳祐年间又建有武侯庙,祭祀蜀汉诸葛亮[49]538。宁宗嘉定五年(1212)冬,史弥宁知武冈军,修葺军学学舍,并建濂溪(周敦颐)祠与二程先生(程颐、程颢)祠,“俾学者知所宗焉”[50]439。像武侯庙、濂溪祠、二程先生祠,实则是儒家精英文化的物质化。武冈军地方当局,试图使儒家精英文化社会化,从而达到政权安稳之目的。
四、下考:知军牟巘满肚子的委屈
对武冈军这样的所谓荒服之地,其主官政绩好坏的考课,主要看其任上是否做到了“省民峒丁,各守条约,不相侵犯”[51]1727。从上文所述来看,牟巘在武冈知军的岗位上是竭心尽力的。然而在上级主官考课时,他却只收获了下考。从其所作的文字来看,其内心是有起伏的。《谢书考启》[5]531:
……初非孑孑之姿,徒有区区之志。读抚字劳心之传,则窃慕唐之高贤;诵《中和》《乐职》之诗,则思发汉之盛德。中更纷纠,遂堕谬悠。厥既血指而汗颜,何能为役;不适医创而剜肉,祇复可怜。怅始愿之浸乖,冀后图之是勉。阅时云久,课效益疏。而况兵旱相仍,民尤寡遂。疾病居半,吏率多偷。虽复竭韈线以为长,强铅刀而使割,竟无强诩之效,自见当时,惟有凋瘵之余,以待来者。居然不武,何以自文。薇亦柔,薇亦刚,荐成岁律;瓜而往,瓜而代,已迫戍期。然且监牧不加诃,士民不推去。再获书于下考,庶遂保于末涂。永惟此恩,讵无其自。某官端委廊庙,砥砺臣工。
大意是:我没有特别出众的才干,志向也不宏大,但仰慕唐尧、两汉时的高贤硕德,做武冈知军,不愿欺压百姓,强取民脂。自己体弱多病,而属吏又多浅薄苟且之辈,不幸的是又兵旱相继,虽然竭尽全力,奈何才疏力薄,政绩平平。幸有司不苛责,百姓宽容体谅。满任获下考,已铭感于心——这是具廊庙之才的上司在“砥砺臣工”哟!显然,牟巘对其勤免王事而没能获得上级较高的认可颇感委屈。又作有《书考谢运使启》:“自惟负乘之悰,幸免谴诃之域。满百乃报,已辱并包;有七不堪,所当亟退。……察吏已熟于见闻,而报国乃吾之职分。共理良二千石,曷称上求,参错得数十人,乃惬公意。”[5]532意思是说:我没能履好知军之职,所幸上司并没责难,且能宽容我的过失。有司熟知我任职的情况,像我这样不称职的理当退黜。但体君报国是臣的职责,我不会刻意去追求考课成绩的好坏。牟巘向这个姓谢的转运使大倒苦水,考课应是这个上级所定的等级。
上文提到,牟巘在武冈军工作生活了近十年,至其任武冈知军时已并不年轻,四十余岁了。下考的课绩,牟巘可能意识到对其仕途前景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便干脆向朝廷申请获得一个闲职的祠禄官。其《申省乞祠状》(一)[5]495-496:
领事以来,尽力所至,虽一毫未有于实恵,而千里或谅其苦心。顾以资浅望轻,平时不足以镇压,数奇命薄,所至辄值于艰虞。妖虽人兴,咎将谁执。何敢效相尤之语,但知为自治之规。赖庙朝远畅于德威,幸封境获清于旬浃。有如旁郡之元恶,亦为多方而悉擒。……兹遂书于下考,正当勉于后图。外则蔽障容邪,内则补治元气。必得精神强诩之吏,庶无岁月玩愒之风。重念某鼠技已穷,马力既竭,况以跨年之久病,凛乎永路之难全。深恐疾颠,有辜隆使。敢摅真悃,上渎公朝;欲乞矜怜,特赐敷奏。纵未加于显黜,愿亟畀以闲祠。得稍遂休息之私。
从这篇状文可以看出,似乎他的下考,主要是因治下有“妖人兴”,也就是上文说的紫阳乡的“婆婆鬼”的变乱。他除了感叹“数奇命薄”,与他共事的并非“精神强诩之吏”,也就是所谓的“吏率多偷”外,自感“鼠技已穷,马力既竭”,加之“跨年之久病”,请求朝廷将其调离,“畀以闲祠,得稍遂休息”。内心的不甘,跃然纸上。不久其又上《申省乞祠状》(二),大意与上一篇同。牟巘的结局,正说明了在武冈做知军或县令,并不是什么美差,“往往为者鲜克终”[35]。当然,从上文所述来看,离开武冈后,牟巘又任职浙江提刑,朝廷并没有让其为祠禄官。入元后,牟氏终老乡野,这虽然有忠于前朝思想的因素,但恐怕也与其曾为武冈知军的仕宦生涯有关:既苦又累,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倒不如像陶渊明那样乐享恬淡的百姓生活。
五、简短的结论
武冈军与宋朝其他的军县一样,其财政状况并不好,由于地处僻陋,甚至更为不堪,需要其他州郡进行财政援助,代其完缴赋税。尽管如此,遇到国之圣节与大典,武冈军地方官员仍然得进奉礼钱,这更加恶化了其财政的困境。武冈军境内又多少数民族,自北宋以来,时有变乱发生,其中以南宋高宗时期杨再兴的反叛影响最大,持续时间长,波及地域较广。杨再兴事件之后,宋廷在武冈军境内设新宁县,又恢复了绥宁县的设置。自北宋以来,宋廷还在武冈军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军事性的寨堡,以提升其控制力。至牟巘为知军时,窘困的财政与军内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仍然是其难以回避的问题。财政方面,他撙节浮费,创设大礼例库,尽量轻减百姓的负担,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军事上,由于武冈县紫阳乡“猺人”在其任上作乱,平息过后,他自我反省,主张在管控力较弱的该乡和长溪乡建新寨堡。
牟巘在武冈军任上,还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那就是发生在咸淳五年(1269)六七月间的大旱。与大多数封建官员一样,牟巘祈求神灵的护佑,以渡过难关。他所祈求的,既有本土的神祇,也有来自蜀中的二郎神等神灵。牟巘所崇祀的蜀中之神,除二郎神外,还有梓潼神、射洪神、蜀侯蚕丛。这固然与其时蜀中信仰已渐在全国扩散这一大背景有关,其实也与武冈军当时的官员有好几人来自蜀地是分不开的,牟氏的前任知军杨巽,牟氏本人及其属下通判公孙止、杜姓李曹掾四个蜀籍人士,都极有可能推动过蜀中信仰落地于武冈军的工作。牟巘大灾之年,忧心如焚,积极祈求神灵,也有稳定地方政治与社会秩序的考量。武冈军本就有尚巫的习俗,作为知军,其自然担心某些有政治野心的巫觋利用这次灾乱,通过附丽于其身的神力,来积聚人众而致发生变乱的可能——这样的事,武冈军境内确实也曾发生过。他之所以崇祀神灵,一是寄希望能驱赶旱魔,二是试图将地方信仰的主导权掌握在官府手中。
应该说,牟巘为官武冈期间,是尽心履职的,其知军任期届满的考课,却被有司定为下考。从其自我申辩的文字中可见其内心充满了委屈。牟巘的遭遇,管中窥斑,可见宋地方官员所处的官场环境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