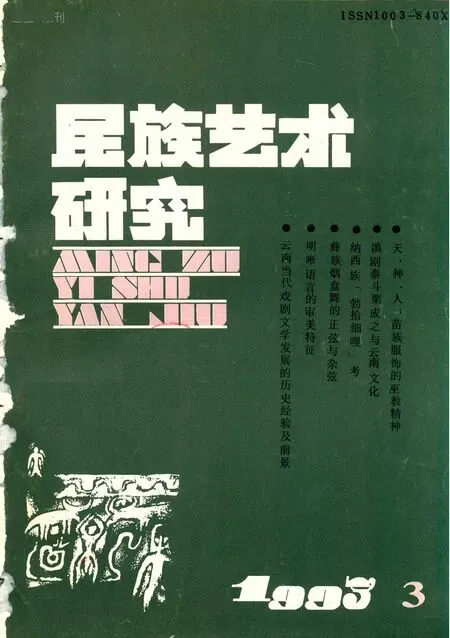脑科学与认知神经美学融合视域中视知觉感知建构的身体美学理论
李 伟
“人是美的存在”,而“美就是自然之秘密规律的显现”(歌德语),我们认为,身体既是审美的客体,又是审美的主体,“身体审美感觉不能解释或证明我们的审美判断,但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甚至增强我们的道德力量” (舒斯特曼语)。认知神经美学是脑科学在认知神经科学和美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但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忽略了在美学建构过程中身体的参与性。认知神经美学即是将形式知觉模式延伸到身体意识和身体表现之中,将脑科学、神经科学、身体化认知等完美整合,提出认知审美模块的学说。所谓身体化认知,即“身体对棉被的感觉为柔软,对钢板的感觉为硬,比身体大的事物被认为 ‘大’,反之则被认为‘小’。这种通过身体之感觉和体验进行比较和想象,以及由内向外、由此及彼的认知过程,就叫作身体化认知。”①张之沧:《身体认知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8—90页。
一、身体美学的哲学内涵及学理思考
(一)身体美学概念源考
“身体美学诞生的标志,是理查德·舒斯特曼1999年在美国杂志《美学与艺术批评》上发表的论文 《身体美学,一个学科提议》。”②李伟:《身体美学视阈下人工智能发展断想——人的本质属性与“缸中之脑”模型》,《美与时代(下)》2019年第11期,第11页。除舒斯特曼外,更早的如柏拉图(Platonic)、笛卡尔(Rene Descartes)、尼采(Nietzsche)、梅洛·庞蒂 (Maurece Meyleau-Ponty)、福柯(Foucault)等都对身体的文化属性和符号属性有过深入探讨。“舒斯特曼之所以选择使用‘身体美学’这一称谓来诠释他的研究,也是在前人实用主义美学注重实践的基础上,将身体(美的承载体和最真展现)作为最基础和实用目标而进行的。舒斯特曼之所以使用‘身体’一词而放弃‘肉体’一词,至少出于两方面的用意。一方面是身体美学所谓的身体是活生生的身体,这意味身体首先是一个有感觉、有意识的身体;其次,活生生的身体还意味着身体是一个具有动态性、扩张性的身体。身体渴望运动,渴望向外界扩展世界是它获取滋养、再生和行动的场所,身体有其自然的生长规律,其生理系统也时时自我更新。”①李伟:《身体美学视阈下人工智能发展断想——人的本质属性与“缸中之脑”模型》,《美与时代(下)》2019年第11期,第11页。
(二)身体不仅是审美对象,更应该是审美主体
人类的“认知系统并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大脑,由于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是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的,真正的认知系统包含三者的统一系统。”②张之沧:《身体认知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0页。故而身体要与大脑共同完成审美活动。“身体美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对普天之下民众身心之关注,二是对身体本身之美之力之欲望的重视。”③严前海:《影视见证:意欲与肉身》,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山东大学程相占认为,“完整的身体美学图景应包括三个层面,身体作为审美对象、作为审美主体、身体化的审美活动,同时认为身体区别于心灵的根本特点在于:必须占据特定的空间,必须与环境进行不间断而健康的能量交换。”④朱立元:《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4页。身体化指“我们身体的生物的、物理的呈现和到场,它们的呈现和到场是主体性情感、语言、思想和社会互动的前提条件。”⑤朱立元:《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64页。身体化认知包括身体感受之美以及脑神经科学美学等,这些都统摄为身体化认知。身体化认知中的认知主要指利用认知美学原理和脑神经科学美学理论,尤其是认知美学提出的形式知觉模式这一范式,这一范式不仅包括脑神经活动,同时也蕴含身体知觉模式,将审美活动与被审美对象恰当地结合起来,避免了以往传统美学理论对“美是什么” “美的本质”等问题的诘难,着重研究的是审美过程而非审美概念本身。而且形式知觉模式和审美认知模块这些概念的建立和阐释是有理有据的,“海德在1920年《神经病学》中把身体图式定义为一种身体的姿势(姿态)模式,认为身体图式不同于那些由脑皮层控制的表征,具有前意向性的功能。”⑥何静:《身体意象与身体图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也可以说,形式知觉模式虽由脑神经科学控制,但其产生和行为确是由全身来完成,也就是身体化。身体化与电影视像之美的研究是为了肯定人的存在以及道德、文化等上层建筑在凝结我们美好心灵中的作用。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自然与人类,物质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就是道德,可以说具有道德的躯体是我们物质性与意义的价值交汇之处,正是通过道德自然的身体 (包括快感)与文化政治才能联系起来。”⑦朱立元:《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74页。
二、认知神经美学拓宽身体美学的包容性,身体由“我在”转变成“我能”的系统性存在
众所周知,达尔文的进化论使我们确信且明确了一个事实,即在众多具有高智商能力和行为的动物中,唯独人类可以完成从猿到人的质变进化过程,其重要因素是人身体的参与,确切地说是人双手的解放。我们思维的形成和进化开始于身体的学习和进化,也即身体的“思维”应早于大脑的思维形成。历经百万年到今天,我们大脑虽然已经发达到具有了完整的抽象思维能力,但身体的学习本能依然存在,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某些动作便会在大脑中形成动作的模型而学习之,这便是认知的过程和本能行为。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电影 《2001太空漫游》中有更形象化的描述从猿到人的这一演进过程,工具的使用和双手的解放在人脑思维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这些习得的能力会储存在人的神经细胞中延续下来,在后续的进化中会不断地被激活和演进。因此,认知能力、神经细胞、身体意识和身体化认知等都有着共生共长的关系,割裂或者否认某一个方面都只会产生片面认知。
(一)审美认知模块假说的立论依据
审美认知模块学说的理论精髓与“格式塔质”相似,只不过后者属纯心理学范畴,前者属于审美范畴。“格式塔心理学派所说的‘格式塔质’,就是这种超越事物实体的艺术表现性——深远绵长的艺术极致。”①李定广、陈学祖:《试论“稼轩式用典”的美学意蕴》,《江淮论坛》2003第2期,第114页。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由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提出,德文的格式塔译为中文 “完形”,完形即整体的意思。在审美过程中,待审美物与审美主体以及审美环境等这些因素都共同作用于这一过程,审美活动弥漫出的“意义或灵魂”一般会大于各个部分之和,当然这里的大于不是物理上的,而是心理层面的,也即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且能够抽象出形式。美学家布洛克说:“把一个柠檬放在一个橘子旁边,它们便不再是一个柠檬和一个橘子了,而变成了水果。”②[德]鲁道夫·爱因汉姆:《艺术与视知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页。在认知神经美学中,这个“意义或灵魂”形象化成“形式知觉模式”和“审美认知模块”。雕塑或绘画艺术中,表现性是基于作品的动感和样态显露出来的,如《掷铁饼者》或《夜巡》等,但这种“意义或灵魂”的显现比较隐晦,对大多数人来说偏高雅。电影艺术是大众艺术,是现实的渐近线且无限地接近现实却无法与现实重合。电影这一特性的绝妙之处在于接近现实的即得性和与现实距离的神秘性,也即距离的掌握恰到好处。电影的最大特点之一是运动性,而且是最接近现实的运动形式,这一特性使其超越其他艺术形式而能更好地被大众接受。所以电影演员必须要能够在表演中通过“运动”,使动作具有“倾向性的张力”,从而将身体的“表现性”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这种力才会推动我们的情感,显露“意义或灵魂”,依靠 “格式塔质”和审美认知模块,使观众在接收抽象的形式知觉模式的过程中完成审美。对于观众来说,身体的“表现性”具有的“倾向性张力”集中体现在欲望(爱欲、情欲、性欲、本能等)和社会认同方面。
认知模块的两大特点:一是认知模块的类化,包括纵向和横向认知的类化,一般来讲纵向的认知对类的划分效果最好、最直接。如:罂粟花很好看,这是人们对于其作为花的横向认识;但对某些人来说,毒品侵害过他,那么这种纵向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其归类,以至于他们对罂粟花投以恶感。“类”这个概念很重要,也很关键。有人提出,从来没见过大海的人,第一次见到大海却很兴奋,感觉很美,这是大海本身含有美的事物或美的本质。实则,大海本身也许只是单纯的水这一自然物,但换个角度来看,如果看到的不是大海中的水,而是水缸中的水便不会产生有如大海般的美感,这是因为大海的宽阔和浪潮的汹涌与我们内心中的对自然物所崇拜的崇高感而形成的认知是契合的,这种崇高感是在早期记忆中对高山、天空等一切比自己庞大的事物观看时形成的,其成为潜意识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也一同构筑起我们的认知模块。“只要从褶子的角度来理解、观察和感受山脉,便可以使山脉去掉其生硬性,使此亘古之物重焕青春,使其不再是持久不变之物,而变为纯粹现实的、柔韧之物。”③Gilles Deleuze:《Negotiations-1972-199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157.同理,水的柔美也与我们婴儿期所期盼的母亲柔软的怀抱相类似,并以格式塔的原理存贮于我们内心中。这些认知模块都是按照形式知觉模式类化的,大海某些类化形象或形式正好与我们的认知模块中的类化形式吻合,于是人们开始对其审美并产生美感。二是认知模块的内隐性,我们自我存在的认知模块类型也许我们自身都不是很了解,就如潜意识一样,由遗传或由小时候的经历等在我们心中(包括身体中)留下印记——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男女主人公是一见钟情的典范,两人感情升温迅速,直到船头飞翔造型达到顶峰,这里就汇聚着满满的认知神经美学和身体化认知。
(二)身体的表现性促成形式知觉模式的构建
身体造型是展现爱与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尤其在电影的视觉形象中,而对影视中身体造型的理解需要我们神经细胞的参与,审美认知模块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身体造型之美。现扼要说明一下认知美学中认知模块的含义,如设计术语中的模块所遵循的原理,在我们人类大脑中也有类似的模块。换个角度来说,之所以我们能设计出模块这一物理结构,正是因为我们大脑中已经有此类的机体结构,这是一个物质到思想再到物质实现的过程。对于一个待审美对象,它是否会引发我们的美感,取决于我们审美主体当时的内在机体运作状态。众所周知,人类对于一个物体的欲望大致可以分为肉体和精神两大类,也即是肉身的快感和精神上的美感。这两种 “感觉”并不是处于此消彼长、有你没我的状态中,而是共生共存的。唯一的关键就是彼此在不同的情况下,哪种感觉会让我们更舒服,这种感觉就会呈显现状态,另外一种就是隐在状态。马斯洛曾对人类的需求提出了著名的“五层次说”,最低层次就是生存需要层次,那么肉体的需要是最低的,但也是最基本的。所以待审美物对于审美主体来说是满足肉身需求的时候,其必然会压抑精神需求,即快感大过美感。但美感并不是不存在,只是没有显露出来。正如纯白物体放在纯白的墙上你看不出来,并不能说纯白物体不存在。而且按照自然的进化论,只有到了脊椎生物这里才产生大脑这种思维聚合体。单细胞生物只能靠身体的感知来生存,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才有了思维,大约于8000年前才形成抽象思维能力。所以说精神需要不存在,哪怕是一秒钟的不存在都不可能,那将是倒退式的进化,不符合自然进化论。阐述这么多原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我们审美的时候,美感是无功利的,不由人的内心控制,但审美从某些角度来看是功利的,这里的功利是指我们喜欢欣赏符合自我心内需要的东西。而只有在我们的肉身需要不那么强烈的时候,精神需要才会显露出来,从而在审美过程中产生美的感觉。这也是人类生命体中的审美模块在起作用,同时这个模块不是封闭的,而是处于不断运动中。只有不断地充实和学习,不同的人才会有不同的、更多的和更高层次的审美爱好。现代认知科学发现:“人类的推理来自一种动物推理,它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特殊结构紧密相关;人的身体、大脑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日常思辨的无意识基础,即关于‘真’的意识。”①Lakoff,G.,Johnson,M:《PhilosophyintheFlesh:TheEmbodiedMind and Its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York:Basic-Books,1999,p.4.比如吃一样喜爱的食物,现今大多数水果、食物都是圆形或者接近圆形的,这固然是由于风的原因或者大地、水等,使其需要以圆形抵抗外力,久而久之我们对圆形有特殊的好感,同时由于圆形不易使我们受到伤害,而记住这一物体的形状,输入模块不断得以强化。同理,我们欣赏巴洛克的建筑,虽然其尖尖的挺拔样态初期看并不美,但因为其唤起我们的崇高感,一样能输入我们的模块,古典美学中的壮美、和谐,甚至丑陋等都是这种作用的结果。若要对这一过程以图示的方式说明,则要使用一个倒三角模型,处于下顶点的角是审美对象,上面两个角是肉身的快感和审美的美感。审美对象同时作用于人产生快感和美感,只有当肉身快感的作用退居次要位置的时候,美感才会呈现。但要注意的是,审美的过程一直存在,也就是说只要人类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则审美便可以实现,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呈现出美感。正是缘于此,在审美过程中,才会出现很多人认为的只有快感、没有美感的情况。
卓别林的大皮鞋、高礼帽、紧身衣、小胡子以及走路时的八字脚,基顿始终严肃、冷静的面孔,劳埃德的大眼镜以及他的鬼马灵精,都体现了早期喜剧电影表演者对自身进行的深入挖掘,他们将喜剧发展成为一种身体叙事并添加了喜剧表现元素的戏剧。卓别林最大的特点就是萝卜裤、拐杖和酷似鸭子的站姿,这是和鸭子的审美意象相通的,这也跟鸭子在我们审美主体中长期形成的知觉模式有关。憨态可掬、走路摇摆的视觉形象让我们欢喜,剧中卓别林的性格也有如我们常说的歇后语 “鸭子煮熟了,嘴都是硬的”。在电影《淘金记》中,卓别林饰演的夏洛尔属于下层平民,但他喜欢富家女乔琪娅并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这本来就有一种讽刺意味,无论相貌还是身家等,他与她都不平等。但由于卓别林的身体造型表现出来的喜剧效果大大化解了我们对这件极具讽刺事件的怀疑性,反而对其抱有深深的同情。试想如果不是查理的这身装扮,而是普通“正常人”的造型,那么给观众带来的视觉效果则完全不同。
电影《驴得水》改编自周申、刘露的同名话剧作品,讲述了民国时期一所偏远学校,教师们将一头驴虚报成老师冒领薪水而引发的故事。剧中的张一曼是剧中戏剧化最重也是最被熟记的角色,充分显露出中国女性要求解放而现实残酷、内心浪漫主义盛开了花,外表还要古典到家的一个性格矛盾体,她剥大蒜时都可以想象着蒜皮被抛向空中而变成雪花漫天飞舞的美景。在严重缺水、物资匮乏的西北荒漠,她依然烫着上海滩流行的大波浪,穿着自己缝制的合身旗袍,踩着优雅的高跟鞋,这一形象在很多人看来是“装”,但导演塑造这个人物的形象寓意很明确,她是拥有自己底线和贵族气质的仙女不慎落到了凡世间,但终究是只能化作尘土。《泰囧》中王宝强染着金色的西瓜皮形状的头发,可爱而放荡不羁的形象,细看其背包和仙人掌两样东西都有非常神似的地方——那就是带刺。王宝强饰演的角色性格活泼开朗,看似无忧无虑,但正如弗洛伊德冰山理论所揭示的,我们看到仅仅是意识层面的东西,还有更多潜意识的东西我们不能看见,甚至越是开朗的人越是要掩饰某些不愿意被人发现的心理。
(三)以电影 《泰坦尼克号》为例的身体化审美和形式知觉模式
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经典画面——船头二人飞翔姿势。这个动作姿势和船头这一物理空间的限定,让我们的视觉感受到的是飞翔和跳海两个极端的动向,然而其所指则是上天或入海,总之不在人间,这样才能与身处现实的我们拉开距离,促成审美实现,而且不管是上天还是入海,审美主体(观众的身体)与画面主人公的身体之间的 “力”随着距离的拉伸而越来越大。此时镜像神经元在发挥作用,因为飞翔与纵身一跳的形式知觉构成与我们脑中早期的镜像基本一致,也即亲身体验或者观察鸟类、鱼类等后天习得的起飞和跳海的知觉模式。而在这种力的作用下生成的关系则是我们对爱情的向往和终极归宿——只有爱情没有生活,也可理解为殉情。审美主体的身体与审美客体的“身体”之间因为“差异”而使前者对后者进行关注,进而生成这种关系。这里的差异主要是世俗爱情的低质化和殉情爱情的高尚化之间的鸿沟,也可说属于电影造梦的一种形式。再审视这个画面的一个特写镜头,我们观众的视觉重心是在何处?答案很明显,那就是露丝的胸部,是画面的黄金分割点,而且画面背景和演员的衣着都是深色,露丝的抹胸则是纯白的。这也是好莱坞的手段之一,当然也是审美的需要。“目光与欲望的衔接,目光与诱惑物的衔接注定使目光在具有既是叙述艺术(因此是欲望的变形)又是视觉艺术(因此是目光的艺术)的双重特征的艺术中发挥这种核心作用。”①[法]雅克·奥蒙:《现代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这时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差异”再次呈现,即观众的身体与杰克的身体(因为杰克此刻拥抱着露丝)出现差异,这也是欲望上的差异。“一切经典叙述都在欲望主体及其欲望客体之间掘出最初的一道裂隙,作为攫取观众的开场。随后,叙事的全部艺术在于如何调节对于这个欲望客体的一次次追逐,而欲望的实现始终被延迟,被阻碍,被破坏和被耽误。”②[法]雅克·奥蒙:《现代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这里的关系就是欲望的体现。而此种姿势在我们生活中经常能体验到,这里面的形式知觉模式很容易生成,画面张力(表现性)随着船的前进逐渐增加,在杰克低头与露丝耳语交谈的时候张力达到顶峰。因为这时候观众的镜像神经元在发挥想象的能指,二人要有下一步动作了(接吻),爱情要升华。
再有距离很重要。这个画面不是真实在船上拍摄,而是在室内造型的,那么就完全可以不用身体旁边的铁索,乍一看这铁索非常煞风景,与爱的感觉格格不入,这里审美距离的重要性又一次提升。如“欣赏金字塔,太近则眼光从下到上一步步地移动,领会的过程中想象力也随着达到最大值,当达到塔尖时,石头台阶重叠之美已经淡化掉了,而对金字塔的拍摄无法完成;太远则重叠的石头只会带来模糊的映像,使领会打折或完全不能完成而影响审美。”③[德]康德:《康德三批判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画面的取景很重要——近景和全景。再说铁索存在的必要性,“张力”太小无法使观众与审美对象之间产生差异,但也不能无限大到无法触碰,否则其表现性则会断裂。“因为作品如不能与观众的感情交错开来,不能与观众的情绪拉开距离,它反而无助于调动观众的感情,无助于观众情感的升华。”④严前海:《影视见证,意欲与肉身》,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所以画面必须有表现俗世的道具作为身体附属物,以保证客体的身体与主体的身体能在“力”的统摄之下而形成审美关系。巴赞在 《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中,提出了“摄影的美学特征在于它能揭示真实”的美学原理。他说:“摄影机镜头摆脱了陈旧偏见,清除了我们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面貌,吸引我的注意,从而激起我的眷恋”,也即“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铁索的作用就是将画面造型往现实拉近,使其接近现实。而且按照柏拉图的影子理论,电影与真理之间隔了一层,隔了爱的表现(包括拥抱、接吻等)这一层,电影是真理的影子。铁索的在场也恰好实现了缩短电影与真理(理式)之间的差别,使审美活动合理生成。
片段中,露丝的表情刚开始十分羞涩,也带着几分害怕和担心,但这与她丰满的身体(包括波浪头)和超前的服饰(披肩等)形象形成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减小,但影片张力却逐渐增加,这就是电影的魅力,也是导演对影片画面控制的手段,更是演员身体表现性之所在。杰克是“灵”的象征,而露丝是“肉”的体现,随着二人站到甲板船头上,差异减小,灵肉开始趋同。张力逐渐增大到二人接吻;画面渐隐随海风海景消失时候,张力达到顶点。正如安格尔的名作《泉》一样,少女(露丝)所特有的那种拘谨而又开放的特征,这种羞怯又被整个身体的服饰抵消了(这里主要是演员服饰的性感化)。就如同玛丽莲·梦露的姿势正是拘谨的动作(内在的羞涩)与奔放的外形(外在的浪荡)相结合最完美的形象。影片中女性作为被看的对象,也是欲望的客体,必须要在灵与肉之间达成一致,灵与肉的不可分在认知领域就是一种“身体化”的认知活动。
三、镜像神经元与共情夯实身体造型形式之美的生理学基础
(一)镜像神经元与共情理论
“1996年,里佐拉蒂的团队在 《大脑》(Brai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就这类新发现的细胞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文章题为:‘前运动皮层中的动作识别’,该研究重复1992年的大多数发现,当猴子抓握物体和观察实验者执行相同或相似动作时,F5区细胞均产生了反应。作者创造了‘镜像神经元’这个术语来指代这一类细胞。”①[美]格雷戈里·希科克:《神秘的镜像神经元》,李婷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镜像神经元散布于我们大脑的一些关键脑区——运动前皮质和负责语言、移情和疼痛的中央脑区。它们不仅在我们执行某种动作时被触发,而且在我们观看别人执行那个动作时也会被触发。”②[美]格雷戈里·希科克:《神秘的镜像神经元》,李婷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MN(镜像神经元)是一种在灵长类动物大脑运动前区的一种具有表征其他动物视觉编码运动功能的特殊神经元。”③Fadiga L,Fogassi L,Pavesi G,et al:《Motor Facilitation Dur-ing Action Observation:a Magnetic Stimulation Study》.《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1995,73:2608-2611.由镜像神经元可以引出“共情”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由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提出的,是指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镜像神经元从原理上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认知,而 “共情”则是更多地在现象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和沟通的一种感知。通俗地讲就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超越自身的自恋而去理解别人的能力。共情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人类感受、理解和分享他人情感的一种独特能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然而以第四军医大学陈军教授领衔的团队在近期的研究发现中,啮齿类动物和其他物种的疼痛共情极大地挑战了这个观点。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大鼠在与同笼大鼠社交30分钟后,疼痛共情可长时间存在,并探查出内侧前额叶参与其中,提示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存在一个与疼痛共情有关的神经网络环路。这表明共情可以经过后天培养习得,这一研究对我们大脑审美认知功能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人类学意义上的促进。也即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审美可以增强我们的共情能力,而“美”在宽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我们都认可的一种积极的精神存在和内心感知尺度。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大自然美的造化、欣赏具有美学韵味的艺术作品、与具有美感认知能力的人交往等,都能提高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审美认知能力,促进社会的和谐。目前在我们的社会文化教育中提倡传播正能量,这个正能量的传播有很多种途径,可通过讲座、报告、理论学习、课堂讲授等,但这些方式方法都不及对正能量行为的欣赏和感知。如:教育人们不随意丢弃垃圾,大篇幅地宣讲垃圾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等,其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人们无法在大脑中直接形成垃圾对人类生活影响的印象,而在生活中看到捡拾垃圾的行为,我们的身体会不自主地学习这种行为,以至于我们再次遇到这种情况会不由自主地去捡拾垃圾,这就是因为镜像神经元在起主导作用,进而促生共情能力。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先驱马尔科·亚科波尼写到,“电影对我们而言是如此逼真:因为在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为我们复制在银幕中所看见的苦难。我们对小说中的主角能感同身受,我们能知道他们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有过相同的感觉。当我们看到电影明星在银幕上接吻时会怎样?这个画面同样会点燃我们大脑里头那些细胞,就像我们正在亲吻自己的爱人。‘替代’这个词汇并不足以描述这些镜像神经元的效应。”④[美]乔纳森·歌德夏:《讲故事的动物—故事造就人类社会》,许雅淑、李宗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82页。
“在YouTube上有根据海德和齐美尔实验重新制作的画面(图2)。海德和齐美尔让受测试者看过这部影片之后,给他们一项简单的任务:‘描述你看到了什么?’有趣的是114位受测试者中只有3个给出真正合理的答案。这些人说他们看见几何形状在屏幕上四处移动。其他受测者都和我一样,他们眼里没看到无血无肉的几何图形四处滑动,他们看到一出肥皂剧:门被大力撞开,求欢的舞蹈,追求者的挫败。当我第一次看这段影片,映入眼帘的不是粗糙的动画线条在屏幕上乱跑,而是一则既奇怪又动人的几何寓言故事。小三角形和小圆形一起入境,两个就像一对情侣,然后大三角形冲出房子(大正方形)。大三角形粗暴地碰撞且进逼个头比较小的主角(小三角形),并且把试图反抗的女主角(小圆形)赶进屋内。接着大三角形前前后后追逐着小圆形,想要把她逼到角落,这一幕给人暴力求欢的感觉。最后大正方形的门打开,小圆形逃了出来和小三角形在一起。接着这对情侣(小三角形与小圆形)在大三角形穷追不舍之下在屏幕上四处乱窜。最后这对幸福的情侣总算脱身,而大三角形勃然大怒地把自己的房子击碎。”①[美]乔纳森·歌德夏:《讲故事的动物—故事造就人类社会》,许雅淑、李宗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41—142页。在另一个类似的研究中,由姆本巴·贾比所领导的神经科学团队把受测试者放在核磁共振的机器中,让他们看一段画面,画面中有人喝了一杯东西后表现出痛苦地扭曲神情。他们也扫描受测试者听到研究人员大声朗读一小段脚本的大脑反应,这段脚本要求测试者想象自己走在街道上,意外撞上一个酒醉呕吐的行人,然后接住对方嘴里吐出来的东西。最后,科学家在受测者真的尝到令人恶心的饮料时,扫描他们的大脑。结果显示,大脑中掌管呕吐的前脑岛,在前述三种情况下都亮了起来。正如其中一位神经科学家所说:“这代表不论我们是看一部电影或者阅读一篇故事,都发生了相同的事,亦即当我们觉得恶心的时候,大脑掌管恶心感觉的区域都会受到刺激,这也就是为什么读书和看电影能让我们直接感受主角所经历一切的原因。”②[美]乔纳森·歌德夏:《讲故事的动物—故事造就人类社会》,许雅淑、李宗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85页。
(二)共情理论增进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之间的情感交流
这里引出一个现象就是不同的人被相同行为引发的感受是不同的,尤其是女生经常会看情感电影泪流不止、恐怖电影会惊恐万分,而对那些对此无动于衷的人习惯的称谓是“神经大条”。这虽是诙谐之语,但却言之凿凿。人对疼痛的敏感性会直接影响其共情的能力。胡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及其团队招募了150名身心健康的大学生参与实验,采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和经典共情范式测量个体的共情能力,采用激光刺激和冷痛仪测量个体的疼痛敏感性,并采用多个问卷对个体的疼痛认知、人格特质和情绪状态进行了测量。他们的结果中,激光痛和冷痛相关的疼痛敏感性指标均表明,个体的疼痛敏感度越高,情绪共情能力越强,即越怕疼的个体越能受到他人疼痛的感染。这预示着个体的疼痛敏感性与共情能力存在共变关系。他们的发现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考察疼痛共情的神经机制,还为探究低水平感觉功能与高水平社会认知的联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当我们在电影中看到某些惊悚、性感或危险的剧情时,大脑的某些神经元会产生反应,就像这些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样,而不只是电影中虚构的情节。例如,在达特茅斯的大脑实验室里,由安妮·科伦德尔所带领的科学家让受测试者观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西部电影 《黄昏三镖客》,同时用功能性核磁共振仪器扫描他们的大脑。科学家发现观众的大脑能 ‘捕捉到’银幕上所演出的任何情感。当伊斯特伍德生气时,观众的大脑看起来也在生气;当剧情发展到充满悲伤的情节时,观众的大脑看起来也和剧中人一样难过。”①[美]乔纳森·歌德夏:《讲故事的动物—故事造就人类社会》,许雅淑、李宗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85页。这项实验表明了观众的身体感知与剧情展现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共情的一个现实表现。在这里,观众的大脑变化属于比较直接的反应,电影中还有一些身体动作是需要依靠观众内心活动引起的联想而产生间接反应的。电影《码头风云》是由伊利亚·卡赞执导,马龙·白兰度主演,于1954年7月28日在美国上映的影片,讲述了码头装卸工人特里·马洛伊为了揭发码头老板的罪行,以及替工人们伸张正义,联手大学生伊蒂·多伊尔和牧师巴里发起反抗的故事。该片获得第2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第1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最佳影片、第12届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等。“在电影《码头风云》中,女人做出一个暧昧动作,男人捡起手套把玩并戴在手上,男人感到有罪和害羞。这如同动作—影像的一个遗传符号或胎记,人们可称之为印记(信物),它在行为范畴中具有一种‘象征’功能,它以奇特的方式将演员的潜意识和作者本人的负罪感、影像的癔疤联系起来。在最普遍的定义上,痕迹是渗透情境与爆发动作的可见内在关联。”②[法]吉尔·德勒兹:《运动·影像》,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页。同样的例子还是在这部电影中,“《码头风云》马龙白兰度因对出租车那场戏不满,要求换剧本:那你就冷静地伸出手把枪压下去,一个人非要在枪指着时才肯吐露心事,是低廉肥皂剧才有的情景。”③[法]吉尔·德勒兹:《运动·影像》,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还有,“在《码头风云》第一场和伊蒂的戏中,白兰度添加一点东西:他捡起她的手套,戴在自己手上,这一动作妙笔生花,使他们的关系血肉丰满:像男孩之间的友谊,显示他的意图(调戏她),揭示了两人教育和修养的差异,还是一种性暗喻。同时这也给伊蒂在后续中一个可行的目的——要回她的手套。”④[法]吉尔·德勒兹:《运动·影像》,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这些电影片段都很鲜明地展现出剧中人的身体动作与观众内心体验之间的微妙思维关联。在前述的这几个例子中,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是手套,那么手套是如何从一个非生命的物体而成为能够蕴含演员思维意识并传递给观众的物件的呢?这完全得益于演员的动作和行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手套就是一个普通的保暖御寒物件,本身不具任何指代性意义。在商店杂货铺中陈列摆放的手套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无生命力的物品,也即是一件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而当这个商品 (手套)被买主买回去并随身戴着,商品本身就已经吸收了人的气息而具有了生命力,这不仅是手套,任何一件商品如衣服、首饰、水杯等都如此。然而手套的穿戴方式不同于其他物品,其意义展现取决于戴在谁的手上以及戴的过程与情境等。一个熟知的现象或者说心理活动就是,借助一个替代物可以进行两个人的间接接触,如男女共引一杯水可以说是两人之间的间接接吻等,而戴手套的动作因为需要有伸入这个动作就使得其不同于共饮一杯水这样表层的含义,因为这个动作会使人联想到男女之间的性爱之事,这完全是因为动作的相似性而使人产生的联想。同时,之前我们提到手套的意义展现取决于戴在谁的手上以及戴的过程与情境,戴手套的过程已经使其有了这样一些心理暗喻,而情境的因素也非常重要,且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动作可以体现这里的情境。“典型环境”这一提法是恩格斯在 《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首次提出的,指文艺作品中典型人物所生活的、形成其性格并驱使其行动的特定环境。我们这里是对典型环境驱使其行动一个方向应用,也即动作需要寓于典型环境中才具有典型意义。电影中,男主人公将女主人公的手套戴在自己手中,这一动作本身所蕴含的意蕴远远大于在其他环境中的同样动作,只因为有典型环境在那。试想在寒冷的季节,男人戴上女人的手套携手前行只会让我们感到感情的浓烈,这里的典型环境是什么,那就是在现实情境中不需要男人戴女人手套并且其戴的动作不是现实所需的时候,戴手套的动作和意义才由能指跨步到所指行列。如同在审美活动中,形式知觉模式贯穿于活动中,但我们在饥饿的时候虽看一眼就能体味到一种食物形式上的美感,但很难产生关于它的更深入的审美活动,因为身体本能需要的迫切性会阻止我们去对它展开更深入的审美活动。戴手套动作的功能本身是御寒,这是其功利性,只有使其超越了这种功利性 (戴手套这一动作不是为了御寒)才能形成无功利的愉悦,产生美的感觉。“审美时,人的机体基本处于平衡状态,没有急切的生存需求,这时以视觉和听觉对事物的外形进行认知也能获得愉悦感。即:由生存性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快感或好感;由对事物外形的认知而产生的愉悦感是美感。换句话说,快感和美感都是由对人和事有利的事务所引起的;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快感由有利事物内在的有利性价值所引起;美感由有利事物的外形所引起。”①李志宏、王延慧、孟凡君:《认知模块:大脑审美活动的核心结构》,原载于《美学教育杂志》2018年夏季号[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A&HCI索引期刊]。对一个有形的物品来说,外形就单纯指其外部形态,而对一个动作来说外形指的是动作形式本身。这样就很好理解戴手套这一动作了,其“有利性价值”是手套的基本御寒功能,能产生快感;“有利事物的外形”是指戴手套的动作这一形式完成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活动中生发的美感。“例如面对一串新鲜的葡萄,当人处于饥渴难耐的功利需求状态时,首先注意到的是葡萄的实用价值,其动机是吃进这串葡萄;当人机体状态相对平衡,处于没有功利需求的状态时,不形成对葡萄实用价值的注意,也不形成吃进葡萄的动机。这时才可以对葡萄的外形加以观赏,形成美感。如果人对某一事物形成了美感,就会把引发美感的事物称为美的事物,进而称之‘美’。”②李志宏、王延慧、孟凡君:《认知模块:大脑审美活动的核心结构》,原载于《美学教育杂志》2018年夏季号[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A&HCI索引期刊]。
(三)镜像神经元在审美认知活动中的作用机理
这里以最大众化的审美形式——电影为例,我们知道作为审美对象的电影,其影像是虚构的,即使在极度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直接对电影中的食物或生活必需品产生直接的功利性需要,而只有在电影所展现的情境能使我们产生“极度需要”的感受时才会形成快感,如前述在寒冷季节戴手套这一动作就形成了快感,形成了身体的舒适性;然而在非“极度需要”的情况下,事物内在的有利性价值则不会显现即手套的御寒功能不显现,而以动作行为本身为架构的外形起作用形成了愉悦,也即所谓的美感。这一切的活动流程也从侧面说明了身体的参与性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元素,甚至可以说没有身体的参与审美无法完成,因为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判断待审美物是停留在快感层面还是已经进入到美感层面。电影的视像通过演员的身体表演直接使观众的身体产生镜像反应,这种反应就是我们在面对食物等审美对象时的直接功利性。
关于镜像神经元的作用机理,现在假设有三个电影画面:情节是一个人拿着大砍刀横向劈砍过来,而画面1是观众的主观镜头,也就是没有客体,大刀直接砍向屏幕;画面2是客观镜头,大刀砍向一个动物如狼等,动物被砍中倒地哀号;画面3也是客观镜头,但大刀砍向的是剧中的一个人的腹部且鲜血喷涌。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三个镜头画面哪一个对观众的刺激更大一些。经过问卷调查结果一致,那就是画面3更刺激,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但身体的反应却也异常激烈,说明思维的最初阶段应该是镜像神经元将动作传递给身体的对应部位和器官,器官对此作出反应并传给大脑产生疼痛的感觉。画面1其实对我们的感觉刺激应该更强烈,因为其给人的感觉是直接有刀向我们砍过来,这种真实的触感是画面2和画面3所不及的,但这里我们只是视觉器官看到了动作行为,同时身体的本能使得我们会不自主地躲闪,无暇思考疼痛与否及其他情况,而镜像神经元将这一行为传递给身体与不自主地躲闪是同时进行的,只不过躲闪是动物本能而掩盖了身体可能产生的痛感,待身体无伤后大脑的思维和意识才会产生恐惧的联想并做出反应。这也是现实中很多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会下意识地做出反应而来不及恐惧,待事情过后才会产生害怕的心理,产生所谓的“后怕”感觉。电视中经常出现面对行凶歹徒时冲上去的英雄,事后采访问他当时怎么想的,一般回答都是“没想那么多”,很多人以为这句话是谦虚和自我标榜的说辞,而其实这就是人的身体最本能的行为和想法。这种原理扩大来看和朱光潜的“雾海行船”的例子是异曲同工的,站在事发的船上本能的做法就是逃避,而站在岸上的人通过镜像神经元作用于身体,大脑的思维功能会思考其恐怖的后果。这些例子可以表明,身体的直觉反应会先于大脑的思维意识。也即是长期的身体习惯会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下意识的产生反应,痛定之后才会经过大脑的思维和意识。不仅如此,有些看似大脑思维做出的反应,其实也是身体的长久习得性结果。“关于描绘印象和关联如何创造转折这一点,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有一桩逸闻:一位女士得知丈夫意外死去,立在原地脑中盘旋问题,他不回家,准备的晚餐怎么办?人在遭遇无法处理或不能接受的信息时,思维就会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运作,在妻子脑海中,‘丈夫’的印象与‘晚餐’相连接,并没有触及更深远的想法,因为人的思维就是那样运作的。”①张楚廷:《人是美的存在》,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只有长期固定做晚餐的妻子头脑中才会有如此的联想,所以这已经属于下意识的身体习得性行为。再如“倒水等动作在头脑中完成并预见它的结果,这是‘内化的动作’。②费多益:《寓身认知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版。所以说更多时候我们在欣赏电影或其他艺术时,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在‘表演’并被自己确认。”这种内化的动作有时会使得我们无法分辨出是身体还是大脑在起主导作用,但关键是都能被自己确认,也就是进行人的自我确证。因此电影中最适合表现的镜头就是那种能被我们头脑中“内化的动作”,也即最具普适性价值和行为的动作,因为这些动作更易于被我们身体模仿而内化,其本质还是自我确证的。正如我们观看奥运会,破世界记录等身体的极限突破不是为了单纯的狂欢,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认识。“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莎士比亚的舞台剧、看电影或读小说?最终,从科赛尔的观点来看,这些都不是为了要拓展心灵、探索人类的现状,或者是有任何高尚的理由。我们到头来只是为了‘寻求刺激’。③[美]乔纳森·歌德夏:《讲故事的动物:故事造就人类社会》,许雅淑、李宗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40页。这里的刺激就是身体的刺激,但对我们人类这一生物机体而言,刺激是直接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作用于大脑从而拓展思维和意识,巩固作为类的人的存在。“如在攻击场景中,观众既对攻击者产生认同(出于施虐快感)又对受攻击者产生认同(出于焦虑),同理还有求爱场景等,看出使电影的乐趣变成一种混杂的乐趣的这种处境的矛盾性,这种乐趣往往更暧昧和更含混(也许是所有想象关系的特征)经过合理与简单化的再次提炼后,观众会甘愿承认和记住这种乐趣。《群鸟》中当女演员站起身时,必须采用特写跟拍她的脸,若机器移动形成运动镜头,势必打碎观众对人物的认同。可以从侧面理解影像的大小是重要元素。”④[法]雅克·奥蒙:《现代电影美学》,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四、认知神经美学与身体化认知的模块化共铸现代身体美学理论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理解身体化认知的含义,强调的是身体与环境之间的能量交互及其神经元群的模块化。就颜色这一最常见且客观实存的现象来说,并不存在红色或者其他颜色物质使我们认为其就是某种颜色,而是脑神经、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投放到具体的物体中使我们认为其就是某种颜色。而这里的 “红色”这个词是概念化的抽象用语,在认知领域并无实际的意义,仅是一个符号。当然,对于颜色的认知是我们眼睛对光线过滤和拾取的结果,这是纯粹的生理功能。一支笔是绿色的,并不是这支笔就是绿色的存在,而是太阳光照射到笔上,笔吸收了其他光线而反射了绿色,同时我们眼睛的通过颜色的轮廓结构出笔的样态存于我们脑海中,再加上我们实际应用过这支笔且知道笔的功能,这一系列行为综合作用才能使我们感知到:这是一支是绿色的笔。对于一个从来未用过笔的孩子(不包括看过别人用笔写字的孩子,因为这时在孩子大脑中也会储存笔的功能)来说,能感知到颜色和轮廓,但无法说出这就是一支笔。“正是通过身体化作用,才在我们的身体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外部环境的共性基础上形成我们的概念系统,所有颜色都不存在于外部世界,这些颜色都是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不断进化所创造出来的结果。”①张之沧:《身体认知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6页。
综上,身体化认知和呈现使认知神经美学与脑科学不再是抽象和高端的实在,而是可以触摸并随时随地感知的具体和确证的行为。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美学的研究风靡云蒸,而身体化认知也许是最直接易入的研究进路。毕竟身体是我们每个人最真实的存在和感知物,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得那么神秘而干脆:每个人都是神殿的建造者,这座神殿是人的身体,所以任何高贵之处都是从锤炼人的特性开始,任何的卑微和淫荡之处也是从使之堕落开始的。据此,我们将审美主体的神经系统理论范围也扩大到整个身体,因为整个身体就是作为一个审美认知模块而存在和生成的。也即:我们并非“拥有”一个身体,而是我们的身体以“存在”的系统论思维去构建审美认知模块。其效果是:初看是作为 “肉身”的身体,再看已是 “我想”而在世的身体,复又看则已是“我能”而意识到的审美身体。由此达到所谓“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审美认知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