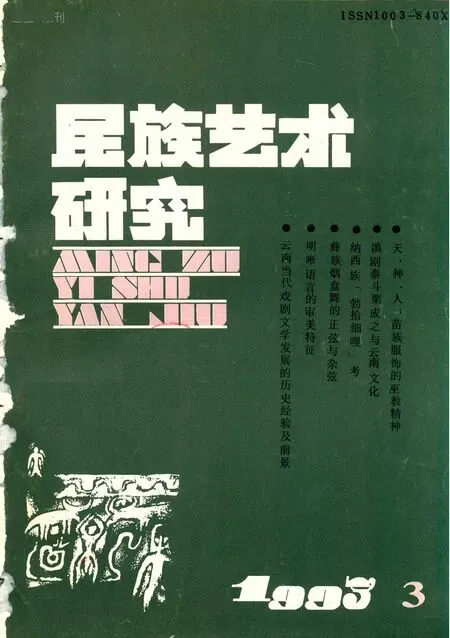汉代石椁墓神树图像方位结构研究
王 倩
就考古学的分类而言,石椁墓有三类:一是积石冢,即用块石垒堆成的石头坟墓;二是仿制“黄肠题凑”式墓葬建成的墓室;三是仿制木椁建成的石棺墓葬,此类石椁由底、盖、侧、档板构成,内置木棺。①燕生东、刘智敏:《苏鲁豫皖交界区西汉石椁墓及其画像石的分期》,《中原文物》1995年第1期,第79页。本文所探讨的石椁墓为第三类,并不包括前两种类型。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统计,近年苏北、鲁南、豫东、皖北地出土近200座石椁墓,其中正式见于报道的有近百座。②参见燕生东、刘智敏:《苏鲁豫皖交界区西汉石椁墓及其画像石的分期》,《中原文物》1995年第1期,第79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约有30座石椁墓中刻画了数量众多的三角形树形图纹,较为典型的当属江苏沛县栖山石椁墓、③徐州博物馆、沛县文化馆:《江苏沛县栖山画像石墓清理简报》,《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12页。连云港锦屏山西汉石椁墓④李洪甫:《连云港市锦屏山汉画像石墓》,《考古》1983年第10期,第894—896页。,山东枣庄小山西汉石椁墓⑤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枣庄市博物馆:《山东枣庄小山西汉画像石墓》,《文物》1997年第12期,第34—43页。,山东枣庄临山汉石椁墓,⑥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枣庄市博物馆:《山东枣庄市临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1期,第49—59页。山东临沂庆云山石椁墓⑦临沂市博物馆:《临沂的西汉瓮棺、砖棺、石棺墓》,《文物》1998年第10期,第68—75页。,山东微山县微山岛西汉石椁墓⑧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汉代墓葬》,《考古》2009年第10期,第21—48页。,山东滕州市山头村汉石椁,⑨燕燕燕:《山东滕州市山头村汉代画像石墓》,《考古》2012年第4期,第92—96页。河南夏邑吴庄石椁墓⑩商丘地区文化局:《河南夏邑吴庄石椁墓》,《中原文物》1990年第1期,第1—6页。,安徽萧县陈沟石椁墓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萧县博物馆:《安徽省萧县陈沟墓群(地区)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第31—40页。郑同修:《汉画像中“常青树”类刻画与汉代社祭》,《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第62页。汪小洋:《枣树:汉画像石中树图像的一个原形》,《齐鲁艺苑》2004年第3期,第26页。,等等。
因这些石椁墓葬中刻画的树形近似三角形,其造型与柏树这类常青树外形有些相似,多数研究者将这类树称为“常青树”。当下多数学者探讨的内容依然停留在石椁墓中树种的考辨方面。譬如,郑同修先生就断言,“这类所谓‘常青树’类刻画,有的原来是汉代社树的摹画,汉代社祭一如前代,也有立社植树、以柏树为社之俗。”①郑同修:《汉画像中“常青树”类刻画与汉代社祭》,《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第62页。汪小洋先生则指出,根据河南省偃师县南蔡庄汉墓出土的《肥致碑》内容推断,“这类树有一个原形是枣树,表现的是修炼成仙的内容。”②汪小洋:《枣树:汉画像石中树图像的一个原形》,《齐鲁艺苑》2004年第3期,第26页。不可否认,以往关于汉石椁中树形图纹的探讨极大地丰富并拓展了汉画像石图像阐释的范围,但多数研究者皆将这种树图像视为现实生活中树木的描绘,并未虑及其象征意蕴,并且方法论上割裂了图像与图像情境之间的关联,致使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基于图像阐释的情境性之规约,本文将这类树形图像置于石椁结构之中,对图像结构的象征意义进行深度分析,并探讨其生成的概念性源头。
一、树形符号的图像结构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公布的苏鲁豫皖四省石椁墓中,绘有树形符号的共计有30余座,其中明确标有出土地名的有37座。树形图像主要出现在石椁墓的后档板和左右侧档板上,尤其是后档板上,有的树形图像同时出现在后档板与侧档板上。在这些图像中,足档上出现的图像有树、树+鸟、树+鸟+玉璧三种组合。树和鸟的组合居多,树+鸟+玉璧这三种符号同时出现的机会最少。侧档上出现的符号组合则有树+玉璧+鸟、树+玉璧+屋舍、树+车马,其中尤以树+玉璧+鸟图像组合居多。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何种图像组合,三角形的树符号均是画面表现的中心,居于图像的中心或显著位置。
在上述图像组合中,石椁墓后档板上的图像组合均与前档板上的图像相对应,而石棺前档上刻画的图像无一例外皆为玉璧。这就表明,前档板玉璧与后档板树形符号必定是相互对应的,二者意义亦相互呼应。与树形符号相关的符号分别为玉璧、鸟、房屋、车马,尤以玉璧居多。不论是后档板还是侧档板,其上刻画的树形符号均呈三角形,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图像模式。
从图像所属地域来看,石椁墓中的树形图像仅仅出现在苏北、鲁南、豫东、皖北等地,同时期陕西、四川汉画像石中并未出现类似的树形符号。这些树形图像出现的时间大致在西汉早期到东汉初,东汉中晚期之后这类树形符号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扶桑、连理树这些神话中的树木。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的画像石仅绘有呈三角形的树形图像,并无其他类型的树形符号出现。而东汉早期之后,这类抽象的三角形图像便消失不见,汉画像石中更多出现了《山海经》《淮南子》等神话文本中表述的若木、扶桑、连理树等神树。由此我们可断定,西汉早期至东汉早期苏鲁豫皖四省石椁墓上的三角形树图像一定是抽象的,它并不是柏树等常绿植物。换言之,石椁墓上的树形符号并不具有实指意义,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指向了多种树木类型。那么,这些树形符号究竟象征着什么?它在石椁墓中具有怎样的作用?
根据结构主义思想可知,图像是一个符号体系,其意义由各种符号建构而成。换言之,单独的符号与图像是不具意义的,其意义存在于它与其他符号与图像之间的关联之中。因此,要解读一个单独符号或图像的意义,必须将其置于图像体系与图像生成情境中。在这样一种规约下,我们要探寻苏鲁豫皖四省石椁墓树形图像的意义,必须将其置于石椁墓图像体系及其生成环境中。
二、作为天梯的神树
人是推崇象征行为的动物,也是意义的制造者。人类社会通过象征行为建立一套文化体系而区别于动物群体,此种象征行为包括语言交际、神话思维和科学认知。换言之,“人类生活在一个象征的世界里。甚至我们当中最有文化和头脑的人,也不断地使用象征并认识到象征的作用。穿着某种宗教的衣服象征着一个人献身于上帝。衣领上的彩色绶带表明与艾滋病患者的团结一致。一个单独的耳环意味着同性恋团体成员的身份。通过向一面旗帜致敬,唱一首颂歌,穿上球衣、制服或一种特殊的服装,可以激发出民族自豪感、群体归属感以及团队支持感。”①[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对于汉代的人们而言,石椁墓既是埋葬死者的地方,也是亡灵居所的象征性建筑。石椁墓葬结构模拟的是死者亡灵的归宿地即天界之结构,石椁图像内容自然也是天界的象征。巫鸿先生曾对东汉石椁画像的象征结构做过总结:“天空的场景出现在顶部;入口的场景和宇宙的象征分别占据着前档和后档;石棺两侧的画面由多种题材组合而成,但总是突出了某种特定主题,如对灵魂的护卫、宴饮、超凡的仙界儒家的伦理。”②巫鸿:《四川石棺画像的象征结构》,载《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巫鸿著,郑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5页。对于苏鲁豫皖四省汉代石椁画像而言,其图像内容与宇宙结构之间同样存在这种内在的象征性对应关系。只不过相对于四川石椁画像而言,苏鲁豫皖地区的石椁画像内容较为简单,更加突出墓主亡灵升天过程中的路线与方向。
就树形图像所在的棺椁结构而言,它主要存在于后档与侧档,而后档与侧档上描绘的图像内容是一个整体,因此在解读树形图像的象征意蕴之前,必须了解石椁前档与侧档描绘的图像内容。从石椁前档雕刻的画像来看,它主要以表现天界大门的情景为主,因此象征天门的玉璧与铺首衔环成为石椁前档画像的主要内容。铺首衔环图像的环实际上也是玉璧,而铺首则是神话世界看守天门的神兽。在汉代墓葬结构中,玉璧象征天门是墓葬图像的固定象征模式,它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图像规约。我们这里仅举两例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重庆巫山县的汉代鎏金铜牌。重庆巫山县出土了东汉晚期十四块鎏金铜牌饰,其中四块铜牌上绘有玉璧图像,并且在玉璧上方刻有“天门”榜题③具体参见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第77—86页。,玉璧在这里显然是作为天门的象征符号而出现的。与上述玉璧相关的图像中刻有象征天界的有西王母、双阙、羽人,神兽等符号,这些符号从侧面表明玉璧为天门象征符号的属性。第二个例子是东汉晚期的洛阳市郊烧沟村东61号汉画像石墓葬。洛阳市郊烧沟村东61号汉墓前堂后室隔梁后壁描绘的图像(图2)内容,使得玉璧象征天门的蕴含一目了然。隔梁画面呈梯形,画面中间为两门扉,其中一门扉半启。门扉上部绘有五个浅绿色玉璧,玉璧下方为菱形。画面两边为对称性图像,各绘足踏紫绿色山峰的飞龙,一羽人坐于龙背之上。玉璧位于门扉顶部,明显象征死者亡灵要进入的天门。这就表明,玉璧象征天门的意味在全国各地汉画像石墓葬中是一致的,无须借助于文字,人们见到玉璧便已领会其象征天门的特殊意味。
汉代石椁墓是一个微型的宇宙,它模拟的是宇宙中心的结构。进一步说,石椁前档是死者头部所在位置,后档则是死者足部所在位置。根据图像象征规约,二者描绘的内容必然是相关的。具体说来,石椁前档图像描绘的是死者亡灵要进入的天门,即宇宙中心的边界,而后档描绘的图像是进入作为宇宙中心通道的天梯。这就意味着,苏鲁豫皖四省石椁墓后档上刻画的树形符号是象征着宇宙中心通道的天梯。关于这一点,安徽萧县陈沟墓群(东区)石椁墓编号为M12的墓葬图像中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图3)。该石椁前档被菱形纹饰一分为二,菱形纹饰一侧各有一个玉璧,玉璧上端雕刻一个箭头;后档刻满呈梯形状直线,中部一条直线将后档一分为二,两边各有一个树形符号。在该石椁画像中,前档上的玉璧图像象征天国门户,玉璧上端的箭头显然寓表天国方向。后档上的树形符号则表明亡灵是通过这株树而抵达天国的。萧县陈沟墓群M12石椁画像表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亡灵已经通过宇宙中心的通道,借助于作为天梯的神树而抵达天国大门。这座石椁画像表明,后档山刻画的树是神树,也是通天的宇宙树,它是亡灵升天的工具。更是宇宙中心的通道。
作为天梯,石椁墓中的神树连接天地,它一端是天界,一端是人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山东枣庄小山西汉石椁墓M2描绘的画面中得知(图4)。在这座石椁的南椁室西档(后档)上,一条小河将画面分为两个部分,同时将画面中间的宇宙树分成两个部分。树的上部有两位女性翩翩起舞,两位男性站立一边侍立,这显然是恭候亡灵升天的场面。树下部是骑马准备升天的死者,两位侍者站立一旁伺候。山东枣庄小山西汉石椁墓M2画面描绘的场景表明,树形符号是宇宙树的象征,人神之间的交流通过它而进行,亡灵也通过它而升天。这样一来,我们便很容易理解石椁后档玉侧档上以树为中心的树与鸟、玉璧、屋舍、车马等图像组合的象征意义了。在神话世界里,鸟白天在天空飞翔,夜晚栖息于大地,而神明居于天界,人类居住在大地之上,鸟类因此成为沟通天地与人神的使者。石椁画像与那些栖息于树上的鸟类实际上是导引死者亡灵升天的使者,负责将亡灵引入天门。至于双阙、屋舍这类建筑物,它们均是天门的象征符号,寓意死者亡灵要抵达目的地①参见赵殿增、袁曙光:《“天门”考——兼论四川汉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第3—11页。。在汉画像石中,车马并不象征天门,但它是亡灵升天的工具。②参见王倩:《论安徽宿州褚兰汉画像空间结构》,《中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55期。明白上述这些符号的象征意义,我们便理解了石椁墓刻画的图像蕴含:所有这些画像场景表述的皆为亡灵升天的内容,前档描绘的是天界的大门或入口,后档则是宇宙中心的通道,辅助性的鸟、车马等符号则是导引亡灵升天的使者或工具。至于侧档刻画的内容,则基本上是天界的内容,强调亡灵已抵达目的地,享受不死的天上生活。
那么,苏鲁豫皖四省石椁画像的树究竟是何物呢?其石椁画像提供的相关性细节仅仅表明其功能为导引亡灵升天的宇宙树,并未就此提供更多的信息。从画像描绘的场景来看,这种神树应是汉代神话文本中表述中的建木。《淮南子·地形训》曰:“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①陈广忠译注:《淮南子》(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4页。建木是宇宙树,亦即众神上下、天人交往的天梯,也是标志宇宙中心的神树。这种树的形状极为奇特,《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如此表述:“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②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329页。《山海经·海内南经》关于建木的表述乃是采用类比的方法进行的,我们无法得知其具体形状,不过《山海经·海内经》有明确的表述:“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③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509页。文中所言九丘实为宇宙山,立于其上的建木自然为宇宙树无疑。建木有九枝,这一点与石椁画像描述的简略呈三角形的树形状有所不同。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石椁墓中的树图像更多地与民间信仰和神话相关,因石椁画面的特殊性,它描绘的更多的是建木功能方面的内容,而不是建木的外形,有九根枝丫并且色彩艳丽的建木于是仅仅被表现为三角形的简略树形。不过,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出土的西汉晚期陶建木倒是提供了较为生动的实物模型(图5)。这尊陶制的建木模型扎根在象征宇宙山的三角锥体基座之上,笔直的树干上有九个枝丫,其上有鸟、蝉等动物。这些动物皆攀爬在树上,只有神鸟立在树端。这就表明,建木实为宇宙树,不管其外形如何变化,其沟通天地的功能并未改变。
进一步讲,苏鲁豫皖四省石汉代椁画像中的树形图像表明了这样一种方位模式:宇宙以神树为中心划分为两个部分,天界居住着神明,地上则生活着人类,二者之间通过神树而交往。此种二分的方位模式并非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普遍存在于中国汉代文本神话与少数民族的神话、仪式、图像中。①参见王倩:《论陕北汉画像圣树符号的宇宙论意义》,《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5—22页。换言之,苏鲁豫皖四省汉代石椁神树图像描绘的垂直方位模式是中国宇宙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神话一起,共同建构了中国垂直的宇宙模论。
三、圣树图像的原型
苏鲁豫皖四省刻有圣树的石椁画像多半为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的作品,距今不过两千年,但它所反映的以圣树为中心的宇宙论模式却可以上溯到无文字书写的口传时代。进一步说,苏鲁豫皖四省石椁树形画像具有悠久的图像渊源,它与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圣树崇拜与信仰密切相关。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大批以考古出土实物为主的神树符号以图像叙事的方式讲述了圣树图像的史前原型,也揭开了苏鲁豫皖四省石椁墓神树图像的口传源头。
距今约7100—7300年的安徽蚌埠双墩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刻符号,据考古发掘报告表述,其中14件陶器上刻树形符号,其中刻画单体树形符号8件,重体树形符号5件,二组合体树形符号1件②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表2。。标本标号为91T0819(15):83陶碗底部刻有单株树符号,树干细直无叶,有九根枝丫笔直立于树干之上(图6)。我们无法确认这株树就是神话中具有九个枝丫的建木,但却可以肯定,它是一株非同寻常的神树。理由很简单,安徽蚌埠双墩文化遗址的制陶技术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陶器是当时极为昂贵的器物,刻画于陶碗底部的树一定不是俗物,它要么是神树,要么是具有某种神圣象征意味的树。不管树形符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背后都有深厚的神树崇拜或信仰作为认知基础。由此可以断定,安徽蚌埠双墩文化遗址14件陶器上的树形刻画符号绝非当时人们随意而为之,而是出于对于神树的某种神话信仰而被创造的。不管这种神话信仰的具体内容如何,它皆与神木相关,并且与宇宙论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树形符号的形状来看,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的树形符号与安徽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玉树形状非常相近,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神树信仰在史前时期是非常普遍的。安徽凌家滩圣树玉树系新石器时代产物 (编号为87M4:68-1),距今约5300年左右,其造型(玉树图像参见图7)具有较强的象征意味。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提供的墓葬剖面图(图8)可知,安徽凌家滩编号为87M4的墓葬主人头向南而葬,玉树位于墓主的肚脐附近,与此玉树连的出土器物有编号为29的玉龟,编号为30的玉版(图9),编号为34、75-1、82的玉璜。根据图像相关性规约可知,这些图像的意义与其位置密切相关。位于肚脐附近的玉龟与玉版具有宇宙论象征意味,而这又与龟的形状相关。“龟有圆圆的穹拱形的背甲和宽平的腹甲,这与古代中国人认为天是圆拱形的,地是平的这个想法有所联系。”①[美]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2页。玉龟所在的位置象征着宇宙的中心,而玉版雕刻的内圆为八角星,小圆外接着大圆,外圆内刻画八个对称圭形纹饰的图像结构更进一步表明了肚脐象征宇宙中心的意味。至于编号为34、75-1、82的玉璜,其宇宙论象征意义显而易见。神话学界目前达成的一种共识就是,玉璜的形状与彩虹的形状非常相近,璜与虹发音相近,因此玉璜就是玉虹,虹是通天的神话动物,玉璜因此象征着通天的天桥。玉璜所在的位置自然就是宇宙中心,因为只有宇宙中心才是天地交汇所在,也是神人交往的通道。那么,玉树的作用也就明确了:它是宇宙中心的神话,也是墓主人登天的梯子。这种通过宇宙中心的宇宙神树抵达天界的理念并不限于史前时期的安徽,它在史前时期的四川地区同样普遍存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星堆遗址先后出土过八株青铜神树,这就意味着,圣树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图10)树干残高359、通高396厘米,青铜神树的底座为穹窿形,基座下部下呈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的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以此暗示神树生于圣山之中。青铜基座上雕刻着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上述符号暗示神树与天界相关。三星堆青铜神树的这种造型形象地表明它是一株接连天地的宇宙树,树上站立的神鸟、苍龙等神物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了这种属性。前文已经阐释,鸟类白天飞翔于天空,夜晚栖落与树枝间,其活动路线为上下垂直型,与太阳的运动路线类似。三层树枝间镶嵌的九只神鸟为沟通天地的使者,也是神树与太阳的伙伴。这样看来,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就叙述了这样一种神话宇宙论:宇宙以垂直方式分为天与地,有一株宇宙树位于作为天地中心的宇宙山上,它是连接天地的唯一通道,其间有神鸟、苍龙等神兽行走,它们来往于天地之间,传递两个世界的信息。就宇宙模式而言,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凌家滩玉神树描绘的宇宙理念是一致的,二者都将宇宙分为天堂与人间两个部分,并且皆将圣树视为连接天地的通道。
以比较神话学的视野来看,这种以圣树为中心的宇宙论是非常普遍的,圣树造型在世界各地的神话图像中尤为突出,迈锡尼时期的希腊各地普遍存在圣树图像,①各类圣树图像与相关阐释,参见Arthur.J.Evans,Mycenaean Tree and Pillar Cult and Its Mediterranean Relation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 21(1901),p.99—204.甚至在两河流域尼姆鲁德遗址也出土了亚述时代的圣树图像(图11)。尽管我们从图像中无法知道亚述圣树的具体所在位置,但从圣树身边站立的两位神明的保护性姿态可以知道,亚述的圣树是一株宇宙树,它是宇宙的核心。这棵宇宙树也是一株生命树,与宇宙的存亡相关,更是神明与人类交流的渠道。从以上圣树图像中能够看出,尽管世界各地的史前圣树图像在细节上有差异,但其所表达的宇宙论却如出一辙:宇宙以垂直方式分为天堂与人间两个部分,圣树位于天地之间,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单就这一点而言,史前圣树图像不啻为苏鲁豫皖四省石椁墓树图像的史前原型,而神树神话信仰则是其思想源头。
结 语
通过对苏鲁豫皖四省汉代石椁墓神树画像的分析可知,石椁画像中的神树实为神话中的宇宙树建木,更是亡灵升天的工具。催生此种图像类型的是汉代二分式神话宇宙论。此种宇宙论强调,宇宙被垂直划分为天界和人间,二者通过位于宇宙中心的神树而得以感通。天神是永生神明的世界,人间是必死凡人居住的空间。对于地上的人类而言,死者亡灵能够通过宇宙中心作为天梯的神话而升天,继而获得永恒不朽的生命。表面看来,二分宇宙神话宇宙论仅仅强调宇宙的空间结构,而未涉及时间层面的内容。深入分析便会发现,汉代石椁神树画像描绘的实际上是时间结构,因为它将天界刻画为死者亡灵最终的归宿地,人间则是死者生前生活的空间。上与下,天上与人间,二者对应的是人死后与生前,即彼世与今生两个时间段所在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汉代石椁神树图像的时间结构是借助于空间结构而得以表现的,画像内容表述的宇宙论为时空混同的神话宇宙论,与汉代神话文本《淮南子》 《山海经》等表述的神话宇宙论并无两样。
——中国历代玉璧纹饰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