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从“读书种子”到四大导师(上)
余灵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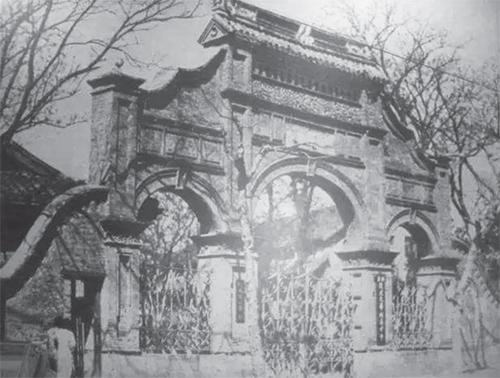

在留日大潮中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击穿了大清帝国深闭固拒的铜关铁锁,也催醒了一部分优秀士人去睁眼看世界。随着1901年更加屈辱的《辛丑条约》尘埃落定,“救亡图强”成为时代主旋律,一批批青年学子跨海渡洋,去向打败了中国的“先生”——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偷经学艺,以期收拾山河,振兴中华。这时,已从南昌移家江宁(南京)的陈三立也打算将两个儿子——衡恪、寅恪送往日本求学。他在1901年秋冬之交(《辛丑条约》刚签订不久)写有七律《晓抵九江作》以抒心志:
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
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鼾声邻榻添雷吼,曙色孔篷漏日妍。
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万峰巅。
这是一首直指《辛丑条约》的嫉世忧时之作,是没有问题的。其颔联、颈联直吐胸中愤懑而破腔排空,苍凉悲切又怀有希望。末句那高翔于万峰巅上的“啼雁”,正是其希望所寄。诗中“曙色”“啼雁”,既泛指当时的留洋或留日浪潮,又暗喻即将投入这个浪潮的两个爱子——他们既是国家复兴的希望,也是自戊戌维新以来遭到重创的义宁陈氏家族再度崛起的希望。
中日甲午战败后,举国震惊之余,人们开始瞩目日本。陈宝箴、陈三立倾力参与的戊戌维新运动便以日本为效法对象。日本政府为缓和甲午之后的对立情绪,遂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1896年,大清国驻日公使裕庚因使馆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翚、唐宝锷等十三人到日本留学,开留日之先声。到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一百四十三人。
从1901年起,鉴于《辛丑条约》带来的困境,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给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政府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救亡图存与发展自己的一条出路。而日本政府则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顺带获取一些外汇;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留日学生势如潮涌。据统计,1901年留日学生人数为二百七十四人,1902年夏为六百一十四人,1904年为一千四百五十四人,1905年冬为二千五百六十人;1906年夏为一万二千九百零九人,年底达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为留日学生人数的最高峰。
1902年3月24日,年仅十三岁的陈寅恪,在南京长江码头登上了日本轮船“大贞丸号”,幸运地成为皇皇留日大潮的一员。
作为世家子弟的陈寅恪,虽然家世已经没落,但仍能靠着亲戚的关系来赢取这次赴日留学的机会——尽管只是自费。这样的机会,举目四万万中国人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为他带来幸运的那位亲戚就是他的亲舅舅俞明震。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在陈寅恪出生那年的1890年中进士。这进士好像是专为小陈寅恪中的一样——在后者十三岁这年,俞明震已凭进士资历做了江南(南洋)陆师学堂兼附矿务铁路学堂的总办(即校长,实于1901年就任)。其时俞明震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赴日本视察学务,兼送江南陆师学堂及附矿务铁路学堂二十八名学生官费留学日本,于是顺便把两个外甥陈衡恪、陈寅恪送出国门,带到日本。
陈寅恪后来回忆说,他于赴日途中,在上海碰见了李提摩太——就是那位先前在中国大力鼓吹西学,狂热支持维新变法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用熟练的汉语夸奖陈氏昆仲的此次東洋求学:“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能得到这位差点成为光绪皇帝顾问的洋人如此称赞,少年陈寅恪当然“甚喜”;但当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在此,而是这位“老外”那口流利的京片子(即北京话)。这件看似不经眼的事,成为以后陈寅恪去发奋通晓十几二十国外语的一个重要诱因。
陈寅恪抵日后,即与长兄衡恪一道,以舅舅俞明震家族随员的名义,获日本外务省批给的“家族滞在”签证,以“听讲生”的身份,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同学中有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林伯渠、李四光等。是年底,衡恪获官费留学生名额,仍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两年后,即1904年夏,陈寅恪在暑期中返回祖国,同仲兄隆恪一同正式考取官费留日。是年秋,他再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5年冬,陈寅恪因脚气病日益严重,已不能再坚持学习,遂于寒假之时,与陈衡恪、隆恪一道从东瀛归国,此后再未踏上前后呆了三年多的这片所谓“日出扶桑”之土。不过衡恪、隆恪则于1906年返日继续求学,相继获得大学文凭;周树人、林伯渠、李四光等也先后学成归来,只有陈寅恪仅为弘文学院的高中肆业生,未有文凭。
陈寅恪求学日本的三年多是否失败了呢?不然。第一,这三年多,他已全面掌握了日语,这是他平生精通的第一门外国语言。第二,在这三年多,他大体了解并能剖析日本历史和社会风俗的流变及现状。第三,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对日本学术文化的由来、特点及其内容作有较深入探讨。有了这三个成就,陈寅恪留学日本就没有成为空话。因为有了这些铺垫,陈寅恪尔后才能顺利完成像《元白诗笺证稿》这类涉及日本文化的力著。更重要的是,由于陈寅恪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心理具有深刻认识,所以后来方能在抗战未起之时即识透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抗战中坚持民族大义,抗战末期为盟军出谋划策。
尽管如此,从当时的表象看,陈寅恪在日本的三年多求学可谓星光暗淡,这让望子成龙的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颇为不甘,一直耿耿于怀。这样就为陈寅恪更多的留学经历开启了大门,为他更远更为开阔的读书之路留下空间,为其最终修炼成“读书种子”埋下伏笔。
复旦的“学霸”
一个人日后的学术成就当然是和他的读书经历息息相关的,虽说这当中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那时作为父亲的陈三立,已经深谋远虑地为儿子们设计了多种前途。1907年,陈三立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儿子陈寅恪送到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的新兴大都会——上海读书。他的想法是陈寅恪如果不能去东洋看世界,至少也要到国内西学最为发达的地方去长见识。
“千年中国看北京,百年中国看上海”,百年上海浓缩了百年中国剧变的历史,并成为近代中国的象征,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陈寅恪从日本回到国内的1905年,上海正好诞生了中国学者独立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那就是由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建的复旦公学。以此为标志,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新中心。
这所刚刚成立的中国学者独立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化高等院校,成立之初,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自然云集了当时教育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包括一批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
复旦公学是从成立于1902年的原震旦公学分出创建的,教员和学生大多从震旦公学而来,所以复旦公学在刚刚创立的1905年基本上没有对外招生。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陈寅恪,能轻易地进入复旦公学中学部学习,其间家世背景和父亲与舅舅的精心运作起了关键性作用。
已经十八岁的陈寅恪也没有让父亲和舅舅失望。进入复旦公学之后,陈寅恪渐渐展露出超乎常人的学习天赋。这应该得益于其家学渊源及祖父和父亲的早年培养。
1893年—1894年,在陈寅恪只有四五岁时,便进入祖父陈宝箴任职地的武汉一家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895年祖父出任湖南巡抚后,还请到湘潭大儒周大烈专门教寅恪几兄弟读书。1898年祖父、父亲被罢官后,更是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对子孙的教育上。年幼的寅恪则把陈家和舅舅俞家的书房当成乐园,嬉戏之中亦能自觉承继家学,以捧读诗书为乐趣。
陈寅恪在复旦公学十分勤奋,加上与生俱来的天赋,很快便在班上名列前茅。这是因为他一直怀有去海外留学的愿望——日本留学的戛然而止,更加强了这个愿望。在现今保存的复旦公学中学部丁班的《考试第名册》(藏复旦大学档案馆)上,陈寅恪在1908年竟考出94.2分的高分,系班上第一名。这个成绩,比他的同桌、后来成为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的竺可桢(班上第四名)足足高出7.6分。还值得提及的是,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求学的四年间,亦是中学部的“学霸”,几乎各科成绩都是魁首。陈寅恪就这样第一次展示出那个年代“读书种子”的鲜明特征。
篙目时艰多乡愁
那个年代,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几乎成了上层社会教育后代,期望孩子学有所成的一种共识。虽说陈寅恪在复旦公学的学习成绩极好,陈三立还是毅然决然地让儿子中止学业,去国外留学。1909年秋天,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陈三立到上海亲自送儿子登上开往德国的轮船。此时的陈寅恪已经二十岁。他此次离开上海漂洋过海,目标与上次东渡日本相比,是更为明确,那心境自然也就大不一样。陈寅恪第一次留学时,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而这次已经是一个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的大小伙子了,可谓满怀抱负,心雄万夫。临别时,父亲以一首题为《抵上海别儿游学柏灵……》的古风相赠,中有“后生根器养蛰伏,时至傥作摩霄鹰”句,显然对远去的儿子寄予厚望。
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了几个月之后,陈寅恪顺利到达德国。踏上德国土地不久,1910年,陈寅恪就考上了柏林大学,开始学习语言文学。这一年8月29日,日本武力并吞朝鲜,颁布朝鲜贵族令。陈寅恪在柏林闻此消息,悲怅之中,写就一首古风,中有“长陵鬼馁汉社屋,区区节物复何有”“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句,对朝鲜的沦亡与清廷的无能扼腕叹息。这里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显见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唇亡齿寒式的悲凉,是对“清”这个老大天朝上国大厦即将倾覆的哀惋。是诗为现存陈诗中的第一首,蒿目时艰,忧心国难,满纸沧桑,开局便不凡。
进入柏林大学不到一年,1911年春天,陈寅恪的脚气病又犯了,需要转地治疗,从而离开了这所久负盛名的世界性大学。
于是陈寅恪到了挪威。陈寅恪虽然“脚气病重”,卻被北欧春天美丽的冰雪景致所吸引,在那里心旷神怡地游逛了二十多天。他自述“游踪所至,颇有题咏”,后来追忆起三首,其中一首尾联为“回首乡关三万里,千年文海亦扬尘”,乡愁系肠,令人欷歔。末句似对万里之外祖国方兴未艾的白话文运动表示关切,隐约感到天翻地覆的时代巨变即将来临。
陈寅恪在挪威住了二十来天,居然将长年困扰的脚气病疗养好了。他后来回忆此事,以为不可思议。1911年入夏不久,陈寅恪便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迷人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乘船横渡浩瀚的北海,入多佛尔海峡自加来登陆,进入法兰西共和国。他在这片曾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继文艺复兴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心的湿润的土地上盘桓有一二十天,沿塞纳河浏览了巴黎盆地及东的广袤的葡萄园、波光粼粼的大运河及沿河星罗棋布的建筑群,造访了诞生过伏尔泰、卢梭、雨果、巴尔扎克等人文大师及发生过热月政变、七月革命、《人权宣言》等重大事件的文化历史遗迹,虽是浮光掠影,却感触良多。1911年9月26日,陈寅恪在法国东北靠近德国的孚日山脉乘车观光,于山间小驿赋诗一首(题作《己亥秋日游Les Voges 山……》)寄友人,起首便是“一突炊烟欲暮时,万山无语媚秋姿”,语句清幽而凄迷。其意趣所向,并不止于异国的山光水色,更应是触景生情,由此及彼,对故土倾诉那无尽的牵挂与愁思——是诗颈联那一句“中原迢递事难知”,传达了个中消息。
他乡通读《资本论》
1911年秋,陈寅恪从法国边境进入卢森堡,再入德国,沿莱茵河溯流而上,抵达有“世界公园”之称的端士。10月初,陈寅恪在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完成了大学转读手续:从柏林大学转入苏黎世大学。后者建校历史虽仅有七十四年,却是瑞士规模最大、最富现代气息的综合性大学,名气甚至盖过瑞士最古老的大学——巴塞尔大学(建于1460年)。陈寅恪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就读,首先因为它是欧洲第一个由民主国家而不是封建君王或教会创办的大学,民主、多元、国际化是其显著特色,二是因为瑞士同时使用德、法、意三国语言为官方语言,而苏黎世大学也同时运用三国语言教学,这对其迅速掌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语言无疑是条捷径。陈寅恪认为,无论研究中华文化还是民族史、别国史抑或世界文化、中外交流史,首先就要过好语言文字关。这就是他常说道的:“读书须先识字。”所以,他十六年间游学西方,每到一国,排在其课程表首位者就是该国语言文字,其次才是该国的思想文化与学术。陈寅恪于幼年启蒙时期,即下苦功夫学习《说文解字》和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的训诂学著作(如《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四种),这为他后来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唐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小学基础。他在私塾读书期间,还向留日归来的大朋友学习过日语。他少年时两番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除继续提高日语水平外,更主要地是学日本文化及现代科学知识。
陈寅恪入苏黎世大学还未满一周,国内就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并号召各省起义,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消息很快传到欧洲大陆,英、法、德、意文的各种报纸纷纷列入头版头条争相报道。陈寅恪一看到报道,便立即赶到图书馆,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巨著《资本论》抱回寝室,日夜通读,很快就“啃”完了这部三卷本的大部头。《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在根本利益上互相对立的阶级,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马克思的这部书,花费了他毕生精力,其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而陈寅恪则在中国人中第一次通读完它的原版,亦堪称奇事。作为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尚处于初生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度的知识分子、且本人又是封建官宦世家子弟的陈寅恪,何以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这部经典著作抱以如此大的兴趣?这是今人一直不好理解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厘清陈寅恪面对旧制度、面对辛亥革命的态度问题。应该说,陈寅恪对清王朝所延续的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并无太深感情。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积极推进戊戌维新的终极目标,就是试图引进西方民主制度,改家天下的国家政权为君主立宪制,从而富国强兵,将国家引上近代化的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可是这一良好愿望却为当局所不容——绚丽的民主之花还未绽放,就被扼杀于摇篮之中。这种难以名状的委屈与伤痛十多年来像阴霾一样挥之不去,从陈宝箴、陈三立一直曼延到陈寅恪那里。虽说陈寅恪像父辈一样并不赞成革命党的激烈方式,但对过往的不甚愉快的记忆和对民主、自由、独立的向往以及年轻人特有的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使得他对旧政权的覆灭并不觉痛苦,反倒是乐观其成。1912年2月12日,当清帝宣告退位后,陈寅恪写了一首题作《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的七律,尾联即为:“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其与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心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陈寅恪在瑞士获悉武昌起义成功以后,竟然兴致勃勃地去恩嘉丁山欣赏雪景,归来后还赋七古一首(即《宣统辛亥冬大雪后……》),为后人留下一幅清新纯朴、不染纤尘、楚楚动人、秀色可餐的异国山水画卷。我们试读其中几句:“车行蜿蜒上绝壁,苍龙翘首登银台。杉松夹道戴冰雪,风过撞击鸣琼瑰。碧泉喷沫流涧底,恍若新泻萄葡醅。直须酌取供渴饮,惜我未办玻璃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陈寅恪面对旧制度灭亡的好心情——那简直就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而此时的他或许意识到自己在天地翻转、乾坤挪移的大变局中的历史责任,急需补充相应知识以应对,所以才急急赶到苏黎世大学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后来他在向学生石泉、李涵谈及此事时说:“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1]
陈寅恪早年读《资本论》一事,说明他是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并准备参与新世纪的建设。陈寅恪同他的父辈一样,从来就不是不问政治者。在他的血脉里,一直流淌着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火烫血液,壮怀激烈,凛然可敬!
“试水”新政权
1911年底,陈寅恪“因学费筹措困难”,不得不中止了在苏黎世大学的学习,从欧洲返回祖国。1913年春,他经西伯利亚再赴欧洲,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直到翌年秋,在长达十七八个月的时间里,陈寅恪都在这个大学的社会经济部学习。一个文史学者去学经济,看似怪异,其实不然。1935年10月,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拾卷第肆期发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熟稔地“考释唐代京外官俸制不同之问题,及证明肃(宗)代(宗)以后,内轻外重与社会经济之情势”,应该与他二十多年前在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的动态分析等方法及工资理论等有关;再往上溯,还应与1911年在苏黎世大学读《资本论》、学政治经济学有关。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今为波黑首都)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刺死;7月,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8月,德、俄、法、英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并很快席卷欧洲,波及亚洲、非洲。恰逢此时,陈寅恪接到江西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电报,要他回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陈寅恪于是匆匆赶回祖国,以应新政权的召唤。审阅留德学生考卷的工作连续进行了三年,但每年都有很长的休息时间。这期间,陈寅恪于1915年春赴京,短暂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督办、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蔡锷的秘书。这里面有个小插曲,就是陈寅恪在担任蔡锷秘书期间,他早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周树人即鲁迅,也在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连续赠送他在日所出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第二集以及齐寿山《炭画》一册。鲁迅与陈衡恪(即陈师曾)是知交,又与寅恪同船赴日留学,故有赠书之举。此事见载于鲁迅《乙卯日记》一九一五年四月六日条,但未见陈寅恪提起过。个中原因,无从得知。
1915年11月,蔡锷在梁启超和小凤仙的帮助下,金蝉脱壳,挂冠而去,经天津东渡日本,旋又南下云南,成功脱离袁世凯的控制。蔡锷出走后,陈寅恪即于1916年至1917年在长沙出任湖南省公署交涉股股长。这段时期,除南昌阅卷外,陈寅恪的后两项工作应该算是从政吧!这说明陈寅恪对取代清王朝的以“共和制”标榜的新政权是拥护的,并投以相当大的热情参与其中。
不过,蔡锷于1915年冬的出走,给陈寅恪很大的冲击。这一年,袁世凯酝酿称帝;12月便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戴戡等在昆明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以讨袁为号的护国战争迅即震响半个中国。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怒潮中忧惧而死。一场闹剧终于落幕。此时离中华民国的诞生不过四年又四个月,历史却走过了从民主共和重返专制独裁再返共和的曲折而荒唐的坎坷路。这令以满腔热血参与新政府工作的陈寅恪大为失望。他对像袁世凯这样的满嘴国家大义、一肚子祸国心肠的宵小之徒以及投机取巧之人很是蔑视,对“共和”与“民主”的旗帜还能打多久极为忧虑。1916年夏秋之际,陈寅恪有《寄王郎》诗一首,可看出他这期间已对新政权渐生疏离之意:
泪尽鱼苦不辞,王郎天壤竟成痴。
只今蓬堁无孤托,坐恼桃花感旧姿。
轻重鸿毛曰一死,兴亡蚁穴此何时。
苍茫我亦迷归路,西海听潮改鬓丝。
是诗文字圆熟而轻俏,意绪黯然而惆怅,显出作者对白云苍狗般的世事变迁的惊诧与无奈。其颈联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泰山”“鸿毛”典及《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五淳于棼“槐梦”典,讥袁世凯复辟梦;尾联则讲他于苏黎世大学听闻国内革命涛声,归来却是风景煞人,颇有李贺“我有迷魂招不得”的韵味,但是又有谁能解开他那“當孥云”却无路的少年心结呢?
陈寅恪于1915年至1917年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工作,应是他对问政、从政的人生选择的一种“试水”。这种“试水”由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而告结束。陈寅恪从此与陈宝箴、陈三立的入仕报国的理想决绝,心无旁骛地走上学术救国的道路。
注释:
[1]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98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