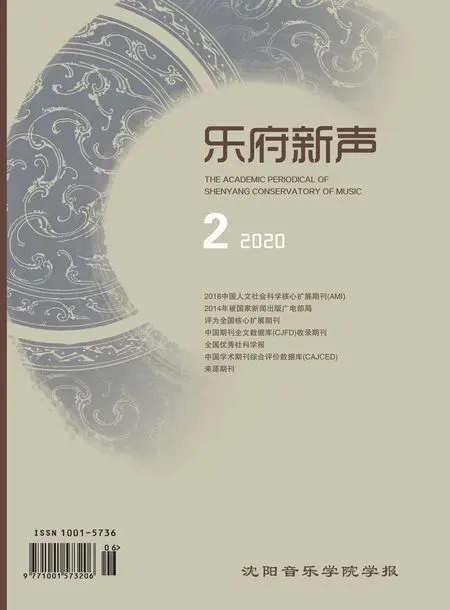卡特早期交响曲创作中的平民化倾向及其成因探微
邓连平
[内容提要]在关于卡特音乐创作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大部分都聚焦于他中后期的创作,而对他早期的音乐关注较少。但若要深入了解卡特整个创作生涯的情况以及他思想观念的转变,就必然要对他早期的音乐进行考察。本文就从他早期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入手,探寻其中不同于他中后期创作中的平民化倾向,分析该倾向的具体表现形态,并从政治、环境、历史等多视角对这一倾向的成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提起卡特,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想到他中后期音乐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艰涩与复杂。毋庸置疑,这种艰涩与复杂不仅是他中后期一贯坚持的创作理念,同时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特别是他的“速度转换”(Metrical modulation,又译作“韵律转换”等)之技法,更是成为他创作技法中的重要标签。但是,卡特的此种风格并非始终如一,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与他中晚期相对晦涩的创作风格相比,他早期的交响曲则体现出“平凡”的一面。在早期,他秉持一种让“许多人可能会理解和轻松享受[2]Allen Edwards.Flawed Words and Stubborn Sounds:A Conversation with Elliott Carter.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72,p.57-58.”的创作态度,追求音乐的大众化、平民化,他的《第一交响曲》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与直接体现。
所谓平民,“泛指普通的人(区别于贵族或特权阶级)[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 版)[M].商务印书馆,2005:1053.”,与“庶民”(《尔雅·释言》:“庶,侈也”)含义相近,主要指与人数寡少的精英阶层相对的人群。而关于平民的社会思潮——平民主义(Democracy或populism),在全世界范围都曾出现,比如,在中国,以李大钊先生为首而提出的平民主义思想,不仅牵涉到政治运动,而且对政治之外的文化、经济、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音乐领域内诸如黎锦晖、刘天华、萧友梅、赵元任等大家人物都曾为此努力奋斗过,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音乐财富。在这些以倡导平民音乐思想的作品中,大多以白话文作为歌词,并从民间音乐中提取素材,最大限度地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表达底层人民的情感诉求。在美国,平民主义运动发生在19 世纪70 年代初至19 世纪末,在这场运动中,经济底层的农场主通过抵制垄断,从而极力地维护平民群体利益。由此可见,尽管各国的平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各异,但本质大体一致,都以追求民主、平等以及反精英主义为目的。
从音乐发展的历史来看,音乐自产生之时并没有雅俗之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类阶层的差异化,才导致了音乐的受众逐渐出现了分化,开始有了民间与专业、通俗与雅致、传统与现代等区别。在芸芸众生中,精英阶层由于经济的优越性,往往有着良好的音乐教养,甚至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他们大多以诸如精致的室内乐、艺术歌曲以及技法复杂的交响乐、歌剧为主要的音乐精神食粮。而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以及知识层次的局限,则主要以民间歌曲或简单的器乐重奏等艺术形式为主要消遣方式。相对于精英阶层,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平民更喜欢音乐中清晰流畅的旋律、透明简练的织体以及通俗易懂的音乐语言。而交响曲,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艺术形式,由于它思想内容的深刻性、结构形式的缜密性以及管弦乐手法的丰富程度,一直以来,更多的是作为精英阶层所热衷或推崇的一种艺术消费品。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或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与考虑,作曲家在为交响曲进行创作时,为了扩大受众面,照顾到平民阶层的欣赏诉求,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平民化倾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卡特的《第一交响曲》就是朝这方面做出的一次努力尝试。
一、平民化倾向的表现形式
在卡特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创作了三部以“交响曲”命名的作品,分别是《第一交响曲》(1942)、《三个管弦乐队的交响曲》(1976)以及《交响曲:我是流动希望的奖品》(1993-1996)。从创作风格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技法差异。在早期创作的《第一交响曲》中,卡特作为从法国学成归来不久的学生,在创作中还明显地存留有其它前辈作曲家创作手法的影子,比如斯特拉文斯基对非节拍重音的运用以及巴托克对调性叠置的处理等等。从总体技法来看,卡特的《第一交响曲》具有十分明确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它节奏相对较为均衡,配器清淡,织体透明,音高语言建立在自然调式的基础之上。作品存在的调性叠置以及变拍子、复合节拍等现代技法也属于新古典主义时期主流作曲家的典型做法。比如下例:
例1.《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第83-90 小节的变节拍现象

在这个片段中,前四小节木管演奏前景旋律,弦乐用同音反复的音型作陪衬,作曲家为了突出前景旋律中每一个小音组的音头,频繁变换重音,从而使得音乐在表面拍号2/2 拍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内在的节拍律动,形成了变节拍现象,先后出现3/4、4/4 的节拍交替,并引出随后的长号独奏。在后四小节中,长号通过变节拍,出现了5/4、3/4、2/4、2/2 的强弱律动,为原本以平白单调的四音组为单位的音型重复带来了丰富的变化。
除了新古典主义的典型做法之外,在《第一交响曲》中,还表现出一些平民化的音乐特征,这在第三乐章中尤为突出。首先,从乐章主题来看,上行的分解和弦式进行以及之后的同音反复音型与莫扎特的《d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主题有着某种相似的气质,而且在伴奏和声上,也极为清淡。这种怀旧的做法,在吸引民众的注意以及帮助民众理解音乐等方面无疑大有裨益。
例2.卡特《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主题与莫扎特《d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主题

其次,在音高的处理与选择上,作曲家引入了美国流行音乐的一些元素,比如爵士乐中的“蓝音[1]丁铌.爵士乐——美国古典音乐[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63.”。在美国的蓝调(Blues)音乐中,降三度音、降五度音与七度音被称之为“蓝调三音”、“蓝调五音”与“蓝调七音”,也被统称为“蓝音”(Blue note)。因为这三个音在实际演奏中,可以略高或略低,常常通过滑音的手法使其具有特殊的韵味,它们作为特征音级广泛应用于各种蓝调音乐中。这种音调的运用不仅带来了丰富的色彩变化,而且由于其浓郁的布鲁斯风味,从而极大地拉近了音乐与平民大众之间的距离。比如第三乐章主部主题中主音上方的降三度音以及单簧管伴奏中的降七度音、降五度音与降六度音。
例3.《第一交响曲》第1-9 小节单簧管和小提琴声部

再次,在节奏的运用上,第三乐章也显得十分简明,大范围纵向整齐的节奏与偶尔带有布鲁斯音乐特征的切分节奏交替出现,使得音乐的主题旋律清晰明朗,同时又不乏通俗流行的意趣。比如下例中,木管组乐器与小提琴声部基本保持均等的四分音符节奏,小提琴以同音反复的静态音响衬托上方木管组乐器活泼跳跃的主旋律。而相对应的中、大提琴声部,却通过跨小节的连续切分,将上方声部建立的节奏律动充分打乱,用具有摇摆性质的低音节奏附和着上方相对稳定的音响,从而加强了乐章中的流行音乐风味。
例4.《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第70-75 小节节奏缩谱

在织体形态方面,乐章以主调性织体为主,但为了增强乐曲的通俗性倾向,作曲家在作品的某些地方又借鉴了民间音乐中极富趣味的重奏织体形式。
例5.《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第221-230 小节

上例是建立在低声部主属持续音上的一段模仿美国民间常见的二重奏,音乐十分生动活泼。长笛与单簧管以短促的三音组为基本单位,时而同度齐奏,时而相互错开,形成卡农式模仿。从而体现出民间二重奏中既相互竞赛又相互合作的诙谐气质。此外,其中休止符的巧妙运用,使这段二重奏听起来更加接近民间演奏形式中所特有的即兴性成分。而在发音点的处理上,卡特在多处设计了类似我国民间音乐中“鱼咬尾”的衔接方式,既是为了音乐的连贯,也模仿出民间艺人演奏中的趣味性。
最后,在音乐的整体结构安排上,作曲家为了让主题多次出现,加深主题在听众心中的印象,在第三乐章中采用了回旋性结构。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前两个乐章在结构上也有类似的安排,第一乐章的变奏性结构与第二乐章的三部五部性结构都具有主题的多次反复这一特征,这种具有主题多次再现或变化再现的结构形式其实也是平民化思维的一种具体表现。
总之,作曲家在《第一交响曲》,特别是第三乐章中的做法真实地流露出他当时为大众而写的创作理念。上述这些音乐特征以及相对应的创作手法的运用对于增强音乐的可理解性与扩大音乐的受众面大有裨益,从而使整个作品具有雅俗共赏的气质,这与他战后的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平民化倾向的成因
反观卡特早期的生活经历与学习历程,他在《第一交响曲》中所表现出的大众化创作倾向似乎与他早期追新求变以及对现代音乐的浓厚兴趣并不相一致。早在他十几岁就读于贺拉斯曼中学(Horace Mann School)时,就十分迷恋现代音乐,惊奇于现代音乐所具有的紧张度与力量,并立志日后成为一名作曲家。在1924 年初次跟艾夫斯见面之后,艾夫斯就在他们偶尔的碰面之时在卡特面前弹奏以及讨论现代音乐,这种生活经历更是为卡特开启了通往现代音乐的大门。1925 年夏季,卡特跟随其父亲去维也纳旅行时,他仍然不忘从当地搜集当时在纽约还不能经常看到的一些作曲家的乐谱,比如勋伯格、贝尔格以及韦伯恩等人的序列音乐作品,并开始研究它们。除了新维也纳乐派之外,卡特还在这一时期接触到其它国家一些现代作曲家的作品,比如匈牙利的巴托克、美国的拉格尔斯(Carl·Ruggles,1876-1971)以及瓦雷兹、苏联的斯克里亚宾与斯特拉文斯基等等。当卡特于1926 年进入哈佛大学之后,该校音乐系老师所持的保守态度远远不能满足他对现代音乐的渴望,为了更加便利地去听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的现代音乐,他舍弃了哈佛大学音乐系的课程,进入离波士顿交响乐团更近的隆基音乐学校(Longy School of Music)学习音乐理论与双簧管。1935 年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之后,由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持续影响,卡特为了生计,于1936 年底至1946 年夏季期间签约成为《现代音乐》的供稿者,这不仅解决了他经济上的困境,而且让他有更多机会去现场聆听各种形式的现代音乐。
从上述的种种经历来看,卡特在其早期对现代音乐的痴迷程度一直未减。按照这种发展逻辑,卡特在创作《第一交响曲》时,应当以更为激进的现代音乐技法作为其表达手段。然而,事实恰好相反,卡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早期转入一个短暂的创作阶段,他避开先锋派激进的笔调,退回到古典主义,以调性语言作为其创作的基础,追求清晰、简朴、明快的音乐风格,顾及普通民众的欣赏需求。之所以会如此,我想这里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受战争环境的影响
在卡特的《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首演后不久,二战爆发(1939 年9 月)。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心系民众,想方设法投身于战争,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1941 年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即便当时卡特还在圣约翰大学担任教职,他都尝试去参军,但由于健康原因被拒绝。在一次采访中,卡特表示他有过敏史,并对记者说:“这让我十分愧疚,所以我尝试各种途径去加入到战争中[1]Carter.In an interview with Nicholas Wroe,Guardian,6 December 2008,http://www.guardian.co.uk/music/2008/dec/06/Elliott carter classical music.”。之后,由于学校的教学任务严重地影响他创作的时间,他又于1942 年夏季离开了圣约翰大学,隐退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在那里,他开始尝试“以一种故意受限的音乐语言”去写作。与《波卡洪塔斯》不同,这是一种对于普通音乐听众来讲,更为容易理解的音乐。卡特这种短暂的创作倾向的直接结果就是1942年的《第一交响曲》。
在1943 年,他与妻子定居纽约后,仍然非常想用自己的外语知识服务于军队的情报机构,但在相关的测试中又落选了。最终取得的一项工作是作为音乐顾问服务于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这项工作始于1943 年后期,直到1944 年6 月6 日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当1944 年8 月巴黎解放的消息传到美国之时,卡特受此鼓舞,快速地写了一首管弦乐作品,即《假日序曲》。该作品如同这一时期创作的《第一交响曲》以及少数其它的作品——几乎都为声乐作品,比如《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三首诗歌》(1942)、《早晨的和声》(1944)——一样,是卡特真诚地希望能被所谓的普通听众接受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卡特,音乐中完全没有现代音乐所应有的刺激、不协和之感,与他四十年代后期所创作的音乐截然不同。
在多年之后,卡特在谈及《第一交响曲》时,说道:“当我离开巴黎之后第一次开始写作时,我写的作品相对容易接受和理解……最近,著名爵士乐作曲家艾灵顿(Duke Ellington,1899-1974)在听完《第一交响曲》之后握着我的手说’我认为你开始理解爵士乐了’。[2]Alan Baker.An interview with Elliott Carter.American Public Media,July 2002.”从卡特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当时在《第一交响曲》中追求简单易懂的创作思路。
面对人类浩大的灾难,作曲家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不免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往往以灵敏的艺术嗅觉去捕捉社会重大事件中的各种现象与形态,从而用他们自己的笔触表达出他们内心的各种情绪与反应。比如在俄国,比卡特大两岁的肖斯塔科维奇于战火纷飞的列宁格勒中写出以战争为题材的恢宏巨作——《第七交响曲》(1941),乐曲中恢宏的气势以及最后以俄军胜利的象征性结局极大地鼓舞了在前线殊死抗敌的官兵,为俄军最后的突围胜利起到了不可忽略的精神作用。在中国,鼓舞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黄河大合唱》(1941)同样是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它以黄河为背景,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斗志与英勇形象。而《华沙幸存者》(1947)则是身处异国他乡的勋伯格用夸张的笔调对战争暴行赤裸裸地揭露与谴责。
与上述一些战争题材的作品相反,卡特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以《第一交响曲》为代表的一些作品既未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那样拥有宏大的篇幅与气势,也不像《华沙幸存者》那样辛辣与极端,而是以一种相对通俗易懂的音乐语言,精致、细腻的配器以及简明的织体形式,来表达作曲家对战争受害民众的人文关怀。他这一时段的音乐如同一注清新剂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了战时人民的受伤心灵,表达出卡特当时的社会责任感。
(二)受科普兰的影响
科普兰(Aaron Copland,1900-1990)作为布朗热(Nadia Boulanger,1887-1979)的第一个美国学生,也是布朗热最为得意的门生之一,在返回美国之后,积极创作,迅速地在美国作曲家群体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在他早期偏重复杂抽象的实验性创作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恶化,经济、政治危机的加剧以及战争的临近,科普兰的创作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他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坦言:“在那几年(1930-1935),我开始对爱好音乐的听众和活着的作曲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感到不满。……我觉得我们作曲家面临着在真空中工作的危险,……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继续写作,不管他们,就像他们不存在似的。我觉得应该努力试一试,是否可以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表达我要表达的事情。[1]Aaron Copland.Our New Music.New York,Whittlesey House,1941,pp.228-229.”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比 如《墨西哥沙龙》(1933-1936)、《比利小子》(1938)以及《阿巴拉契亚山的春天》(1944)等,一改他早期客观、理智的创作风格,通过在作品中运用美国民间或大众化的曲调,从而使这些创作带有浓郁的美国民族特色,深受普通民众喜爱。
作为科普兰的同代人,卡特比科普兰小八岁,而拜在布朗热门下却比科普兰晚了整整十余年。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科普兰作为师兄,他的创作对卡特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以致在卡特接下来的创作中,比如1942 年创作的《第一交响曲》与1944 年创作的《假日序曲》,完全步其后尘,将自己置身于科普兰的影响之下。
除此之外,科普兰对卡特的影响还体现在舞剧《波卡洪塔斯》的演出失败以及由此带给卡特的创作反思上。卡特的《波卡洪塔斯》创作于1939 年,不幸的是,《波卡洪塔斯》的首演与科普兰的《比利小子》被安排在同一个晚上。后者是美国音乐的一种全新形式,与艾夫斯、超现代主义以及欧洲现代主义的风格都不相同,音乐通俗易懂。而卡特的《波卡洪塔斯》则相对较为晦涩、技法生硬,其中糅合了多种不同的音乐风格:乐曲开始不协和的和声以及弱拍上的重音带有浓厚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野蛮气息,当英国人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与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出场的时候,音乐立刻转变为欣德米特式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和声干涩、不协和,强调线性对位);而主角波卡洪塔斯的音乐则又具有浓郁的美国流行音乐风格,充盈着爵士乐的华彩性段落;在乐曲的高潮处,艾夫斯音乐中所具有的混乱与嘈杂又成了音响的主体。整部音乐犹如一个混搭体,与科普兰的《比利小子》相比,显得十分的不协调。
这两部芭蕾舞剧音乐同时首演对于卡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卡特后来写道,《波卡洪塔斯》“由于不和谐,属于无法被理解的、陈旧的风格,而被忽视,然而科普兰的芭蕾舞剧被称赞为表达一种新的,更为透明和容易理解的风格”[1]Carter Elliott,Bernard Jonathan W.Elliott Carter:Collected Essays and Lectures,1937-1995 Eastman Studies in Music,1071-9989.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ublisher,1998,p.205.。由于科普兰的消极影响,卡特在纽约过得并不如意。科普兰在他的著作《科普兰1900-1942》中无意提到一个细节,他引用了自己给指挥家库塞维茨基(Sergey Koussevitzky,1874-1951)的一封信的内容,其中谈到《波卡洪塔斯组曲》——“我无须告诉你这部作品的质量,因为你自己可以看得出(言下之意,指这部作品质量低下)[2]Aaron Copland and Vivian Perlis.Copland 1900-1942.London,England,St.Martin's Press,1984,p.283.”。此外,科普兰还从他的著作《新音乐1900-1960》中删除了有关卡 特的言论。对此,卡特曾在一封信中“感谢”科普兰删除这些内容,“因为通过这些可以十分清楚的知道我的音乐是朝着相反的方向[3]Aaron Copland and Vivian Perlis.Copland Since 1943.London,England,St.Martin's Press,1990.p.296.”。
正是因为科普兰有意或无意的影响,卡特才认识到,像《波卡洪塔斯》中的这种创作方法在听众中并不受欢迎,而科普兰简约、清晰的创作观念恰好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范与创作导向。如此一来,才有了后来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假日序曲》等相对较为通俗、平民化的一系列作品。当然,这也可以看做是卡特对听众反馈信息的一种回应,体现出他当时短暂地迎合大众、服务于普通民众的创作理念。
结语
由上文可以看出,卡特早期交响曲创作中的平民化倾向是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的产物,从他整个创作生涯来看,由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创作只占其中一小部分。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美国实验性、先锋性创作的不断涌现,他越来越意识到寻求既往风格的突破点、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化音乐语言对他在美国乃至世界乐坛的话语权和地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从他的《钢琴奏鸣曲》开始,他笔锋一转,开始踏上了“卡特式”风格漫长的探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