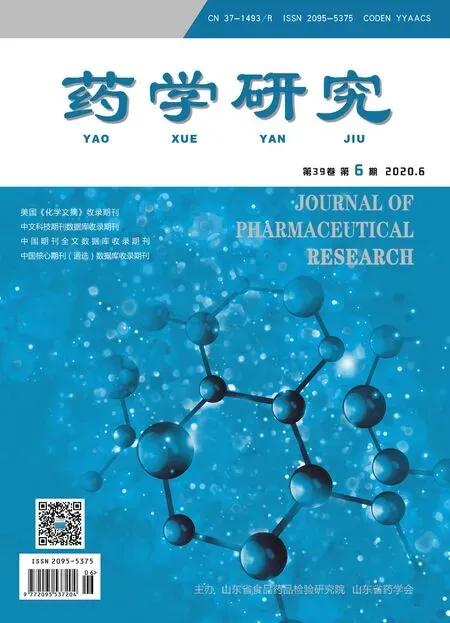靶向铁死亡的癌症疗法
全菲,杨勇
(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科学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1198)
细胞死亡对维持机体正常发育、内稳态以及预防过度增生性疾病(如癌症)等至关重要。调节性细胞死亡(regulated cell death,RCD)过程受专门的分子机制调节,因此可通过特定的药理学方法或基因干预进行调控[1]。铁死亡的发现源于小分子erastin对癌基因RAS突变的细胞具有致死选择性,大量铁依赖性脂质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致死性累积是其主要特征,可被铁螯合剂去铁胺(deferoxamine,DFO)和脂质ROS清除剂ferrostatin-1所抑制[2]。研究表明,除RAS外的其他致癌因素也与铁死亡信号通路有关,此外部分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抗癌药物已鉴定为铁死亡的诱导剂[3-12],因此靶向铁死亡成为一种有前景的癌症治疗策略。随着对铁死亡调节机制的深入探索,不同类型的铁死亡诱导剂应运而生,为触发癌细胞铁死亡提供可行性。本文将阐述影响铁死亡的主要代谢途径,并综述靶向癌细胞铁死亡的研究进展。
1 铁死亡调控机制
自2012年提出铁死亡的概念以来[2],大量研究显示,其主要的调节机制和信号传导途径包括铁离子的转运以及脂质ROS的产生与清除,此外含铁蛋白的分解、辅酶Q10(coenzyme Q10,CoQ10)的合成以及谷氨酰胺分解代谢也影响癌细胞对铁死亡诱导剂的敏感性(见图1)。
1.1 铁代谢 铁是人体正常生理活动所必需的,然而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铁离子可通过催化可溶性脂质自由基的形成,以酶促或非酶促的方式氧化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PUFAs)。一方面胞内不稳定铁池主要由Fe2+组成,Fe2+参与芬顿反应所产生的OH·是一种具有高度流动的水溶性ROS,可启动脂质过氧化;另一方面铁和铁的衍生物如血红素或铁硫簇,也对产生ROS的酶如NADPH氧化酶(NADPH oxidases,NOXs)、脂氧合酶(lipoxygenase,LOXs)和线粒体电子传递链复合物的活性至关重要,因此细胞对铁的摄入、储存和利用可影响胞内有毒的游离铁水平[13]。
胞外铁可由血清中的转铁蛋白(transferrin,TF)通过相应受体TFR介导的内吞作用转运至胞内。铁调节蛋白(iron-regulatory proteins,IRPs)能精确感应胞内的铁稳态,在铁离子浓度下降时与铁反应元件(iron-responsive elements,IREs)结合,阻遏铁蛋白(ferritin,FT)的合成。FT充当贮库,储存过量的铁并在需要时动员游离铁。虽然铁转运蛋白(ferroportin,FPN)是哺乳动物细胞唯一的铁输出蛋白,但近期研究表明,FT也可经外泌体转运至胞外,释放游离铁。研究显示,在多种癌细胞中发现FPN的下调和TFR1的上调,使癌细胞对铁的需求高于非癌细胞,这种“铁成瘾”使癌细胞更易受铁过载和ROS累积的影响[3,14-15]。
1.2 脂质代谢 PUFAs的丰度和位置决定了细胞中脂质过氧化的程度。脂质组学表明,含有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或肾上腺酸(adrenic acid,AdA)的磷脂酰乙醇胺(phosphatidylethanolamines,PEs)是铁死亡中发生过氧化反应的主要底物。长链脂酰辅酶A合成酶4(Acyl-CoA synthetase long-chain family member 4,ACSL4)将AA或AdA活化为花生四烯酰-CoA和肾上腺酰-CoA,再由溶血磷脂酰胆碱酰基转移酶3(lysophosphatidylcholine acyltransferase 3,LPCAT3)将这些衍生物酯化为PEs,形成AA-PE和AdA-PE并入膜磷脂,最后被LOXs氧化为脂质氢过氧化物,执行铁死亡[16]。
脂质过氧化物可能通过两种机制对癌细胞产生毒性:分子水平上,脂质氢过氧化物可能分解为4-羟基-2-壬烯醛或丙二醛,破坏蛋白质;结构上,脂质的广泛过氧化使生物膜变薄和曲率增加,并进一步氧化,最终形成膜孔和胶束[17]。
1.3 抗氧化代谢 作为细胞内重要的抗氧化剂,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的水平影响脂质ROS的清除效率,而胞内半胱氨酸的耗竭,可导致GSH合成减少。氨基酸反向转运系统Xc-由12次跨膜蛋白溶质载体家族7成员11(solute carrier family 7 member 11,SLC7A11)和跨膜调节蛋白SLC3A2通过二硫键链接而成,谷氨酸和胱氨酸以1∶1的比例在细胞膜两侧通过系统Xc-进行交换,铁死亡小分子诱导剂erastin可抑制SLC7A11,减少细胞对胱氨酸的摄入[18]。除了利用系统Xc-外,部分癌细胞也可在胞外半胱氨酸缺乏的情况下,利用富余的蛋氨酸通过转硫途径(transsulfuration)合成半胱氨酸,因此这些细胞对系统Xc-抑制剂具有抗性[19]。Xc-下游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lutathione peroxidase 4,GPX4)是细胞膜的监护员,辅助GSH将有毒的脂质氢过氧化物转化为无毒的脂肪醇。GPX4对硒代半胱氨酸的利用赋予其出色的抗铁死亡特性,硒代半胱氨酸活性部位的合成与甲羟戊酸途径相关[20]。
胞外高浓度的谷氨酸能抑制系统Xc-对胱氨酸的摄入,虽然谷氨酰胺经分解能产生L-谷氨酸,但胞外高浓度的谷氨酰胺并不能诱导铁死亡。有研究表明,抑制癌细胞对谷氨酰胺的摄入或谷氨酰胺的分解有助于抵抗铁死亡,且仅与谷氨酰胺酶2(glutaminase 2,GLS2)相关[14]。另外,谷氨酰胺分解的代谢产物α-酮戊二酸(α-ketoglutarate,αKG)也参与铁死亡,尽管线粒体在铁死亡中的作用存在争议,但αKG回补三羧酸循环中的富马酸酶是肾癌中重要的肿瘤抑制蛋白[21]。
除GSH-GPX4抗氧化系统外,新发现的铁死亡诱导剂FIN56提出了铁死亡发生的其他机制,FIN56同时耗竭GPX4和甲羟戊酸途径产生的CoQ10,CoQ10是内源性的脂溶性抗氧化剂[22]。最近研究表明铁死亡抑制蛋白1(ferroptosis suppressor protein 1,FSP1)经过豆蔻酰化修饰靶向细胞膜,还原质膜CoQ10,以平行于GPX4的方式抑制脂质过氧化,是强效的铁死亡抑制因子,也是多种癌细胞抗铁死亡的生物标志物[23]。
核因子红系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调节细胞抗氧化,是一种关键的抗铁死亡转录因子,激活p62-Keap1-NRF2通路可抑制肝癌细胞发生铁死亡。NRF2正向调控铁稳态相关基因如血红素加氧酶1(heme oxygenase 1,HMOX1)、FTH1、FPN,以及GSH合成相关基因如SLC7A11等[24-25]。最近发现的ferroptocide,是NRF2靶点之一硫氧还蛋白的抑制剂,可诱导多种癌细胞发生铁死亡,属于新型的铁死亡诱导剂[26]。
2 (抑)癌基因与铁死亡
(抑)癌基因与铁死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证明了铁死亡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为诱导肿瘤细胞铁死亡提供了更多的靶点。
2.1 p53 p53是人体重要的抑癌基因,几乎在一般以上的人类肿瘤中可检测到p53的突变或失活,其主要通过转录或翻译后机制调节铁死亡。在细胞应激状态下,p53通过抑制SLC7A11的转录来抑制对胱氨酸的摄取,从而使细胞对铁死亡更加敏感。p53乙酰化缺陷型突变体p533KR显著下调移植瘤中SLC7A11的蛋白和mRNA水平,野生型p53可被高水平的E3泛素-蛋白连接酶鼠双微基因2(mouse double minute 2,MDM2)蛋白降解,设计能够干扰或阻止p53-MDM2相互作用的亲脂小分子已成为癌症治疗的重要目标[4]。p53促进亚精胺/精胺N1-乙酰基转移酶1(spermidine/spermine N1-acetyltransferase 1,SAT1)的转录,而人类肿瘤中SAT1发生下调,过表达SAT1可促进脂质过氧化诱导的铁死亡,SAT1与花生四烯酸15脂氧合酶(arachidonate 15-lipoxygenase,ALOX15)的表达相关,但p53-SAT1--ALOX15具体机制仍不清楚[5]。在非应激和应激条件下,p53均可促进GLS2的转录,肝细胞癌中GLS2的表达显著降低,过表达GLS2则显著减少肿瘤细胞的集落形成,同时GSL2是一种新的小GTP酶Rac1蛋白的负调控因子,介导p53抑制肿瘤转移的功能[6]。p53阻断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2(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2,SREBP-2)的激活,而SREBF-2调控甲羟戊酸途径,p53功能缺失突变会使甲羟戊酸途径更加活跃,增加肝癌的患病风险[7]。
在一些癌细胞中p53是铁死亡的负调控因子,erastin诱导人结直肠癌细胞发生铁死亡的过程中,野生型p53可与核内的二肽基肽酶-4(dipeptidyl-peptidase-4,DPP4)结合促进SLC7A11的表达,而p53的缺失阻止DPP4的核聚积,使膜相关DPP4与NOX1结合触发脂质过氧化[8]。p53通过调节CDKN1A(编码p21)的转录,延缓了人纤维肉瘤细胞由胱氨酸缺乏所诱导的铁死亡,MDM2抑制剂可增加p53的表达,阻断由系统Xc-抑制剂所诱导的铁死亡[9]。
2.2 BRCA1 肿瘤抑制因子BRCA1相关蛋白1(BRCA1 associated protein 1,BAP1)的核上调与肿瘤侵袭性相关。BAP1编码一种核去泛素化酶,可减少染色质上组蛋白2A泛素化(H2Aub),BAP1依赖去泛素化的方式减少SLC7A11启动子上H2Aub的占有率,抑制SLC7A11的表达。BAP1功能缺失与肾透明细胞癌、眼部肿瘤、胆管癌、间皮瘤等癌症的发生有关[10]。
2.3 RAS RAS是癌症中最常见的突变癌基因,RAF激酶抑制剂索拉非尼(sorafenib)[27]在美国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肾细胞癌,诸如erastin之类的铁死亡诱导剂在致癌基因HRAS、KRAS或BRAF突变的人类肿瘤细胞中表现出更强的杀伤力。最近研究表明,高迁移率组蛋白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HMGB1)通过RAS-JNK/p38通路调节铁死亡,是治疗白血病的潜在药物靶点[28]。这表明RAS-MAPK信号通路在介导肿瘤细胞铁死亡的发生中具有重要地位,RAS下游信号分子的抑制剂或可能是重要的抗癌药物。
3 铁死亡诱导剂的抗癌效应
研究表明,部分小分子化合物和FDA已批准的药物可诱导肿瘤细胞发生铁死亡。系统Xc-和GPX4是开发铁死亡诱导剂的重要靶标,干扰铁代谢相关通路或借助纳米材料直接向肿瘤细胞“输送”铁离子,也可增加肿瘤细胞对铁死亡的敏感性。
3.1 系统Xc-抑制剂 Erastin是最早发现的系统Xc-抑制剂,能有效抑制小鼠体内卵巢肿瘤的生长[29]。有研究表明在现有的系统Xc-抑制剂中,erastin的类似物imidazole ketone erastin (IKE)是较为有效且代谢稳定的铁死亡诱导剂,有潜在的体内应用价值,能有效抑制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实验模型中肿瘤的生长[30]。柳氮磺吡啶(sulfasalazine)是FDA批准用于治疗某些类型关节炎的免疫抑制剂,也可有效抑制系统Xc-,与化疗药吉西他滨(gemcitabine)联用可显著抑制胰腺癌的生长[11]。直接抑制GSH形成的谷胱甘肽合成酶抑制剂丁硫氨酸-亚砜亚胺L-BSO可抑制小鼠乳腺肿瘤的生长[31]。
系统Xc-常作为联合疗法的纽带,在卵巢癌和黑色素瘤模型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可特异性降解胞外胱氨酸和半胱氨酸的人工合成蛋白酶cyst-(e)inase联用,能显著增强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其中免疫疗法激活的CD8+T细胞通过分泌IFN-γ,抑制SLC7A11的表达,诱导肿瘤细胞发生铁死亡。人类黑色素瘤临床样本也显示,CD8+T细胞浸润较高的肿瘤组织中,SLC7A11和SLC3A2表达水平较低[32]。免疫疗法激活的CD8+T细胞和放疗激活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所产生的IFNγ,相互独立但协同抑制SLC7A11,免疫疗法通过促进肿瘤细胞铁死亡使肿瘤对放疗更加敏感[33]。放疗后接受手术切除的食道癌患者临床样本显示,放疗所诱导的铁死亡伴随着SLC7A11和GPX4的适应性上调,相应的铁死亡诱导剂可减轻放疗过程中癌细胞对铁死亡产生的抗性[34]。铁死亡在传统治疗方法与新兴的免疫疗法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联合疗法提供理论依据。
3.2 GPX4抑制剂 对177个癌细胞系的敏感性分析显示,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和肾细胞癌对由GPX4调节的铁死亡特别敏感。(1S,3R)-RSL3(RSL3)是发现的第一个GPX4抑制剂,与GPX4的亲核活性位点硒代半胱氨酸共价作用,导致酶不可逆性失活,可抑制小鼠模型中纤维肉瘤的生长[35]。FDA批准的抗肿瘤药物altretamine用于治疗卵巢癌,可抑制GPX4诱导肿瘤细胞铁死亡[12]。FIN56促进GPX4的降解,同时与角鲨烯合酶结合,降解CoQ10[22]。他汀类药物通过抑制甲羟戊酸途径的限速酶,抑制由p53突变所引起的甲羟戊酸途径失控,从而减少硒蛋白GPX4以及CoQ10的合成,使细胞容易发生铁死亡,这和服用他汀类药物与多种癌症死亡风险的降低有关[7]。
CoQ10上游FSP1的高表达与肿瘤对多种GPX4抑制剂,如RSL3、ML210和ML162的抗性相关。体内实验表明,当GPX4失活时,FSP1可以在体内维持肺部肿瘤的生长。研究表明FSP1的表达水平可用于预测促铁死亡药物在癌症中的有效性,并强调了FSP1抑制剂在克服癌细胞对铁死亡耐药性中的潜力[23]。FINO2通过使GPX4失活和氧化铁,促进脂质过氧化,诱导癌细胞铁死亡[22]。Withaferin A除了抑制GPX4,还通过HMOX1介导的血红素降解,增加游离铁,抑制神经母细胞瘤的生长并降低复发率[36]。
3.3 铁过载 癌细胞对铁的摄取增加或输出减少都会使其胞内铁离子浓度增加。溶酶体干扰剂sirameine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lapatinib 促进转铁蛋白表达升高,在24 h内协同诱导乳腺肿瘤细胞死亡[37]。BAY11-7085不依赖其作为IκBα抑制剂的功能,通过NRF2-SLC7A11-HMOX-1途径,降解血红素释放游离铁诱导癌细胞铁死亡[38]。除了通过上述抑制剂调节铁代谢相关通路富集铁,也可外源性添加氯化铁、血红蛋白、氯化高铁血红素和硫酸亚铁铵等直接增加胞内游离铁,研究表明硫酸亚铁铵或血红素通过增加不稳定的Fe2+触发神经母细胞瘤铁死亡[39]。
此外,由核受体共激活因子4(nuclear receptor coactivator 4,NCOA4)调控的铁自噬(ferritinophagy)可降解铁蛋白,在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和人纤维肉瘤细胞中过表达NCOA4可增加铁蛋白的降解[40]。乳腺上皮细胞和乳腺癌细胞中高表达的prominin 2,促进包裹铁蛋白的多泡小体和外泌体(exosomes)的形成,将铁转运至胞外[15]。自噬和外泌体相关信号分子在诱导细胞铁死亡中的作用,也促使我们思考铁死亡与其他RCD之间的交集。
3.4 纳米药物 借由纳米材料调控肿瘤微环境中的铁富集和ROS水平,开启了肿瘤治疗的“铁器”时代。目前大部分纳米药物的设计基于向肿瘤细胞递送Fe2+或Fe3+,参与芬顿反应诱发铁死亡。Ferumoxytol是FDA批准用于临床治疗铁缺乏症的氧化铁纳米颗粒(iron oxide nanoparticles,IO NPs),可抑制早期乳腺癌的生长[5]。IO NPs可设计为同时负载顺铂,一方面顺铂激活NOXs,促进ROS的产生,另一方面纳米颗粒以内吞的方式进入细胞,逆转细胞对顺铂的耐药性[41]。脂质过氧化氢纳米颗粒(lipid-hydroperoxide-tethered IO NPs)可适应肿瘤酸性微环境,产生活性单态氧用于癌症治疗[42]。将p53质粒封装在金属-有机网络(metal-organic networks,MONs)中制备的MON-p53,可经铁死亡和凋亡双重途径清除癌细胞,抑制肿瘤生长,并延长荷瘤小鼠寿命。由于具有促进细胞内氧化应激的能力,MON-p53可以减少肿瘤的血液转移、肺转移和肝转移[43]。
4 展望
癌症治疗的挑战之一在于如何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保持健康细胞的完好无损。癌细胞通常在细胞死亡执行机制方面有所缺陷,这与癌细胞本身的代谢重编程和肿瘤微环境密切相关。癌细胞“铁成瘾”,而铁代谢直接影响铁死亡中脂质自由基的形成;癌细胞长期处于缺氧环境,而抗氧化代谢直接影响铁死亡的执行;以及癌基因突变与铁死亡信号通路之间的联系,这都提示我们从癌细胞独特的代谢方式出发,寻找合适的铁死亡诱导剂靶向肿瘤微环境,对癌症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耐药性进行方案改进,并为联合用药提供理论依据。另外,铁死亡介导免疫系统的抗肿瘤效应表明,靶向铁死亡通路并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未来颇具潜力的肿瘤治疗策略。总之,探索铁死亡调节机制和癌细胞代谢通路之间的交集,可为靶向铁死亡的癌症疗法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