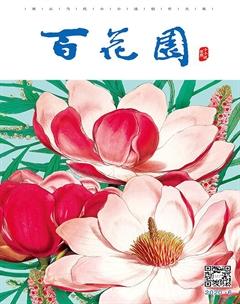第71号
赵光志

我们15名新兵刚分到艇上就听说我们艇要去远航,大家心里都很兴奋,明明知道新兵是不能参加远航的,但那份自豪如脸上的青春痘一样是藏也藏不住的。碰到一起入伍的老乡,无论侃到哪里,嘴里总会控制不住地冒出一句:“我们艇要去远航了!”
老兵司马空因为心脏有问题没有通过远航前的体检,被淘汰下来,身份一下子由老兵变成了我们新兵的班长。
班长对我们要求很是严格。我们仿佛就是他抽屉里的红皮条令本,动不动就拿出来翻一翻,有谁不遵守纪律,让他给逮住了,准会挨他一顿“电”:“老同志都去远航了,剩下你们几个新兵蛋子在家闲得蛋疼,还给我整事!都出队列去!”于是大家迅速站成一排,开始班队列动作,往往是出完了隊列还要在营区里拔一会儿草,回寝室之后要继续整那永远也整不完的内务。
在我们艇远航十几天的时候,有支队首长和机关的人在我们艇员宿舍进进出出。刚开始大家并没在意,但他们肃穆的表情和我们刚到部队的那火热的氛围有点儿不合拍,我们感到有点儿压抑。问班长,班长只扔下一句话,语气能砸死人:“不该问的别问!”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不知是谁传出来:“我们艇出事了!70名官兵全部牺牲了!”这晴天霹雳把我们这帮新兵都震蒙了,时间停止了,整个世界都静止了……我们都眼巴巴地望着班长,他是我们这帮新兵蛋子的主心骨。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没有了艇长,没有了政委,也没有了部门长、军士长、老兵……除了班长,我们什么也没有了,班长就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寄托。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遗体的辨认和出舱。首长和机关怕其他人辨认错了,就初步决定由干部与军务部门联合完成,但班长主动请缨,他说:“我们成天在一起生活,最熟了,不需要什么辨认。”支队首长想想也是,就同意了。
班长带着我们下舱,卫生科的人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防毒面具,以防舱内空气有毒。班长看也没看就抢先上了舷梯,却用嘶哑的声音命令我们:“戴面具!”我们哪敢怠慢?按动作要领戴好之后就紧随其后。
下去之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才知道为什么上级会给我们配备防毒面具。我们无法正常呼吸,那股多日密闭的污浊气浪穿过面具,不留一点儿缝隙地将我们包围住了,我们直到今天也无法知道没有戴防毒面具的班长是怎么呼吸的。他就像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一样,从面上没有看出半点儿异常。那些我们称作战友的人,有的倒在自己的战位上,有的坐在自己的战位上。他们的脑袋都让海水浸泡多日了,比正常人的脑袋要大许多,从面部表情依稀可以看出他们依然在操作着指挥员的口令……
班长有条不紊地指挥我们扶扶这个,正正那个,嘴里小心翼翼地说:“大家动作一定要轻,潜艇上的东西全是铜、钢和铁之类的硬家伙,别蹭着他们;往担架上捆时,绳子上一定要缠上软布,别勒着他们,让他们舒服一点儿。”
班长的语调让我们想哭,但我们哪有时间啊!
我们忙着把战友往担架上放,班长铁青着脸弯腰忙着给他们编号,以防别人搞混了。他依次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粘纸条,嘴里轻声地说,仿佛怕吓着他们似的:“1号——艇长王业达,2号——政委张常仁,3号……”
把70人的纸条粘完后,班长又重新核对了一遍,嘱咐我们:“一定要按顺序出舱,不能乱了。”然后他清清嗓子,想站好。透过防毒面具,我们发现班长的身体有点儿颤抖。大家想扶班长一把,却被他的眼神坚定地拒绝了!终于,他扶了扶旁边“艇指”战位的把手,才立正站好,正式命令我们:“抬——艇——长!”
我们一起抬起1号担架,把艇长的遗体向舱外传递。
这边班长一声长恸:“王——艇——长!一路走好!我司马空给你送行了!”紧接着扑通一声巨响,班长长跪不起……
我们15人抬了70次,班长就这么吼了70次、跪了70次,一声高过一声,谁也拉不起。特别是最后一句:“陈——波!一路走好!我司马空给你送……送……”声音撕心裂肺,大家一听感觉不对头儿,忙去搀他。谁知一碰班长的身体,他竟轰然倒地。大家再细看时,班长已经停止了呼吸,脸上的神态仿佛是从外面刚刚回到家里一样安详……
我们不约而同地摔掉了防毒面具,扶着班长大声地哭着、呼唤着,但班长安详地躺在“艇指”战位上,并不理会我们的大恸!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班长是真的随艇长他们去了,任何人也不会再把他淘汰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班长抬上担架,抬到舱外,这才跪下给班长送行!班长的胸前也粘着一张容易分辨的纸条,上面写着:
71号——舱段三期士官司马空。
[责任编辑 吴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