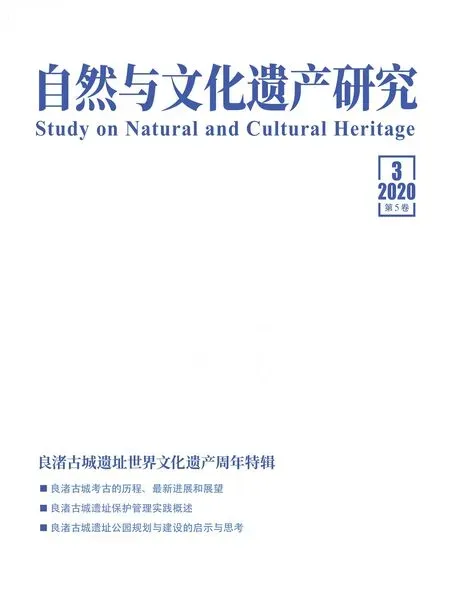良渚古城考古的历程、最新进展和展望
刘 斌,王宁远,陈明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2)
良渚古城遗址是整个良渚文化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一般认为,在良渚文化大部分时间内,良渚古城遗址都是文化的都邑性遗址。通过80余年、4代考古人的努力,良渚文明的轮廓已经得到清晰的揭示,随着申遗的成功,良渚古城考古也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3个部分:回顾良渚遗址考古的历程;介绍良渚古城考古的最新进展;并展望良渚古城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
1 良渚遗址考古的历程
笔者曾将良渚文化的历史分为3个阶段:发现与命名(1936—1972年)、区系的建立及社会认知与文明起源的研究(1972—2006年)、良渚古城与5 000多年王国的研究(2006—2019年)[1-2]。作为良渚文化的都邑,良渚遗址考古的历程与良渚文化考古的历程息息相关但又略有差异,在良渚遗址考古中,1936年良渚遗址的发现、1986年反山的发掘和2006—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标志意义,因此,良渚遗址考古也分为3个阶段,其中第一、二阶段以1986年反山的发掘为分界。
1.1 第一阶段:遗址点考古阶段(1936—1986年)
1936—1937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其家乡良渚镇进行了调查和试掘,确认了12处遗址点,并出版了发掘报告[3-4],标志着良渚遗址考古的开端。1949年以后,又发掘了老和山(1953年)、双桥(1953年)、仙蠡墩(1954年)①朱江.江苏无锡仙蠡墩发现古遗址及汉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5(1);江苏省文管会.江苏无锡仙蠡墩新石器遗址清理简报[J].文物参考 资料,1955(8).、朱村兜(1955年,属良渚遗址)、邱城(1957—1958年)、水田畈(1959年)等遗址,以上遗址除了仙蠡墩外均属浙江省,夏鼐先生据此于1959年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59年之后,良渚文化的遗址在以江、浙、沪为中心的长江下游被普遍发现,并对部分遗址进行了发掘,如浙江的苏家村(1963年,属良渚遗址)等遗址,上海的马桥(1960、1966年)[5]、广富林(1961年)[6],江苏的梅堰(1959年)[7]、越城(1960年)[8],丰富了我们对良渚文化内涵的认识。1973年草鞋山M198中琮璧钺等玉器与良渚文化陶器共存,从而首次确认了这些以往认为属于周汉时期的玉器其实是良渚文化的玉礼器[9]。随后江苏省和上海市先后发掘了张陵山(1977年)[10]、寺墩(1978、1979和1982年)[11-13]、福泉山(1982—1983)[14-16]等随葬大量玉礼器的良渚文化大墓,开启了长江下游文明化研究的新篇章。良渚文化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1977年后到1986年,“良渚文化的研究在近10年中,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把良渚文化社会性质的探讨提高到了其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高度,认识这一文明的发生和模式,以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贡献,成为良渚文化当前探索的焦点”[17]。
然而这一时期,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良渚遗址范围内仍未发现高等级墓地和大规模聚落,观察视角尚处于单个遗址点时代,对于良渚遗址尚未形成整体概念,对于该遗址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尚缺乏明确的认知。
1.2 第二阶段:遗址群考古阶段(1986—2006年)
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对浙北地区的史前遗址,尤其是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成了研究所工作的重要内容。1978—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发掘了浙北的7处遗址,包括1981年吴家埠遗址的大规模发掘,随即建立了浙江省的第一个考古工作站——吴家埠工作站,奠定了长期开展良渚考古的重要基础。1986年以来反山(1996年)、瑶山(1987、1996—1998年)、莫角山(1987、1992—1993年)、汇观山(1991年)、塘山(1996年)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大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人工营建的大型工程、具有意识形态特色的祭坛等发现震撼了学术界,使人们认识到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中心聚落。1986年,王明达首次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指出在30~40 km2范围内已发现四五十处遗址[18]。反山发掘之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投入了更多的考古力量,持续进行了考古工作,遗址数量增加到55处,良渚遗址的面积为33.8 km2;1998—1999和2002年分两次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共确认遗址135处,良渚遗址的范围扩大到42 km2[19]。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良渚遗址已经接近或进入了文明的门槛[20-21]。
遗址群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良渚遗址整体性概念逐步形成,但结构与功能性认识尚不清楚。
1.3 第三阶段:都邑与王国考古阶段(2006—2019年)
2006—2007年发现确认了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四面城墙,面积达300万m2,开启了都邑考古的新阶段。200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共同组建了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2010年以来,通过对城内外10.8 km2的勘探,摸清了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城墙、台地、河道的边界和演变过程,通过勘探和数字高程模型分析,发现城墙外还存在一圈面积达8 km2的外城。2009—2015年,陆续调查确认岗公岭、鲤鱼山等10条水坝遗址,年代多集中于距今4 900—5 100年,它们和塘山遗址一道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水利系统。这一发现也使良渚遗址的范围扩大到100 km2,同时我们开始以良渚古城为核心来整体看待良渚遗址和良渚遗址群(图1)。

图1 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将其视为一个都邑整体来研究,同时将杭州地区整个大“C”形盆地的所有良渚遗址,包括临平遗址群、德清杨墩-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等统一纳入观察,形成王国考古的基本范围。
2 良渚古城考古的最新进展
2019年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了“考古中国——从崧泽到良渚: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2020—2025年)”大课题,同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2019—2022年)”也正式启动,良渚古城遗址是这两项国家级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古城考古将在大课题的指引下,创新工作思路,并为后期申遗开展了全新的考古工作。
按照大课题设计,良渚古城考古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可划分为3个层次:良渚古城城址区格局的新认识和精细化考古发掘的开展、良渚古城郊区聚落的全覆盖式勘探、良渚古城腹地的区域系统调查。
2.1 良渚古城城址区格局的新认识和精细化考古发掘的开展
原先我们认为良渚古城的城址区可分为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结构[22]。随着近年来城址区考古成果的丰富,良渚古城城址区已可按照功能和结构划分为四重:最中心为面积约30万m2的莫角山台基;莫角山连同其南部的皇坟山、池中寺,西部的反山、姜家山、桑树头,北部的毛竹山、朱村坟、高北山等台地,海拔在8 m以上,为宫庙区、王陵及贵族墓地区、高等级行政管理区和贵族居住区等高等级功能区,是城址的核心区,可作为第二重,面积约110万m2;内城城墙以内其余台地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区,内城城墙包含的面积为300万m2,作为古城的第三重结构;最外围是由众多环绕内城的台地组成的面积近800万m2的外城(图2)。

图2 良渚古城城址核心区及城内外重要遗址点位置图(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5—2019年钟家港的发掘使我们认识到:莫角山以东的内城东区分布有大量手工业作坊,包括玉器、石器、漆木器、骨角器等丰富的手工业活动。2018—2019年,我们又陆续对城内外的台地进行了长探沟发掘和试掘,在城内的毛竹山、高北山、沈家村、小马山、钟家村(偏北部)、野猫山、西头山、公家山、张家山、桑树头和城外的盛家村、金家头、美人地、迎乡塘的表土或边坡的良渚文化生活废弃堆积中,发现与制作玉器、石器相关的成品半成品和加工玉石器的磨石、燧石,说明城内外的手工业生产活动相当发达,充分证实良渚古城核心区外主要是各类手工业作坊区,尤其是玉石器作坊。这些作坊的原料来源、生产过程、组织模式、产品流向是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结合城内发现的大量稻谷、家猪骨骼,与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相关的经济考古将是良渚古城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2019年,为了配合陆城门展示,对陆城门进行了长探沟发掘。遗憾的是,由于历年的破坏,城门内的3处门墩仅存高度不足1.5 m,其上未发现建筑遗迹。但发掘证实陆城门内外均为人为挖低后形成的湿地水域,当时并不存在联通城内外的南北向陆上通道,显然不具备以往我们所推测的陆城门功能。湿地水域范围内仅发现良渚晚期后段堆积,推测陆城门在建成后很长时间内是作为仪式性而非实用性城门(图3)。
2.2 良渚古城郊区聚落的全覆盖式勘探
在古城城址区以外分布着面积超过40 km2的郊区。良渚古城城址区的勘探结束之后,勘探工作的重点转入古城以东的郊区聚落。通过勘探了解到,在原先认为没有遗址或遗址分布较稀疏的地方发现了更多遗址,且遗址密度成倍增加。良渚古城东北已完成360万m2的勘探工作,共发现良渚时期台地97处,而原先调查仅发现约20处遗址。姚家墩遗址周边早就引起学者的密切关注。笔者根据对卢村的发掘、姚家墩的试掘情况,及以姚家墩为中心的共7处遗址的调查,指出姚家墩聚落组位置相当重要[23]。因此,将勘探的重点调整到古城北部姚家墩周边一带,完成勘探面积150万m2,探出良渚时期台地25处、河道7条。勘探结果显示,姚家墩一带存在由一处中心遗址及多处小遗址构成的聚落组,如早年便得到辨认的姚家墩聚落组,又如此次确认的东黄头聚落组和百亩山聚落组。根据以往的调查资料,在此次勘探区以东还分布有梅园里聚落组、官庄聚落组、下溪湾聚落组等,各聚落组占地面积50万m2左右,其中下溪湾聚落组面积最大,这些聚落组可能是等级低于古城城址区的社会组织在聚落分布中的表现。

图3 陆城门结构图(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根据以上论及的调查和勘探情况,我们推测良渚古城以东的郊区聚落台地总数将会超过600处,占地总面积预计250万m2,居住人口有2~3万人,与古城城址区居住的人口大致相当。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大课题——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支持下,2020—2025年,郊区聚落的勘探工作仍将继续,每年勘探的面积预计为3 km2,2025年 之前大致可完成良渚古城遗址郊区聚落的系统勘探工作。届时将会对古城以东郊区聚落中台地、河道等遗迹的分布情况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分析良渚古城的控制范围、城乡结构、人口规模、组织形式、经济生产、统治模式奠定坚实的基础。
2.3 良渚古城腹地的区域系统调查
良渚古城的腹地——整个“C”形盆地及邻近的德清、临安、富阳、萧山2 000多km2内,还分布有许多良渚文化遗址。近年来,我们开始组织力量,与山东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良渚古城腹地范围内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截至2019年,该腹地范围之内,良渚遗址群之外,已发现良渚文化遗址近150处。
良渚古城以东30 km左右,曾调查出由20多处遗址组成的临平遗址群。1993年横山遗址发掘出两座良渚晚期的贵族墓葬。近些年又大规模揭露了茅山和玉架山遗址,其中茅山遗址揭露出一处典型的依山傍水的聚落,包括墓地、居住区和稻田区[24];玉架山遗址面积约15万m2,由6个环壕共同组成,清理墓葬560余座,并发掘出以M200、M214为代表的10余座高等级贵族墓葬,是良渚文化聚落考古的重要发现。由于与临平遗址群良渚文化遗存的陶器组合、丧葬习俗、用玉制度与良渚遗址群非常接近,临平遗址群与桐乡东南-海宁西北遗址群之间有10~20 km的遗址分布空白区,可能是因太湖与钱塘江之间古河道所在,陶器组合、丧葬习惯、用玉制度也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也将临平遗址群视为良渚古城腹地的东端。
另外,近年来德清雷甸中初鸣一带的调查、勘探、试掘及发掘显示,距离良渚古城约18 km处的德清雷甸一带分布着23处与玉器制作加工有关的遗址点,分布总面积达100万m2,年代距今4 500—4 800年,已命名为中初鸣制玉作坊群(图4)。其中木鱼桥、小桥头、保安桥、桥南、王家里等经过发掘,均出土数量不等的,带有加工痕迹的玉料、玉锥形器、磨石、燧石等。这一玉器加工作坊群产品种类集中,以玉锥形器等小件玉器为主,玉器及原料数量丰富,说明这里有着相当大的生产规模。从保安桥、王家里清理的7座墓葬资料可知,随葬品的组合和风格与良渚古城遗址的墓葬接近[25]②朱叶菲,周建忠,费胜成,方向明.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遗址群2019年度考古勘探和发掘收获,“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 2020年1月8日。。在德清雷甸及余杭塘栖除了中初鸣作坊群外,还分布有下高桥、西坝头、南塘角、高地廊、六墓里等遗址,构成一处小型遗址群,可作为良渚古城腹地的北端。

图4 中初鸣制玉作坊群遗址出土玉器(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6—201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瓦窑里遗址发掘了30多座墓葬,年代属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随葬陶器组合与良渚古城遗址墓葬基本一致,富阳一带应是良渚古城遗址腹地的东南端,与良渚古城遗址直线距离40~50 km。目前,富阳区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点10处左右,数量不多,遗址保存情况一般,等级不高。再往西的桐庐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5处左右,其中小青龙发掘了44座良渚文化墓葬[26]。尽管墓葬中出土漆觚、玉琮、玉钺等与良渚古城遗址近似的遗物,但墓坑方向为西北—东南向,而非南北向,墓葬随葬陶器以双鼻壶为主,缺乏成套组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暂不归入良渚古城遗址的腹地范围。
萧山一带发现良渚文化遗址10余处,但发掘较少,所获遗存不多,从距离来看,应可作为良渚古城遗址腹地之南端,距良渚古城遗址40~50 km。再往南,浦江 塘山背遗址清理了44座良渚墓葬[27],墓坑为东西向,随葬陶器组合以鼎、豆、双鼻壶、三鼻簋、圈足罐、釜为主,其中大部分鼎、三鼻簋、釜、双鼻壶等器型在良渚古城墓葬中不见或极少见,二者差异明显,不能归入良渚古城遗址的腹地范围。
3 展望良渚古城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持续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良渚古城考古未来将向着科学化、国际化、理论化和公众化4个方向开展。
3.1 科学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极注重开展各类多学科合作研究。目前,已建立了完善的覆盖整个古城遗址的田野考古测量系统,获得了完备的矢量地图、无人机航拍图和历史时期的地图资料,RS、GIS等数字考古手段在考古工作中广泛应用,并在寻找外城、水坝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尤其是环境和资源领域的地质、动物、植物、古环境考古、工程科技方面已经储备了专业的人才,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具体合作研究项目方面,除继续完成已有的课题研究,计划重点围绕“水利系统与工程技术”“技术与文明”“资源与社会”“信仰与艺术”4个方面展开全面研究,以技术与文明为主轴,建设多学科国际协作团队,通过多学科和国际合作的方式开展工作。如与浙江大学地质系、浙江省地质调查院等开展“良渚遗址群石玉器鉴定和石源研究”系列课题,项目共分垫石、石器、玉器3个阶段,目前已经完成良渚古城垫石鉴定和来源研究,石器鉴定及来源研究在研,其后将进行玉器来源研究。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大等开展良渚古环境的合作研究,复原距今7 000、5 500、4 200、3 800年等关键时点较高精度的区域水文,地貌,气候环境,成为研究考古学文化的环境基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古DNA实验室等开展浙江地区崧泽-良渚时期人类古DNA的取样和研究。与河海大学合作,从水利和工程的角度开展对良渚遗址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就良渚水利系统考古研究中水坝结构与功能分析、古流域调查、水坝营建工艺研究、坝体测年等问题开展合作研究,主要进行资料分析、数值模拟、数据检测及对比验证等工作。另外,玉器、石器、陶器、漆器、木器等手工业技术研究,科技考古研究和实验考古研究也是今后的重要研究方向。
3.2 国际化
在“十四五”期间,计划利用良渚遗址申遗的契机,加强硬件和软件建设,设立“良渚国际考古研究中心”, 参考国际国内的成功经验(如土耳其的加泰土丘遗址),每年有计划地适度开放良渚古城的勘探、考古和研究、保护工作,与国际知名团队开展合作,摸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际合作研究的模式,全面提升我国考古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使之成为一个针对良渚考古的国际化合作研究平台,建立常态合作交流机制。
计划开展的课题如: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日本宫崎大学、爱媛大学、东北大学等合作开展植物遗存调查、农耕遗迹调查等研究;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东京大学等合作,开展动物考古研究和碳氮同位素分析,复原良渚先民的食物结构,揭示良渚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和生业形态,阐明良渚文明的农业基础;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和日本奈良教育大学合作,开展土壤微形态、生物微化石、地球化学研究,复原良渚文化时期的古环境,研究良渚时期的人地关系以及文化兴衰;与日本金泽大学、爱媛大学等合作,通过成分测试、微痕分析,揭示良渚生产、生活、宗教等方面器具的加工工艺,评估当时的技术水平;与日本奈良教育大学合作,开展饱水有机质文物的脱水保护技术的合作研究。
另一方面,将致力于相关考古成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这其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是良渚考古报告及著作的中翻英及出版工作,《良渚玉器》英文版已于2018年出版,《权力与信仰》英文版已于2019年出版,近期拟陆续推出《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良渚王国》《反山》《瑶山》《卞家山》《文家山》《良渚考古八十年》的英文版。目前,一部分良渚相关的考古著作也已经开始着手中翻英和出版,届时,国外的考古学家可通过这些译著了解良渚文明研究的最新考古成果。同时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和良渚博物院合作,翻译与良渚同时期和近似社会发展阶段的古文明研究著作,出版世界早期文明译丛,内容将涉及尼罗河流域(古埃及、努比亚)、两河流域(苏美尔)、印度河流域(哈拉帕)、伊朗(原始埃兰文化和古埃兰、赫尔曼德、吉罗夫特)、中北亚(阿姆河)、爱琴海地区(基克拉底、克里特)、欧洲(巨石阵、特列波里)、日本、东南亚(吴哥)、北美(卡霍基亚和查科)、中美(奥尔梅克、特奥蒂华坎、玛雅等)、南美(卡拉尔、查文、帕拉卡斯、纳斯卡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参与了科潘遗址的发掘工作(发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科潘是与帕伦克、卡拉克穆尔、蒂卡尔齐名的四大玛雅城邦之一。科潘遗址群核心区面积2 km2,由王宫区、拉斯塞普拉斯贵族居住区和埃尔波斯齐贵族居住区3部分组成。公元426年建立城邦,共传承了17位国王,历近400年,公元822年统治结束,遗址逐渐废弃。科潘遗址群和科潘核心区的建筑是石头砌筑,保存完好,使得科潘遗址公园具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且玛雅文字的破译,使学者们对玛雅世界和科潘遗址有更丰富的认识和更多视角的解读。玛雅世界与良渚世界尽管有着上万千米的空间距离和5 000多年的时间间隔,但二者处在基本相当的历史发展阶段,均属早期国家和成熟文明。二者的城址布局、文明模式等方面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深入了解科潘及玛雅文明的考古成果,对于开展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和研究良渚文明内涵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3.3 理论化
良渚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8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尤其是近年良渚古城、寺墩、福泉、等遗址的发掘成果所显露出的良渚社会发展状态,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张忠培、严文明、李伯谦、赵辉等先生就良渚文明的模式、特征和国家形态等皆进行过讨论[28-35]。国际业界泰斗伦福儒先生也指出良渚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形态[36]。
尽管学术界对良渚文明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已有了比较高的评价,但作为一个复杂的史前文明,现在还只是揭开了良渚文明的面纱,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化。
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最重要的子课题,是归纳总结长江下游地区区域文明的特点和区域文明演进的模式。其重要工作包括:基于扎实的年代学及聚落演变过程研究,探讨环太湖地区复杂化、文明化的途径、特点和模式;通过环境研究、资源调查和经济技术的专题研究,归纳良渚文明的农业、手工业及贸易方面的特点,总结当时的经济生产方式和模式,揭示良渚文明的经济基础;探索良渚文明的社会组织的基本状况及其演变,复原良渚时期社会形态;探讨宗教信仰对于良渚国家形成的作用;探索战争在良渚国家形成的作用;推测良渚文明的政治控制模式。从中国与同时期其他区域文明对比(如屈家岭、大汶口)的角度,了解出良渚文明在物质表象、文明形成过程、文明要素等方面的特征,归纳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总结长江下游区域的文明模式及长江下游区域文明在多元一体中国文明总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通过对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的梳理,开展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对比研究,为世界早期文明研究提供重要案例,丰富世界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理论。
3.4 公众化
良渚古城考古的公众化与古城考古历程如影随形,不可分割。我们曾梳理过良渚古城相关的公众考古实践,发现与良渚相关的公众化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媒体宣传、展览及现场参观、组织公众活动及讲座、出版公众考古读物等[37]。
近年来,良渚古城的公众考古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如在出版读物方面,有越来越多更通俗的普及读物陆续出版,2019年,在浙江省文物局资助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从事良渚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家为主的作者,撰写了由11册良渚相关的图书组成的“良渚文明”丛书。同时出版的还有刘斌领衔执笔的儿童历史普及绘本《五千年良渚王国》,成为国内第一部良渚主题的童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良渚文明”丛书和《五千年良渚王国》双双入选“2019浙版好书年度榜top30”。随着良渚博物院改陈开放和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良渚古城的展示系统也日益完善。
良渚古城城址区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也进入“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边展示、边利用”的新阶段。古城内将每年选1~2个遗址点进行精细化解剖发掘,并对文化层土样进行全淘洗,发掘区将搭建保护棚供公众参观,淘洗将在良渚遗址智能平台内完成,该平台也对公众开放。同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和良渚博物院合作,拟在钟家村设立永久的良渚实验考古作坊,在考古发掘和科技考古的基础上,开展房屋建筑、陶器、玉器、石器、漆木器、骨角器等方面的实验考古工作,复原以上遗迹或遗物的操作链和生命史,同时形成展示和公众体验场所。
4 结束语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良渚真正走向世界,标志着中华5 000多年文明史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良渚遗址是4代考古人一点点挖出来、研究出来的文明,是从仅发现若干村落遗址到确认数十乃至上百处遗址点,再到整个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的揭示,是从以陶器、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到以玉器和大型墓葬为代表的复杂等级社会的文明曙光时代,再到以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为代表的王国时代,这一切来之不易。
良渚遗址的成功申遗,是各方面力量几十年来通力合作的结果,是全国大遗址考古的成功典范。在浙江省文物局的领导支持下,在各级地方政府和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的互动合作下,随着考古认识的不断深入,保护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如果没有这几十年来考古与保护的互动,就不会有如今完整保存的世界遗产。从之前的良渚工作站到如今的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实现了合作共建。良渚古城发现后的10年来,团队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为今后的良渚考古创造了更好的工作条件。
考古工作是一项科学工作,我们长期以来以科学精神要求自己,被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不断发现问题和探索答案。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国家起源一直是考古界关注的核心问题,良渚就是我们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中不断追寻的结果。申遗成功是对以往考古成果的肯定和阶段性总结,但考古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我们仍需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