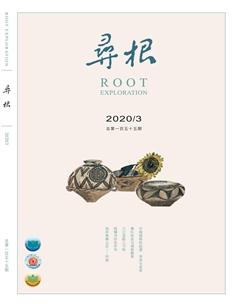涮火锅的变迁史
吴正格
一
内蒙古敖汉旗一座辽代墓葬,木椁上绘有契丹人宴饮的情形。其中三人于穹庐中,坐在火锅旁,中间一人用食具在锅中搅动,前置一长方几案,上摆簋和酒器,右侧是三足圆鼎,里面似有食材。敖汉旗博物馆的解说员介绍:“根据这处壁画,可以把发明涮火锅的专利颁发给契丹人。后来的满洲人、蒙古人的火锅吃法,都是向契丹人学的。”
契丹人怎么发明的涮火锅?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载一个故事,大略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军进攻渤海国,攻克扶余城后,继续向纵深推进。至天门岭附近时,他下令部队宿营,埋锅造饭,主要是煮肉,方法是:将牲畜或野兽宰杀、放血,再剥皮去脏,砍成大块,置大锅中添水煮之。当锅水起沸时,忽听探兵来报:有渤海国军队向宿营地进逼!阿保机意识到是炊烟暴露了目标。可是,契丹兵昼夜行军已疲饥不堪,何能迎敌?于是他果断下令:兵不离刀,马不离鞍,锅不撤火,将肉速削成片,大火煮熟,轮流快吃!将士们依令行之,将肉片放进锅里煮。阿保机则将切好的肉放进滚沸的锅中,一搅和,即已近熟,一张大肉片足能吃饱。当渤海国军队快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填饱了肚子,列队迎战。渤海国军队不是对手,被打得落荒溃逃。
战后,契丹将士自然感恩使他们能获得胜利的这顿“铁锅涮肉”,这也是阿保机在紧急情况下的一种选择。此后,“铁锅涮肉”就在契丹军民中传开了。这个故事虽然未经考证,但是辽墓壁画中契丹人涮火锅的情形不会是编的。
辽国在塞北草原和大漠间,历来有渔猎风俗。《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人“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这被称作“四时捺钵”。“捺钵”为契丹语,犹汉语的“行在”,即辽帝出行所在之地。简要地说,“四时捺钵”即一年四季中所要循行的规俗。涮火锅,为入冬后的“帐篷食品”。辽墓壁画中的这一物证,是当年食俗的写照。
辽国灭亡后,契丹人“四时捺钵”风俗被女真人保留下来,在顺衍中亦有变通。经历金、元、明后,又被女真人的后裔——满洲人沿袭。因而,老作家张友鸾在《谈北京菜》一文中说:“涮羊肉所用的火锅,是从东北随着清兵入关的。”这话,概括着涮火锅久远的历史。
二
火锅入关,在清宫里谓“野意家伙”。“野意”即野味。清帝涮火锅用的野味食材都是“关东货”,称“野意家伙”,是传统的满洲菜。康、乾、嘉三朝,宫中举办过六次千叟宴,每次与宴者三五千人不等,均是从全国各地诏选的65岁以上“给还原品大臣、官员、护军、兵丁、士庶”。宴中的主馔即是涮火锅,实为火锅宴。康熙在宴时还亲赋《千叟宴》诗,与宴老臣按律作合,并敕为图,率为定例,以传后世。
头一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是在畅春园庆贺康熙六十大寿。一下子来4240人,耆老过多,宴场容纳不下,就分两次承供,一次是在康熙的生辰日,隔三日又办一次。第三次千叟宴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正月,在乾清宫举办,可谓康熙即将告别帝坛的“谢幕宴”,也是隔三日又办一次。据御茶膳房的档案记载,宴中每桌设火锅两个,一等桌为银制、锡制各一,与宴者为王公、一二品大臣、外国使节等;次等桌都是两个铜火锅,与宴者为三品至九品官员、蒙古台吉、庶民等。一等桌的馔品是:羊肉片一盘、猪肉片一盘(供涮火锅用)、鹿尾烧鹿肉一盘、羊肉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蛳盒小菜二盘,另备肉丝烫饭。次等桌没有鹿尾、鹿肉和四碗荤菜,有烧狍肉,其他与一等桌同。宴时,康熙还命诸王以下、宗室子孙20岁以下10岁以上者六七十人,为耆老们执觞劝侑,“年未及岁皇子、皇孙,命侍立观礼”。
乾隆年间的千叟宴,吴振在《养吉斋丛录》(卷十五)中记载:一次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依康熙间例,在乾清宫举办,“筵席以品级班列,凡八百筵,与筵者三千人,用柏梁休,选百人联句。闽人国子监司业衔邓钟岳,年百五岁,自闽至京赴宴,尤为盛事”。一次是八十五岁的乾隆禅位嘉庆,于嘉庆元年正月在宁寿宫皇极殿举办,与宴者3056人。宴时,乾隆、嘉庆和康熙七律诗原韵,与宴者亦俱许依韵作诗。“与宴老民熊国沛一百六岁,邱成龙一百岁,赏六品顶戴;九十岁以上老民八人,赏七品顶戴。”这次千叟宴用了多少火锅呢?御茶膳房在嘉庆元年正月底档《千叟宴》记:共用1555个。按与宴人数计,约八百桌,每桌用火锅两个。
这几次千叟宴,等于为涮火锅打了御牌广告,并经赴宴人的传播,在各地官场和坊间引起热议,对京都餐饮市场也起到了趋附皇食的效应。
乾嘉之际,安徽桐城有位文人杨米人,著《都门竹枝词》,对当时京都的民俗做了有趣描写,其中有一首记道:“锡暖锅儿三百三,离汤添满好加餐。馆中叫个描金盒,不比人家请客难。”“锡暖锅儿”即涮火锅,民间多为铜制,内壁挂锡。“三百三”是引用千叟宴用了甚多火锅之意。“描金盒”是涮火锅的配套用具,盛佐料、小菜用的,类似千叟宴中的螺蛳盒,也是从宫中变通过来的。“不比人家请客难”是隐示宫里头请高寿人吃涮火锅,在民间食肆也能做到。可见,千叟宴已为涮火锅扬名,那“三百三”的锡暖锅儿,则是京都食肆膳所起俗于斯的缩写。
三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河北沧州回族人丁德山到京城谋生,起先在东华门一带做苦力,给各煤厂运黄土。两年后,他省吃俭用攒几个钱,在王府井大街挨着东安市场的金鱼胡同口搭个简易棚,挂起“东来顺粥铺”的招牌,只想养家糊口。
宣统三年(1911年),东安市场突遭火灾,也殃及东来顺粥铺。那时,大清朝已是夕阳西下,管理皇家养马场的老太监魏延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以便有个依靠,就解囊相助丁德山,帮他盖起三间大瓦房。多年的辛勤经营也使丁德山攒了些银子,他开始盘算如何将买卖就势做大。当时,生火锅在食肆中流行对他是个最大诱因,但他却瞄定专营以羊肉片使“俾客自投之”的火锅之馔。民国3年(1914年),丁德山挂起了“东来顺羊肉馆”的招牌,并在选择羊种、饲喂、取材、切制、火锅改造、蘸料诸方面,不断探颐履新,而且环境温馨,不唯利是图,人又随和,生意扶摇直上,越做越大,由三间瓦房开成三层大楼,百八房间都不够容客,楼顶也搭起暖棚卖座。后来又在京郊买了几十亩地,建起菜棚,种植蔬菜。接着又开酱园子,自制蘸料、调料和酱菜,形成产业链,使成本下降、价格低廉,生意愈发火爆。丁德山出身贫寒,虽然发迹却不忘本。东来顺挨着吉祥茶园,后面的茶炉房旁边有块空地,他又建起一处餐堂,专供贫民来此就餐,只售成本价。可见,东来顺的成功,也来自丁德山的商德和他行善济贫的人品。
说起“涮”字,还得说一下这个字的来历。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涮”字才始見于《大宋重修广韵》,其中对新增的“涮”字注释为:“涮,洗也。”可领会为“什物需洁净时在水中摆荡洗涤”。这虽是涮食法的动作,字还远未入俎,与吃火锅毫无关系。因而,谓契丹人发明涮火锅,或谓千叟宴中的主馔是涮火锅,其“涮”字都是后人也是本文为表述方便而追加的。此字自始造以来,别说经籍中难见其踪迹,就是在自宋至清的食书中亦未用之。其组词就是“刷洗”“洗涤”“漂洗”等。
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京都餐饮市场上时行“生火锅”。何谓“生火锅”?《清稗类钞·小酌之生火锅》中记:“京师冬日,酒家沽饮,案辄有一小釜,沃汤其中,炽火于下,盘置鸡鱼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以各物皆生切而为丝为片,故曰生火锅。”其实,这即是涮火锅。但是当时的京师尚无以“涮”连食的用语。这里,历史选择了丁德山去操纵“涮羊肉”,也反映了那时京师社会对饮食文明的一种需要和追求。
“东来顺羊肉馆”生意的兴隆,使“涮”字融入火锅里,并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字新星,以致有了“涮肉何处嫩,当数东来顺”的谚语。来这里就餐的主顾们,有“文涮派”和“武涮派”之分。文涮是筷子夹肉片沸汤涮熟,夹回碗内蘸着品啖,再喝一口“小二”(小瓶的二锅头);武涮是整盘肉片倾入沸汤,一阵急拨,然后裹卷佐料大嚼,再大口喝酒。此后,京人又将“涮”字从涮羊肉的鲜汤中提炼出来,演绎成独具风格的北京俚语方言:他大爷的,出了澡堂子奔茶馆儿,里外都挨涮;好家伙,您是拿我开涮呐……
时至今日,由“涮”字衍生的涮食法,不仅是我国餐饮市场中最流行的品种之一,也常在百姓家庭的餐桌上沸汤飘香,薄霞舒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