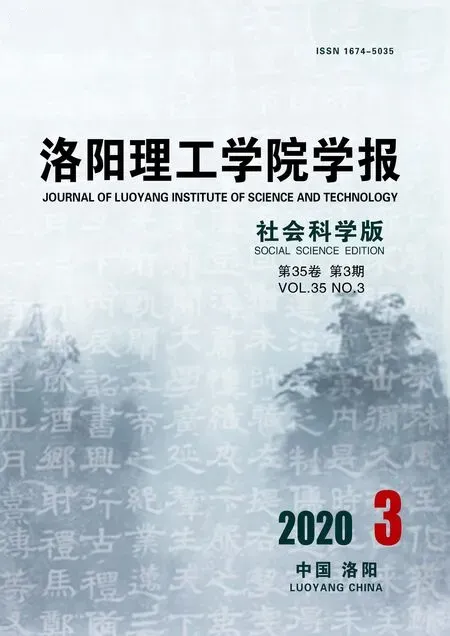防嫌之下的冲击
——明宗人内争因素探析
王浩淼,王小丰,徐梓又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明初在弱化亲王政治权力、加大军事权力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宗法制度的范本,从洪武年间的《皇明祖训》到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颁布的《宗藩条例》,无不展现出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宏伟蓝图和规划。然而,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分封制衍生出的问题愈发暴露,尽管统治者不断根据突发问题对制度进行修缮,但是尖锐的宗室矛盾使国家制度暴露出腐朽的一面,导致明朝统治制度呈现出一种规律:制度的设置—首例矛盾的出现—首例矛盾成为常例—制度的抑制或修订。宗人内争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甚至漫延到军事、文化层面。明朝宗人内争的因素涉及诸方面,从宏观看主要根植于祖训的不可违抗性,造成制度无法与时俱进;从微观来看,宗室之间因待遇的反差而出现冲击,也因共同的目标、利益而相残。宗人内争的主要表现有违法斗殴、辱骂、抢劫、互相向朝廷申诉、参与政党纷争等,到南明时甚至兵戎相见。
史学界对明代宗人犯罪、宗禄问题、政治防嫌等有所研究。如周致元的《明代的宗室犯罪》对宗室犯罪类型、司法程序等作了考究[1];孟凡胜、周致元的《明代宗室禄饷制度影响之探究》探究了禄饷对宗室制度的影响[2];梁曼容的《明代藩王研究》系统地对宗室政治防嫌作了考察[3]。这些研究考察了明宗室所处之尬境,却没有真正从宗室党争原因进行分析,雷炳炎的《明代宗室的倾轧与争斗述论》也仅是对部分案件作了初步分类,没有从国家本质和宏观层面展开具体分析[4]。
一、宗法体制下立嗣引发的觊觎斗争
朱元璋鉴于元朝的覆灭起因于各行中书省权力的过于强大[5]7,在掌握政权后意识到分封诸王于各地将是一剂稳定社会秩序、保持王朝长久的良药,不但能有效抑制地方势力的膨胀,而且能够提高中央政府的绝对影响力。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册封以皇次子朱樉为首的8个儿子为亲王,目的是让他们监视地方、翼卫朝廷,仿照西周众星捧月之势以成屏藩,同时又吸取各朝宗室制度中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的部分,制定出一套全新的宗法模式。朱元璋要求诸王及其子嗣必须严格贯彻本朝规章制度,“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6]3557。这项制度是明朝宗法制的基础,对明朝近300年的历史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朝廷为修复已被破坏的礼仪制度以及调整宗法制不合时宜的部分,颁布了符合当时情况的《宗藩条例》,该条例是在洪武朝“封藩制度”的基础上对细节加以约束和调整。宗室子孙凡是未犯大罪者,皆有爵位。在宗法制发展过程中,皇帝在国家层面上是所有朱氏子孙的大宗,只受祖制约束;而在家族层面,每个王府、家族、家庭中的朱氏大支长辈(包括摄府宗室)是诸支的大宗,家族制度由其执掌,形成等级森严的家族礼制文化,他们受国家制度制约。随着家族成员的繁衍生息及人口暴增,每个支系家族贤庸杂出,有野心者对家族的大宗位置起了觊觎之心,他们用非法匿丧、冒充王子、夺嫡等手段来提高自身身份,以取得更多宗禄。毫无疑问,这些方式的目的明确且有用,但却逾越了国家制度,扰乱了宗法程序。

明朝皇帝在抑制宗室权力上呈现出由轻到重的趋势,而在管理宗室制度上却是由重到轻,从原来杜绝冒袭爵位、旁支袭爵位演变成对其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尤其在嘉靖以后,特例不断出现,并被其他宗人援为前例效仿,从此特例成为常例写入玉牒。这种“非常态”的容忍误导了宗人,使他们一再挑战“制度”,继而为权力卷入政治争斗中。宗人在立嗣上出现的争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在继承权问题上,宗法制和家庭偏爱观念总有差距,从而造就由偏爱引发对继承权的野心。唐庄王朱芝址被弟弟承休王朱芝埌所侮,而朱芝埌的母亲是唐庄王继母。朱芝埌的母亲殴打唐庄王,朱芝埌也趁机上告唐庄王冲撞其母,于是双方均向朝廷申诉,最后朝廷裁定革唐庄王爵,但不久又恢复其爵位[13]1248。可见,亲王的伦理道德低劣,如罪大恶极、觊觎上位、私设武装等,朝廷绝不姑息;而如果只是违背道德或顺应“君主时代”,朝廷在保证大宗“脸面”的基础上相应给予薄惩,即强干弱枝的体现。
第二,立嗣不按宗法。立嗣没有按照宗法制度,即与国家法律相违背,成为其他宗人争抢大宗位置的有利借口。明朝血缘关系以外的矛盾逐渐得到缓和后,血缘内部问题逐步暴露出来。明朝制定分封制的初心是建立良好的等级观念。洪武时期,国家的重心在巩固政权和处理国、民之间的矛盾。建文帝时期,抑制诸王权力的措施,最终导致“靖难之变”。燕王朱棣以第四子身份获得皇位。同样的,嘉靖以旁支入继皇位,他要求修撰的《宗藩条例》规定“亲王绝嗣,可由亲支袭封,以重大宗,但必须是亲弟或亲侄,旁支不得继爵。郡王绝嗣则不得请爵”[14]537,其目的在于防止滥袭。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鲁府乐陵王第二子朱当渮、第四子朱当洅迟钝,而第三子朱当渿聪慧,老师滕胤将具体情况告诉乐陵王,乐陵王属意于第三子,其他二子害死老师发泄不满。在传统宗法制根深蒂固的时代,如果乐陵王能严格按照宗法制,不以贤愚为念,滕胤也不会因此而丢掉性命。但是宗法和贤德的先后次序是每个时代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乐陵王择贤顺应了时代,而宗法制是传统的规则,滕胤之死是传统与时代相抗争的牺牲品。率先出现的以贤作为择嗣依据的事件将进一步激化围绕是否贯彻宗法制下的宗室斗争,而实际上明朝君主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用强硬的政治权力阻碍违背传统理念的选贤方式,尤其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登基上位的君主更是想彻底贯彻传统宗法制。明成祖知道自己得位的“不正统”必然会引发对礼仪的冲击,嘉靖也意识到“兴献帝”的册封也将产生同样的后果,因此,他们即位后加紧防嫌,防止相似情形在各个领域出现,妄图以制度手段和道德关怀化解血缘矛盾和正统纷争。
第三,立嗣不以血缘。这主要针对大宗冒领他子、旁支冒充世子等问题。朱元璋在位时,为了扶植亲信、招徕人才,给予兄子朱文正、继子沐英特殊待遇。但此法违背了分封的目的,所以,自生有皇子后,朱元璋尽量避免异姓参与家族事务,并强调本支继嗣者必须是血缘最亲的男性成员。明亲王绝嗣可由旁支按照亲疏、嫡庶顺序过继,但郡王不能跨支承封。《宗藩条例》还规定一系列非法子女的封爵限制,如冒妾、滥妾及革前子女不许请封,寄养子女不许以改封为由滥请封号[14]566-574。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韩府襄阳王府奉国将军朱旭柱因无子收买流民女,生下三子,事泄后三子革爵[9]6993。汉阴恭惠王17岁即薨,无子,其妃父周恂冒领他人子袭爵,事泄被赐死[6]2763-2764。
明朝宗法制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传统僵化的规则不能与时俱进。明朝涉及继承制的宗室内斗一方面体现了宗室对宗法制的尊重和忌惮,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宗法制的局限性。因此,一面是权力的社会,一面是发展的社会,宗法制只能在巩固中央集权方面起到一定成效,但是无法遏制正在酝酿的社会变革。而明政府一面实行王府自我管理,一面派遣地方长官监督,同时又在宗人内部形成牵制力量。正是这种内部高度自治、王府官员的责权转移、内外相互联系的牵制手段造成监察体系的脆弱,继而引发种种宗室利益争斗。
二、宗禄不均引发的贫富斗争
明初,宗禄之制变更过一次。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定下郡王以下宗室的宗禄以永业田60亩为依据,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又改以不同的赐予标准。初期,每位郡王每年可得米6 000石、钱2 800贯,郡王之子及其后代只能从60亩永业田内获取俸禄。量减后,每位宗室成员每年可根据自己的爵位等级获得200~800石不等的俸禄,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加大了宗室费用。此后“宗禄不均”“游手好闲”“无以为生”三大问题日益突出。朱元璋只注重现实上的“量减”,未考虑到宗人“实质”上的增多,只顾虑到眼前的矛盾,却限制了未来的发展,使明朝经济制度始终未能与时俱进[15]。明朝宗禄制度不合理的原因是缺少与呈几何增长的人口基数相关的制度改革。尽管每位明朝皇帝都想以多种方式量减宗禄,但是不明智的授予和有失远虑的制度增加了“‘坐縻厚禄’,徒享安乐,于国家无利,于地方有害”的现象,激化了宗人内部因为财政问题而发生的矛盾,使山西、河南“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6]2001。在明朝的量减方法中,除明确的制度外,还有折色法,即将粮食折成钱钞下发给宗室。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发放宗禄的方式从原来的本色制转变为本折兼支,这项改革顺应了社会时代的发展。本折兼支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却引发出政治舞弊、滥发滥印、官员受贿等的社会问题。
永乐时期,朝廷通过下达缩减岁禄的敕令以达到减少宗禄、消耗的目的。如洪武间唐王的岁禄有1万石,后朝廷提倡节俭而只给其2 000石。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唐王奏禀王府财政困窘,朝廷复“增给唐王岁禄二千石,俱折钞”[12]1059。削禄、夺禄和绝禄也是行之有效的量减方法,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因犯过重罪而发配高墙或守陵的庶人、论死者,他们的子孙或多或少也受到播连,朝廷会支给发配高墙的庶人及子孙一定粮薪以度日。如果有机会从高墙释放,朝廷仍会“岁给半禄赡”。如果论死者及其子孙被处死或被永远禁锢,那么宗禄就不再给。明政府夺禄、革禄、削禄、绝禄的措施都是从国家财政角度出发。由于宗人人口基数大、宗禄少使他们的经济从原先的“经济收入甚为优渥”转变为“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垢有司”[6]2001。
尽管明政府用尽方法节省财政,但顾及“亲亲”之道还是会对藩王采取有求必给的态度,并要求宗长或管理者按级别层层下拨宗禄,将宗禄有计划、有条理地分配到每一位宗室成员手上,同时设置本府管理本府的方法以方便王府内部管理和监察制衡。如果朝廷所给宗禄不足,只需让亲王或摄府宗室上奏即可,再按程序下拨。当拨付宗禄过程中出现宗长贪污现象时,宗人之间便相互联结进行反抗,进而闹到中央。楚愍王让辈分最高的宗室——崇阳王之裔朱显休负责管理王府宗禄。朱显休因贪污被宗人揭发,镇国将军朱显桍向朝廷申诉,楚愍王反而“笞桍,毙(舍人)虎,罚桍千金”,并与崇阳王联手,与朱荣湑等“无术之徒”将朱显桍打死。朱显桍长子在楚愍王死后联合武冈王朱显槐等140多位宗人上告,朝廷以楚愍王已死,只将作恶多端的朱显休处死,其他涉案宗人幽禁高墙[13]1216。明朝规定了各地本府管本府的原则,这在一定层面上缺乏必要的内部监察体系和处置措施。而对于在王府内部出现的贪污宗禄、虐待宗人或延误上报宗人信息等违法行为,很多时候被朝廷所无视,这就更加激化了亲王派与普通宗人间的等级分野和派别划定,最终将朝堂从相互告讦的现场演变成“定罪议罚”的刑场。
由于宗室不许从事四民之业,宗禄是宗室唯一的经济来源,“惟恃岁禄为衣食”。许多人认为宗禄是引发宗室争斗的原因。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明政府禁令过密,法又不善,禁宗室谋生之路,是宗法制败坏的首因[16]642-643。赵翼的评论虽过于绝对,但也有一定道理。确切地讲,宗法制的破坏并不是明朝政府故意为之,而是与时代发展相悖的传统理念激化造成的。从传统的宗法制看宗室内斗,凡是冲击旧制度的宗室都是“乱贼”。
三、“食禄不治事”引发的利益争夺
成化以后,宗室的政治权力大幅下降,宗室只能向社会领域索取额外经济利益[17]。“有明诸藩,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然徒拥虚名,坐靡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6]3659是后人对明藩王状况的总结。张岱认为:“我明自靖难之后待宗室,其制愈严愈刻,在诸王之中,乐善好书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当其一出藩封,两长史、一承奉如古之三监,王不得纵意自为。”[18]49明初期,政府企图用“完善”的祖制来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但没有想到这会使宗室制度成为中央管理地方皇族的最大败笔。对于国家而言,政治腐败会在经济领域率先体现,而对于宗室来说,在囿于宗禄匮乏的情况下,宗室开始涉足土地、财产、关税、盐等官方管制严格的资源,甚且“行劫杀人”。
大量的宗室弟子因不能从事仕、农、工、商而被“边缘化”,“王不得纵意自为,而一藩宗禄出于本郡太守,故见太守如见严师畏友……而本郡乡绅亦畏之如虎,受其欺凌,不敢与校”,朝廷还要求其“不许擅离境外”,否则按罪行轻重定罚。面对高压政治和残酷的法律,“宗室之人大略皆幸灾乐祸”[18]49,庆幸自己没有成为朝廷制裁的对象。查继佐对此叹息道:“弱之以不教,等于锢废,虽才无所自利,其不才不可言也。”[13]1201明宗人为逃避狭窄的生存空间而屡次冒犯祖制,高爵宗人霸占土地、争取额外暴利而无视法律,而低爵者互相勾结、窃取并霸占财物以夺取额外利益,甚至按爵位高低拉帮结派。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襄陵王朱融焚联合260余位低爵宗室上告韩王朱融燧兼并山田市肆、虐杀无辜,韩王亦上奏诸宗凶淫不法,朝廷以各有诬言,将将军革爵、郡王罚禄,而亲王只停留于戒饬层面[9]6966-6967。韩王兼并土地之事,成为小宗讦奏的把柄,由于其身份是大宗,朝廷默许了韩王的行为,因此,在这次争斗中韩王处于上风。
宗室利用外家共同致富现象屡见不鲜。宗室结姻于地方势力以稳固自身在当地的地位,地方派也因此走上政治舞台。武昌卫军余刘贵倚仗楚府势力骗财害人,在楚愍王死后为防备怨家夺财,余刘贵请自己的姨夫中尉朱显椐帮忙守家。宗室崇阳王朱显休、永安王长子朱英焌及将军等,相互纠合实行抢劫,朱显椐不能抵挡,通城王朱英焀闻讯赶来,却遭到众宗人殴打,于是通城王向朝廷申诉[9]5870-5871。这些宗人对余刘贵施行抢劫,从表面上看是宗室对不法利益的争夺,实际上是宗室内部因“不治事”而针对皇田、资财引发的经济纠纷。最终崇阳王等4位郡王被罚禄。对于此事,朝廷用家法进行薄罚,因非忤逆、违(宗法)制之事,且闹事双方都有恶行,所以未用大刑。在争夺权力地位及维护既得利益上,面对可以使自己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没有生计能力和治事权力的王府宗室对制度束缚产生不满情绪,并开始挑战祖制,而王府大宗是一个王府的最高管理者,这些忤逆的宗室即用诬陷和诉讼手段与大宗对抗。
明朝王府拥有最高地位的人除藩王及世子、世孙外,还有作为辅弼的摄政人员,但藩王与藩王之间也相互攻讦。通城王朱英焀与武冈王朱显槐就摄政位置相互告讦[9]6420-6421。而代恭王也曾上奏饶阳王暴悍险贼、挟私凌长及囚禁殴辱公差等事,饶阳王随后揭发代恭王的私事。朝廷派出的勘官查明除代恭王无法遏制王府左右侍卫与民争利外,饶阳王所言皆不实[9]7115-7116。
总之,宗室在明政府的高压下无法正常生活,处处受约束。不完善的宗法制造成富宗养尊处优、贫宗衣食无着,从而导致贫宗与其他宗人互相争利而引发纠纷。然而,在国家维护大宗利益的基调下,往往是普通宗人处于下风。
四、环境因素对王府的影响
不同地域文化呈现不同的风格和信仰,整体环境因素能引领个人及家族的发展。
其一,家庭模仿因素。宗室成员出生后第一个模仿对象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性格、习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平时的家庭形象模仿而来。晋定王弟弟朱济熿胆大妄为,诬告晋定王父子,使自己坐上晋王位置。但朱济熿无恶不作,烝父妃、绝兄食、做巫蛊、不服丧,最终在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被幽禁在凤阳。终明一朝,整个晋府宗室多淫乱不堪。庆成王朱济炫子朱美埥非法强奸女妓,又模仿其父隐匿盗寇,其子朱钟镒“妃妻可二十人,四十四子,及女可百人,皆长育,五百有十曾孙”,朱钟镒子朱奇涧“抗父命,杀人,奸占乐妇”[13]1208-1209。明末的晋府宗室更加淫暴无道,“另城宗室宣隰、怀仁等暴横纵恣为地方害”[7]9648。晋府犯罪的宗室多是父子相袭。宗室家庭成员在生活中耳濡目染,在追求生活质量及生活习性上有共同的嗜好。在奢靡之风盛行的时代,父子之间的性格和行为相互影响,极易铸成整府的普遍性格,并伴有因共同的利益驱使而造成的竞争。
其二,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建文三年(公元1402年),在朝廷削夺军权的政治重压下,燕王朱棣带领胡汉军队“清君侧”。建文帝削夺诸王军权对南方诸王的利益损失不大,南方诸王大多没有参与燕王朱棣的“清君侧”;北方诸王中,辽王朱植和谷王朱橞等选择支持建文帝,宁王朱权等则跟从燕王朱棣。燕王朱棣登上帝位后,反对燕王者都被削王。宣德初,汉王朱高煦面对宣宗开始削弱诸王王权的压力悍然发动叛乱。明朝的政治高压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位拥有高等爵位的王府宗人头上,而一些王府受影响尤重,不满情绪和反抗斗争也随之产生。如天启年间谋叛的朱睿鉴和嘉靖年间杀了陆应旸的奴隶以陷害陆应旸的朱可涧等。明武宗在位时,朝政极度荒乱,引发了全国上下对皇位“合法性”的质疑,尤其是各地洪武时期所封的亲王及所属郡王的后代,他们对皇位的觊觎心骤然膨胀,利用时人对朝局的不满而进行忤逆行动。这些亲王及所属郡王首先突破祖制,结交大臣、宦官攫取军权、招揽豪杰等,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即发动叛乱,于是就有了安化王朱置的18天叛乱、宁王朱宸濠43天的“北伐梦”。
其三,地域人文环境因素。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人文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明代,山西多乐师,江西讼风与官风盛[19]。远在广西的靖江王府,由于处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民族矛盾又十分突出的地域[20],宗人党争和犯罪的次数居高不下,乃至“启、祯两朝迄无宁岁”[21]693。山西地区曾是宋辽的军事冲突区,在明朝是蒙古和明王朝的缓冲区,此处的人民,包括诸王都有极强的生存技能和战斗理念。从晋府宗人整体来看,胆大妄为是当时该地区的特征。代府同样如此,“大同极边之地,宗室繁衍,俗习刁悍”[9]7116。靖江王府丑闻屡见不鲜,又加之土地贫瘠人口众多,作奸者不可胜数,趋武文化造就了王府宗人傲骄的性格。相比较而言,四川、江西、山东等地区的地域文化更趋向于文。蜀、宁、益、鲁等王府的文风较盛,宗人多好读书,唐府所居的南阳也拥有较为雄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环境使宗室的价值观具有趋同性,并形成风俗。就蜀府华阳王府为例,因第一任郡王华阳悼隐王性情暴虐不孝顺,该王府被迫迁至澧州,在人文环境和血缘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华阳王府经历了三代半个多世纪的兄弟内争,最终在华阳悼康王被革爵后才终止。而封于建昌的益府宗人多贤明,端王、庄王、恭王皆以文学著称,有名当世,“天下称贤藩二,蜀与益云”[13]1286。宁王府中,作为迁入者,初任亲王朱权的道学素养较高,撰写了二十四卷的《异域录》,该书使人们认识到“土地是万物之本”的道理[22];即使是娼女所生的朱宸濠也“颇能饰以儒雅”[13]1236,利用文学招徕宾客士人。山东西南地区历来是儒家文化圣地,由此,鲁府儒风兴盛。但文化繁荣的王府内部常会因文学引发争执,不过争执的方法有时很新奇。周府新会王朱睦樒喜欢文章几到发狂的地步,其兄朱睦因通经被提名为本府宗正,朱睦樒由此嫉恨他,“诬以献女得宗正,为艳曲,使府中歌以辱之”[13]1211。人文环境给宗室内部的发展带来了利与弊,铸造了一府一地的性格,也成为宗人内争的内在因素之一。
五、君主属意下党派激化的政治斗争
明末士大夫的党派斗争以争夺政治利益为核心,谏官权力的扩大激化了朝内的党争,同时也削弱了国家行政效率,以致“黜陟之权,吏部不能主”[6]6259,然问及具体事务时,“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国之将亡也,先自戕其善类,而水旱盗贼乘之”[6]6348,各类小人借机投入其门下出谋划策,败坏士林和朝局。因此,后人指责士大夫“进不以正,其能正邦乎”[6]6524。由于明后期诸王只是一个皇族象征,不具备任何实际政治权力,他们完全沦为坐吃宗禄的皇家地主。时朝内党派竞争十分激烈,王府宗人便想利用这个机会找一下存在感,使朝内党派将注意力集于己身,这些宗人处心积虑地想成为党争中的一分子。
《明史纪事本末》将东林党议的起始点设定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癸巳的京察,吏部尚书孙砻与右侍郎赵用贤相继被罢免。此后,士林喧嚣充斥朝廷。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明神宗以礼部尚书沈鲤、朱赓为东阁大学士,沈一贯请求重新任命内阁人员,沈鲤被迫上奏请辞,明神宗不许。明神宗此举是为了分割沈一贯之权,故意安排与之不合的沈鲤到内阁,借助两党的牵制来巩固皇权。让明神宗没有料到的是党争因此愈发激烈。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楚宗人朱华越纠合29位宗人告发楚王朱华奎及其亲弟弟不是楚恭王的儿子[11]1029。礼部侍郎郭正域感到此事蹊跷,就根据众多楚宗人的控词,强烈要求朝廷派大臣进行勘查。阁臣沈鲤同意他的看法。但内阁首辅沈一贯倾向于楚王,“以亲王不当堪,但当体访”为由拒绝朝廷调查此事,“一时阁、部互相龃龉”。此案最终造成以下影响:一是朝廷倾轧日趋严重。就楚王真伪问题,户部尚书赵世卿认为楚王不假,给事中姚文蔚弹劾郭正域收纳楚宗人贿赂诋毁楚王,刑科谏官群起弹劾郭正域及沈鲤,而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反对楚王派,郭正域告发楚王对朝臣行贿。明神宗的处理只是将此案的宗人罚禄削籍、郭正域罢官了事。到第三年的妖书案兴起,双方又重提旧事,有心治理朝政的有识之士几乎无法在朝政存活。二是引发宗人杀官事件。此案未了,又有因楚王贿赂案引发的宗人杀官事件,湖广巡抚赵可怀奉旨查办,也被宗人打死。在朝廷的追查下犯案宗人全部被捉,“斩二人,勒私人自尽,锢高墙及禁闲宅者复四十五人”。
在此案中,明神宗从未细问楚王的身份是否有假。究其原因,正如查继佐所言“不闻神光之间,必尊继统,而以百世不迁与兴献也”。一方面,明神宗利用朝廷两个派别的争斗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祖父这个系统的“非正统性”,同时暗中属意符合其心意的一派,从而使楚王能在闹得如此大的案件中保持完好。另一方面,明神宗想警告世人宗法制的严格性已不复存在,而只有朝廷的处置结果才是制度的指向。
明后期对宗室的防嫌和政治压制在福王政权及以后的诸南明小朝廷中得到大幅宽松,出现了有悖原来制度的非法袭爵(如兄死弟及、冒袭等)、宗人入阁、藩王领兵等行为,这种变化不仅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小步,而且对明朝宗室制度来说也是一种对朝廷高压的反抗表现。总之,由士绅主导的福王政府是南明宗人关于国家层面党争的加速点,宗室权力逐渐并入皇权,在皇权极度弱化的形势下,宗室之间的政治斗争加剧了南明政治的腐败和动乱,加快了其灭亡的步伐。
六、结 语
从明成祖时期到南明弘光年间,宗室防嫌制度十分严苛。宗室在政治高压下,富者尚能培养文化内涵,或谋求利益,穷者饥餐露宿,寄希望于朝廷宗禄的公正、制度的宽容。由于缺乏必要的监察体系和制度变迁,宗人间贫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宗室内斗的大部分原因与明朝宗法分封制的弊病、环境造就的个性、国家政治腐败等有密切联系,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与时代、法与德的冲突。明朝皇帝多纵容亲王而罪责郡王以下小宗,对亲王宗禄的支出几乎达到有求必应的地步,对关于宗法制的冲击采取容忍态度。查继佐认为“倘流氛之日,以太子抚军,而使贫宗得奋臂咸就行伍,且以出身可自致通侯,数百年郁抑一旦腾掷,必有大异寻常者”[13]1249,表明了对宗法制弊端的无奈。宗人内斗与明朝相始终,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自身皇族地主的利益,却最终拖垮了自己的保护伞——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