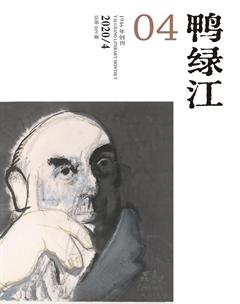疾病体验与文艺思潮
在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除了战争之外,大概就是瘟疫的暴发。瘟疫即烈性传染病。公元前430年,一场始于非洲、传播于波斯的瘟疫到达希腊,使雅典军队五分之一的士兵死亡,迅速扭转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局势,扑灭了雅典帝国野心的火焰。这场瘟疫在希腊徘徊了4年,夺走了四分之一希腊城邦人的生命;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暴发的黑死病夺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口;14世纪中叶,西欧蔓延的黑死病使许多地方锐减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随后欧洲殖民者把传染病带到美洲,扫掉了美洲土著95%的人口;1555年,墨西哥天花大流行,200万人不治而亡。20世纪,天花杀死了3亿多人,这个数字远超20世纪所有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难怪有人会说:“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更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了他们的心灵。”考察世界疾病史与世界文艺史的轨迹,它们之间至少有两次纠缠不清但又意义深远的交会,一次是14世纪黑死病的暴发与文艺复兴的发生,一次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结核病的流行与浪漫主义的联想。在此我想简要勾勒一下黑死病暴发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交会历程。
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14世纪中叶的意大利,而这正是意大利瘟疫肆虐的恐怖时期。首先是在诞生了人文主义先驱但丁与彼特拉克的佛罗伦萨,瘟疫从1340年开始,平均每十年一次,不断地摧毁这座城市,最可怕的是1348年黑死病大暴发。黑死病即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仅1348年佛罗伦萨就因此死去了十万人。1348年后,黑死病很快横扫了整个意大利,并迅速蔓延至英国、法国乃至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最后甚至到达了印度和中国。
黑死病的疯狂肆虐对人类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仅从死亡人数来看,这场瘟疫也堪称一场灭顶之灾。但也正是黑死病的大暴发加速了中世纪神学体系的土崩瓦解。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教会的无能暴露无遗,平时道貌岸然的牧师等神职人员,在灾难中争先恐后地逃走,不肯为死于瘟疫的病人进行临终洗礼,而大批神父染病死亡的事實,也动摇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这一基本信条。黑死病横扫一切的恐怖事实,让人们意识到宗教神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与此同时,面对死亡的逼迫,人们恐惧、焦虑、惊惶而又无计可施,生命变得如此短暂和不测,朝不保夕。
在这种情形下,及时行乐的思想恐怕就成了大部分尚且活着的人的生存信念;而死亡使人口锐减,为了保证种族的繁衍,追求饮食和性爱的享受,“以实现生命机体的强壮、后代的增殖和人类社会内在的和谐兴旺与完善的恢复”则成为社会新观念。这些观念都是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相悖的。
正如有论者说:“产生这些现象与结果的原因当然是丰富而又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决定性意义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但是人类对那次大死亡的体验也曾被众多的历史学家、学者们深刻忽略了。即使从一般常理或现象也能领悟到:对一个生物族类来说,最高的生命律令必定是生存并繁衍下去。当一种与最高律令对逆的趋向或事态发生之时,也就是死亡普遍地威胁着整个族类之时,人类怎么不对自身既定的存在方式发出最深刻的自省和怀疑?怎么不从最根本处激发出顽强倔强的生命向力?于是意味着普遍死亡的黑死病,却迎来了人类当初发展历史中最灿烂的时代。”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是在黑死病造成的巨大的死亡威胁面前,“人”的意识苏醒了。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曾说:“我们的城市陷入如此深重的苦难和困扰,以至令人敬畏的法律和天条的权威开始土崩瓦解。”被尊为人文主义运动开山之作的《十日谈》创作于1349年至1353年间,作者开篇即描写了1348年黑死病在佛罗伦萨猖狂肆虐所造成的“死亡狼藉、十室九空”的悲惨情景。小说中的三男七女为躲避疾病而结伴出城,蛰居乡间,为消磨午后的炎热时光,他们约定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人十天共讲了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大多表现出追求现世幸福和情欲享乐的精神倾向,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新意,但在黑暗的中世纪却是对神性要求的一次彻底反叛。
彼特拉克曾这样宣布:“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恋人劳拉因黑死病骤然离世,带走了他所有的生之欢乐。有论者说,彼特拉克的抒情诗,“第一次将世俗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从万物之主套在人们头上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在意大利的诗歌创作史上,爱情还是第一回被描绘成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感情”。彼特拉克不仅写下了凡人的情感痛苦,也写下了凡人的恐惧和疑惑。彼特拉克的弟弟是意大利蒙纽斯修道院的35个修士中唯一的瘟疫幸存者,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亲爱的兄弟,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之前死去。我们的后世子孙会相信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有谁曾经见过或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吗?在任何一部史书中,你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吗?人们四散逃窜,抛下自己的家园,到处是被遗弃的城市,已经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到处都蔓延着一种恐惧、孤独和绝望。是啊,人们还可以高唱祝你幸福,但是我想只有那些没有经历过我们如今所见的这种凄惨的状况(的)人才会说出这种祝福,而我们后世的子孙们才可能以童话般的语言来叙述我们曾经历过的一切。
在不可控制的灾难面前,在不能遏止的恐惧和悲伤之中,彼特拉克开始怀疑“高唱祝你幸福”的实质意义,开始怀疑“惩罚”的合理性,这是对上帝的怀疑,对曾经的信仰的怀疑。
在瘟疫所到之处,人的生命显得那样匆忙和脆弱,在对神性的顶礼膜拜的信仰轰然倒塌之后,人们开始呼唤人类自身的力量,而对人的力量的追求和颂扬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所着重表现的主题之一。如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创作的《巨人传》。在拉伯雷笔下,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不断学习而成为文武双全的巨人,巨人是比神更具有力量的,在象征着教会的权力和威严的巴黎圣母院,高康大的一泡尿居然淹死了26万教徒。同时,人也是自由、平等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小说着力渲染的享乐之一就是大吃大喝的“盛宴”。在那样一个瘟疫盛行、死亡遍野的年代,还能吃能喝就意味着生命的存在、种族的繁衍,“盛宴”即是活着的人面对死亡、战胜死亡的狂欢。
在瘟疫反复现身的佛罗伦萨,“劫后余生的人要做的贡献并不随瘟疫的消弭而停止,除重建那由于丧失父母儿女、亲属友朋而疮痍满目的个人生活而外,他们还得恢复那些集体的活动——公社、行会、教堂、社团等等,这些东西也都面临解体的危险。在这番重建事业中,最使人灰心丧气的可能就是瘟疫还会卷土重来的顾虑,瘟疫一来,所有重建的努力就会烟消云散”。也许正是这种害怕重建的努力转眼成空的心理,在佛罗伦萨的建筑中,石材更多地代替了木材成为建筑的主要材料,而象征着永久纪念的雕塑或雕像艺术在这一时期也空前地繁荣起来。
桑德拉·苏阿托妮说:“当时,以古典雕刻为榜样重新兴起了半身雕像、骑马雕像、纪念碑式陵墓的建造和叙事性浮雕的艺术创作。”她认为:“文艺复兴精神最深刻的表现之一是肯定自我和希望万古流芳。”的确,面对极为短暂的人生和难以预料的死亡时刻,人们都极为渴望让自己的形象以石雕或青铜雕像的形式屹立在人间,成为永远的纪念。于是,在黑死病大暴发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雕像不再是圣母或基督的专利,而成为大众的普遍追求,为某个个人而做的半身雕像几乎是遍地开花。在经历了深刻的死亡体验和沉重的信仰打击之后,雕刻艺术在主题意蕴的表达上也从颂扬神性转变为表现人性,甚至出现了《无名士半身雕像》这样的名作。
在不可抵擋的死亡面前,出于同样的恐惧和渴望心理,在雕刻艺术兴盛的同时,传记文学也繁荣起来。如薄伽丘的《但丁的生平》、菲利波·维兰尼的佛罗伦萨的名人《列传》等。除作家创作的伟人、名人的传记之外,自传的写作也颇为流行,如庇护二世的《回忆录》、本文努托·切利尼的自传、吉洛拉漠·卡尔达诺的《个人小传》等等。此外,有论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悲剧艺术与精神的重新发扬光大也与黑死病大死亡的体验有关,是深刻的死亡体验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在形式方面恢复了悲剧传统,并充分发展和完善了悲剧艺术,这也是有道理的。
最后,联系到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在湖北的肆虐,并蔓延全国。如今,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欧美国家,传染病的大流行再一次痛击了人们的身体和灵魂。值得庆幸的是,以21世纪的行政能力、科技发展和医疗水平而言,新型冠状病毒已不可能再现中世纪黑死病的杀伤力,目前除湖北武汉之外,各地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正如彼特拉克所怀疑的那样,“高唱祝你幸福”或许毫无意义,那些在病毒肆虐之中骤然失去的曾经鲜活的生命,应该永远被铭记,以警醒我们保持敬畏、悲悯、质疑和思考,并积极寻求或期待一些可能的改变。
参考文献:
[1][英]罗伊·波特主编.剑桥插图医学史(修订版).张大庆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2][英]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李玉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美]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朱龙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意]桑德拉·苏阿托妮.文艺复兴:从神性走向人性.吕同六主编,夏方林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5]宋耀良.黑死病与文艺复兴运动.广州:社会科学战线.1988(3)
[6]桑林等著.瘟疫:文明的代价.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7]余凤高.瘟疫的文化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程桂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2016-2017),现为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专著《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及编著《苏州作家研究系列·苏童卷》《莫言批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三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项、省级课题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