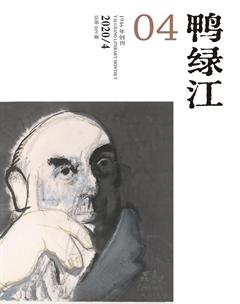书写即记忆,即抵抗
直到这次新冠肺炎爆发,许多人才惊觉到,SARS竟然已经过去17年了。这也提醒我们一个事实,17年来,除了须一瓜的《白口罩》和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竟然没有多少以SARS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在这期间,我也读到了一些师友和普通人的记录。他们的文字朴素平实,有点点滴滴的生活,日日夜夜的守候,而没有廉价的感动和煽情,也没有悲愤的怨恨和控诉。这次疫情出现了许多让人心碎痛苦的场景。问题是,在我们看过听过经历过如此多之后,我们如何去讲述,如何将事实融入虚构,又如何在虚实的共同指认中去检省、去清理我们自己和社会的病灶?
1
在世界文学史上,疾病(此处指传染病)书写不在少数。从视之为神的惩罚,到具有敬畏心的实录,到充满信念地以行动相博弈,再到以之为文明危机的指喻符码,这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学思想和书写的变化发展过程。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瘟疫皆因世人坏了伦理纲常而触怒天神所致。瘟疫袭击了忒拜城,“田间的麦穗枯萎了,牧场上的牛瘟死了,妇人流产了”,家园一片荒凉,冥土充满了悲叹和哭声。俄狄浦斯王忧心如焚。在神的谕示下,他追寻弑父凶手,真相大白后刺瞎双眼放逐了自己,这是一个在道德伦理上进行自我更新和赎罪的过程。1350年,薄伽丘以1348年发生在佛罗伦萨的鼠疫为背景创作了《十日谈》。由于人们无法认识疾病的源发性原理,只能视之为“天体星辰的影响”或“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霆”的降罚。这是前现代的叙事方式,神秘主义元素对应着命运的变化无常,我们今天当然不应也不会去提倡这种写作。我们早已科学地认识了传染病的发病原理,也深知它们带给人类的巨大危害。因此,对于疾病书写来说,如果做不到在虚构中进行指认,那么至少应当学会诚实和敬畏,学会甄选真实的史料记下所见所闻,比如笛福的《瘟疫年纪事》(1722)。这部小说以发生于1665年英国的瘟疫为背景,通过鞍具商H. F.的回忆展开叙事(有一说H.F.是笛福的叔叔亨利·福)。瘟疫漫卷而来时,H. F.选择留在伦敦,并决定记录下自己和周围人经历的一切。他说写作此书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备忘录,万一再有类似的灾难降临,可以提供一些指导。这场瘟疫“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他看到人们一天天无助地死去,尸体堆积如山,政治、权力、财富都让位于生存。瘟疫全面引发了信仰和道德危机。政府捂着消息导致谣言满天飞,王室干脆避祸于乡间,全国治安大乱。1665年瘟疫发生时,笛福才五岁,应当对灾难没有太多记忆,但这并不妨碍他寻找并筛选史料,假叙述者之口将史实和盘托出。为了达到求真的效果,笛福淡化了作家的身份,而返回了他从事过的记者行当。他研究了很多医学论文、官方小册子、1665年的《死亡统计表》,采用编年体方式进行讲述,从1664年9月到1665年底,几乎是逐月报道瘟疫的进程和影响。笛福非常喜爱伦敦的街道,他让H.F.总是在街上游来荡去,叙述基本上也是以H.F.所在的地理位置展开的。据统计,小说中一共提到了175处以上的街道、教堂、酒馆、村庄、济贫院、菜市场、市政厅等地理坐标。有的地名兼具隐含意味,如贝尔胡同(Bell Alley,bell一意为“丧钟”)。H.F.对街道的了如指掌突显了瘟疫的恐怖程度:它将已知变成了未知,将通行之途变成了死亡之地。H.F.所熟悉的伦敦已经完全陌生。我们跟随这位姓名不详的叙述人游历街道,带着心酸、痛苦、绝望和恐惧,重新认识这个死亡空间。有人为了避免闻到房子里飘出的臭味而行走在街道中央。有人在街上大叫:“再过四十天,伦敦就要灭亡了。”有人在街上裸体狂奔哀号:“噢,无上而威严的上帝呀!”有病和无病的人被同屋隔离,江湖医生和星相家诈骗钱财,护理员闷死患者夺走财物,病人疼痛难忍跳楼或开枪自杀,运尸车通宵忙碌,教堂里满是哀吟祈祷的人……一幅末日景象。
《瘟疫年纪事》的价值首先是史实的真实性,其次才是文学的可读性。文献、数据、图表、符箓、广告、政府公告被镶嵌在文本之中。这种近似于非虚构和报告书的方式使小说不太像小说,这正是笛福的创作动机所致。他就是要让小说像是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匿名抄本,如小说开篇故弄玄虚的题记:“由始终居留伦敦的一位市民撰写,此前从未公之于众。”这种写法有着坚实的可信度,含纳着不断重返过去的令人心碎的熟识感。就像编辑辛西娅·沃尔在《导言》中所说:“纪实因故事而得以充实,故事由于纪实而得到保证。”其实,描写这场瘟疫的书不少,但最后,只有笛福的这部小说流传了下来,被人们视为“大疫年”的百科全书。事实上,在瘟疫次年,伦敦发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城市的五分之四被烧毁,昔日街道悉数消亡。《瘟疫年纪事》因此具有了双重价值:它是病理学的纪实,也是地理學的记录。
2
如果想要了解人类如何与瘟疫进行搏斗这一主题,加缪的《鼠疫》(1947)当属“样板”。小说详细描写了奥兰城发生的烈性传染病,塑造了封闭隔离空间之下各种各样的人:失控的人、恐惧的人、麻木的人,还有勇敢的人、纯洁的人、高贵的人。通过对“人”的切片取样和具象微观的考察,加缪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人”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里厄医生,叙述自始至终贯穿着他的视角。他看到老鼠摇晃着,口吐鲜血并倒地身亡,他听到老鼠垂死挣扎的轻声惨叫,他注意到发烧死亡的病例短时间内大为增加,他意识到这就是曾经吞噬过一亿人的鼠疫。他向政府提出“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使省府同意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他和里夏尔医生、卡斯特尔医生向省长说明严重性,强调必须立即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省长纠结于这究竟是不是鼠疫,一直犹豫不决,直到疫情不断恶化,医院很快爆满,才不得不正式宣布封城。一旦城市封闭,大家只能是“一锅煮”。人们被放逐在自己家中,过一天算一天。消息不通,外援难以进入,医疗和物质资源严重匮乏。各色人等纷纷上演着死神追逐之下的本性。病人精神错乱,商人囤积居奇,警察疲于奔命,官僚在等待上级的命令,市民们在疯狂抢购据说可预防传染的薄荷糖,垂死者怀着仇恨和无意义的希望拼命缠着活人。鼠疫在生活庞大的体表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裂缝,裂缝不断扩大,直到成为深渊,遂使整个现实都沾染上了地狱的瘴气。在奥兰城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不同的人各有行动,“人”的层次感清晰而饱满,每个人都构成了鲜明的某一类型、某种典型。医生里厄忙着救人,神父帕纳卢忙着布道,公务员格朗忙着推动卫生防疫工作,志愿者塔鲁忙着记录疫城的生活。两个逆袭的例子是,性情孤僻多疑的科塔尔走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外地来的记者朗贝尔最开始一心要出城,在得知里厄医生的妻子因染病被送到外地救治时,他自愿留了下来。他说,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的幸福,那是羞耻的。加缪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将这一理念投射到了里厄医生身上。医生与瘟疫博弈,时常感到孤独无力。妻子病亡,他没有办法接她回来。母亲担忧他的安危,他也没有办法安抚她。在他要隔离病人被骂心冷心硬时,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因为他一直坚定地认为,作为医生的责任就是与病毒做斗争,使尽可能多的人活下来,使尽可能多的人不至于永远诀别。里厄医生从来不认为投身于抗疫工作就是英雄。他说自己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他还说:“同鼠疫做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这样的话,我们何等熟悉,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却要一再付出生命的代价。
3
《鼠疫》的现实指认很清晰。加缪以封闭的奥兰城指喻1940年以后被纳粹占领的法国,以鼠疫病菌象征法西斯及其统治下的恐怖时代,以奥兰城人民忍受的绝望隔离象征当时法国人民经受的生离死别。这种指喻性在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1995)中体现得更为普遍,更具文化和文明危机的警示意义。在《失明症漫记》中,一种奇特的传染病发生了:失明症,仅通过目光对视就可传染。它是一种“白色眼疾”,染病者仿佛是睁着眼睛沉入了明亮浓密的牛奶海里。第一个失明的是一个司机,“那人的眼睛似乎正常,虹膜清晰明亮,巩膜像瓷器一样又白又密”,然而他却冲着人们绝望地喊叫:“我瞎了!我瞎了!”送他回家的路人立刻被传染了,这个路人实为偷车贼。车到手后,他没有走出30步就失明了。眼科医生是第三个受害者,当时在诊所里的其他病人无一幸免。眼科医生把病情报告给自己医院的医疗部主任和卫生部官员,但他们粗暴地拒绝相信。失明症迅速蔓延,城市陷入了恐慌和绝望。当局下令将所有患者赶进一个废弃的精神病院进行隔离。一排房子住失明者,另一排房子住失明症嫌疑者。如果一个疑似者真的失明了,他会立即被同伴赶进对面的房子,所以无须操心患者的挪移问题。当局派出士兵武装把守,规定如果有人想离开就开枪打死,如若出现起火、骚乱、斗殴,无人会去救援,死者由患者直接就地埋掉。小说中的城市没有明显的地理特征,人物也都没有名字,只有身份、性别或外形特征的命名:男人、女人、医生、医生的妻子、斜眼小男孩、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等。他们是被隔离的人,是被疯狂射杀的人,是在尸体旁边吃饭的人,是遭受屈辱践踏的人,是在污秽肮脏中苟且偷生的人,是摸索着铁锹埋了别人尔后又被别人埋了的人。这种毫无主体确定性的修辞暗示着,他们就是你和我,是我们每一个人。《失明症漫记》包含着丰富的想象、比喻的笔法、结实的细节,这使得抽象的恐惧和形而上的指喻具有了可感知的外形,叙事的可信度和情感的黏合度如影随形。它在实证主义层面上雖不可能发生,但却是完全有可能的一种令人恐惧的“未来”。在这个黑暗的绝境里,人性所有的原始之恶都被激发出来:食物被霸占,妇女被强奸。强者欺压弱者,野蛮战胜了文明。人性骨子里被规训的“野兽”挣脱了文明秩序的桎梏,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廉耻丧失殆尽,千百年来培养的教养礼仪犹如风中之烛顷刻灭迹,转眼就回到了蛮荒时代。看完这本书,大概每个读者都会暗自庆幸:还好我没有失明,我还看得见。可是,谁又能保证自己的“看得见”就是“看得见”呢?“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这是《失明症漫记》的题记,取自于《箴言书》,而小说中提到的“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在生活中大有人在。这个句式我们也可以改成“能听但又听不见的聋子”“能说但又说不出的哑巴”。器官和功能都正常,但就是没有办法行使“真”的权利。“失明症”只是萨拉马戈的想象,但这想象造就的寓言却与现实息息对映。世界确实感染过或正在感染诸种恶疾,无数人在灾难中失去肢体、器官、至爱、亲人和生命。加缪在《鼠疫》结尾提醒过我们:“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瘟神再度而来并不可怕,最可怕可悲的是,在科技和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竟然在遭遇相似的传染病时还会犯下相同的错误。这或许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深陷于繁荣和发达的幻觉之中,从而使得厄运的重复降临有如初见,携带着新鲜的狰狞和死亡。就像老黑格尔所说,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一次,希望我们能够留下一些生命的呼吸、节奏、颜色、状态,留下一些人们之前不甚了解的“谜语”。这样,在下一次灾难到来时,我们或许会少一些狂妄和傲慢,多一些诚恳和谦逊。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曹霞,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两部。曾任教于日本爱知大学。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入选天津“五个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