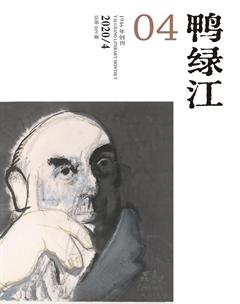疫病、真相与文学的尊严
1
大学时读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我更多感到的是恐惧以及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不一定属于文学,而是人在灾难面前的脆弱和黯然神伤。加缪写了医生、记者与普通人的生存梦魇,这是否就是命运本身?那时,因认知和能力有限,我根本没有想多深,小说中节制的冷静,更符合一个初入文学殿堂的读者对经典作品的盲从心态。后来,再读到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说里的霍乱只是五十年爱情的一个背景,而爱情也如同霍乱一样,隐喻着某种无法控制的病症。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阅读,我在时间流转中领悟了其中更多文学与人世丰盈的可能:加缪有他深沉的哲学,马尔克斯很具洞察力,但他们都以“瘟疫叙事”的方式写出了自己内心的寓言——这个世界的神秘,我们很多时候捉摸不到,可一旦它成为侵袭我们身体乃至生命的魔鬼,我们就被带到了另一条关于源头、真相与代价交织的逻辑轨道上:它不仅仅涉及人性的陰暗与善良,还有面对恐慌和死亡时的纠结、无望。人确实有其复杂的一面,但很多时候,我们失察于自己的有限性,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大自然缺少谦卑和敬畏之心时,人定胜天会显得多么狂妄与无知。在疾病和瘟疫面前,同样如此,那些悲剧性的文学个案的呈现,让我们更靠近人世的真相。
这几部作品也许是我最早关于瘟疫文学的启蒙,至今,它们仍然是隐藏于内心的一个无法解开的症结,这个结也可能永远无法解开。因为那里面所暗含的神秘,必须有打开密码的钥匙,这属于心灵的感受力,有偶然的“闯入”性,而无必然的精神终极归宿。有人说,理解这种文学作品是需要时间,需要人生阅历的,否则,我们很难看清人在面对瘟疫和灾难时到底有多无助。疾病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生死亦如人生常态,天意的,命定的,这种自然的人生走向,无须我们多做探讨。就是在突然的瘟疫和灾难到来的时候,这种偶然性让处于紧张和恐慌状态中的人会更加脆弱,而关于坚强、英勇与无所畏惧,都可能体现为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能坚持,更有韧性。美国文学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的两篇文章中分别谈到了梅毒、结核病、癌症与艾滋病,当这些疾病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一种符号时,它们就有了极其强烈的隐喻或象征色彩,连疾病都代表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内涵,这个世界在具体的现实与文学中就更为丰富和复杂了。
在各种瘟疫和疾病面前,社会与人性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复杂?当人将疾病和与生命相关的东西发生关联时,桑塔格说,疾病本身就变成了隐喻(《疾病的隐喻》第53页)。而瘟疫同样如此,它看似侵袭人的身体,其实也在异化人的精神与思想。桑塔格所说的“疾病的军事化隐喻”有其现代性的背景,她之所以反对疾病成为隐喻,是因为她以癌症亲历者的身份从学术上论述了疾病作为隐喻的可能性,这种现实如果被投射到其他个体或群体身上,也会发生更大的化学反应。因为每个人在面对疾病时的处境与心态都不一样,它带给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和高度也不同,这正是关于瘟疫和疾病的素材一直以来就是文学书写重要母题的原因。我们在阅读具体作品时,更多是以感同身受的读者视角切入虚构的现场,用心阅读会有一种代入感,这与桑塔格作为亲历者的身份所体验到的角色感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动地接受来自疾病对身体和意志的摧残,她主动直面“身体的灾难”并将其化解为一道关于人生和政治的学术命题。在逐渐被疾病和由疾病所隐喻的政治所破坏的秩序中,她迎难而上地去承受疾病带来的伦理压力,担起道义的责任,而我们仅仅是作为旁观者在消费别人因疾病而遭受的痛苦与悲欢离合。
撇开纯粹情节和意绪上的感动,有一段时间在读关于瘟疫、疾病和死亡的小说时,我总是感觉隔了一层,它与学术上的科学分析构成了不同的“影响的焦虑”,有一种一眼看到底的简单化之嫌。这样的作品很难让人获得至情至性的满足,因为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它只能在虚构的情感层面打动人,但它无法在事实和科学的高度上给人以更有公信力的价值认同。尤其是在公共的价值序列里,那样的写作是安全的,既有单纯文字上的安全,也有道义的豁免权,可唯一让人觉得不安的是,作家必须承担良知拷问的内在压力。没有自我追问精神的写作,很难在更为整全的谱系中为我们提供可以充分言说的空间,作家在封闭的文字世界里作孤芳自赏式的修辞游戏循环,我们看不到动态的能够开启民智的叙述、唤醒机制与终极理念。因此,在有关瘟疫和疾病的文学作品,我们一方面需要感受经验细节和现实景观,另一方面还要去呼应“超现实”暗示的启蒙和反省之力。
2
再一次与瘟疫文学相遇,是在2003年SARS时期,那年春天,我大学毕业后在报社已工作两年,正值从社会新闻记者岗位调到副刊编辑的岗位之际,这个调岗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我本该和其他同事一样,在疫情防控的一线去采访,可我回到了离心灵最近的文学,看似远离了鲜活的现场,又回归到了封闭的自我世界里。因为对瘟疫的恐惧,我又开始阅读加缪,这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再一次震撼了我,这次不仅仅是因为重读他的《鼠疫》,还有叙述和阐释更为冷静的《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我觉得这次我触摸到了加缪作品的某根神经——人活于世,固然有荒诞和悲剧,仍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向死而生”。这才是文学的力量,它在更多无法解决的人世冲突中承受悲剧的惩罚,不过,在对生命唤起良知的场域中,我们还是要去寻找真相,尤其是我们认定的内心的真相。
记得那年编报纸副刊版面时,我及时编了两版“献给白衣天使”的诗歌特刊,非常时刻,这种给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文学道义上的支持与鼓励,应是有必要的。但后来在一些刊物出现了更多热情洋溢的浅白之言,突出了社会功能,几乎放弃了审美价值。那些“应景之诗”我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们无法用“力量感”这一标准来衡量这些诗歌以及写作这些诗歌的人,他们中有我的同事和朋友,更多则是自然投稿的普通读者,那些口号性的文字,表面上激情昂扬,似与真正的本体文学无关。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读到宣传性的“新闻诗”,就条件反射般地想起“假大空”模式。我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蜕变何以能打破“人生过客”的无奈,主动参与创造新的时代现实,也像一束始终没有熄灭的微光印在了我的理想中,它是否一直照耀和指引着我脱离表象的命题,而为深层次的反思赋予向内的意义?也许这里面有虚荣心在作祟,此时,我可能还无法领会《鼠疫》中里厄医生的困惑:在瘟疫和灾难面前,有什么是值得我们用生命来守护的?是一种活下去的执念,是求生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作品中涉及的信仰与宗教精神,我们可能因为不同的文化环境,很难对等地去理解和领受,但自由思考的权利是我们可以共同把握的存在。
时隔五年之后,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当时我正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读博,这场大灾难在文学的意义上也许还是提供了一批诗歌,甚至还形成了一股热潮。那些被命名为“抗震诗”的文本,因其追风的即时性和歌颂性,绝大多数我也像当年SARS时期编诗歌特刊时已忘得差不多了,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朵渔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这是一首富有反思力量的诗歌,其力量在于它竭力靠近真相,道出一个地震的“旁观者”作为思考主体的能动性,他哀悼,他批判,他反思,他写出了更多读者感同身受的灾难之殇。当然,也有人不理解这样的诗歌作品,认为字里行间充满了矫情,但我还是看到了诗人在公共事件中的良知和清醒。如果和一篇事实性的非虚构文字相比,它负责的不仅是真相,还有对真相的反思。而我们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要求灾难文学重生呢?它很可能就是《鼠疫》在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变体,无论我们从中读出的是歧义还是分裂,诗人只是在记录和见证,他以批判之语刺痛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經,也以人文知识分子的修养重建了灾难文学的价值体系,那就是必须反思引起灾难发生的一切。毕竟,这样的诗也能警醒那些被“岁月静好”所蒙蔽的心灵。
我想,在大的灾难和瘟疫、疾病面前,对人心的抚慰很重要,安宁和思考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面向,而这些都需要建立在试图挖掘或靠近真相的基础之上。假设我们能够想得更为深入一些,真理似乎就成为我们在面对瘟疫和灾难时的终极目标,真理能负责解释一切吗?“毫无疑问,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一个政治事件,此外,还是一个经济事件。”《疾病的隐喻》的翻译者程巍用这一连串看似平行结构的罗列,指涉实际上正在发生的递进式的社会难题。当事件一步步恶化时,我们既需要安抚的力量,也需要获得事实真相。如果缺乏一种更为透明的内心书写,那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也就只能通过颂歌来获得暂时的麻醉,等清醒过来,还是要承受生离死别的人生至痛。我没有要将道德问题强加给写作者的意图,什么样的文字更能契合读者悲伤的心境,他们自有判断,而用什么样的文字来引导他们,则在于一个作家的专业素养和思想格局。这就是灾难文学的价值诉求,它需要根据具体的现实来进行自我内部的调整,否则,缺乏深邃反思的灾难文学,只会是降低我们精神免疫力的心灵鸡汤。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是需要“鸡汤”的,他们可以屏蔽具体的日常和真相,完全活在幻想的童话世界里,可那些充满感动元素的虚幻美好,能麻痹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离需要的真相越来越远。这种鸡汤文学所导向的歧路,虽然不是邪恶的,可难免会让我们一遇险境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恐惧里。
在青春时代阅读那些关于瘟疫、灾难和疾病的作品,对我而言,可能都属于“成长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是在实施教化的功能,而是在文学与道德的范畴中激活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虽然它是以修辞的手段,可也从另一些侧面重塑了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写作者。
3
直到2019年底,我博士毕业工作十年之后,又一场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疫情突然而至,起初因为各种原因,我们确实感到猝不及防。相比于2003年的SARS,时隔17年之后的这次新冠病毒性肺炎疫情更让人恐惧,一方面在于它的传染性强,另一方面则在于我们没有心理准备。因为身处疫区的湖北,除了响应号召在家里坚持宅着,别无他法,每天看手机,心情跌宕起伏,长久难以平静。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我一直比较关注疫情发生的中心武汉,接着是我身处的宜昌和我的家乡荆门,再是整个湖北以及蔓延至全国的其他省市,每天不断变化的数字,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正在受病痛折磨和死去的人。这一次,我才真正理解了很多人所言的,死了两万人,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一个人死了两万次。那种痛不是一些虚幻的文字所能形容的。无一例外的是,疫情发生后,那些过去曾经使用过的词汇和句子,又开始进入一些人笔下。世界在上演同一场悲剧,他们也就在为这一悲剧赋予同样的悲哀、麻木与乡愿。在事先搭建好的悲剧书写模板里,我们是否只需要往里填充用滥了的词汇就能够创造新的岁月静好的现实?太简单了。周而复始地循环,都多少年了,还是那一套殇之语,它们要召唤谁成为这次疫情的主角?而谁又能为这次“重大事件”承担相应的责任?文学在病痛、疫情和死亡面前,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一种乏力。瘟疫和疾病,让一个社会暴露出了它的某些真相,也让我们窥见了一个地区低效能运转所付出的代价。就像加缪早在《鼠疫》中说:“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为什么这次疫情发生后,人们又开始关注鲁迅和加缪,重提闻一多和北岛?面对历史和现实,我们在他们的作品里找到了共鸣。
严重的疫情导致武汉及其湖北其他地市相继封城,面对汹涌而来的病毒传染,大家都在远方喊“武汉加油,湖北加油”,可一旦真正的武汉人和湖北人出现在面前,某些人还是会像躲避瘟神一样远离他们,甚至歧视他们。这是不是人的本能?但在隐喻和文化层面,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避让”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我只能想到尼采所感叹的,人性的,太人性的。这也真正在桑塔格那里获得了印证,疾病有着极强的传染性,更重要的是,它成了一种身份的标志,令人感觉吊诡的是,这样一种远和近的人性悖论是否需要构成对很多人道义上的谴责?其实大可不必,在人性本能反应中,其因无防护措施时对瘟疫的应急机制就会是拒绝。湖北天门的一位货车司机在封省之前送货到了四川,等他从四川返回湖北过年时,他可能遭遇了此生无法忘却的痛:因各地都严查外地尤其是湖北车辆,他不能下高速公路,他沮丧地开着车在高速上走走停停地过了近20天,直到地域歧视现象在网络上被炒得沸沸扬扬,他方在陕西汉中的高速服务区得到了交警的救助,这位司机面对高速交警送来的温暖百感交集,痛哭不止,想必内心更是五味杂陈。这一辛酸的个案虽不能代表全部流浪在外的湖北人所处的困境,但也真正折射出了在疫情面前,人性、制度与空间区隔之复杂。
更让我难以释怀的,还是在疫情病毒肆虐之际,有些写作者又试图以惯性思维“唱赞歌”,但很快就被网民彻底打回了原形。因此,有人说,疫情是一面“照妖镜”,所有人的真实面孔都能够被清楚地映照出来。与2003年我所经历的SARS一样,在疫情面前,冲锋在第一线的,仍然是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而这次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承担的任务,要比SARS时期大得多。一场又一场的攻坚战让他们疲惫不堪,有不少医生因为感染病毒而去世,医者仁心当然是我们应该敬重并书写的。然而,有些人写的诗歌并没有抓住主题要害,依然是号召性的陈词滥调,尤其是在那么多的死者与病患面前,缺乏道义和人性的煽情是轻浮的。他们遵循的是从词到词的规则,而这些词的滑动,又有哪一个指向了这场疫情的内核?无处发泄的压抑,只能以词的方式滑向虚无的空洞,它强化了某种“围观苦难”的心理,而我们又如何在趋于缥缈的诗中维护写作者的尊严?即便是创作诗歌这种精粹的语言艺术,与日本捐赠给武汉的救援物资上所写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相比,我们那些口号式的修辞又是何其贫瘠、粗鄙。
我希望读到的文学应是鲜活而有力量的,是靠近真相的,这一次,当我再读到那些为完成指标和任务硬写的“抗疫诗”时,更多的不是无力感,而是愤怒。不是说诗人们没有靠近真相,也许他们所书写的正是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但还是显得狭隘、局促和乏味。时代在进步,可有些高高在上的诗人并没有转换自己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还沉浸在对低层次的廉价抒情的重复之中。当文学必须介入时代,它不仅要经受词语的磨炼,更要经受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检验,这样它才不至于是一场文学的“失败”之战。相反,我在很多非虚构的文字中读到了力量。他们的文字有性情,有温度,在靠近真相的同时,也在直指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他们的人文情怀不是通过刻意煽情的文字来体现,而是在字里行间渗透了一种追求真相的职业责任感。还有,更多文字中有作者的专业精神和诗性正义,不管是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医学科普,还是批评有些部门的不作为,既直指要害,又尖锐得体。在疾病和瘟疫面前,一切可以形成有效功能和秩序的文字,必定暗藏着内在的责任,不管它选择什么样的词语和方法,也无论它是否具有抗争精神、道义评判和爱的给予,都是在更高的价值观念中能为我们提供一份可信任的真相和期许。
不知是不是年龄渐长和认知变化的缘故,我越来越倾向于理性的力量。这种理性在于对真相的不懈寻求,也在于科学的态度和求真的意志。瘟疫和疾病對人类的伤害,需要医学来救治身体,需要社会公共卫生管理和应急机制的加强,同时也需要自我精神的修复,这种自我修复里就有来自真相的慰藉。对于作家来说,写出好作品是最大的真相,而对于批评者来说,审美判断与价值衡估则是至高的标准。这也是我对那些有良知的记者所写的深度报道和有情怀的作家所写的疫区日志更有好感的原因。它们精准地呈现了特殊时期的公共经验,重要的是,它们替我们大多数无声者表达了期待社会治理改善和科学进步的诉求。文学的发声有权力的限制,但是它投射出的微光,更是我们所希望治愈和康复社会肌体的话语机制。
在生命面前,疾病和灾难是无情的;在谎言面前,追问和反思当更有必要。在需要真相和真言的同时,我也一再想起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说的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刘波,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等专著七部。曾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扬子江诗学奖·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