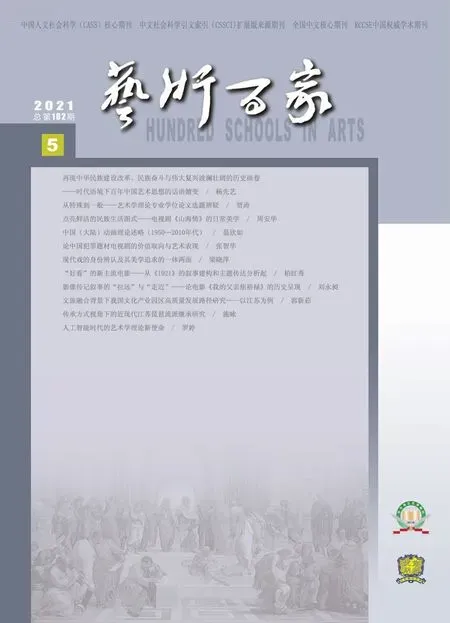人生境界:中国电影审美的哲学本体探究*
陈 阳
(1.北京电影学院 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 100088;2.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从中国电影乃至更大范围的华语电影来看,人生境界问题往往与电影审美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哲学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儒释道三家都旨在确立或追求某种卓越或超然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提出四种人生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对于中国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叙事和审美研究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生境界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意境具有重合叠加和相互提示印证的关系,高尚的人生境界在精神上获得高度的自由,与山川日月一同焕发出勃勃生机,因此引人向往,催人联想,并随之进入到美的情感和优美的意境之中。可以说,这一中国电影的审美机制普遍存在于各个时期的中国电影之中。
之所以在已有的电影意境审美以外,再提人生境界与中国电影审美问题,是因为这实则关系到中国文化和哲学影响下的电影艺术本体以及叙事等诸多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显现出极强的文化生产力。除此之外,以人生境界为审美基础的电影本体意识,也可在哲学层面超越电影艺术和商业的传统理论界限,对于中国电影未来的健康发展极具启示意义。
一、人生境界在中国电影艺术中的表现
在电影如何存在的问题上,技术的存在形式和人的存在形式同样重要。而就电影所表现的人的存在方式来看,中国电影以及更大范围的华语电影则更多地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中国文化中,人的存在和天地世界的存在保持着“合一”关系,而非是主客体的对立或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关系。因此,这种“合一”乃至和谐的关系,也反映在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上,并进而转化到日常文化的诸多方面。在艺术创作上,又体现为追求超越日常欲望目标而抵达某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并在价值选择上表现出“利他”而不是“利己”的总体特征。从中国电影发展史来看,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伦理剧”,还是30年代的“新兴电影运动”、国防电影以及抗战胜利后的电影,均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本质样态。近些年来,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华语电影,如《卧虎藏龙》《一代宗师》《刺客聂隐娘》《桃姐》《英雄》《天下无贼》《那山那人那狗》《我不是药神》等,都能在中国文化所讲求的“人生境界”方面找到共性特征。尽管这些电影分属于不同的类型、题材,并且在风格上也有诸多差异,但是在叙事方面所表现出的人物内心世界,却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可以超越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从而显现出中国哲学和美学总体影响的特征。
按照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所分的四种人生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国电影中的主人公形象大抵可归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些人物对世界、人生均有较高程度的“觉解”。道德境界中的人物,以有利于集体、社会和他人为人生基本原则,即便是平凡普通的人物,也能令观众感受到其内心世界的高尚,至于舍生取义之人,则能达到崇高美的审美境界。能达到天地境界之人,对于宇宙人生有着更高的“觉解”,能够将对生命的感悟融入日月山川,将有限融入无限,即是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人物,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社会,都属于大众社会的普遍存在,满足于基本生存或自我逐利的本能欲望。属于这两重境界的人,不止是普通大众,也有许多是有了很高社会地位、名望的人,但因为他们对于社会人生缺少“觉解”,只能停留在以私欲为第一位目标的精神层次。即便如秦始皇、汉高祖这样的帝王,也仅能停留在功利境界,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为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的《新原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哲学概括的内里饱含中国历史文化精髓,充满理性的分析把中国数千年文化的价值内核予以逻辑层级化、明晰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称抗战时期是中华文化觉醒的时期并不为过。因为这一时期不仅有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大量引入,更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人格精神意识的弘扬提倡。冯友兰先生所撰写的人生哲学著述,无疑是形而上层面的大力提升。人生哲学的本体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从中国文化历史来看,具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才具备了文化意义上的人的标准。同时,明确了真正人的意义并非个人生理欲望的满足,也非对世界的征服和对他者的掌控,而应该是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有着“为公”“利他”“忘我”“与天地合一”等品格。在此两种境界的参照下,中国人生哲学本体意义上的人,需要经过长期的修炼、修养方可达到此种境界,并且升华出打动人心的情感和美感。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中华文化始终以提升人的生命境界为己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人对文化功用的恒久理解,并不因世事变迁而消弭,在遭逢艰难困苦之际,尤显人生境界之可贵。因此,也不难理解费穆在抗战最艰难时期拍出《孔夫子》的用意,儒家的人格精神有着促使中国人文化意识觉醒、充分激发人们爱国热情的文艺功效。
或许,有人会质疑如此高蹈的人生境界标准,能否适应电影的大众化取向?对于这样的问题,武侠片的拍摄历史似乎更具有例证意义。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武侠神怪片,除惊险刺激的视觉效果之外,很难找到人生境界对电影叙事的影响。但是,随着武侠片的文化意识不断增强,人生境界在武侠片中的表现也就变得越发明显,至《卧虎藏龙》《英雄》和《一代宗师》等影片的出现,侠义精神及内在人生境界的凸显,则把武侠片推到了中国文化的新高度。如果从类型电影的角度看,近年出现的《我不是药神》是21世纪中国类型电影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人生境界思想对于该片叙事模式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片主人公程勇的人生无疑跨越了两重境界,即从前期的功利境界转换为后期的道德境界。前期,他是为了个人生计而去印度贩卖仿制抗癌药品,而到后期则是为了拯救众多癌症患者的生命,此时,不能不说他已经进入到了“利他”的道德境界。这重内心境界成为他行为的动机,进而推动整部电影情节奔向感人的高潮。实际上,我们在其他类型片里,也经常会看到人生境界的提升成为情节反转的关键契机,其中人物从小我走向大我,从自我转向利他,由此展现人生的成长和人性的成熟。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生境界的转换也是中国电影叙事的一个重要机制,并普遍存在于各种不同时期的类型题材中。无论是人格、人性光彩的显现,还是人品的堕落,我们都可以从人生境界的考量中找到内在的理据。中国人生哲学数千年积累的深厚底蕴,在近代以来的百年激荡中愈发显出其对社会现实和艺术创作的关照能力。尤其是在社会艰难时期或人生低谷时刻,人生境界意识既是品评现实人物的标准,又是把握生活方向的尺度,同时也赋予高尚情怀以美的评价基调。例如,抗战胜利后问世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影片,对人性的高尚和人格的低下均有精彩展现,其所鞭挞的社会乱象和“私欲”人格,就不仅是政治意义层面的,更是文化价值尺度在电影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而影片在当时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力,也说明了这一文化价值尺度早已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的文化共识。
在这里,不妨说中国电影中存在着一种赋予民族精神的“坚韧美学”,其与中国人对人生境界的信仰密切相关,它是中华民族能够渡过各种艰难困境的精神源泉。抗战时期是如此,同样,在“文革”之后,谢晋导演的“反右三部曲”,即《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在政治层面“拨乱反正”的深层意义亦可反映出文化价值的支撑基础,因此,政治信仰和文化信念的双重作用,才使艺术化的人物和故事成为时代的象征。人物坚韧的性格必然闪现出人性的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境界的差异在电影中转换成一种普遍的戏剧性张力,由此可以演绎出无数感人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具备了叙事母题的根本特征,这或许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独特的思想性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十七年时期”生产的大量红色电影中,英雄成长主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境界”也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传统文化中的“为公”和“利他”与革命中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基本并行不悖。
二、人生境界与电影审美意境
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诗意不断融入和显现的过程,中国传统诗词艺术在电影中也有着或局部或整体的表现,同时,我们也会切身感受到这种电影诗意与人生境界的深层关联。如果从世界电影发展史来看,电影诗意与生命意识也是一个恒久的研究话题。早期法国电影先锋派认为,诗意是电影艺术性的根本所在,只有能够显现出所拍摄的人或物体的内在精神和生命意识的电影,才能登上艺术电影的殿堂。当然,法国先锋派的电影诗意理论赋予了电影艺术本体论的发展取向,但却因其竭力隔绝电影与历史、叙事乃至社会与人生而留下诸多问题。中国电影的诗意始终与人生境界连接在一起,这里自然也包含着生命意识问题,宇宙自然与人的生命、人性保持着总体的内在联系,因此也具有中国人生哲学的深层根基,是一种“大全”而不是单一或片面。自然山川及万物所显现的诗意,与人生状态保持着有机联系,在写实的同时又不断发掘诗意的呈现特质。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意境这一传统审美范畴在进入电影学研究领域后获得了普遍认同。早期中国电影便开始尝试将富于诗意的意象植入电影,开启了古典诗词意象的电影化之路。电影诗人费穆更是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道义担当熔铸到“国防电影”之中,以激发人们的抗战热情并唤醒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在费穆的电影中,人生境界与审美意境得到了十分精彩的诠释。新中国电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一步探索电影民族化之路,在电影民族风格方面曾做过多种尝试,尤其是在诗歌意境的电影化呈现方面为中国电影理论积累了不少经验,例如,郑君里在《林则徐》中化用古诗词拍摄出登高远望的意境场景。意境无疑是诗意的显现方式,但如何将其与电影叙事有机相连,如何处理好电影静止与运动的关系,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与本文更为直接的问题是,意境和人生境界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显然不是简单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因为在意境中既有客观世界的景象,又包含着人这一主体的感悟和情思;而人生境界不仅是内化的存在,同时也有溢出时的外显与折射。能够从眼前意象中感受到意境的人,其人生境界必然进入到某种审美状态,这一时刻也是对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超越。当然,这样的时间过程得以持续,在电影时空中浸润着主客体交融的情感状态,心灵在大自然的浩淼中尽情体验着超越的审美境界。人生境界需要不断淬炼、提升,至于天地境界的人,其生活的世界必然充满诗意,亦可说时时处处皆可见意境。应该说,人生境界向高层级转化的过程,是一个“觉解”程度加深的过程和结果,当达到一个类似于“顿悟”的时刻,眼前的一切必然获得诗意的情采和深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人生境界尽管属于人生哲学范畴,但它的最终指向却是审美的人生状态。李泽厚曾在《悼念冯友兰先生》中讲:“冯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即是我所讲的‘审美境界’,在这境界中的人,是‘参天地、赞化育’,启真储善的自由人生。”[1]25李泽厚明确地将两者联系甚至等同起来,指出能够进入到“天地境界”的人,实际也就是进入到很高的“审美境界”之中,此一种与宇宙同一的人生精神状态,也便是审美的状态,同时也具备了真与善的人格状态。张世英先生近年也曾提出新的“人生境界”说,即“欲求的境界”“求实的境界”“道德的境界”和“审美的境界”,把“审美境界”视为人生境界的最高层级。[2]13—14
冯友兰先生从形上学的方法论角度,论述了人生境界跨越哲学和美学领域的问题。冯友兰先生认为形上学的方法可分为“正”和“负”两种,“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3]869。实际上,冯先生所讲的“负”的方法,即是诗的方法,这里也包含着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和体悟。冯友兰将诗分为“进于技底诗”和“进于道底诗”,“进于道底诗亦可以说是用负底方法讲形上学。我们说‘亦可以说是’,因为用负底方法讲形上学其是‘学’的部分,在于其讲形上学不能讲。诗并不讲形上学不能讲,所以它并没有‘学’的成分。它不讲形上学不能讲,而直接以可感觉者,表显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及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这些都是形上学的对象。所以我们说,进于道底诗‘亦可以说是’用负底方法讲形上学”[3]960。这实际上是在说,诗虽然不属于哲学、形上学,但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却可以同样达到形上学的思想深度。
那么冯友兰所讲的“进于道底诗”有哪些呢?他所举出的诗词例子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应该说是有意境的,这种意境既包括“南山”“飞鸟”这些可见的景象,同时也包含了诗人内心不可见的感觉和思想。而末句的“欲辨已忘言”则表明了内心感觉的无限指向,“南山”“飞鸟”把人的思绪带入了更加广阔的世界,绝非眼前所见、所感能涵盖的,即进入到冯友兰所讲的“大全之浑然”状态,世界也因此从“形而下”的可见转换为“形而上”的不可见。陶渊明这首诗看上去是在写自然风景,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对人生的“形上学”思考,因此才可以称得上是有“意境”的佳作。如果落实到诗人所能达到的人生境界,当然应该属于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
达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的人物,也就具有了人格美的诸多特点,因为在他们的生命意识中,饱含着人生、历史和宇宙的深刻“觉解”和体悟,而不再视通常的自我欲望或功利目的为唯一,显现出超越且豁达的人生襟怀。因此,林则徐登高远眺,目送邓廷祯远行的那个充满意境的场景,就不仅仅是对古诗的电影化用,也是在表现不可看见、感觉,“不可思议”实际又是引人联想、深思的内心世界。这样一个富于意境的场景、镜头,即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显现,因此可以说其既是诗意盎然同时又是富有哲思的。
中国电影意境研究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积累,但是如果要从中国哲学的高度抽象概括电影本体问题,人生境界无疑更具有全面的涵盖广度和深度,因为它既可以深入到叙事动力内在机制,也可以是各种影像画面场景创作的内在理据。它还可以跨越各种题材类型,无论是所谓的艺术电影、作者电影还是商业电影,甚至是各种与人类社会相关的记录电影。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跨越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也无论电影技术和媒介形式进入到怎样的发达阶段。因为高科技所带来的创作想象力的自由,必然以人生境界所能实现的审美高度为标准,并以此来彰显其存在的价值。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生命境界为最高目标,把人的生命境界提高到审美境界中来,而中国电影无疑在此满足了哲学的根本诉求。
三、中国电影艺术的“形而上”本体之思
叶朗在《再说意境》一文中提到,“宗白华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说过,中国艺术常常有一种‘哲学的美’,中国艺术常常包含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另一方面,宗先生又认为,中西的形上学分属两大体系:西洋是唯理的体系,它要了解世界的基本结构和秩序理数;中国是生命的体系,它要了解、体验世界的意趣(意味)、价值”[4]109—110。由此看来,意境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它所蕴含的“哲学的美”还应该联系哲学“生命的体系”来考量,从人与世界同一的高度来讲,人的价值体现有赖于对世界的意趣(意味)和价值的了解及体验深度。因此,中国哲学中的人与世界,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总是密切、有机地连在一起,而不是主、客观的对立状态。所以,冯友兰所讲的“天地境界”及其“大全”,即是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并体验到意趣(意味)和价值的真谛,至此境界的人自然会有云淡风清的从容和镇定。如果从时间的角度看,这可能是历史瞬间的呈现,但又可延伸至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汇聚了叶朗在《再说意境》一文中所提到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人生和历史经验由此上升到哲学高度。在中国电影时空中,叶朗先生所讲的三种感受亦表现在电影叙事的多个层面。
宗白华先生所讲的中西形上学之分,亦可启发我们思考中西电影研究的本体问题。由于西方形上学“唯理的体系”特点,延伸至艺术哲学乃至电影理论体系,也相应体现出“了解世界的基本结构和秩序理数”特征。因此,巴赞的“真实美学”理论在西方电影经典理论中所独占的特殊位置,与西方形上学保持了逻辑上的高度一致性。而中国电影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努力,又的确是按照“了解、体验世界的意趣(意味)、价值”的生命体系路径发展。与此同时,电影技术的进步也暗合着“了解世界的基本结构和秩序理数”的根本诉求,相对来说,中国生命哲学的价值取向,在技术进步的需求动力方面便显得有些被动且不足。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方电影理论由哲学形上学衍生出的本体论,对于物质性和技术性的考量占绝对的基础地位,而中国由哲学形上学延伸出的电影本体论问题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并且处于被淹没以致难以言说的状态。
电影本体论的问题最早由巴赞提出,因其具有哲学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意义,使电影本体论对于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发展方向影响深远。陈犀禾、刘宇清曾在《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一文中提到英语语境中的Ontology,即本体论的原意可解释为“对事物或存在的性质进行形而上学研究的分支”,“本体论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对事物的性质进行研究的理论。对电影而言,本体论研究是对电影性质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并没有限定电影本体论只研究电影影像的性质”[5]77。因此,陈犀禾、刘宇清在文章中认为,对电影本体的研究不应该限于对电影材质、形式、感知方式的研究,还应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他们借用罗伯特·斯丹姆《电影理论》所提出的观点,认为电影文本复杂多样,电影本体论研究的视角也应该更加多元才能匹配。应该说,这样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也为我们从中国哲学形上学思考电影本体问题提供了依据。概括地说,中国电影所体现出的意趣和价值大多可以归结为生命哲学的“形而上的意味”,也可以体现人生境界从本能向崇高的升华过程。这便是中国电影文本的普遍存在形态,也是由中国哲学衍生出的中国电影本体基本状貌。当然,由人生境界生发出的电影崇高之美,在世界电影中也可以找到众多的相似例证,因此也具有普遍价值的特点,并且形成与西方电影本体论相互对比互补的对话关系。
西方电影本体论研究,往往在物质现实和幻想世界、主观和客观之间摇摆。美国学者斯坦利·卡维尔针对帕诺夫斯基和巴赞主张的“电影描绘和表现现实”的观点,提出了“电影命中注定要揭示现实与幻想”[6]179的电影新本体论主张。实际上,长期存在的蒙太奇理论和巴赞理论的对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两种电影本体论思想的分歧结果。在巴赞现实主义理论盛行的同时,现代主义电影却以表现心灵梦幻世界风靡世界。如何弥合这种长期精神分裂的事实,的确是西方哲学家和电影理论家思考的重心,即西方新电影本体论。德国学者托马斯·埃尔塞瑟在《作为思想的电影:关于“电影与哲学”的论争》一文中说:“在最基础的含义上,21世纪的新电影本体论将是一个分类系统,它抛弃了许多我们通常在电影研究中运用的范畴(比如‘作者’‘类型’‘现实主义’‘虚构’‘纪录片’‘先锋’‘古典/后古典好莱坞’‘后电影’)。这意味着抛弃作为中心范畴的‘再现’,它是诸如文化研究领域中几乎所有工作的基础,涉及对种族、阶级、性取向、民族与宗教少数群体的再现。新的分类方式并非是武断、全凭个人选择的,而是根据许多传统的哲学领域来评估电影,比如认识论与知识论(我们如何知道、知道什么)、心灵哲学(他人心灵、其他世界)、美学(真理与美,或优美与崇高的关系)与阐释学(人为符号系统与符号行为)。”[7]21
“内在性”和“外部力量”是托马斯·埃尔塞瑟所关注的焦点。围绕着与思想、世界和自我相关的电影自动机制问题,他总结了德勒兹、卡维尔、朗西埃和巴迪欧等人的观点,从而指出电影自动机制使人从内在性、主体性中解放出来的哲学意义。对于德勒兹而言,电影是一种存在状态,“在其中,我们的头脑与身体是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并通过同时把自我与思想交付给精神自动装置(spiritual automaton),将我们从内在性中解放出来,弥合主体—客体、心灵—身体的分裂,以及主体性的自我分裂和虚幻的自我呈现”[7]25。我们可以看出,电影“自动装置”提出的意义,在于提示电影对西方哲学思维的深刻影响,即电影改变了西方哲学既往的“内在性”取向,而这种“内在性”又曾直接导致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心灵和身体的对立和分裂问题。卡维尔更是直接宣称,摄影满足了人类“逃出主体性与形而上学孤独的愿望”[7]25。但是,在巴迪欧看来,“自动装置”对“内在性”放弃的结果凸显了“外部存在”,但却又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外部存在,而是“更为深刻的外部存在”,也可将其称为电影所具有的“外部的力量”。但是,这种“外部的力量”没有任何外部世界与之对应,也没有对应的“内在性”和主体性世界。“深刻的外部存在”到底又是什么?看来,“内在”和“外部”的对立纠缠似乎仍在不断延续,托马斯·埃尔塞瑟索性跳出去,提出欧洲当下最为重要的是维持启蒙运动的有效性和紧迫性问题。
或许,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欧美从哲学到电影的新本体论路径,是否也是中国电影本体论所必须遵循的?其中较为关键的问题是,对于电影“自动装置”这一欧美当下理论的重要概念,我们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应该如何理解?是否我们也需要“从内在性中解放出来,弥合主体—客体、心灵—身体的分裂”?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始终视主客体为同一的存在,因此人生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才是“天地境界”。从人生哲学意义上说,这既是人生的理想,也是人生的目标,人只有不断从自我走出并融入世界,也就是达到主客观的融合,方能进入此一境界。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强势影响,一些电影也表现出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身体分裂的取向,这种电影意识或许在欧美电影本体论的转向中受到启发,或许会在对中国人生哲学的重新思考中寻找到新路。
如果从中国人生哲学本体出发,人生境界应该是评估电影的一个重要标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一人生哲学所探讨的终极问题,既严肃又充满灵动的意趣。无论是历史变革的时代,还是高科技革命的时代,人生的四重境界都有着丰富的表现,因此能够涵盖人类历史的纵深,不断提升人类社会的总体生命境界。这种人生境界的标准更加符合大道至简的原理,我们以此可以更加清晰地审视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甚至可能在新电影本体论理论和实践格局中获得更广阔的空间。
从人生境界的高度审视中国电影,可以看到其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阔。从普通个人到社会、国家乃至更广大的宇宙,均在一个有机的整体范畴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参透个体人生亦即参透整个世界,这便是哲学的抽象性向美学的普遍性的转换过程。个体人生的价值意义,在超越自我的局限性之后,才具备了与宇宙世界同一的博大与精彩,正如苏东坡在《赤壁赋》中所言,“哀吾生之须臾,念天地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样的人生态度所转换出的审美画面,同样也表现在众多中国电影之中。人类从小我里跳脱出来,眼前就是一片广袤的宇宙世界,如果加以概括,这是一种“无我而生美”的境界,无论是一个镜头、一个场景还是一个故事,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类型片,这种美都有着广阔的生长空间。
对于大多数商业类型片来说,剧中人物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向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转换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叙事逻辑与中国的文化逻辑、人生哲学形成天然的同一关系,随之产生的精神、情感的升华,启示着电影叙事、文化和审美的一致性逻辑,这也就产生了中国电影研究或评价体系的总体感问题。因为电影叙事的核心是变化,如果剧情缺少变化,就难以产生戏剧性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大转折。一个人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为了个人生计或者是为了个人功名忙碌奔波,但是突然有一天受外界触动而内心有所“觉解”、醒悟,从而有新的行动并进入到另一种人生境界。无论是《我不是药神》里的程勇、《天下无贼》里的王丽和王薄,还是电影《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他们均经历了人生境界的转换过程,因此,尽管故事内容或历史背景相差悬殊,但是总体来看这一电影文化现象本身又体现着中国人生哲学的高度,也令观众产生深切的认同感。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生哲学所蕴含的生命意识和诗性气质,在中国电影叙事表意中有着全方位的体现。从叙事的内在动力机制到人物的精神成长过程,从镜头画面的含蓄隽永到镜头内外的情感张力,人生境界既是创作的起始点同时也是影像情感表意的内在理据。中国早期电影文化自觉意识的萌发,基本的叙事结构便是以不同的人生境界差异、冲突为基础,而至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及更大范围的华语电影,类似的叙事建构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生产能力。
如果说电影本体论讨论的是电影如何存在的问题,境界或许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朱良志认为“境界不是认知的世界,而是人体知(即体验)的世界”,“境界所反映的不是人对这个世界的概念把握、知识累积,而是将人放入这个世界中的际遇、境况、体会,并由此而形成的审美超越、人生感喟、人格启迪、气象熏陶等。人不是在世界之外认识这个世界,人就与这个世界同在,这世界就是人的语言。因此,境所反映的不是知识,而是人的生命的信息。境是存在者的世界”。[8]281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国电影的“人生境界”本体论能够成立,与西方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电影本体论之区别就十分明显,而与西方新电影本体论在感知体验方面是否能形成更多的互动,将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