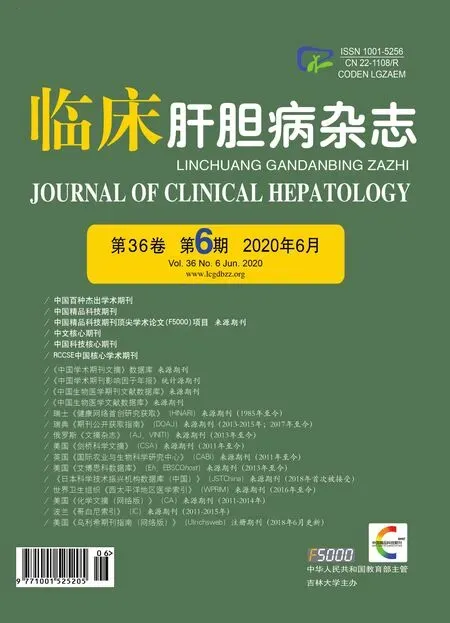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进展
涂荣芳, 杨 雪, 唐映梅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 昆明 650101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是一种慢性胆汁淤积性肝病,病理特点为进行性、非化脓性、破坏性肝内小胆管炎症,最终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衰竭。血清抗线粒体抗体(AMA)阳性,尤其是AMA-M2阳性对PBC的诊断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73%的PBC患者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1]。合并的肝外疾病通常在PBC病程中发生,也可早于或与PBC同时发生。这些肝外并发症可改变PBC患者的疾病进展及预后,增加其诊治的难度, 迅速识别肝外疾病能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2]。研究发现PBC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涉及多个器官及系统,本文就PBC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PBC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疾病谱
不同国家和地区报道的PBC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比率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以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硬化、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风湿性疾病及甲状腺疾病最为常见[2-17](表1)。
PBC合并系统性硬化的患者多表现为CREST综合征。CREST综合征是系统性硬化的一个特殊亚型,是一组表现为钙质沉着、雷诺现象、食管运动功能障碍、指端硬化和毛细血管扩张的综合征。Powell等[12]回顾性分析显示,558例美国PBC患者中3.9%合并CREST综合征。意大利相关研究[13]则显示,6%~15%的PBC患者合并CREST综合征。PBC患者中最常见的甲状腺疾病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是一组由T淋巴细胞介导的以甲状腺为靶器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最常见的是格雷夫斯病和桥本甲状腺炎。Gershwin等[5]回顾分析了1032例PBC患者的病历资料,发现11%的PBC患者合并甲状腺疾病,其中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的患者达9%。Floreani等[4]的研究发现,20.4%的PBC患者合并桥本甲状腺炎,3.2%的PBC患者合并格雷夫斯病。

表1 PBC合并风湿性疾病和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率
除风湿性疾病和甲状腺疾病外,PBC患者还可合并胃肠道、肺、皮肤等多个器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16,18]显示,2%~7.5%的PBC患者合并炎症性肠病。一项纳入47 325例炎症性肠病患者的研究[19]表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PBC的患病率较普通人群升高2倍以上。合并炎症性肠病的PBC患者多为溃疡性结肠炎,PBC合并克罗恩病患者多作为个案报道出现,尚无研究表明PBC患者中克罗恩病的发病率升高[20-21]。乳糜泻是一种遗传易感个体摄入含麸质蛋白及其相关醇溶蛋白后引起的以小肠受累为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也是PBC患者常见的胃肠道合并症。研究[5,22]显示,1.4%~11%的PBC患者合并乳糜泻。一项纳入8000多名受试者的研究[1]证实,乳糜泻患者中PBC的患病率比普通人群高20倍。同时,短时间无麸质饮食后PBC患者的组织学和生化学指标均有显著改善。
肺组织同样是PBC患者自身免疫反应的潜在靶点。5%~15.7%的PBC患者合并间质性肺病,一半以上合并间质性肺病的PBC患者同时还患有其他结缔组织病[23-24]。研究[25]显示,高达39%的PBC患者中存在肺弥散功能下降,且在合并干燥综合征的PBC患者中更为显著。其他研究[22-25]还发现,PBC患者肺弥散功能的降低还与肝病的严重程度、抗着丝粒抗体(ACA)阳性以及是否合并CREST综合征有关。目前,PBC患者合并皮肤病的发生率尚存在争议。Terziroli等[26]认为尚无某种皮肤病与PBC存在明确相关性。然而,Floreani等[4]的研究则显示,PBC患者中白癜风、扁平苔藓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皮肤病的发生率为5%。Efe等[27]的研究显示,PBC患者中白癜风的发生率为4.2%,银屑病的发生率为2.8%。
除上述疾病外,重症肌无力、炎症性肌病、血管炎、1型糖尿病、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结膜炎、膜性肾小球肾炎、间质性肾炎等疾病作为PBC的罕见合并症,国内外均有相关病例报道,但目前尚缺乏大型流行病学调查。
2 PBC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由遗传基因、感染、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而发生的,不同自身免疫性疾病在遗传背景和致病机制之间存在交叉从而出现自身免疫重叠现象。随着分子遗传学、风险相关单核苷酸多态性研究和人类全基因组学关联研究的进展,很多学者认为基因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共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4及干扰素调节因子5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1型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炎症性肠病和PBC的突出风险基因[28]。此外,人类全基因组学关联研究还发现PBC与类风湿关节炎存在膜型基质金属蛋白酶4、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趋化因子受体5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Ⅱ类抗原HLA-DQB1等多个共同易感基因[14-15,29]。蛋白质酪氨酸磷酸酶非受体22多态性与PBC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的发病显著相关[30]。而趋化因子受体5和酪氨酸蛋白质激酶2则与PBC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易感性有关[29,31]。这些共同的风险基因可能是PBC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重叠现象的遗传背景,但仍需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和验证。
PBC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存在共同抗原及抗原交叉反应可能也是发生重叠现象的原因之一。丙酮酸脱氢酶复合物(pyruv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PDC)是PBC特异性抗体AMA的主要抗原,肾小管间质性肾炎患者的肾小管细胞中检测到PDC的异常表达,而体外研究也证实,PBC患者体内纯化提取的免疫球蛋白可以转移到肾小管细胞中与PDC共存,从而推测PDC可能通过干扰肾脏线粒体代谢诱发肾小管间质性肾炎[32]。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类基因在慢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患者的有髓神经纤维及PBC患者的胆管中均有表达,提示胆管上皮细胞和Schwann细胞中存在共同抗原。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特异性抗体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与AMA-M2之间存在交叉反应[33],而在炎症性肌病患者的肌肉组织中同样发现AMA特异性受体蛋白的存在[34]。此外,AMA还可以通过抑制核苷酸转运来干扰心脏能量代谢,并通过与Ca2+通道蛋白发生交叉反应而诱导细胞毒性作用[35]。
干燥综合征作为PBC最常见的肝外合并症,在遗传背景和发病机制方面与PBC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干燥综合征和PBC均以免疫介导的上皮组织破坏为特征,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腺和泪腺为主要靶器官,而PBC患者主要以小胆管受损为主。在拥有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干扰素调节因子5、HLA DR2、HLA DR3等多个共同风险基因的遗传基础上,感染及环境等外源性因素诱导唾液腺、泪腺和胆管上皮细胞凋亡,凋亡过程中因缺乏PDC的修饰保护,自身免疫耐受被含有PDC的凋亡小体打破,形成以CD4阳性T淋巴细胞浸润为主的细胞免疫反应和以IgA为主的黏膜免疫反应[8]。此外,有学者[36]研究证实, PBC合并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唾液腺上皮细胞中存在PDC。系统性硬化与PBC均可以导致靶组织纤维化,从而推测两种疾病的靶抗原中可能存在一些相似的表位或序列。Mayo等[37]发现,与单纯患有PBC的患者相比,合并系统性硬化的PBC患者体内T淋巴细胞受体8链可变区3阳性T淋巴细胞明显升高,因此推测其可能参与PBC和系统性硬化的发病过程。
3 PBC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熊去氧胆酸(UDCA)是目前唯一被国际指南推荐用于治疗PBC的药物,可改善PBC患者的生化指标,延缓对UDCA有生化应答的PBC患者的疾病进展。PBC患者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时,需在UDCA治疗的基础上选用适当的治疗方案,并且在治疗过程中严密监测肝功能的变化。
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硬化、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发性肌炎等风湿性疾病目前尚无根治方法。对于合并风湿性疾病的PBC患者而言,治疗主要以缓解症状及控制病情活动为主。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依然是治疗风湿性疾病的主要药物,部分患者还需配合使用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进行治疗。PBC合并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应戒烟、戒酒,可使用人工泪液、人工唾液、凝胶等局部替代品以缓解干燥症状,必要时可服用M3受体激动剂[20]。钙离子通道阻滞剂是治疗雷诺综合征的一线药物[1]。甲氨蝶呤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首选药物,对于PBC合并类风湿关节炎的部分患者,需采用甲氨蝶呤联合UDCA的方案治疗。然而,有研究[20]显示,甲氨蝶呤无论是单独或联合UDCA使用,对患者PBC的病程进展均无明显改善。对于PBC合并多发性肌炎患者,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效果较佳,并且可以降低患者病死率[7]。
合并格雷夫斯病的PBC患者治疗以降低甲状腺激素水平为主,包括抗甲状腺药物治疗、131I治疗和手术治疗。对于严重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一般不选择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合并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主要以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为主。部分PBC患者可能会使用利福平或舍曲林控制瘙痒症状,而有报道[20,38]发现,利福平和舍曲林会影响甲状腺激素替代药物左甲状腺素的代谢,导致患者体内促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因此,当PBC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需要服用大剂量的左甲状腺素才能使促甲状腺激素维持正常时,应考虑是否存在其他药物的干扰。同时,由于缺乏针对PBC患者应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的研究,应注意加强对该类患者的随访,以防服用过量左甲状腺素而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增加。
4 PBC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预后
PBC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对于患者预后的影响尚存在争议。研究[39-40]发现,合并干燥综合征的PBC患者较单独PBC患者的肝脏损伤进展缓慢,但是发生间质性肺疾病和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的风险更高。ACA是系统性硬化的特异性抗体之一,约30%的PBC患者ACA阳性。尽管Rigamonti等[39]的研究中,PBC合并系统性硬化的患者肝移植及死亡风险显著降低。但另有研究[14,41]发现,ACA阳性的PBC患者胆管损伤更严重,门静脉高压发生风险更高。Wang等[7]发现,PBC合并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血清免疫球蛋白和碱性磷酸酶水平更高,提示合并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导致PBC预后欠佳。而PBC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GGT和免疫球蛋白水平更低,大部分患者肝损伤不明显,提示系统性红斑狼疮可能会减缓PBC的病情进展,并使肝硬化和肝移植时间推迟[28,42]。然而,Fan等[43]则发现,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的PBC患者接受UDCA治疗后生化反应欠佳。Floreani等[20]的研究显示,与单纯的PBC患者相比,合并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在诊断时的组织学分期、失代偿期及肝癌发生率、肝移植率以及对UDCA的应答率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目前尚未发现合并炎症性肌病对PBC的临床病程和预后有负面影响,但Bian等[35]的研究显示,4.1%的PBC患者合并心律不齐、心肌病等心脏受累表现,且在男性和病程长的PBC患者中更为显著,而合并炎症性肌病是PBC患者出现心脏受累表现的独立危险因素。
5 小结
PBC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可涉及多个器官及系统,目前发病机制尚不清楚,部分疾病与PBC的发病之间仍缺乏明确相关性。PBC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影响患者的临床表现及预后,但如何影响患者预后尚存在争议。因此,仍需对其发病机制、诊断、治疗以及预后进一步研究。同时,临床上应重视筛查可能合并的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提高其诊断率,改善患者的疗效及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