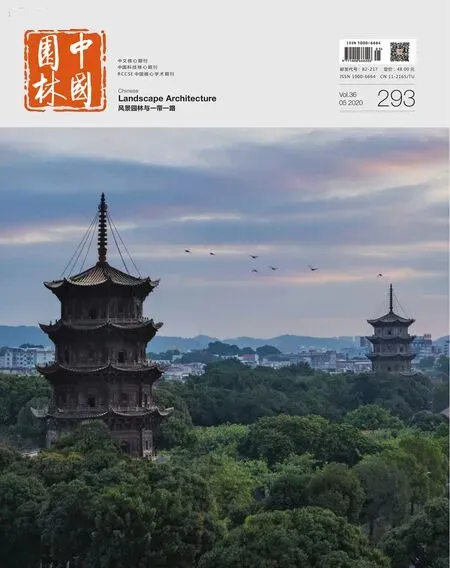古埃及园林植物种类及应用形式研究
董 杰
杨滨章*
由于古埃及园林在世界园林史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它一直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其中对植物种类和应用形式的探寻也从未停止。英国皇家植物园植物学家F. Nigel Hepper和丹麦埃及古物学家Lise Manniche分别著有《法老之花——图坦卡蒙的植物宝藏》(Pharaoh's Flowers:The Botanical Treasures of Tutankhamun)和《古埃及草本植物志》(An Ancient Egyptian Herbal),二者的成果确定了墓室壁画和象形文字中描述的许多植物种类及应用情况。由于历史原因,今天追溯古埃及园林的发展轨迹,只能依赖于古代保留下来的各种史学文献、文学作品,以及各种考古发掘的碑文、壁画、园林遗迹和墓穴中的陪葬品等。值得庆幸的是,在无数前辈学者的艰辛努力下,那些零散的线索已成为我们研究的向导和素材——尽管尚不够系统和完整。本文结合古埃及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探讨了古埃及园林的植物种类和应用形式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1 历史背景
1.1 自然赠礼
5 000多年前的尼罗河及其流域滋养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古埃及文明,洪水将营养丰富的土壤馈赠给沿河的“黑土地的居民”[1]。尼罗河为所经流沿岸的水生和沼泽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而那些热带或亚热带植物及能够适应荒漠环境的灌木和草本植物也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地带自然地生长。
1.2 绿洲农业
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古埃及衍生出一种独特的农业文明模式,当围合的树木阻隔了热浪和风沙,古埃及人尝到了从居无定所的游猎人到成为农夫的甜头,植物的绿洲除了具农业生产的功能外,更成为人们心灵的庇护所,而这或许就是触发他们营造园林的最初动机。随后由园林植物的应用慢慢演化出多种园林形式——庭院园林、宫殿园林、神庙和墓地园林。
1.3 神灵信仰
古埃及人对神灵的崇拜与信仰也促进了园林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他们认为世间的动植物是神对人类的恩赐,很多植物都有象征意义。他们为神灵建立神庙和园林,祭奉植物和植物制品,他们还相信人死后可以在自己的陵墓园林中享乐。这种信仰使得古埃及人对建造园林和应用植物的热衷度一直较高。
2 植物种类
2.1 植物名称辨异
目前中外园林专著、教材和文献中一些古埃及园林植物的名称上存在同种多译、品种混淆等现象。其原因既有作者专业背景的差异,也有中外文化和不同作者或译者使用词汇的差异。如出现频率最高的“Sycomore fig”(Ficus sycomorus),有的直译为西克莫无花果,有的译作埃及榕,还有的译为美国梧桐。本文所使用的植物名称以拉丁名为主,以原著的英文为辅,再通过文中对植物科属种及生物特性的描述,最终确认相对应的中文名称。通过对Tom Turner、Geoffrey、Gothein、Alix Wilkinson和针之谷钟吉等学者著作的整理与对比,结合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译名存在差异的古埃及植物整理归纳如表1所示。
2.2 植物种类统计
据笔者统计,古埃及园林植物共有40余个科,品种较多的有棕榈科、豆科、伞形科等。其中,乔木达20多种,用于观赏、遮阴及食用,且大部分为常绿乔木;灌木10余种,多为带刺的沙漠植物;草本40多种,主要为谷物、蔬菜、花卉、草药、香料和水生植物。这些植物用途广泛,除观赏和食用外,还用于制香、化妆、医疗、祭祀、家具和建材,甚至制作木乃伊等。除了少量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植物,如《圣经》提到的开心果(Pistacia vera)外,其他大多是从古埃及象形文字、壁画、考古遗迹和古代史书中发现并经核实确认的植物种类。
2.2.1 乡土树木

图1 采摘无花果,Beni Hassan墓室画(引自https://dwz.cn/m6bnM1Rr)
古埃及最受欢迎的乡土树木有3类,分别是无花果(包括西克莫无花果)、埃及鳄梨和棕榈树(包括海枣、埃及姜果棕和扇叶棕榈等)。西克莫无花果是最常见的果树,古埃及人自前王朝就开始栽种,是古埃及人的“生命之树”。除了西克莫无花果,普通无花果也很受欢迎。贝尼·哈桑(Beni Hassan,公元前2465—前2323)墓地中的一幅壁画展示了猴子帮助古埃及人采集无花果的情形(图1)。
埃及鳄梨是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独有的树种,古希腊医师迪奥斯科里季斯(Dioscorides)将它命名为“Persea”[2],它是樟科鳄梨属的常绿乔木,其果实和枝条均可用作装饰物,是具有神圣意义的园林树种。其他乡土树种还有阿拉伯金合欢、角豆树、尼罗河柽柳(Tamarix nilotica)和用作香水和医疗用途的辣木(Moringa oleifera)等。
2.2.2 乡土水生植物
在古埃及最有代表性的水生植物就是纸莎草(Cyperus papyrus)和睡莲。“Papyrus”是纸莎草的希腊名称,可能来自埃及语“Papuro”[3],这种沼泽植物来自上尼罗河南岸的努比亚地区,在三角洲的沼泽中大量生长,由它制成的莎草纸是古埃及独一无二的书写材料。
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石雕上,埃及人就刻有埃及蓝睡莲(Nymphaea caerulea),它是尼罗河上象征着赋予生命的神圣植物,其早上开放,晚上闭合,让太阳神阿蒙雷(Amun Re)晚上进入花朵,在黎明时分重生[4]。白莲花(Nymphaea lotus)是奥西里斯神(Osiris)的象征,有圆形的花瓣和锋利的锯齿状叶子,花瓣在下午开放,早上闭合。莲花和纸莎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用于上下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艺术。上埃及国王戴着一顶白色的莲花王冠,而下埃及的国王戴着一顶红色的柳编王冠,造型均源于纸莎草[5]。

表1 译名存在差异的植物
2.2.3 其他乡土植物
当地农作物主要为小麦(T r i t i c u m aestivum)、大麦(Hordeum vulgare),此外还有各种豆类、洋葱(Allium cepa)、大蒜(Allium sativum)、莴苣(Lactuca sativa)、韭葱(Allium porrum)和葫芦巴(Trigonella foenumgraecum)等蔬菜。
西瓜(Citrullus lanatus)和葡萄(Vitis vinifera)是古埃及最常见的水果,古埃及人是最早种植西瓜的民族。葡萄原产于地中海、中欧和西亚地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有紫葡萄种植的记载。公元前3200年之前就有供古埃及统治者和贵族使用的葡萄园,传说中的奥西里斯神是第一个喝葡萄酒并教人们如何种植葡萄的人。
古埃及也有很多本土草本植物用于食用、生产、医疗等。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可以做亚麻布、绳索、篮子,提取亚麻籽油,散沫花的提取物可以作染料。蓖麻(Ricinis communis)和芝麻(Sesamum indicum)也比较常见,古埃及的医者很早就发现了蓖麻的通便和润肤功能。
2.2.4 外来植物
公元前1500年左右,地中海东部和东南部的外来引种使当地的树木和花卉种类不断增加。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女王(公元前1503—前1482)和拉美西斯三世法老(Ramses III,公元前1198—前1166),在征服利比亚、叙利亚期间就将各种珍奇树木和花卉带回埃及。在这一时期的墓室壁画出现了葡萄架和石榴(Punica granatum)[6]。石榴大约在公元前1550年从里海地区引种,它不仅是水果还是药物,可以治疗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壁画还表明,那个时代已经引进了苹果(Malussp.)、扁桃(Prunus dulcis)、茉莉(Jasminum sambac)和欧洲没药(Myrrhis odorata)[7]。曼德拉草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一幅墓室画中出现,图中还有矢车菊(Centaurea depressa)和来自东方的罂粟(Papaver somniferum)。
引种于国外的花卉和其他草本植物还有番红花(Crocus sativus)、百合(Lilium candidum)、蔷薇(Rosa)、银莲花(AnemonecathayensisKitag)、小蓟(Cirsium setosum)和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等[8]。从地中海沿岸引进的树种有栎树(Quercus Linn)、油橄榄(Olea europea)、樱桃(Cerasus pseudocerasus)和桃等。此外还有来自南方的乌木(Ebony)和比布鲁斯(Byblos,今黎巴嫩一带)的雪松(Cedrus),这些树木的板材通常被用来做箱子和棺木等。

表2 Ineni果园的植物种植情况
文献显示,哈特谢普苏特女王为了祭奉阿蒙(Amon)神,专门从东南部神的国度“蓬特”(Punt,今索马里一带)取来香树(Incensebearing trees,木料燃烧时有芳香)[9]。32棵香树被挖出种植在盆中,被水手带到船上,移植到神庙的台层上,一起带回来的还有肉桂(Cinnamomum cassia)。埃及人热衷于制香,他们把香水当作一种奢侈品,当时香水配方中不用睡莲这种本土材料;相反,没药、乳香、肉桂等进口产品备受青睐[10]。
Hepper在《法老之花》中提到,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公元前1339—前1327)墓中发现了面包、水果、葡萄酒、油膏和其他已被确认的植物。墓室中有一个装满了谷物和蔬菜种子的谷仓,还有用来清洁死者身体和头部的油。有的树脂从地中海黄连木(Pistacia lentiscus)中提取,而针叶树树脂则来自地中海白松(Pinus halepensis)、西里西亚冷杉(Abies cilicica)和东方云杉(Picea orientalis)。熏香来自阿拉伯南部或索马里的阿拉伯乳香(Boswellia sacra)和一种没药。软木材的树有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大果刺柏(Juniperus oxycedrus)、冷杉和松树,而硬木则有橡木(Oak)和梣木(Ash),埃及人更喜欢用其做箱子,并用桦树皮(Birch bark)做装饰[11]。
3 应用形式
古埃及园林植物的应用形式比较丰富,而且有些形式在不同场合还有着不同的功能。按照主要用途可以大致分为生产生活、娱乐观赏和祭祀礼仪类。

图2 多样化种植形式,Thebes壁画(引自Gardenvisit网站)

图3 葡萄棚架,Nakht墓室画(引自https://www.pinterest.es/pin/374009944045421349/)

图4 私人花园,Nebamun墓室画(引自维基百科)
3.1 生产生活类
3.1.1 葡萄园
古埃及人种植葡萄较为普遍且有一定规模。为防止鸟类破坏葡萄,常用人工进行驱赶。在果实成熟时采集、酿酒,而后再将酿成的葡萄酒倒入又高又尖的容器中。斯尼夫鲁(Sneferu,公元前2600—前2576)统治时期,埃及北部三角洲地区的管辖者梅腾(Methen)的墓碑上记录了他的花园,其引以为傲的花园“大约1hm2,连着一个405多hm2的葡萄园”[12]。除了用于生产,葡萄园还会种植在神庙附近,它是祭祀的重要物品。
3.1.2 蔬菜园
古埃及人很早就开始在围起来的土地上种植蔬菜,用以食用、交换和出售。除了前文提到的蔬菜种类,还有蚕豆(Vicia faba)、鹰嘴豆(Cicer arietinum)、甜瓜(Cucumis melo)和小扁豆(Lens culinarus)等多种食用植物[13]。由于干旱少雨,大部分蔬菜和花卉都种在种植床里,有些树木也会种在树池中,以防止水分流失或减少蒸发。公元前2000年前古埃及人已经开始使用“桔槔”把尼罗河水引到水渠或水罐,再灌溉到由土墙构成的正方形种植床里。贝尼·哈桑墓室的壁画显示,园丁正在浇灌王室花园的蔬菜地,一条以圆形池塘为终点的运河四周都是种植床[14]。同时期的另一幅壁画也展示了象棋盘一样正方形格子的种植床,里面有许多蔬菜和盆栽植物。
3.1.3 果园
建造果园在古埃及比较盛行。图特莫斯一世(Tuthmosis I)国王时期(公元前1528—前1510),他的建造师伊纳尼(Ineni)列出了果园的20多种树木(表2):包括常见的埃及鳄梨、阿拉伯金合欢和石榴等[15];还有埃及槲果,用于制造芳香油的树[9];用作香水和医疗的辣木;一棵濒临灭绝的扇叶棕榈;还有5棵尚未明确品种的“Twn”树,可能是一种阿拉伯金合欢(Acacia nilotica),能产出树胶和珍贵的坚硬红色木材;此外还有5种未经确认的树[12]。
3.1.4 草药和香料园
在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70—前1070),鲜花成了宗教仪式不可或缺的部分,花园里除了花卉,还开辟了种植药草和香料的场地,种植有孜然(Cuminum cyminum)、马郁兰(Origanum majorana)、茴芹(Pimpinella anisum)和香菜(Coriandrum sativum)[16],以及有喙欧芹(Anthriscus cerefolium)、百里香(Thymbra spicata)和薄荷(Mentha piperita)等。值得一提的是古埃及人擅长制作香精和香膏,将香草植物、花卉或香木碎片浸泡在油中来提取精油。比较著名的香膏有Metopion,由小豆蔻(Eletteria cardamomum)、灯芯草(Juncusef fusus)、菖蒲(Acorus calamus)、蜂蜜及葡萄酒等制成[17]。比较常用的香精Sampsuchinon主要用到百里香(Thymus vulgaris)、肉桂、南木蒿(Artemisia abrotanum)、桃金娘叶和马郁兰[17]。
3.2 娱乐观赏类
具有娱乐观赏意义的庭荫树、葡萄架、水池植物、花坛和盆栽等多种植物应用形式在一幅著名的壁画上一览无余——阿孟霍特普(Amenhotep)时期(公元前1514—前1493),由底比斯(Thebes)的官员塞努弗(Sennufer)负责设计的园林,这幅著名的壁画显示了一个规则对称式花园的平面图(图2),沿着围墙有林荫大道,庭荫树有高大的海枣和埃及姜果棕,大门和房屋建筑之间有一个葡萄架,4个矩形水池中的植物清晰可辨。水池四周是盆栽的睡莲,其中2个水池边上的凉亭前有花坛[18]。
3.2.1 葡萄棚架
与早期大规模种植的葡萄园有所区别,当葡萄藤架应用在庭院里的时候,它表明园林植物的应用开始由实用性向娱乐性转变。那时栽植葡萄的方法主要有2种:第一种是竖立2根木柱,上端叉开,顶部搭一根木柱,支撑藤蔓生长;第二种是用树枝做成藤架,末端放在地上形成拱门型葡萄棚架[19]。后者是更富娱乐性的形式,通常位于庭院花园和宫殿花园的中轴线上,葡萄的枝条缠绕在棚架上形成一条绿廊,为户外活动提供舒适的场所(图3)。
3.2.2 庭荫树
私人庭院的中心一般为水池,庭荫树多采用环植、有规律间植的手法,外围沿围墙种植7或9棵庭荫树。宫殿花园面积更大,多采用规则对称的行列式种植。常见庭院树有西克莫无花果、海枣、无花果、石榴、阿拉伯金合欢和柏树等。
3.2.3 水池植物
古埃及的水池多为矩形或T型,里面通常栽植睡莲和纸莎草。在公元前1400年尼巴蒙(Nebamun)墓的系列壁画[12]中可以看到,中央矩形水池中饲养有鱼类和水禽,同时种满了莲花,水池边缘种植象征重生的纸莎草,画中有成排的棕榈树和海枣树,以及多种形态由无花果树间植的庭荫树(图4)。
3.2.4 花坛和盆栽

图5 丧葬仪式中的盆栽,Minnakhte墓室画[12]
第十八王朝时期出现了王公贵族在宅邸旁建造私人花园的高潮,到了后期有钱人还雇佣很多园丁,早晨照料蔬菜,晚上照料葡萄架,打理园中花草。园中花卉大多一对一地种植在正方形的种植床中。文献中提到的花卉有虞美人(Papaver rhoeas)、 牵牛花(Pharbitis nil)、裂叶蜀葵、黑心菊(Rudbeckia hirta)、玫瑰(Rosa rugosa)和茉莉,还有矢车菊、蔷薇、罂粟和银莲花等[20]。前面提到的贝尼·哈桑墓室壁画中也出现过一排整齐的盆栽植物[13],后来这种形式逐渐演变为花园装饰必不可少的方式。庭院植物中的树木一般直接种在地上或树池中,灌木和花卉则种植在花盆或木箱中,摆放在房屋附近的园路两侧[21]。公元前1475年,在墓室葬礼仪式的画中,一条带篷的葬礼驳船载着死者的遗体行驶在长满莲花的水域,水域周围环绕着纸莎草,陆地四周有规律地间植着西克莫无花果和海枣树,盆栽的植物对称摆放在道路两旁(图5)。
3.3 祭祀礼仪类
祭祀类的植物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神庙和墓室园林中,以及其他节日仪式的场合。神庙圣地是高级祭司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由于神庙花园供在世的法老享乐,所以也包含生产性的植物应用形式,如果林、葡萄棚架、蔬菜园和花圃。如位于阿玛纳(Tell-el-Amarna)城的阿托恩(Aten)神庙花园,里面有果林和葡萄藤;而位于卡纳克(Karnak)的阿蒙神庙有26个菜园,旁边还有一个古老的植物园。然而植物应用形式具有非常明显的祭祀和礼仪性质,比如礼仪林荫道和圣林等。
3.3.1 礼仪林荫道
从水体通往神庙的“仪式路线”两旁,都有整齐对称种植的乔木,成排的树木有时延绵几公里。常用树种有西克莫无花果、柽柳、柳树和各种棕榈树,也许这就是最早的行道树。在巴哈利(Deir-el-Bahari)发掘的公元前2065年的曼都赫特普(Metuhoptep)神庙花园,通往入口处有3排西克莫无花果和柽柳形成的大道,国王的雕像被放置在无花果的树荫中,周围有独立的几何形花坛。公元前15世纪,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在山坡上建造了3个台层的巴哈利神庙,沿着长长的大路有双排狮身人面像,路两边的礼仪行道树则是高大的埃及鳄梨。
3.3.2 圣林
在埃及,神庙建筑群周边的“神圣湖”和“神圣树林”[13]被认为是法老死后其灵魂的栖居之所,拥有一片圣林的金字塔陵墓被称为“萨胡尔(Sahure,第五王朝法老)灵魂的光彩呈现”,圣林中一般种植埃及鳄梨、西克莫无花果和柽柳。
3.3.3 花环和花圈
无论是在神庙或陵墓,还是一些节日庆典,古埃及人们都会用花束、花环和花圈做装饰。如在图坦卡蒙墓中发现的花环,由柔软的橄榄树枝与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潮湿土壤中的柳树、野芹菜(Cicuta virosa)和莲花做成,矢车菊和曼德拉果实缠绕在一起,还有埃及鳄梨和橄榄叶做成的花束被绑在一根芦苇上。在古埃及,园丁一定要学的手艺就是编织花圈,这门艺术非常受人尊敬,因为它工艺复杂,而且既用于生者也用于死者。
4 影响
4.1 古埃及文明对西方的影响
古埃及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获益最多、最直接的无疑是欧洲国家。正如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当近东农人(指包括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笔者注)时代的黎明来临时,在西欧仍然徘徊在猎人时代(旧石器时代)。[22]”公元前322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公元前356—前323)结束了埃及长达3 000年之久的“法老时代”,其文明通过古希腊源源不断地传入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古罗马取代了古希腊后,这种交流仍然是广泛而持久的。故将古埃及文明称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源头实不为过。
4.2 古埃及园林对西方的影响
古埃及在3 000多年的园林发展中创造和积累的园林类型、设计理念、使用方式和营造手法等方面经验都被古希腊和古罗马所吸收。特别是花园的规则式布局、轴线控制、植物应用等内容也被其照单接收。就植物应用而言,不论是乡土植物的应用和外来植物的引入,还是庭荫树、行道树、种植床、葡萄棚架、花坛和花池等的使用,抑或是圣林、植物园、葡萄园、菜圃和果园等形式的应用,也都对后来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植物配置的手法如环植、行植、对植、间植和盆栽等都被后来者所借鉴。
4.3 古埃及园林植物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古埃及园林植物应用不仅有实用性和审美性的特点,还有其鲜明的文化性特征;它不仅关注植物的生物学特性,还创造了寄情于植物、喻理于植物、言志于植物的文化内涵。如莲花和纸莎草作为代表上下埃及的象征,体现了当时社会和百姓政治上的隶属感;陵墓周围种植的柏树是死亡和永恒的象征;石榴果实种子数量多被认为是生育和繁衍的象征等。他们喜欢赋予植物某种神圣的意义,并将其与神灵或神话人物联系起来,如以莴苣象征丰产之神、收获之神,白莲花除作为冥王的象征外,还是农业之神等。受此影响,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以植物为人物化身和象征的例子不胜枚举。总之,植物文化不仅丰富了古埃及文明的内涵,也为西方植物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5 启示
“世界景观设计的历史必定是一部人类的文化史……是书写人类思想历史的另一种方法”[23]。中国古代文明与古埃及文明起源虽有先后,但成就却同样辉煌。在各自文明影响下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园林形式与内容,也为各自的文明增添了光彩。本着文明互鉴的精神,古埃及园林在植物应用方面的成就值得我们思考。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古埃及人在园林发展之初就对植物种植和应用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不断地改造、改变和改善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建造自己心中的天堂。相对而言,我国在园林植物种类和应用方面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源条件,但却未很好地加以保护和利用,在园林植物应用方面没有取得与设计风格、营造水平同样高的影响力及声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随着新中式园林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园林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一定会取得巨大的进步。
致谢:感谢东北林业大学扈宇晨和柴斐2位研究生在资料搜集方面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