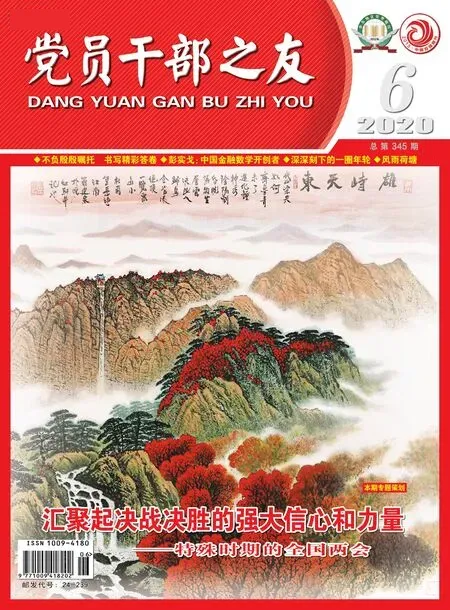故乡的路

孙大勇/图
记忆中,老家村内道路狭窄,异常脏乱,即便家门口六户公用的胡同,也因雨水冲刷,中间低洼,哪家不注意,淌出一些污水,一不小心就会把鞋弄脏。雨天更不用说,鸡鸭猪狗来回几趟就弄得无处插脚,它们顺便再来点“到此一游”性质的排泄,视觉上很是不堪,至今心理仍有阴影。雨水挟带着各家各户的柴草、泥垢、粪便,在街上四处流淌,加上村人来来回回地踩踏和车辆的辙印,路上满是黑色泥浆。因而,老家人有存放旧鞋的习惯。家人的鞋底磨破了,鞋面被趾头顶出大洞,就要被母亲拍打干净,放进柳条筐,说是雨天用,也就是雨天穿着这些旧鞋上街。哪天听到有收破烂、换废品的,我们就偷偷找只旧鞋,去换个白白、圆圆、黏黏的大米球,运气好时还能换上一小把酱螺蛳甚至一小块狗肉。所以常常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雨天找鞋鞋没了”。
雨天上学,手里要带上一根树枝,走一段停一下,找棵树靠着,把鞋底的泥巴刮掉。到了教室,鞋早已湿透,脚冰凉冰凉的。有些心痛鞋子的,便脱了鞋光脚走,开始还不适应,走上几步,那种细细的稀泥从脚趾缝里钻出来的感觉竟然很美妙,反而很享受这种豪放的走法,便故意地使劲儿踩着烂泥和水洼,任凭它们四溅开去,周围的女同学纷纷在惊慌的尖叫中跑开。真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一番折腾下来,鞋子目不忍睹,裤子上也是拖泥带水。偶尔也有父母背着孩子上学,被同学看见了,是要被嘲笑的。光脚最担心的是被扎,玻璃碴子扎脚很厉害,特别是在河里摸鱼,被它扎一下十多天才能好。蒺藜是第二种伤脚的东西,踩上一个要被扎几个流血的小洞。初中上学,周末骑车回家拿干粮,一次路上在鲍楼遇到大雨,胶泥路上推几步,后轮就被黏住了,有泥有草,干脆扛着自行车光脚走了八九里路,还好没被扎到。不知避雨的我第二天天旋地转,大病一场。
虽然简陋,村里的路发挥着很多功能。路边堆粪,放柴火,有水井、磨盘,也会临街搭个简易的厕所,主要是路人使用,有时也是应村人“三急”。乡人们或蹲或站,常靠着墙根晒暖。端着饭碗,看着或跑或走上学的孩童,无论是姑娘还是男孩,都会认得是谁家的第几个孩子。偶有外乡人经过,会被有些不礼貌地盯着细看,内向的路人会被瞧得很羞怯。夏天天黑了,三三两两地扯着席子、塑料布,铺在路边,大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孩子们小的围着大人跑来跑去,大的在附近胡同捉迷藏。累了就依偎在大人腿边或怀里睡了,大人晃着蒲扇替孩子扑打蚊子。等大人也倦了,便抱着孩子,拖着席子回家。街上便静了下来,偶尔传来三两声狗叫。
先辈们曾走在这条路上,一场雨,一阵风,还有无情的时间,湮没了种种历史陈迹。他们的肉体、骨骸也埋入村头的土地,重新变为泥土,变为郁郁葱葱的树木、青草、庄稼。这条路几乎世世代代一成不变,温饱曾是先祖们最高的理想,他们也曾走南闯北,一个又一个理想的破灭,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始于1978年这场前无古人的变革,改变了国家的前进道路、速度与方向,也改变了乡人们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四十多年高速发展,我也会像祖辈一样,长于斯,埋于斯,后代们也会踩在这块先辈长眠的土地上播种、浇水、拔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八十年代初,在公社的帮助下,村东、村南修了“二级路”。路两边栽上整齐的杨树,宽阔平整的路面上摊着一层薄薄的黄沙,显得很是高级。即便“二级路”也有缺点:雨后被踩踏或车辆碾轧,便会有坑洼和泥沟,便需进行整修,敛平凸起,再撒一层黄沙。细碎的黄沙沉入泥土,大颗的沙砾露着半截,或干脆就散布、滚落在路的表面。这些沙砾乡人称之为沙砬礓,有黄色、红色、白色、黑色的,也有杂色的;有的晶莹剔透,有的色泽华丽,有的形状规整,有的甚至是某种动物的模样。夏日的午后或傍晚,小伙伴们割完草,坐在路边凉快,玩会“砍刀”或“鸡叨虫”,也常会有人提出“赛跑”。得了第一名的,喘着粗气,坐在路当中吹牛显摆,任凭汗珠从脸上滑落,偶尔感到脚底有轻微的疼痛,那是在急速的跑动中,踩到了沙砬礓,脚被硌了一下。当然,这种小小的“伤病”是万万不会提起的。
九十年代乡人年节的串门礼物,标配是两包白糖、两瓶酒,讲究的人家加上两包炸果子,礼物放进塑料打包带编织而成的提篮,细碎的白砂糖很容易从简易的纸包里洒出来。过年时节,乡村不平的土路在阳光下常有糖粒折射的耀眼光芒。“二级路”是连接河里、王村、野庄、龙集等几个村的主要交通干道,在2005年“村村通”行动中首先被硬化,这让家乡有了现代化气息,与村里新盖的各类砖瓦房屋显得配套起来。虽然还比较窄,两辆汽车会车时还会比较小心,但当时已是非凡成就,乡人们第一次有了“我们走在大道上”的感觉,赶集、走亲戚已不再担心雨雪天自行车被黏住、地排车拉不动的问题。“二级路”正好横穿我家责任田,生产、生活自此更加方便快捷。
一年回不了几趟老家,对老家的变化,总是看不到过程,看到的都是结果。老家辖区内105国道的拓宽与绿化工程,一段时间内亦成为周围县区乃至全省城乡绿化的标杆,特别是路中间增加了水泥隔离栏,像高速公路一般,减少了多少汽车的迎头相撞啊。玉兰、紫荆、榆叶梅等名贵树木花卉沿路一字排开,四季花开不断,姹紫嫣红,乡人们终于见识了原来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奇花异木。
2014年年关,父亲给我打电话,说村里要修路,在外面有工作的村人都要捐钱,我二话没说捐了八千。过了两年,路终于修起来,两边还做了排水沟,非常洋气。认识的、不认识的乡人们开着汽车,蹬着三轮,骑着洋车子,行色匆匆,竟然有些城市的节奏与感觉了。
越是最后的路,越是不平坦。老家院子多年前硬化了,就剩长长的胡同还是几十年没变,好在村人不再散养牛羊猪鸡,也好在胡同里的几户人家平时少有人住,看着倒还干净、平整,好动的儿子竟在胡同冬青丛里发现了一个编织精美、已经弃用的鸟巢。今年4月26日晚上看新闻,全省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电视电话会在济南召开,要求年底全省全部通户道路完成硬化任务。好一个“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行动!老家与济南,不同地域,土路,简易公路,城市道路,它们都同时存在着,可彼此的世界却是这般相似:105国道、二级路、村内道路、胡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接一个排着队一样被修好,就像济南顺河高架的南延,二十多年下来,眼看就要连接到济南南高速了。
老家县城尤其让我越来越陌生,她像北京、济南,有了一环、二环,据说已有三环的规划。道路两侧,工厂、小区,规划得井井有条,便感叹一张白纸上好作画。每次回家,快到东平,我便跟着导航走。因为到了县城,一个个相似的路口,相似的高大建筑,相似的绿树红花,再加上五色斑斓的广告牌,频繁变换的门脸与招牌,一不小心就走错了,走过了。
人生无论漫长与短暂,都有起点与终点,连接两者的,是人们复杂的心路历程。起点对过程的影响,是持久的,甚至是终身的。自己对城市道路整修中生长繁茂的花木被拔掉,人行道依旧崭新的花砖、依然坚硬完好的路沿石被扔进垃圾车,惋惜,心痛。即便换掉,把这些被替换的建材,运回老家,铺在村中道路、胡同或院落,该多好啊!这种农人情怀估计很多人都有,只是隐而不发而已。1993年我家翻建房屋,四间堂屋封顶,已无多余砖瓦,厨房只好使用拆除老屋留下的多数已残破不堪的旧砖。近三十年过去,厨房依然在无人居住的老家院落里完好、坚强而孤独地站立。
乡野小路,是农耕文化的牧歌;柏油马路,是现代文明的进行曲。经济发展史,其实是路的发展史,路就像社会的血管,越来越粗壮,家乡也越来越富裕。如今,回到老家野庄,路两边种满了绿化树木,左邻右舍,房前屋后,窗前墙下,也常见一丛丛青枝绿叶与花花朵朵,银杏耸立,柿子低垂,红枣掩映,墙头上爬满了丝瓜豆角。在我心里,这才是农村应有的幸福模样。我们这些第一代城市移民,看着空地,甚至大一点儿的花盆,就想种一棵丝瓜、茄子或豆角,心中最大的理想就是拥有一个院落,种满各种果树和蔬菜。我们穿着硬邦邦受罪的皮鞋,却怀念布鞋的舒适与温暖。我们怀念乡间的小路,是因为时间过滤掉了所有的不适、不快,留下了种种加工过的美好。我们讨厌堵车,讨厌汽车喇叭的嘈杂,甚至还有刮擦和追尾,却忽略了它给我们提供的便捷与高速。在这种纠结中,我们不断前行。
故乡的路,像风筝的线,像无形的脐带,牵系着身处异乡的游子。自己年近半百,走过很多路,到过很多地方,见过各式各样的人,感受过很多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也曾取得让亲朋好友引以为傲的所谓“成绩”。无论是山野小路还是柏油大道,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求学之路,无论是从教师还是到职员的岗位变换,一路走来,越走越远。从凹凸不平胡同里学会走路的自己,掌握平衡、把握方向、明确目标、谨慎敬业等人生准则俨然已内化于心,特别是在待人接物上,自己一直谦恭和善,未语先笑,正因为有过泥泞里的成长,才会对眼前的坦途充满感激。自己知道,内心深处,我依然是那个在家乡小路上露着趾头,鞋底有洞,忘了蒺藜秧,忘了沙砬礓,撞开一团团飞虫,撒丫子奔跑,大嗓门呐喊的乡村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