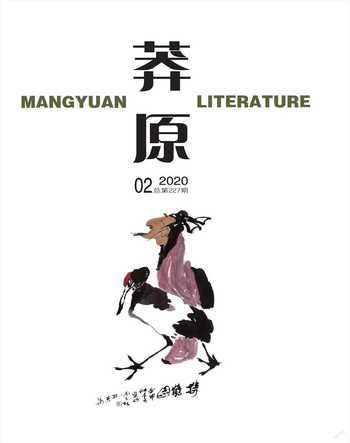一幅画的距离
麓麓
每次听别人谈起初恋的话题,我想到的总是美毓。虽然美毓并非我的初恋,但总是想到她。也许是因为她甩了我,也许是因为她甩掉我的方式过于决绝,也许是因为那次分手把我拖进了一桩刑事案件,也许,还有很多也许。
那个案子水落石出以后,美毓和我都从美院退了学。我出国到芝加哥读艺术史,一待就是五年。本来希望能定居美国,但因种种缘由留不下去,只得回了上海,爸妈安排我去了Moe艺术馆,先做了几年策展人,后来又去了一家艺术品拍卖行。我始终没敢打听美毓的消息,只听说她伤好出院后就疯掉了——谁愿意留恋一个疯子呢?
前不久,美院我们那届同学要搞毕业十年聚会,闵希把我拉进了微信群。
闵希是那个班里唯一和我保持联系的人。在美国时我收到过她的Email,她说想到美国读书,问到申请流程、住宿、交通、各项开支……啰里啰唆一大堆。我挺反感的,这些信息在网上都能查到,没必要漂洋过海向我咨询,但我还是整理了几个文档发给她。当时,我有向她询问美毓境况的冲动,可犹豫再三,还是开不了口。
闵希最终没去美国,我不知道缘故,她也没提。自从加了微信,逢年过节她都会问候一下,有时也在我朋友圈点赞。我翻过她的朋友圈,空空如也,想必她可能把我屏蔽了,便猜想她的生活可能并不如意。
闵希把我拉进同学群,问这次聚会我去不去,我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直接进入群成员,在一颗颗头像和一个个名字中试图辨认哪个是美毓,然后把可能是美毓的头像依次点开,看资料里的签名和朋友圈。
我疯了吗?明知美毓不在这个群里啊。
我没有疯。是美毓疯了——
“脑部遭受严重撞击,不可能再恢复正常。”这是医生给出的最后诊断。
但医生又说美毓还有肌肉记忆,她还能画画。当年,她就那样把脑海里支离破碎的画面画了出来:一幅幅中年男子正面、侧面和背面像,用粗犷如刀割的线条刻画出来,织成一副恢恢天网,让原本毫无头绪的案子水落石出。
之前我也是嫌疑人之一。而那时,班上同学早已整理出关于我的案情重现——血腥,暴虐,污秽,残忍,环环相扣,严丝合缝。那案子让他们因为义愤填膺而红光满面,他们希望罪犯是我,或者是陶冬,因为,美毓和我提出分手就是为了陶冬。但他们并不知道,精液的DNA检测已经将我排除在外了。
当时我跟陶冬并不认识,而美毓认识他也不过几天,我始终没弄明白美毓为什么会选择陶冬而抛弃了我。那几天我刚好在四川旅游,出发前我邀美毓同去,美毓说:大姨妈来了,不想动。我就和一个摄影系的朋友一起走了。
后来,陶冬的那段自我介绍在整个油画系广为流传——
据说就在北山食府,陶冬端了盘两素一荤坐到了美毓对面。
“认识一下吧,听说你也是油画系的,我算是你师哥,大三的。”
虽然没有亲历那一幕,但我能想象出美毓嘴角略带得意和譏讽的笑容,那是标准的美毓式微笑,特别在你要讨她欢心的时候。
接着,陶冬说:“你知道全国有多少个省吗?”
我想美毓脸上的笑容更深了,抑或还有些不屑。
陶冬又说:“你知道全国最穷的省是哪个吗?”
我想美毓的笑容略微收敛一点。
陶冬又说:“你知道那个省最穷的村子叫什么吗?”
我想那笑容就变得有点好奇了。
“我叫陶冬,就来自那个地方。”
好奇变成了些微惊叹?又或许,美毓和我有着极为接近的第一反应——操,那还学什么油画!
至于陶冬如何在那几天追求到美毓的,只有陶冬和美毓自己知道。当我带着耀人的蓝天和雪亮的白云从川南回来后,只得到了美毓最后的告知:我们分手吧。
我以为她因无聊而赌气,只是个恶意的玩笑,就问她怎么回事。
“因为别的男人。”
“谁?”
“陶冬。”
“陶冬是谁?”
“你不认识。比咱们大一届。我爱上他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就这几天的事,你去四川的时候。”
“你背着我勾搭别的男人?”
美毓愣住了,她大概没想到我会用“勾搭”这个词。
当时,美毓的东西已从我租住的公寓搬走了大半,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玩意儿。她愣了一会儿,沉默地蹲在地上整理最后两个纸箱子。我看到她的长发顺着耳侧垂挂下来,挡在胸前,松松的条纹T恤两边露出的赤裸臂膀,呈现出完美的弧度,简简单单的牛仔裤,简简单单的蓝色帆布鞋,简简单单地,却无情地啃噬着我。
不过,她眼神中惯有的傲慢全然不见了,一直侧着脸回避我的直视。我坐在床上盯着她,想象着自己走到她面前,蹲下来,一手扣住她的腕骨,一手摸着她的额发,一点点滑向后脑与脖颈连接的弯曲所在;我想亲吻她的耳根下方,想用牙咬啮那块脆弱的地带。
美毓站起身,端着箱子往外走。我的旅行包还横在门口,脱下的登山鞋散发出潮潮的臭气。她重新放下箱子,将我的东西郑重而轻巧地移开。她不知道就在她的双手碰触的旅行包里,还有我千里迢迢带给她的礼物。千里迢迢,这个词矫情得让我恶心。
我曾经对律师说,如果我想对她做什么,那会儿我就做了,根本没必要深夜约她到公园。后来我又说,只有那些没钱租房,甚至,没钱去宾馆开房的人,才会约在那儿。
我的暗示指向陶冬。我不是故意污蔑陶冬,而是陶冬的证词对我不利,他说听美毓提过,那天晚上我们进行过最后一次面谈,她不想我恨她,想把事情都说清楚。这就说不清楚了,美毓出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我,能说得清楚吗?不过,几轮审讯过后,陶冬也说不清楚了,虽然是他发现了美毓并且报了警,可贼喊捉贼的案例也并不鲜见,他自然也就难脱嫌疑。
无奈警方找不到其他证据——案发当晚下了一场暴雨,现场几乎没留下什么清晰可辨的痕迹,让勘查困难重重。唯一有用的证据只能靠DNA检测,这才排除了我,也排除了陶冬。可警方依旧不能肯定。
警方问:“你凌晨买了去海南的机票,半小时后又退票,为什么?”
我说:“难道你们都没失恋过吗?我只想逃离,永远不想见到她。但我又做不到,我还想看到她,想看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为什么是凌晨?”
“睡不着。”
是啊,怎么可能睡得着?前半夜闷热窒息,后半夜暴雨如注……
一条微信,又是闵希发来的,她催问我去不去参加同学聚会。
“太忙,算了吧。”
闵希说:“哦,那我也不去了,原本就是要见见你。”
我有点吃惊,没想到闵希居然要借着同学聚会见我一面。在大学时我们并没有多少交集,我退学以后,除了她想去美国那段时间有过一些联系,后来她没去成,联系就少了。转念又想,见见也好,也许我能从她那儿得到一些美毓的消息。
挑了个周末的傍晚,我在咖啡馆见到了闵希。闵希先到了,坐在露台的木沙发上,背靠人行街的矮冬青,夕阳金橘色的光从遮阳伞边沿斜打在她的颧骨和鼻梁上,为她镶上了一道金边。闵希样子变化很大,比以前时尚些,化了妆,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当然,她也一眼认出了我,大概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对相貌和骨骼总是格外敏感吧。
寒暄过后,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工作,聊着彼此的现状。闵希如今在一所民办大专当老师,还跟人合开了一个画室,周末和暑期特别忙,带的都是初高中生。她说太累,竞争也太激烈,想从这个画室脱开,另外做一个画室,专门面向白领阶层。
“目前这块市场才刚刚兴起。”她说。
“挺好。”我笑了一下。
“你还画吗?”她问。
“早封笔了。”我摇摇头,轻描淡写地说。
一开始,我很小心,尽量不主动触及大学时的任何人、任何事,但我还是希望她能主动提及,特别是有关美毓的消息。
闵希笑了笑,她的眉毛、睫毛和頭发都被夕阳镀了金光,扬起一缕缕炙烧的火。隔了半分钟,她才接着说:“不是谁都能搞创作的,得有那股疯狂劲儿才行。”
我拿起杯子喝了口咖啡,觉得危险的边缘就要被点燃。正当我要开口,闵希先开口了:“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事,真的。”
“嗯?”
“你还记得陶冬吗?”
我抬起头,看着闵希。
“你肯定记得的,对吧?”闵希也看着我。
我把杯子放到了小碟上,抿了抿嘴:“太记得了。怎么忽然提起他?”
闵希手里端着杯子,却没有喝:“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嗡的一声,像被一块巨石轰然击中了脑袋,耳骨噼噼啪啪碎裂开来。陶冬让闵希来找我?是跟我说美毓的事?美毓情况好转了?她现在在哪儿?他们还有联系?一系列的问题像骨头碎片四下迸溅,我用指头压住太阳穴偾张的血脉:“他要你来找我的?你和他还有联系?”
闵希瞥了眼旁边的红瓷糖盒,笑道:“你刚才问我结婚了没,我说刚毕业就结了,我老公也是咱们这行的。你没继续问,我就把话题给岔过去了。陶冬,就是我老公。”
爆裂的头颅稍稍合拢了些,太阳穴的脉搏渐渐平缓下去。我倏忽听到手里的杯子在碟面上轻颤,便重又端起,将咖啡灌入焦干的口中:“你……和他成了一家?刚才怎么不直说?哦,没关系,说吧,找我什么事?”
“这都不是第一次了……”闵希略微有些不好意思,“还记不记得那会儿你在美国,有一次我跟你打听留学的事,其实,也是帮他问的。”
我感到嗓子内阵阵刺痒,诧异地望向闵希:“你们应该没去芝加哥吧,华人圈子很小,你们去了我肯定知道的。”
“不是我要去美国,是陶冬。他申请到了半额奖学金,但还有别的各种费用,太高了,对他来说不现实,就放弃了。”
我理解地点点头:“陶冬现在做什么?”
“也在我们画室教学生,抽空还画油画,画室那边有他一个工作间。”
“那么,他画得怎么样?”我知道这问题不太地道,国内但凡有点名气的,我那圈子的人都了如指掌,即便多如过江之鲫,但如果有谁提起过陶冬的名字,我的耳朵是绝对不会漏掉的。
“大多是行画,不是流水作业那种,陶冬恨不得天天都在展馆待着,特别是有世界级大师特展的时候,哪里开展他就跑哪里,研究每幅原作,做笔记,可不仅仅单凭网上书上的图去画那些……”
难怪没有听说过,原来竟这么不入流。
“这种画也很有市场,如果画得好。”我说。
“但你也知道,这类画太多了,十几块、几十块的到处都是,放在文化市场、装饰店什么的代卖,或者是放到网上,根本卖不上价钱,除非画廊那边给订单,但好点儿的画廊都有固定合作的画师,再不然,就是压价太狠。”
“然后,一气之下就不卖了?”我有点猜到闵希找我的原因了。
“搞艺术嘛,谁都难免有点心高气傲。”
“那还是不够缺钱。”我笑道,不过话一出口,就感到自己有点刻薄了。我想起陶冬的那段自我介绍,心里一阵无力,面对这么一个人,我竟用钱来找补自尊,这确实很刻薄,也很浅薄。我放低了口气:“那,我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效劳的?”
闵希忙道:“不敢不敢。他只是希望我问问,你这边能不能帮帮忙,联系些识货的买家。如果能引荐,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总得先瞧瞧画,我还没见过……”还没说完,我意识到话题再次跨进了雷区。
“你没见过?哦,是,你看我这脑子,他们毕业画展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学校了。这样吧,约个时间,我带你去他的工作间。”
“陶冬会在吗?”
闵希愣了愣:“不会的,除非你看得上他的画。再说,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他的经纪人,不一定要见面的。”
看闵希的目的基本达到,我也感觉和她谈得差不多了。此时天色已暗,华灯初上,正是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间,但我却不想待下去了,就喊侍应生过来买单。接账单的时候,我装作无所谓的样子问:“后来,你们有美毓的消息吗?”
“谁?哦,你说的是欧阳吧?”
欧阳,是了,同学里只有我叫她美毓,也许……谁知道陶冬会怎么叫她……
“欧阳早就退学了。欸?是在你之前退学的呀。那之后,就再没见过了。”
我摇摇头,觉得不可思议。闵希跟美毓同一个宿舍,不会对美毓的情况一无所知吧?何况还有陶冬,美毓是因为他抛弃了我,难道美毓出事以后,也遭到陶冬抛弃?
“不过,消息还是知道一点。”见我有些失望,闵希接着说,“毕业聚餐的时候听辅导员说,美毓她爸妈一直带她到各地治疗,房子也卖了,还被骗过,弄了个偏方差点吃出人命,总归是情况越来越糟,老师们还为她筹了几次款……只是毕业后大家各忙各的,就没再听过她的情况了。”
我叹了口气,心想,也许就是在那个时段,陶冬已经成了闵希的男朋友,还托闵希向我打听赴美留学的事,而此时此刻,他又通过闵希借着我为自己寻找客源。美毓她太不值了,或者说,这一切对美毓太不公平了。可是,这世上值与不值如何衡量?公平与不公平又有什么标准?
看我叹气,闵希道:“其实有时候想想,欧阳真是挺可怜的……”
那日咖啡馆一别,闵希又联系了我几次,问我什么时候能去陶冬的工作室看看。前几次我都借故推脱了,但她一再坚持,估计是陶冬在后面催得紧——“你就来看看吧,大家都是校友,你看了觉得不行就跟我直说。不过当年的毕业画展,他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曾无数次问过自己,美毓为什么选择陶冬而背叛我,论外在条件,论家庭背景,论风趣,论人缘,陶冬都没法与我相提并论。那么,是因为才华吗?我承认自己不属于有才华那类人,而闵希说陶冬是有才华的。但才华这东西很虚,个人评判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最终,才华还得靠市场上的标价来衡量。也许陶冬只是少了张进入圈内的通行证,也许他真的才华横溢,也许他的才华横溢与人品太不成比例。
可当我走进画室的二楼——那个作为独立工作间的隔层中,就大失所望了。那简直就是一个蹩脚的山寨博物馆,全都是对传世之作俗不可耐的仿制,竟没有一件他自己的作品。我承认,画并不差,尺幅和原画大小相当,专业水准也都在,但无论是外在形态的东西——构图、色彩、人物的手势、肌肉的凸起,还是原画要表现的激情凝聚的一刻,在他画中都有种极不安定的势态,而神色、氛围和灵魂传达的核心又不到位,有一种假模假样的刻意在里面。
“还行吗?”闵希看着我,明显希望得到我的肯定。
“一般般。”我还是实话实说。
我绕过 《抱银貂的女子》,停在了《费罗尼耶的肖像》前。这幅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并非普罗大众熟知的作品。画上的中年女人居然很悦目,问题是这个女人比原作美了很多,嘴角添上了似有若无的微笑。可原作中的女人并不漂亮,也没有笑,有的是高傲和蔑视,是疑惑和无奈,有种耐人寻味的特殊性格,而陶冬把这些最重要的部分全部抹去了。我想不通陶冬为何要仿这幅画,而且改动得如此不伦不类。
扭头看看闵希,我希望她能感到我眼神里的真诚,明白我的评价不是因为嫉妒和报复心在作祟。
闵希嘴角的微笑始终没有停,反而弯得更大更宽:“没事,你今天能来,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你是专家,更了解市场,有什么建议尽管说。”
我退后几步,再次浏览着陶冬的画:“卖是能够卖得出去的,也不至于几十块几百块,上万很难,好一些的,估计能卖两三千吧?最多了。有些买家不一定非要顶级水准的仿作,但也看不上太低劣的,以这些画的水平,两三千应该是个很好的价位。我可以问问我朋友,有个专混高端行画市场的。”
两三千,这是我自己的价位。我用我的价位定了陶冬的价,除了客观公正,还有着某种象征意义。我看到闵希舒展了眉毛,脸上堆起了更多的笑容。
“那太好了,麻烦你多费心了。”闵希握着我的手,指缝间都攥出了热乎乎的潮气。
我这人说到做到,没几日就去见了邵安。
邵安是高端行画市场的大咖,名字斯文,可长相有些匪气,他個头高,长胳膊长腿,却剪了一头板寸,乍一看像是搞装修的工头,说话行事也是大大咧咧的那种,圈内不喜欢他的大有人在,都说他路子野。其实邵安是正儿八经油画专业,在芝加哥那会儿,我们常一起看NBA,关系还算不错。逮了个机会,我跟邵安提起了陶冬的画。他也不跟我客套,摆着手说不接不接,行画师他那儿排长龙也排不完,各个档次、各个价位的全有,真不缺。
我极尽所能地向邵安游说,简直有些没脸没皮起来,对陶冬的溢美之词越是虚妄夸张,就越觉得是一种讽刺,就越想把我定下的价格落实。
邵安眯起眼睛,脸上有了一种坏笑,直到我闭了嘴,他才突然说:“我从不跟男人谈这事。”
我有点懵,随即明白过来,这家伙烦了,故意端出个不着边际的借口堵我。
我打着哈哈顺水推舟:“当然,不是跟我谈,也不是跟陶冬谈。”
“那跟谁谈?”
“陶冬的经纪人啊,美女。”
“美女?美女有多美?”
“当年也是我们系的系花。”
邵安笑出了声,继而笑得前仰后合:“我可算明白了,就说你今天这么奇怪,整个一话痨强迫症,都快要不认识你了。”
“哪有。”
“如果我没有猜错,那个系花是你初恋,不对,你是暗恋,系花看上了别人没看上你,所以现在才……”
“行了,别废话了,”我掐断邵安的话头,“说吧,到底见不见?”
邵安一边晃着酒杯,一边朝我睨了一眼:“那我得会会,到底不要你的女人是何方神圣。”
我不想跟邵安争辩,默认了。
然而到了约好的日子,闵希却来电话说陶冬要去北京办点事,“得缓两天。新画室已经装修好了,这些天在搬,等差不多了再请你们来吧。”
“我们又不见他。”
“可是,给邵先生看的那些画还没选好……”
我立时火冒三丈,埋怨了闵希几句。
闵希一连声地致歉:“到时候我请客赔罪。”
我发信息跟邵安说了。邵安说他过两天要飞香港,要不这事儿算了吧。邵安本来就对陶冬兴趣不大,正好借这个由头推脱了事。我把邵安的回复转给了闵希,闵希那头急了:
“别啊,要不这样,今晚我先请你们吃顿饭,大家碰个面,等两个人都回来了再继续谈。”
邵安对吃顿饭也无甚所谓,就跟我订下了时间。没多久,闵希就发来了酒店包间的信息。
因为这顿饭是临时安排的,我手上还有几件事需要处理,昏天黑地忙完了,就赶紧往酒店赶,好在一路上车很顺。闵希一看我到了,像见了救兵,一边说邵先生还没来,一边搬过菜单让我再补几个菜。
邵安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跨进包间,只随便和闵希握了个手,就大大咧咧坐下了。
闵希连忙笑着说:“路上没堵吧?”
“还行。”邵安说完,便把她晾在一边,掂起筷子夹起熏鱼就吃。
闵希叫来服务员轻声交代上热菜,然后见缝插针帮邵安转起了桌盘。
我看邵安一副彪悍不善的架势,只好先聊了会儿别的,示意闵希拿酒陪他喝点。直到邵安的脸色平复了一些,惯常的神采飞扬又爬回红扑扑的脸上,我才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怎么了,来这儿之前?”
“遇到一个特不靠谱的人。”
“什么事啊?”
邵安咂了一口酒,放下酒杯:“说好了今天交货,本来我飞香港就为这事,结果呢,提前也不打招呼,说不交就不交了,还挂我电话,再打过去,嘿,关机。”
“有违约金呢,照合同来呗。”
邵安顿了顿:“唉,别提了,当初也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出,因为一直合作得很好,就没太在意,谁知道现在蹬鼻子上脸,摆起谱了。”
“您要的货是什么作品?”闵希试探着插嘴问道。
“《丽达与天鹅》。”
闵希眼睛一亮,对邵安笑道:“是哪个?”
“什么哪个?”
“裸的?还是不裸的?”闵希边说边起身给邵安斟酒。
邵安一听,立马停了筷子,这才正眼看了闵希:“不裸的。”
“红色衣服的?”
邵安瞅瞅我:“内行啊。”
我说:“我同班同学啊。”
“哦,系花,系花。”邵安咧嘴哂笑,又扭头对闵希,“你该不是要跟我说,你那里正好有一幅吧?”
闵希避开邵安红彤彤的目光,放下酒壶说:“还真有,陶冬画过一幅,挺好的一幅,比我上次给你看的那些都好。”
“什么尺幅?”
“让我想想,高大概有一米多,宽……具体我得打电话问问。”
“快问问,应该是130×78。诶,到底水平怎么样?”邵安比先前严肃了些,目光灼灼地转向我。
“行不行你得自己看,”我说,“他的画打发一般买家绰绰有余。”
“那个谁,小希是吧,你再问问价,不给个实在价以后不好合作的。还有,付款要一个月后。”
闵希拨了电话,放在耳边听了会儿,放下了:“他手机关机,可能没电了。要不这事儿就我来做主吧。”
“爽快爽快。”
“您放心,价钱咱们已经有个大概了,虽然您要得急,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就漫天要价的。”
看到两人渐渐聊得兴致盎然,我找准时机举起杯子:“来来,我以茶代酒先敬你们,预祝你们合作顺利啊。”
“对对,合作顺利。”
杯子叮叮当当碰到了一处,我的胸中有种异样的兴奋。
吃完饭,闵希已经有了些醉意。我看她强撑着想把这单生意做下去,也希望有个好的开局,就临时充当司机,开车带他们去看画。
车开到画室楼下,还没停稳,闵希就推开门跳到了路边,蹲在地上吐个不停。我一面拉手刹,一面低声问邵安:“干吗这么灌她?”
“心疼了?不是我说你少眼没珠,真看不出年轻时是个系花,矮子里挑出的将军吧?”邵安笑过以后,又认真起来,“不灌她不好砍价,一会儿你得帮我说话。”
“这么急着要那幅画?你别期望值太高。”
邵安拉动车门把手,轻声说:“真的急,很急。”
当我们打开画室的灯,却发现里面都空了,没有画架,没有椅子,只有斑斑驳驳的地上摊着废颜料、废画笔和零零散散的垃圾,几幅学生习作歪在墙角,和摔碎的石膏像堆在一处。闵希拍着油亮的额头:“哎呀我真是喝晕了,都搬新画室那边了。咱们现在赶过去,时间还不太晚。”
“陶冬的画不在楼上了吗?”我问。
“都搬差不多了,我上去看看,应该是没有了。”闵希也不敢肯定。
我们随着闵希沿着逼仄的楼梯上了工作间,推门进去,闻到一股粉尘和油彩残留的酸腐气味。灯亮了,果然屋内空荡荡的,靠墙的几个木架子歪斜在一边,不过角落还剩了两幅画,搭着布,一幅立在架子上,另一幅搁在架子侧后方的地上,吊满蛛网和灰尘。
“能看看吗?”邵安径直往架子跟前走去。
闵希在后面半跟半挡着:“他提过有几幅画得不好,要刮掉重画,估计是放这兒等候处理的。真的,都不好。”
看到闵希的紧张劲儿,我有点好笑,那样子简直像个学生要打开自己的成绩单。
邵安走到架子前,拎盖头似的把遮布一掀一荡。
仔细一看,我和邵安都放声笑了起来。闵希也笑了,不禁弯腰拍手道:“呀呀,你们要是听了我的就走冤枉路了。巧不巧,这幅画居然在这儿,还一下就让您找到了,要不刚说有缘呢,是您的就该是您的。”
邵安也喜出望外:“还行,还行,挺好的,比我预期的要好。”
一边说,一边远远近近地仔细端详。
“这幅画还真的不错。”我附和道。
邵安扶着画框看了看,看了背面和侧边,又细细去看正面,眉头渐渐拧成了一团。
“怎么了?”
“不对啊……画这画的叫陶冬?”
“是啊。”闵希走到了画前。
“陶冬是Tandy?”
“Tandy?”闵希不解地看着邵安。
“这幅画有簽名,在这儿,裙摆边缘这里。T-A-N-D-Y。”邵安一字一顿念了五个字母。
沿着邵安手指的方向,我把眼睛凑了上去,果然有“Tandy”几个英文字母,字很小,同裙摆的纹理交织在一起。
邵安说:“Tandy,陶冬;陶冬,Tandy……Tandy是不是陶冬的英文名?”
闵希眯起了眼睛:“以前陶冬好像起过一个英文名,记不清了。”
“这不是关键,”邵安看看闵希,又看看我,“关键是,今天放我鸽子的人就是Tandy,本来说好要交画的,却突然去北京了。哦,他刚完成的时候还给我拍过照片……”邵安掏出手机翻起来。
闵希疑惑地问:“陶冬……他今天去北京了?”
“你们看,就这幅。”邵安没有回答闵希的问题,指着手机上的照片,“看,上面的画室和这个画室,这里。”
手机屏幕照亮了闵希的下巴,只听她说:“没错,的确是这个画室……以前这边就是这个隔帘……”
“那陶冬和Tandy就是一个人啊,这画本来就是要卖给我的。”邵安说,“这我就想不通了,Tandy在行画师里也算小有名气的,就是人有点怪,从来不让人到画室看货,但因为合作得好,我给他的价也不算低……这些,你们都不知道?”
闵希凝视着那一串藏着签名的红色裙边:“这幅画……我也是无意间看到的,比以前那些都好,当时我就说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可陶冬不满意,还说要毁掉。我一直很纳闷。”
我心头一惊,忙问邵安:“陶冬卖过你多少幅画?”
“哦,那可多了,上百幅是有的,差不多……得赚了百八十万了吧。不对啊,他认识我,都是老熟人了,干吗找你联系新买家?你跟我说也就两三千一幅,他脑子坏了吧?”
闵希打断道:“他卖画的钱呢?”
“我都付了啊。哦,对了,不是直接给他,收款人好像叫欧阳什么的。”
“欧阳……”
我听到闵希嘴里反复念叨着“欧阳”,像一串喃喃的咒语,直冲我的脑浆,我感到好像有一台加速泵,把血液不停地压进脑壳,一瞬间水起浪腾,仿佛有什么东西沆瀣一气,让浓重的腥液从底下翻出,随时都会把脑壳掀开。
闵希滞钝地转过身,推开了我和邵安,直往另一幅画走去。她像揪着幽灵似的将另一张搭布一把拽起,空气中登时腾起厚厚的尘埃。混蒙中,我远远看到那画上似乎是一大片水生植物,当中有一条白晃晃的舞爪的章鱼。
“很久了这幅画,”闵希咬着牙说,“我还问过他,他跟我说是别人搁这儿寄存的。我从来没往那儿想,从来没想过画上这女人就是她,没错,肯定是她!他们一直都有联系,这么多年,一直背着我联系。”
闵希把肩头的挎包重重地甩向那幅画。“咣当”一声,画歪了两下,坠倒在地。
地面上,我终于看清那缠绕摇摆着的是一个污糟的花园,湿淋淋的,满是泥泞和扭绞的枝叶与沟槽,正当中,一个雪亮的女人躺在枯枝败叶和石砾之上,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睁着的那只眼里,带着高傲和蔑视,带着疑惑和无奈。
费罗尼耶的眼神。
美毓最后一刹那的眼神。
我看到那两条胳膊弯曲成蛇形,一条挡在腹部,一条悬在头顶,每只手里都拎着一张泡皱的人皮,似乎在滴滴答答地淌水。人皮上的脸变形得厉害,可我认得出,其中一个还没有出狱,另一个正站在这里。
陶冬一定也猜出了另一张脸,所以这么多年,他一直蛰伏在我身边,等待着时机悄悄收网。难道美毓就要从疯狂中清醒过来?不然陶冬何以要如此逼近我,逼得这么近,近得让这幅画像刀子一样在我面前出了鞘,就差那么一丁点距离就飞起血刃了。
但我发誓,那真的是个意外——我只是推了她一下而已。
后面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