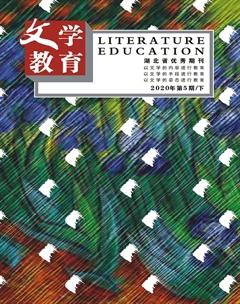我们必须共同生存

关于瘟疫或任何灾难中的众生相,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一批批村庄、一座座城市,全体人民都染上了这种瘟疫,都发疯了。大家都惶惶不安,互不了解,每个人都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看着别人都感到痛苦不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十分痛心。大家都不知道该审判谁,该如何审判,对于什么是恶,什么是善,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大家都不知道该认为什么人有罪,该为什么人辩护。他们怀着失去理性的仇恨,相互残杀。(《罪与罚》)
“每个人都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这个情形是不是我们似曾相识?但这句话是个讽刺。真理,有时候其实是一种症状,一种发热病人的呓语。但瘟疫也会让大言炎炎的真理患者气短、窒息,所以对于易感染真理病的人群,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能让他们获得更强大的免疫能力。当然,也有一些真理会死去。
当然,瘟疫不会自动让真理获得免疫能力,积极的康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以下,就是一位前疑似真理患者隔离期间的康复训练日志——一位曾经的民俗学硕士的读书和思考,关乎瘟疫,关乎混乱,关于我们的社会。
一.《替罪羊》①
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1923-2015)是法国人类学家、文学理论家。如其名所显示的,他这本书探讨的是替罪羊这种社会现象。作者认为,这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普遍主题,遍布于仪式、神话、宗教和谣言,它甚至是人类社会得以构建的根本机制。
替罪羊现象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遭遇自然灾害尤其是瘟疫之时。一旦自然危机无法控制,社会危机就会随之而至。瘟疫的病毒从身体感染到心灵,正如前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的。当自然危机无法控制时,制止社会危机实际上成了首要任务,唯一有希望完成的任务——比抗疫更重要的,是安抚人心。
所以,当务之急,是给危机一个社会的、道德的解释;不是找出灾害的根源,而是一个或真或假的责任人,一个受害者,一个替罪羊。当然,没有人愿意自责,这个责任者/受害者,必然是某个他者。而被选来充当替罪羊的,往往具有下列特征,即平时即受社会歧视的少数民族、不合群者、独特的小团体等等,总之,(身体、生活和行为等方面的)异常者首先会成为受害者。
而替罪羊机制运作的方向,是将危机发生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再通过消灭他们,或至少把他们从被“污染”了的共同体驱逐出去来改变危机。毫无疑问,替罪羊无法治愈任何真正的灾害,无论瘟疫、干旱和水患。但是,由于这个受难者承担了灾难的责任,肃清了人际关系的恶化,从而结束了这场心理和社会危机,濒临混乱的共同体就会得以重建。比如,根据吉拉尔的解释,俄狄浦斯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替罪羊。这个外乡人、跛子、杀父娶母的逆子、国王,被认为是忒拜瘟疫的罪魁祸首,自然而然地成了结束混乱的无辜受害者。
吉拉尔在古老的祭祀仪式、欧洲中世纪驱逐巫婆、犹太人上千年的被污名化经历等文化材料中,发现了替罪羊机制的广泛存在。我们今天超越了这一机制呢?显然没有。问责或讨债的人群,抛出一个又一个(事后往往都被证伪)的替罪羊,气势汹汹,心照不宣,乐此不疲。唯一不同的,这次的名单里犹太人不再显眼,新填上的有5G信号塔;而第一批嫌疑犯甚至丝毫未变,是那些猛兽……
吉拉尔的眼光无疑是毒辣的,但結论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人类共同体的构建和重建,一定要始于一场无辜的暴力吗?何况,吉拉尔得出结论的材料,绝大部分来自西方文化和历史。
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②
尤其,吉拉尔似乎忘了他的前辈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 Durkheim,1858-1967)及其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但对于这本书,我们切不要被名称误导,以为只是一本生僻的宗教学专著。毫无疑问,它是关于宗教的,但涂尔干的关切,恰恰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因为他理解的宗教之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
为了确证这一点,涂尔干回到最简单的宗教形态,比如澳大利亚和美洲人的图腾信仰中,来进行艰苦的探讨。图腾是这些“原始”人信仰的对象,也是他们的群体标志。他们的图腾对象五花八门,从袋鼠、乌鸦、某个颜色的鸸鹋,到负鼠的胃等等,无奇不有。这种古怪的信仰中隐藏着什么秘密和启示呢?一个乌鸦胞族(氏族联盟)的人会说,他们就是乌鸦。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他们说的当然不是经验意义上的乌鸦,他们也不会把自己与乌鸦相混淆。这句话其实是说,他们这个胞族共享着一个本原,这个本原构成了他们的本质特征,乌鸦既是这个本原的外在形式,也共享着这个本原。
所以,图腾不是对一个自然物的盲目膜拜,而是对以图腾动植物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形力量的归属。这个力量,实际上就是氏族、胞族或者说社会本身。或者说,是氏族被人格化了,并以图腾动植物的可见形式表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教中信仰的神秘力量,不过是氏族集体的匿名力量,神与社会其实是一回事。宗教强化的其实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对社会的归附关系。人类正是为了不断激活社会的力量,才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聚会,宗教性的庆典,以及癫狂的“集体欢腾”。这种欢腾甚至可以使人陷入迷狂,完全丧失自我。以至于涂尔干说,过于激越的社会生活对于个体和社会,都是一种暴行,会干扰社会的正常功能。
但无论如何,人类需要共同生存,需要社会,包括在心理层面——但与吉拉尔的看法完全不同。人类总是会遭遇各种危机,但危机恰恰会让人集合起来,商讨对策。团结互助会让人们心生惬意,寻找疗救危机的办法,也会重铸他们的信念。所以,即使涂尔干的论证并非完善,且稍显繁琐,他的结论仍然是明确的:宗教是道德的和社会的,它是人类社会性的一个表征。无论它的形式如何,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超越自身,过一种高于个体放任或孤独无依的生活。尤其在生存危机中,这种以宗教信仰形式出现的集体归属感,会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生存下去信念。
人类自始就在社会中生活,社会本身是神圣的,我们必须信仰社会。涂尔干以这部啰嗦的大部头著作,表达了他在一个分裂的时代(20世纪初)对共同生活的呼唤与信仰。但这个时代是如何分裂的呢?
三.《共同体与社会》③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
1936)的《共同体与社会》正是关于这一论题的第一本名著。滕尼斯赶上的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打碎了人类千百年来熟悉的旧习惯,带来了心灵的巨大混乱。人类必须共同生活,但让人们联结起来的方式和品质,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滕尼斯勾勒了新旧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生活形态,难掩对过去生活的无限怀念。
无论个体和人类,一开始都是生活在一种“共同体”式的人际关系中,它的核心是家庭。首先是作为人类最亲密关系的母子,接着是夫妻、兄弟姐妹、最后是父子。人类成长于母亲的养育和父亲的教育之中,这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最基本形式。家庭之外,共同体的生活还包括亲属、邻里、友谊等等。共同体的生活是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它是一种持久的共同生活,我们在其中分享生活的悲喜;维系它的,是不言而喻的习俗、传统、母语。总之,共同体的生活出于人的“天性”。
新时代之精神的人际关系,滕尼斯称为“社会”。它的精神核心,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全民皆商”。人们只是为了利益和利润,才走到一起,交易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形态和功能,金钱是其唯一的教义,而商人和资本家是其精神领袖和真正的统治者。维系社会的,是理性,是算计,而不是情感。这注定了社会式的结合是短暂的、表面的。社会式的生活不是出自人的天性,而是理性,在它没有触及人类本质的意义上,滕尼斯也称之为一种“任性”。
构成“社会”的意志,是潜伏在人类的可能性之中的。但任何传统文明都没有使之放任自流。比如,商业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始终受到限制。只有“现代文明”,才彻底打开了魔瓶。现在,全民皆商,商业逻辑遍布生活和心灵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是另一个潜在的客户或商品,甚至,在必要时,人会随时准备出卖自己。各种宣传画册上抱肘群立的黑色正装照,就是我们的“社会”的基本象征。他们冷静冷漠,将情感和个性裹藏在黑色的龟壳里;机械的笑容不过是种策略,是面对猎物的缓兵之计;面对(包括来自外部客户和团队内部的)潜伏的敌人,持抱的双肘也只是进击和后撤的预备动作。
总之,我们的“现代”“社会”,就是用商业精神改造一切共同体生活的进程。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从“先进的”西方到“古老的”东方,“社会”现在终于开进了人类共同体的核心,家庭;而未来的前景——如果不加阻拦——大概率是家庭本身的解体,是御宅文化、无缘社会。这将是“社会”的极致景象——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一切人对一切人发动战争。但这是一种必然的命运吗?滕尼斯显然不愿接受。
四.《共同体》④
但是,滕尼斯在19世纪末力挽狂澜的理论构想丝毫没有阻止共同体在世界范围的持续瓦解与社会逻辑的高歌猛进。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写于本世纪初年的这本书,接过19世纪的怀旧之情,试图为新的世纪挽回些许“温馨圈子”(warm circle)。在鲍曼的笔下,共同体的解体与“社会”的泛滥,首先并非源于人性两种意志的此消彼长。现实的道理远比任何形而上的思辨更为简单。实际上,只是因为一小群人的财富冲动,将更大的一群人带入万劫不复的分裂。站在新世纪的开始,鲍曼回望了两个群体、两个趋势在二十世纪的短兵相接。
共同体的解体带来的利益及后果,不是被平均分担的。现代社会创造出了两个群体,资产者和无产者,或鲍曼形象地命名的观光客和流浪汉,他们分别代表了这一进程的获利者和失意者。对于最早的那批进城农民,脱离原生共同体意味着流浪的开始;但对于商人而言,让商业脱离任何人类共同体和道德的羁绊,不啻是一种内在的解放。资本的信仰是利润,它没有祖国,倾向(自己的)自由,倾向全球化,并最终造就了在国际大都会及私人度假地之间飞来飞去的观光者;但世界的另一面,是不得不背井离乡的打工者、非法移民、难民,是无数的流浪者。
资本不仅持续地造就流浪者从共同体中的抛离,它更需要这些人长期保持离散,以免形成任何有共同意识和觉悟的组织力量来反对自己。而在新世纪到来时,资本因为新策略的成功而前所未有地志得意满。这个策略就是“分而治之”,像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观察到的,让美国和世界的底层人民,忙于种族冲突和宗教仇视,从而把注意力从自己的绝望中分散开来,超级富豪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如今,不出意料地,共同体早已失去了。但出乎意料地,无论对于观光客还是流浪汉,这一结局都没有被理解为一场悲剧,而是一场滑稽剧——它允诺所有人都可以轻松地购买一场又一场舞台上的欢笑。对于在巴黎、纽约之间飞来飞去的观光客,他们自然无意于对任何持久之物表示忠诚;对于流浪汉来说——如鲍曼在别处所说的——被迫行为成了上瘾行为,自由,现在成了解体后的意外收获。从购物、身份认同到一夜情,关于时尚生活的真谛——像我们新近也学会了的——多元是一种正在走红的善,而一成不变、一致意见,或者说确定性,即使不是恶,也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于是,事情开始变得难堪。这一难堪,凝结成了自由与确定性的两难这一哲学命题。
五.《來临中的共同体》⑤
世界哲学界的当红明星,意大利的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
mben,1942—)的这本《来临中的共同体》就停留在这个哲学难题的延长线上。作为一本在《共同体》前十年出版的著作,它实际上也参与了这一难题的形成。
没有人能禁止共同体的诱惑,滕尼斯的那本晦涩之作曾是当时的畅销书。但理论家是理性动物。所以,与书名给人的印象相反,这不是一本期待共同体的书,不如说是一本要推迟共同体那诱人的快乐到来的书。我们的哲学家像一位血气方刚的少年,面对唾手可得的幸福,一方面忍受着本能欲望的煎熬,另一方面忍受着禁欲主义教育的煎熬。
通过挖掘一个生僻的哲学传统,阿甘本左右为难地为自己的煎熬寻求辩护。共同体是需要来临的,但首先是保障自由。因为斯宾诺莎说了,共同的东西绝不是构成个别事物的本质的东西。个别的事物,各就其位地发生,即使它们实际上有联系,也不意味着他们在本质中是统合为一的,他们仍然需要在实际的存在中散解开来。
当然,这不意味着不要共同的生存,正如犹太教经典《塔木德》所言,每个人无可避免地要领受一个邻人的位置。为了让他人就位,我必须撤出一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要适合于每个个别性的来临。而且,这个个别性也是不确定的,不应该是确定的。它需要连续不断地按其自身的式样而生成自身,既不是随机偶然的,但也不是必然地……
总之,不要确定性!这是阿甘本要求的任何伦理论述的出发点。伦理不该是套住我们的方式,而是我们使我们自己生成的方式。这完全没错。但这样形成的共同体将会如何呢,它是无预设的,无主体的,在其中,人不知何为沟通,也不知何为不可沟通……
老实讲,我想象不出阿甘本要召唤的共同体究竟什么样,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现实生活远没有哲学那么玄妙。透过种种左右为难的否定论述,我们看到的是理论家们对自由的上瘾行为——即使在疫情中(正如他在疫情中的表态显示的)。但是,什么样的自由不可舍弃,什么样的确定性不敢拥抱呢?这个问题首先是阿甘本们的。
即使共同体绝非滕尼斯勾勒得那么美妙,我们仍然需要共同生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牺牲替罪羊的方式,暗怀鬼胎地建立一个一致对外的利益联盟。共同生活是可以信赖的,是需要崇拜的,它促成我们的合作,也能成为我们的信心之源。毫无疑问,迄今为止的共同生活并不完美,被高声礼赞的种种共同体之下,掩盖着剥削与牺牲。但这不一定意味着要抛弃一切共同的、确定的生活。在拥抱自由之前,要认清被迫行为与上瘾行为,在否决确定性之前,要区分保障与障碍。
吉拉尔说,知道了瘟疫的名字,会增强治愈的信心。现在,因为一场瘟疫,我们至少知道了我们社会病毒的名称,甚至部分原理。所以,最终的治愈仍然是可期的。这个原理就是,我们必须共同生存,只有共同生存才能让我们共同生存……
注 释
①[法]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
②[法]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
④[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意]吉奥乔·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相明、赵文、王立秋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
胥志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學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