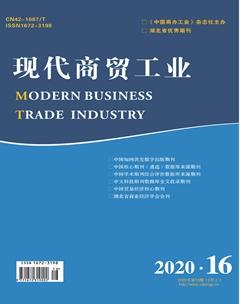短缩二行为犯的结构与重构
赵建勋
摘 要:我国《刑法》中的绑架罪是最为典型的短缩二行为犯。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绑架罪的既遂应当以行为人实力控制被绑架人为标准,勒索财物或提出其他不法要求仅作为绑架罪的目的行为,对其既遂判断并无影响。然而,在勒索财物的目的先于控制被绑架人的行为而实现的场合,绑架罪的完成形态难以认定。对于实力控制他人后才产生勒索财物目的进而实施勒索行为的情形,我国刑法理论界鲜有学者探讨。实力控制被绑架人的行为完成之后,其他参与者参与实施勒索财物的行为能否认定为绑架罪的共犯,刑法学界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对短缩二行為犯的重构是解决以上各种争议问题的出路。
关键词:短缩二行为犯;绑架罪;实行行为;目的行为;重构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6.076
1 短缩二行为犯的内涵和结构特征
1.1 短缩二行为犯的内涵
短缩的二行为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了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之后,还需要自己或者其他人实施构成要件以外的其他行为才能实现目的的犯罪。短缩二行为犯的既遂以实行行为的完成为标准,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目的行为)的实施和目的的实现并不影响该犯罪的既遂。短缩二行为犯的提出源自德国刑法学家宾丁(K .Binding)和麦兹格(Edmund Mezger),其被引入我国以后,对于解释我国《刑法》中的诸多目的犯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所规定的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中的第(一)项,以非法销售为目的,超过限额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配售枪支的,以行为人超过限额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配售枪支行为的完成为既遂标志,非法销售的目的要通过行为人的其他行为来完成,目的是否实现不影响本罪的既遂;第(二)项,以非法销售为目的,制造无号、重号、假号的枪支的情形亦是如此。再如,《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走私淫秽物品罪,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走私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书刊或者其他淫秽物品的,行为人只要以牟利或传播为目的,完成了走私淫秽物品即可构成本罪既遂,而并不要求行为人实现牟利和传播的目的。可以说,短缩二行为犯理论与我国的《刑法》具有高度的暗合性,这或许是该理论能被我国刑法学界接受、运用的理由之一。
1.2 短缩二行为犯的结构特征
短缩的二行为犯的基本特点是,“完整”的犯罪行为原本由两个行为组成,但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以实施第二个行为为目的实施了第一个行为(即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的实行行为),就以犯罪既遂论处,而不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第二个行为;与此同时,如果行为人不以实施第二个行为为目的,即使客观上实施了第一个行为,也不成立犯罪(或者仅成立其他犯罪)。我国《刑法》中最为典型的短缩二行为犯为绑架罪。“完整的”绑架罪包括实力控制被绑架人和向第三人提出不法要求两个行为,这里的不法要求包括向第三人勒索财物以及提出其他不法要求。实力控制被绑架人是该罪的实行行为,行为人一经控制被绑架人即意味着本罪的既遂,而无须不法目的的实现。反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勒索财物及其他不法目的,即使实力控制被害人,也只能以其他犯罪(例如非法拘禁罪)论处。当然,早期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绑架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复合行为,具体表现为“绑架他人+勒索财物”“偷盗婴儿+勒索财物”以及“绑架他人+提出不法要求”。不过,这种理解实则是将绑架罪比附为侵犯财产犯罪,忽视了绑架罪的主要犯罪客体。当下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绑架罪的既遂应当以行为人实力控制被绑架人为标准,勒索财物或提出其他不法要求仅作为绑架罪的目的行为,对其既遂判断亦无影响。
“短缩二行为犯实际上是一种主客观不相一致的类型,是一种主观要件多余客观要件、包含‘溢出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的犯罪形式”。与直接的目的犯相比,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结构具有三个特征:(1)短缩二行为犯的目的要素完全超出了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目的实现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但目的要素本身又必不可少。(2)短缩二行为犯的实行行为即是构成要件行为之全部,又是目的行为之手段。(3)短缩二行为犯的目的行为的实施与犯罪的成立和既遂无关,属于超出犯罪构成之外的行为。
2 短缩二行为犯的理论困境
短缩二行为犯理论为我国《刑法》中诸多罪名的认定提供了理论支撑,但由于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短缩二行为犯的研究不够深入,短缩二行为犯中存在的理论问题并未得到学者的重视,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中,短缩二行为犯的固有结构特征不足以解决争议问题。
2.1 目的行为先于实行行为完成的情形
短缩二行为犯的既遂以实行行为的完成为标准,其本意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法益,使刑法提前介入。然而,实践中存在目的行为先于手段行为完成的可能性。 例如:
行为人甲和乙共谋,绑架丙的儿子丁。按照分工,乙到丁的幼儿园去蹲点,甲给丙打电话要挟。某日下午4:00,乙在幼儿园门口蹲守,下午5:00,甲估计乙应该已经接到了丁,于是打电话,告诉丙:“你儿子在我手里,半个小时之内汇款10万过来,明天你儿子会安全回家,否则撕票。”丙于5:30向甲指定的账号汇款10万。随后,乙带着丁回来。第二天,甲乙将丁放了回去。事后查明,当日下午6:00乙才接到了丁(案例1)。
在这种情形下,甲、乙二人的绑架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如果认为,绑架罪以实力控制被害人为既遂标准,那么该案中,甲、乙二人所实施的绑架行为应当以乙实力控制丁(下午6:00)作为既遂时间,然而,在此之前,甲勒索财物的目的已经实现,乙控制丁的行为实际上失去了勒索财物目的这一主观要素,绑架行为因缺乏主观目的而无法成立。如果认为,甲、乙的绑架行为以甲取得丙的汇款为既遂标准,那么则完全不符合短缩二行为犯的结构特征和理论构造。
2.2 犯罪目的后于实行行为产生的情形
绑架罪的一般情形是,行为人产生勒索他人财物或其他不法目的,之后对被绑架人进行实力控制,并利用他人对于被绑架人的担忧而向他人提出不法要求。然而,实践中可能存在行为人的不法目的后于实行行为(实力控制被害人的行为)而产生的情形,例如:
行为人王某将仇人张某拘禁于自己家中以示教训,拘禁期间,王某萌生向张某家人勒索财物的目的,于是向张某妻子李某打电话,要求李某马上送5万元现金到王某住处,否则将杀害张某。李某遂携带5万元现金到王某的家中交予王某,王某得到现金后释放张某。(案例2)
在该案中,行为人王某的不法目的产生于拘禁行为完成之后,若王某没有产生勒索财物的目的,则构成非法拘禁罪。然而,勒索财物的目的产生以后,王某的行为性质发生了转化,即王某的行为由非法拘禁罪向绑架罪转化。问题在于,行为人王某实施的绑架罪以什么行为作为既遂标准?若以王某勒索财物行为的实施或以其取得赎金为标准,则与现有理论关于绑架罪的既遂标准不符。若以王某产生勒索财物的目的为既遂标准,则缺乏可操作性。
2.3 参与者在绑架罪既遂后仅参与实施目的行为的情形
在绑架罪的共同犯罪中,通常存在角色分工,即控制被绑架人和勒索财物之间的“协调配合”。如二人以上共谋对他人进行绑架,由其中一人或多人实施控制被绑架人的行为,而由另一部分参与者向第三人提出不法目的。此种情形中,各参与者当然构成绑架罪的共同犯罪。然而,还有另一种情形,即绑架罪的参与者有可能在其他行为人实施了控制被绑架人的行为之后,仅参与实施了勒索财物等目的行为。例如:
行为人孙某欲勒索钱某家人的财物,将钱某关押在一间厂房。周某得知孙某关押钱某的事情以后,表示愿意与孙某“合作”。于是孙某指使周某向钱某的家人索要赎金,钱某的父亲将20万元赎金转入孙某的账户。后孙某释放了钱某。(案例3)
该案中周某是在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完成后参与到犯罪活动中来的,并且周某仅实施了向第三个勒索财物的行为。在孙某实施绑架罪既遂的情形下,周某是否是绑架罪的共犯,存在疑问。若作肯定回答,则必然承认周某是在绑架罪既遂之后参与到绑架罪中,该结论在绑架罪现有的理论框架内难以成立。如认为周某不构成绑架罪的共同犯罪,而仅构成其他犯罪(例如敲诈勒索罪),则对周某的行为不能做到全面评价。
3 短缩二行为犯的重构
面对上述的理论困境,刑法学界鲜有学者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果恪守短缩二行为犯的固有结构,则对于绑架罪中的特殊情形难以进行合理的定性。因此,重构短缩二行为犯理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
3.1 从单一行为到选择行为
通说认为,短缩二行为犯是单一行为犯,“是将二行为犯或复行为犯短缩为一行为犯”。这也就是说,短缩二行为犯具有复行为犯的属性,只是立法将其犯罪既遂标准提前,从而使得短缩二行为犯的目的行为失去了犯罪成立条件中的地位。但目的行为又是行为人犯罪活动的终极追求,如果将其完全排除在短缩二行为犯的构成要件之外,则会造成刑法条文和犯罪现实的脱节。诚然,在绑架罪的一般情形中,以控制被绑架人作为既遂标准有利于保护法益,也使得绑架罪作为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基本属性得以凸显。但针对特殊情形的绑架行为,则应当灵活应对。在案例1中,行为人甲在确信实力控制行为已经完成的情形下,对第三人进行勒索,从而取得赎金,而实力控制行为事实上完成于勒索行为之后,在这种情形下,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和目的行为均达到满足状态,只是二者的先后顺序与绑架罪的典型情形存在不同。该情形应当认定为绑架罪的既遂。而既遂的标志则是勒索财物目的的实现而非控制人身行为的完成。若以后者为既遂标志,则在此之前已经得逞的勒索行为无法被该绑架行为所包含,而只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由此,行为人乙所实施的绑架行为和行为人甲所实施的敲诈勒索行为就相互分离,最终可能得出以绑架罪和敲诈勒索罪分别对甲、乙进行论处的不合理结论,而忽视了前后行为的统一性。
因此,对于这种情形的绑架行为,应当采取灵活的犯罪既遂认定思路。即重构绑架罪的既遂标准,由单一行为论发展为选择行为论,恢复短缩二行为犯的目的行为在特殊情形下的构成要件地位。这样的出发点是保护法益,也有利于实现罪刑的均衡,防止对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和目的行为作分别评价,最终得出行为人构成数罪或绑架罪未遂的不合理结论。然而,从单一行为论到目的行为论的变化有可能存在这样的诘责:在目的行为先于实行行为完成的情形下,以目的行为(例如绑架罪中勒索财物的行为)作为既遂标准是否会造成本罪的保护法益与犯罪既遂标准的不一致?绑架罪的主要保护法益为他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权利。若在特殊情形下承认勒索财物行为是绑架罪的既遂标准,则相当于将他人的财产权益作为本罪的主要保护法益。然而,这样的质疑是不成立的。在绑架罪中,所谓目的行为先于实行行为完成的情形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目的行为和实行行为均已达到满足状态,即勒索财物的行为和控制人身的行为均已实现;(2)实施勒索财物的行为人(目的行为)并不知晓实行行为未完成,如在案例1中行为人甲并不知道乙控制丁的行为没有完成;(3)目的行为與实行行为的实现顺序发生了颠倒,即目的行为先于实行行为完成。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方可构成此种特殊情形。因此,此种情形下,行为人即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又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益。因此,将目的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准并不会导致本罪主要保护法益的偏离。若行为人明知实行行为没有完成,而向他人提出勒索要求的,即便勒索财物成功,亦不能认定为绑架罪,而只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在这种情况下,后完成的实行行为只能构成非法拘禁罪。
3.2 从原生目的到派生目的
典型的短缩二行为犯的犯罪目的产生于实行行为之前,例如在绑架罪中,先有勒索财物等不法目的的产生,后有实力控制被绑架人这一行为;在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中,先有非法销售枪支的目的,后有超过限额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配售枪支的行为;在走私淫秽物品罪中,先有牟利或者传播的目的,后有走私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书刊或者其他淫秽物品的行为等。事实上,这不仅是短缩二行为犯这种特殊的目的犯的常态,也是所有目的犯的常态。在典型的短缩二行为犯中,犯罪目的是“原生”的。但是,如果单纯地认为,短缩二行为犯的犯罪目的只能产生于实行行为实施以前,则对于实行行为完成后行为人才产生犯罪目的的情形,短缩二行为犯固有的理论构架很难给予合理的认定。以绑架罪为例,若行为人以非法拘禁的故意对他人实施拘禁行为之后,方产生勒索财物的目的(案例2),根据短缩二行为犯的固有理论构造,恐难以对其进行科学的认定,因为这种情形下的绑架罪的犯罪目的是“派生”的,而非“原生”的。按照目的先于行为而产生的逻辑,如果认为案例2中,行为人构成绑架罪,则必然产生如下疑问:第一,该情形下的该绑架罪的实行行为以何时为开始,以何时为完成?第二,该绑架罪以何行为或何种结果作为既遂标准?
对于第一个问题,或许可以认为,该种绑架罪的实行行为从行为人产生勒索财物等不法目的产生作为开始的标志,并且以此时作为实行行为的完成的标志。然而,这又带来新的问题,即行为人在产生勒索财物等不法目的时,实力控制他人的状态已然实现,行为人未做出任何举动,如何认定实行行为“开始”和“完成”?如果认为,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是以不作为的方式来实施的,即行为人维系了已经发生的实力控制他人的状态,此即为绑架罪的实行行为的话,那么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不法目的产生之前的实力控制状态(拘禁状态)是否应当被单独评价?即评价为非法拘禁罪,进而与其后的绑架罪实行并罚?如果作肯定回答,则这样的结论是荒谬的。试想,如果行为人一开始就具有勒索财物的目的,进而实施绑架他人的行为,构成绑架罪一罪,而当行为人的勒索财物的目的产生于实行行为之后的,却构成两罪,后者的社会危害性并不重于前者。
对于第二个问题,如果认为,此种情形的绑架罪以行为人产生不法目的作为绑架罪既遂的标志,则这样的既遂缺乏外在行为的征表,因而难以将主观要素与外在行为相对应。如果认为,该种情形的绑架罪以行为人勒索财物或取得财物为既遂标志,则短缩二行为犯的固有理论构架无法予以解释。
事实上,对于“派生目的型”的短缩二行为犯,德国的刑法已有专门的规定。《德国刑法典》第239条a(掳人勒赎罪)规定:(1)诱拐或绑架某人,利用被害人对其健康或第三人对被害人的健康的担心进行勒索(第253条)的,或利用由其造成此等情状勒索他人的,处5年以上自由刑。据此,德国的掳人勒赎罪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诱拐或绑架被害人并利用被害人对其健康或第三人对被害人的健康的担心进行勒索的情形,这与典型的绑架罪相同,另一种是“利用由其造成此等情状勒索他人”的情形,即本文所指的行为人在实力控制被害人之后产生勒索财物的目的,进而实行勒索行为的情形。德国将该罪区分为“绑架型”和“利用型”两种,“其用意在于消除在实施绑架行为时不具备主观目的,在绑架行为完成之后才产生勒索目的的行为在绑架型要件中的解释障碍”。基于德国刑事立法的启示,本文认为,对于派生目的型的绑架行为,可参照《德国刑法典》中“利用型”掳人勒赎罪的规定,将其认定为绑架罪。那么这种类型的绑架罪中的何种行为是该罪的实行行为呢?对此,德国刑法学者认为,“只有行为人利用这一持续的、对他人人身控制状态产生了勒索目的并表现出来时,才能成立敲诈性绑架罪(即掳人勒赎罪——笔者注)”。本文赞成这种观点,并认为,行为人在实施了实力控制被害人的行为之后产生勒索财物等不法目的的,以行为人实施勒索等行为作为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并以勒索财物目的的实现作为该种绑架罪既遂的标准。而在此之前的实力控制被害人的行为不宜作单独评价,应与之后的勒索行为一并评价为一个绑架罪,这样的结论有利于避免对案件事实的重复评价,也有利于罪刑的均衡。
将短缩的二行为犯重构为“原生目的型”和“派生目的型”两种,不仅是处理绑架罪特殊情形的需要,也同样有利于处理其他短缩二行为犯。例如,行为人实施了超过限额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配售枪支的行为之后才“派生”了非法销售枪支的目的的,同样符合“以非法销售为目的,超过限额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配售枪支”的情形,应当认定为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行为人走私淫秽物品之后又产生牟利目的进而销售的,亦符合“以牟利的目的走私淫秽物品”的情形,应当认定为走私淫秽物品罪,并且将该情形认定为走私淫秽物品罪也符合我国《刑法》对于“间接走私”的规定。
3.3 从部分评价到整体评价
在短缩二行为犯的既遂不需要客观上存在与犯罪目的相对应的行为,只需要行为人以实施第二个行为为目的实施第一个行为即可,所以,短缩二行为犯中的目的要素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观超过要素”。短缩二行为犯的目的行为在构成要件上表现出“空缺性”,因此有学者将其目的行为称为“空缺的构成要件”。暂且不论该命名准确与否,仅就名称来说,短缩二行为犯的目的行为的确具有构成要件的“影子”。目的行为与实行行为应当是一个整体。目的行为在构成要件中的“缺失”对于认定典型的短缩二行为犯似乎并无大碍。但是对于认定短缩二行为犯的共同犯罪却存在“失灵”状况。正如上述案例3,在绑架罪中,行为人实施对被害人的实力控制之后,其他参与者参与该犯罪活动而仅实施勒索财物的行为,对后参与者应如何评价?通说认为,“认识到先行为人已将他人绑架,加入到犯罪之中、向人质家属索要赎金的行为也应该作为承继共犯被评价为绑架罪”。并且该观点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认可。然而,有学者指出,“承继的共犯场合,成立的时间为实行行为已经开始着手实行,但是尚未既遂。换句话说,在既遂后根本不可能成立承继共犯”。因此认为,“后行为人实施的向人质家属索要赎金的行为已经不属于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只是目的的实现行为而已。因而后人不可能成立绑架罪,而只应承担敲诈勒索罪的刑事责任”。
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认识到了绑架罪既遂后仅参与实施勒索行为的参与者与绑架罪的整体关联性,即该观点是以整体评价的思路认定后参与者的行为。第二种观点看似维护了承继共犯的理论,但割裂了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和目的行为的联系,其实质上是以部分评价取代了整体评价。本文赞成第一种观点,但应当指出,该观点的支持者的论证缺乏说服力。从本质上说,短缩二行为犯是刑法将复行为犯设定为单一行为犯的一种“法律拟制”现象。短缩二行为犯本身的复行为犯“基因”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并且可以在共同犯罪的认定种被“还原”和“释放”。法律拟制的特征在于将A情况拟制为B情况,从而在法律上做出另一种评价,其本质是以另一种法律评价来涵涉原本不属于该评价范围的行为模式,但法律拟制并不能改变行为模式的原有属性。例如,对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情形,虽然法律将其拟制为盗窃罪,但是并不因此而彻底改变该情形的信用卡诈骗的原有属性。正因为如此,对于行为人误将盗窃的信用卡当作拾得的信用卡使用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因此,虽然短缩二行为犯的目的行为在构成要件上存在空缺,但是在后参与者仅实施绑架罪的勒索财物的行为时,目的行为原本的构成要件属性(即实行行为属性)应当得到认可。在评价后参与者的行为时,后参与者的目的行为(勒索财物)与前行为人实力控制被绑架人的行為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对后参与者所实施的绑架罪的认定中来。因此,后参与者实施的勒索行为在其实施的绑架罪之整体中具有实行行为的属性,因此该参与者应当被认定为绑架罪的共犯。
从部分评价到整体评价的重构,旨在解决短缩二行为犯的共同犯罪问题,在短缩二行为犯的实行行为不足以发挥构成要件的功能时,应当还原目的行为的构成要件属性,使短缩二行为犯的承继共犯的认定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
4 结语
对短缩的二行为犯的重构是解释并解决短缩二行为犯理论困境的方法,也是优化短缩二行为犯结构的尝试。作为最为典型的短缩二行为犯,绑架罪成了本文重构短缩二行为犯的“试验田”。重构的目的不在于完全否定短缩二行为犯原本的结构框架,而在于在维持原则的基础上,探讨短缩二行为犯例外情形的适用规则,增强短缩二行为犯理论的灵活性,尤其增强目的行为在特殊情形下的构成要件功能。
参考文献
[1]刘红艳.短缩二行为犯目的要素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7,(7):138-146.
[2]付立庆.主观违法要素理论——以目的犯为中心的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1.
[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300.
[4]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225.
[5]德国刑法典[M].徐久生,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17.
[6]高颖文.绑架罪中仅参与提出不法要求之行为人的共犯性质认定——兼论短缩二行为犯中共犯的承继性[J].刑事法评论,2019,(41):44-66.
[7]张明楷.论短缩的二行为犯[J].中国法学,2004,(3):147-156.
[8]王钢.德国判例刑法(分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09.
[9]王兵兵.短缩的二行为犯“目的”的体系归属及其共犯问题探究[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15,(6):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