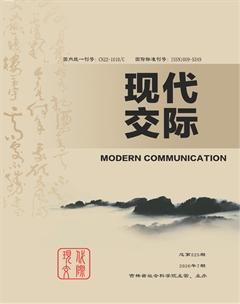试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言小说分类问题
张旭
摘要:中国文言小说内涵驳杂,在历代书目的著录中常与各种不属于小说范畴内的作品相互混淆,由此也带来了文言小说分类的操作困难。刘知畿站在史家立场上分小说为十家,多有不属于小说的作品,明人胡应麟的六分法首次提出志怪与传奇两种小说类型,但也表现出小说范畴被扩大的趋势。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回归汉唐小说观念,分小说为三家,虽然仍有标准不清、界限不明的问题,但相较过去已有所进步。
关键词:文言小说 分类 《四库全书总目》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7-0077-02
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长期以来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不同的时代理解又会有所差异,内涵的驳杂也造成了范畴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在历代公私书目对小说的著录上就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对小说进行二级分类也是一项见仁见智的工作,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对今天的文言小说研究仍有意义。
一、《四库全书总目》之前有关文言小说分类的尝试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呈现了与西方小说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其自身又包含了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两个系统,虽然同属一种文体,但是其各自的命运却有着显著的区别。白话小说虽然在古代不被正统文人重视且常受禁毁而散佚严重,但因其自身的特征较为明显,所以对白话小说的界定与分类相对比较容易。但对于文言小说来说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文言小说的概念较为模糊,导致文言小说与其他书籍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宋代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1]可见,早在宋代就有学者认识到小说与传记、杂家等类之间容易混淆了。
最早对文言小说进行分类的是唐代的刘知畿,他在《史通·杂述》中说:“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2]刘知畿是将体裁作为细分的标准,但这十类当中较为符合今人小说观念的则只有逸事、琐言和杂记三类,其他几类和小说并没有关系。杂记类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志怪小说,而逸事、琐言两类则大致属于志人小说,虽然刘知畿并未直接提出“志怪”与“志人”这样的小说分类。
明代的胡应麟提出了较为科学的文言小说分类,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中说:“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谈丛、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竒,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俱存,姑举其重而已。”[3]胡应麟把文言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其突出贡献体现在小说分类中明确把志怪与传奇作为两个独立的小说类型来看待,虽然《新唐书·艺文志》已经有收录传奇类作品,但传奇在文言小说二级分类中独占一类还是第一次。从分类上看,胡应麟参考了唐宋以来小说书目的著录情况,又单独列出志怪与传奇两类,但是这六种分类当中有些内容明显缺乏文学因素,而且“事实上潜在地扩大了沿着宋人小说观念继续拓展的趋势……使得明代古体小说观念虽然内核仍坚持说理与叙事的主干,但其外衍无限扩大,几乎涵盖了当时主流文学之外的所有表现形式”[4]。
二、《四库全书总目》对文言小说分类的处理
四库馆臣对著录什么样的作品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小序中提出:“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5]1182在对小说分类的处理上,四库馆臣并未直接袭用前人的分类,而是在小说家类中把小说分成了杂事、异闻、琐语三类,“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5]1182。杂事类与异闻类都有故事的成分,但杂事类可能重点在“杂”字,《总目》中说:“案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5]1182異闻类的重点在“异”字,从著录作品来看,大致相当于今人所谓志怪小说,四库馆臣并非一味排斥语怪之作,而是看到了这些作品的另一面,如《拾遗记》虽“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但是“然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欤”[5]1204。琐语类,有学者认为“与胡应麟所谓的‘杂录相类,应指以言语应对为主的短小故事”[6]。如果看到琐语类著录的具体作品的话,就会发现此类虽名曰“琐语”,但是著录的却不是以言语应对为主的短小故事。琐语类著录的五部小说中,《博物志》《述异记》《续博物志》今人都视为志怪小说,而《酉阳杂俎》与《清异录》则较为复杂,其中的内容既有志怪的成分也有志人的成分,现代多有学者将这类作品单独归结为杂俎类。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并不收录文言传奇类作品和通俗小说,何以《四库全书》不收录这些作品呢?其原因在于四库馆臣在观念上更为接近汉唐小说观念,重“道”而轻“技”,摒弃传奇的表现手法,力求恢复汉唐小说应当具备言事说理的核心特征,强调小说所具有的“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的社会功用价值。对于唐宋以来的小说发展,《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5]1182,于是被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馆臣认为“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猥鄙荒诞”的传奇小说和通俗小说自然被排除在外了。
与刘知畿的十分法与胡应麟的六分法相比,《四库全书》这样的三分法更为简明,紧扣汉唐小说言事说理的特征,把一些明显不属于子部小说家类的作品剔除出去,厘清了部分过去容易混淆之处。虽然《四库全书总目》并未系统地论述小说的文体特征,但是在文言小说的著录与分类上,因为紧扣汉唐小说观念所确立的言事说理的特征,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价值,不同于过去的小说书目中小说外延过于宽泛的弊病,分类更为简约,收录的篇目也基本符合传统小说观念。
三、《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分类存在的问题
《四库全书》纂修于集传统文化之大成的清代,在对有关传统小说的认识上本应当有一种总结性的体认,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也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小说家类的小序与提要对具体作品的评价有矛盾之处,小序所阐释的小说标准与具体提要撰写时的标准不够统一,甚至有多重标准的存在[7]。
《四库全书总目》在小说分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没有对细目名称明确定义,导致细目各类之间内部界限不明,分类标准不清晰。虽然《四库全书总目》在小说家类之前的小序中把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5]1182。但却并没有明确定义究竟何为“杂事”“异闻”与“琐语”,导致三类之间界限并不明显,具体作品的分类也似是而非。如杂事类著录唐代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而异闻类著录有唐代郑綮的《开天传信记》,两书皆是记录唐玄宗时的各种轶事,本身体例与内容方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四库馆臣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将两本书著录在不同的类别?或许可以说是因为提要中说《开天传信记》“语涉神怪”而被列入异闻,但是翻检《明皇杂录》可以发现是书同样有“语涉神怪”的内容,既然是两书都有这种“语涉神怪”内容的话,四库馆臣将两书分置不同的类目中就显得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了。此外,如果把异闻类看作主要著录志怪小说的一类的话,琐语类著录的作品实际上可以归入异闻类当中的,因为就著录的作品来看,并不能确定四库馆臣所指琐语是指什么样的内容,如果是指“言语应对的短小故事”的话,杂事中的《世说新语》和《唐语林》一类的作品划入琐语类不是更为恰当吗?可见《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将小说分为杂事、异闻与琐语三类,但实际上主要还是两大类,分别就杂事与异闻两类中著录的作品的大部分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类。
对于《四库全书总目》在小说分类与著录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宜以过分苛刻的眼光来看待它。其原因在于拥有悠久历史的文言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于小说的定义与认识,以及如何分类等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特别是对于文言小说的文类,古人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文言小说各种类型之间相互渗透的特点,而解决方案也只能是视其主要倾向而定其归属,但不同的学者对同样的作品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更何况《四库全书》如此庞大,而提要的撰写又出自众人之手,难免会有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四、结语
对文言小说进行二级分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四库全书总目》在前人已有分类的基础上,对小说范围的把握较为谨慎,剔除了不少明显不属于小说的内容,分类也较为精简。虽然存在分类标准不明确,界限不清晰的问题,但就其分类与著录的具体作品来看,大致上已经注意到了今天文言小说研究所重视的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两大类,对于当代的文言小说研究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817.
[2]刘知畿.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73.
[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2015:292.
[4]郝敬,张丽.论中国古体小说的观念流变[J].明清小说研究,2013(1):39.
[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張进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序文发微[J].晋阳学刊,2012(1):128.
[7]张进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匡误[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5.
责任编辑: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