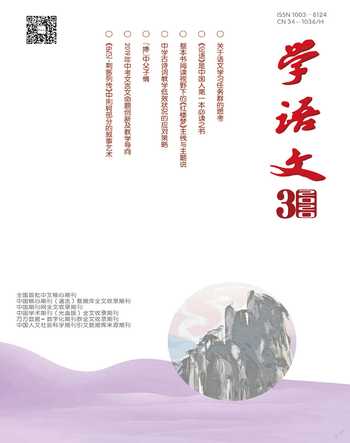试析鲁迅作品的语言
郑清芬
摘要:鲁迅作品的思想博大精深,其语言风格独树一帜,于个性化的表达中酣畅着审美的创造,彰显着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本文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为例,探究其架构语言的7种独特方式:矛盾式、“是”字式、反复式、对比式、描写式、修辞式、隐喻式。这些独特的语言“变奏”,为我们开拓了新的美的广阔的语言空间。
关键词:鲁迅;语言;矛盾;反复;对比;隐喻
“文化巨人”鲁迅的作品语言独树一帜,阅读他的作品,其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如一股清风扑面而来。我们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为例,分析这些文本中常见的语言架构方式。
一、矛盾式
(1)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这里的“似乎”与“确凿”用在一起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似乎”是因为已隔了七八年,不相见的久远,印象自然模糊,然“有一些野草”又“确凿”在记忆中存在。时间的距离,虽然冲淡了一些记忆,却冲淡不了百草园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的无限乐趣。“似乎”与“确凿”的矛盾,彰显了成年的“我”对百草园的铭心之念。
这互相矛盾的不能用在同一个句子中的一对词语,其实,正是作家的苦心孤诣,是作家或作品中人物复杂情感的一种流露,一种表达。
再比如:
(2)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孔乙己》)
(3)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故乡》)
例(2)中的“大约”“的确”,(3)中的“欢喜”“凄凉”,这些逻辑上矛盾、语法上看上去错误的词语,都置于一定的真实情境,形成一种语言张力,别有一般滋味,收到言尽旨远之奇效。
二、“是”字式
(4)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社戏》)
(5)……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社戏》)
仔细品读这些句子,其实都是“是”字句式。构成方式是:“……的是……”。以上两例都是“的”字结构充任主语,是句子的焦点所在。“的”字结构中“的”前部分可以扩展,如“近台的河里一望无际”,意义容量较大,便于表达具体的场景。这类“是”字句,是鲁迅作品中常用的一种重要句式,在他的作品中俯拾即是。
三、反复式
“反复”这一修辞格,是作家们常用的,鲁迅先生更深谙其艺术之道。
《故乡》中,“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碧绿”,这些文字几近相同地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我”回到阔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即将见儿时的伙伴闰土时,在脑里忽然闪出的“神异的图画”,这一“神异的图画”正是“我”记忆中的美好童年的幻影,同时也影射“我”和少年闰土之间的纯真的友谊、透明的欢乐。
另一次是“我”即将别离故乡时。“我”目睹了故乡的破败、萧索,见证了中年闰土的“辛苦麻木”、杨二嫂的“辛苦恣睢”,以及切切感受到“我”“辛苦展转”后的“愿望茫远”……
此时此刻的“神异图画”,仿佛是一个“寻梦人”对故乡未来的呓语,有一种浓烈的期待,有一种炽烈的憧憬,更有一种美好的召唤。
对于惜墨如金的小说大家而言,这些反复出现的词句,是一种强化,一种凸显,这些反复一定是小说在思想感情上的重点着力处,是我们解读小说的密码。
四、对比式
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对比手法是作家们的“大喜欢”。
《故乡》中的少年闰土:“紫色的圆脸”“红活圆实”的手,“头戴一顶小毡帽”。
中年闰土脸色“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头上是一顶破毡帽”,“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小说中通过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肖像、动作、对“我”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等方面的鲜明比照,凸显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小英雄”变成了历尽沧桑、心态麻木的“木偶”历程,这一残酷的现实,这一残酷的改变,给“我”难以磨灭的情感伤痛;这一切从人物角度的对比,无比深刻地表现了小说的主题之一: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和活力是怎样被扼杀的。
阅读鲁迅的作品,我们深知:对比是他着意经营的重要手法之一。
五、描写式
善于使用描写性的语言,当然是鲁迅语言一种重要特征。如:
(6)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社戏》)
“跳”、“拔”、“点”、“磕”、“退”、“出”等一系列驾船的动词,精妙传神,少年们驾船的姿势、样儿,历历地展露在读者眼前,去赵庄看戏的如“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一般轻松愉快的心情呼之欲出。
(7)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彩起来。(《社戏》)
这里,运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
“背”、“蹿”等动作进行逼真的描写;拟人、比喻等修辞进行形象生动的描写。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喝彩”,则从侧面烘托出孩子们架船技术的高超,以及孩子们的聪明能干。
鲁迅先生在遣词造句、描写方法的运用方面是有独到功力的。他所运用的词句凸显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收到词义明确以外的其他效果,或增添新意,或附加色彩。鲁迅作品的描写,整体和谐,或弦外有音,或陡增文采。
六、修辭式
鲁迅先生说:“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
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比喻、拟人等修辞,多姿多彩、新颖别致的修辞常常用得新奇巧妙、出神入化,收到了很好的表达效果,体现出精湛的语言艺术技巧。
(8)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社戏》)
比喻、拟人的修辞,呈现了远山的动态之美;且运用心理描写、化静为动的手法,把人物或景物具体地描绘出来,船行之快、看戏的心情之急迫可见一斑。
(9)“头顶上盘着大辫子……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实在标致极了。”(《藤野先生》)
“大辫子”“形成一座富士山”,作家就地取“材”(“富士山”),因“景”(“留学生”)成句,这一夸张可谓神来之笔。再用“实在标致极了”这一反语后缀,强烈的愤懑,隐忍的无奈,跳跃在字里行间。平静而奇崛的描写中,表现了作家对留学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七、隐喻式
隐喻是鲁迅作品的又一特征,借助隐喻手段,强化了本体与喻体的联系,使作品的立意更为深远。
(10)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孔乙己》)
这里的“秋风”、“初冬”不仅仅指天气、时令,也不仅仅指单纯的景物描写,更是一种氛围的渲染,是孔乙己凄凉、悲催、落寞人生的映射,是孔乙己的命运正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的最好隐喻。
鲁迅作品中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这种隐喻,意象微小而又丰富,如《故乡》中的香炉、烛台,《故乡》中的“神异的图画”等。这些隐喻,正是解读文本至关重要的“抓手”。
我们解读时,既要结合写作背景,又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借助隐喻思维,读出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作为中国文坛巨匠,鲁迅先生的作品充满着无穷的魅力和深邃的哲理。尤其是他运用语言的“变奏”艺术,俨然一位世界级钢琴大师。鲁迅作品的语言,是中国语文的骄傲,为我们开拓了新的美的广阔的语言空间。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市50中学新校天鹅湖校区)
[责编崔达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