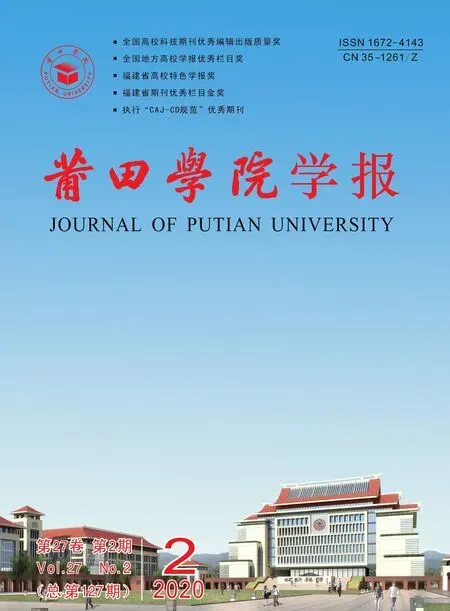原发性乳腺鳞状细胞癌临床病理分析
陈 宇,陈智伟,陈仲辉,李金秋,周 君,林 伟,3∗
(1.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乳腺外科,福建 莆田 351100;2.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病理科,福建 莆田 351100;3.福建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部,福建 福州 350004)
0 引言
乳腺癌发病率高,是影响女性健康的最主要的恶性肿瘤[1]。原发性乳腺鳞状细胞癌(primary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breast,PSCCB)在1908年首次由Troell提出,是乳腺癌中一种特殊类型的浸润性癌,因与浸润性导管癌难于区分,直到2000年WHO才正式将其独立分类[2]。PSCCB在乳腺恶性肿瘤中较为罕见,在乳腺癌中的比例极低[3-4],通常认为其起源于导管上皮细胞的鳞状化生,不属于乳房皮肤来源,也不是由其他部位转移而来的[5]。由于PSCCB极其罕见,缺乏特征性的临床表现及病理特点,治疗上也缺乏公认的国际标准,因而其规范化的诊断及治疗仍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文通过分析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我院)9例PSCCB的临床、病理特征、超声表现、治疗及预后,并回顾相关文献,提高对PSCCB的认识,为今后PSCCB的规范化诊断、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2009—2020年我院9例PSCCB标本,所有患者均为女性,年龄为31~64岁,平均年龄为44岁。均因无意中发现乳房肿物而就诊,左侧7例,右侧2例,占我同期乳腺癌手术比例0.35%(9/2594)。彩超表现为6例囊实性混合回声,1例片状低回声,1例不规则低回声,1例为稍低回声;9例PSCCB均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4例随访中复发,2例同侧胸壁复发,2例对侧乳房复发,平均复发时间为25.7月,3例无明显复发征象,2例失联(随访时间2~125个月)。所有患者均无乳腺癌家族史,无其它部位恶性肿瘤史(见表1)。

表1 9例乳腺鳞状细胞癌临床、病理、超声及预后
1.2 方法
收集所有病理确诊为PSCCB的临床资料,所有手术切除的病理标本采用4%的甲醛固定,常规石蜡包埋组织切片,HE染色,显微镜下观察。免疫组化采用EnVision法。即用型ER、PR、HER2、P63、CK5/6、P53、P120、E-cad、EGFR和Ki-67抗体购自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病理切片均经我院两名副主任医师或主任医师独立阅片诊断。
2 结果
2.1 大体所见
9例PSCCB肿物直径为1.9~5.8 cm,平均直径3.4 cm,6例为囊实性肿物,切面部分出血囊性变,部分灰白,质韧;3例为实性肿物,切面灰白,质韧,见图1(a)。
2.2 镜下所见
本组9例均为PSCCB,2例肿瘤组织可见巢状、团状排列,各个细胞间异型性明显,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角化形成,见图1(b);2例除了有上述组织结构变化外,肿瘤另可见间质纤维化,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坏死及玻璃样变,见图1(c);2例可见癌细胞呈上皮样变化,细胞呈巢状、片状混合排列,细胞质丰富,但其界限不甚清楚,核质呈空泡状,部分细胞核中可见多个小核仁,呈蓝色,并且可见较多的癌细胞的细胞核呈分裂象,见图1(d);2例组织细胞部分呈索状、部分呈片状、部分呈条状排列,并且彼此间相互连接,呈索条状排列结构,纤维组织分布在间质组织中,见图1(e);1例呈团块状、片状、不规则型排列方式,组织未见明显角化征象,见图1(f)。
2.3 免疫组化
7例病理组织ER、PR、HER2均阴性;1例ER、PR阴性,HER2阳性;1例ER阴性,PR、HER2阳性;9例P63、CK5/6、E-cad均为阳性,8例P120胞膜、EGFR阳性,1例P120胞膜、EGFR阴性,Ki-67在30%~80%之间,中位Ki-67为60%(见表2)。

图1 病理特征

表2 9例PSCCB免疫组化结果
3 讨论
鳞状细胞癌常发生于皮肤、口腔、食管等部位,部分乳腺恶性肿瘤虽然也有可能出现鳞状细胞分化,但是PSCCB却极为罕见。Takahashi K等和Yadav S等的研究指出,PSCCB的发病率在0.1%~0.67%[6-7],我院PSCCB的发病率在0.35%,与此研究相符。PSCCB临床诊断困难,病理上的诊断标准采用2012年WHO分类标准:1)所有的肿瘤成分必须全部是鳞状细胞癌;2)肿瘤成分与表皮结构没有相关(包括乳房皮肤、乳头);3)没有其他部位(器官、组织)的原发性鳞状细胞癌,必须排除乳腺以外的部位转移的可能。
3.1 临床特征
PSCCB在临床表现为肿块、质硬,活动度差,大多数病人为无意中发现,发现时肿物常较大,就诊时难以与其他乳腺恶性肿瘤相鉴别,但其仍有一些特点。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相对于临床上最常见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平均直径1.9 cm),PSCCB表现为肿瘤更大,平均直径为2.8~3.5 cm[7],我院9例PSCCB均为无意中发现,肿瘤平均直径为3.4 cm,与文献描述相符。PSCCB通常在年龄较大的患者上确诊,平均发病年龄>50岁,而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平均年龄在45~55岁间[7],在本研究中,平均年龄在44岁,相对较为年轻。
3.2 彩超
本研究中有6例表现为囊实性混合回声,其中2例内部回声不均,表现为混杂回声;1例片状低回声,边缘不光整;1例不规则低回声,边界欠清楚;1例为稍低回声。北京协和医院发表的一篇关于PSCCB文章指出,PSCCB在超声上表现为囊实性回声或低回声,形状不规则,边界欠清[8]。本研究中与其表现基本相符。
3.3 病理
PSCCB常表现为激素受体阴性,即ER、PR阴性,并且多数HER2也呈现阴性,因而PSCCB绝大部分是三阴性乳腺癌[9]。有文献指出,90%的PSCCB表现为EP、PR阴性[10];Wang等在一项关于29例PSCCB的研究中发现,ER均为阴性,PR和HER2阳性数均仅为1例[10]。本研究中全部病例ER均呈现阴性,1例PR阳性,2例HER2阳性,与Wang等的研究结果基本符合。本研究中P63、CK5/6、P120胞膜、E-cad、EGFR均呈高阳性率,已有研究也表明P63、CK5/6和EGFR是诊断PSCCB的重要免疫标志物[11],本研究进一步论证了P63、CK5/6和EGFR在PSCCB诊断中的重要性。P120胞膜阳性及E-cad阳性也对PSCCB起源于导管上皮这一理论假说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多篇研究文献指出,PSCCB腋窝淋巴结转移率较低,在10%~30%之间[5,8],我院9例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为19.8%,也呈现出低转移率表现。
3.4 鉴别诊断
1)乳腺腺鳞癌。乳腺腺鳞癌是一种少见的乳腺恶性肿瘤,镜下可见腺腔和鳞状细胞巢团,病灶周边可见淋巴细胞存在,可根据各种成分的比例与PSCCB相鉴别。2)浸润性导管癌。肿瘤细胞排列成索状,间质少,细胞团可见伴有中央腔隙的小管结构,无细胞间桥和单细胞角化,免疫组化中P63常成阴性也有助于鉴别。3)乳腺原发性血管肉瘤。镜下表现为乳腺间质和脂肪组织之间的血管腔相互吻合,正常小叶结构组织被破坏,血管腔的内皮细胞核深染,间质内见红细胞外渗。与PSCCB的棘细胞松解型常难以区分,但PSCCB表现为假腺管样和假血管瘤样的不典型癌细胞,且CD34和CD31阴性。4)梭形细胞癌。梭形细胞癌中的混合型可能与PSCCB鉴别困难,其表现为梭形鳞状细胞癌和恶性肌上皮癌混合,通过病理组织充分取样可以鉴别。5)髓样癌。癌细胞无腺管样结构,成合体状,淋巴浆细胞弥漫浸润在间质中,并且肿瘤外周有纤维带,界限清楚,而PSCCB角化珠形成,可以鉴别。
3.5 治疗和预后
关于PSCCB的治疗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通常采用手术为主,术后辅以化疗。一项随访28年关于PSCCB的研究中指出,新辅助化疗和术后辅助化疗方案中环磷酰胺的应用对于提高患者的总生存率有一定的帮助,但放疗在这项研究中并未得到生存获益[5]。另一篇文献中同样指出,放疗的获益效果并不明确,但新辅助治疗或许有效[12]。PSCCB的预后被认为比常见的三阴性乳腺癌预后更差,复发时间更短,复发率更高,总生存率更低,病理上EGFR的表达通常被认为与不良预后相关。多项研究指出,5年PSCCB的总生存率仅为34.5%~67.2%[7,13-16]。我院9例PSCCB中8例病理上表达EGFR,在中位随访33.6个月中,4例在随访中复发,3例无明显复发征象,2例失访,平均复发时间25.7个月,复发率为57.1%,平均复发时间同样较短,复发率高。
综上所述,PSCCB发病率低,发病时肿物通常较大,腋窝淋巴结转移率较低,超声多为囊实性混合回声;病理上P63、CK5/6和EGFR是诊断中较为敏感的指标,P120胞膜及E-cad呈阳性可能是支持导管上皮来源的理论证据之一;治疗上通常采用手术和术后辅助化疗,但效果有限;EGFR高表达可能与总体复发时间短、复发率高、5年总生存率低相关。新辅助化疗和化疗方案中环磷酰胺的应用显示了一定的潜力,有待今后的研究进一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