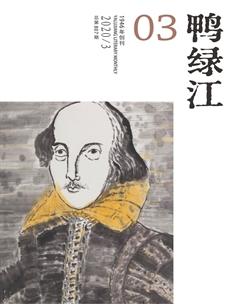蒙古人与羁縻制度的演变
王冬
摘要:宋元易鼎之际,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被蒙古人占领,中原封建王朝长期施行的羁縻制度已不能满足蒙古人的扩张需要,羁縻制度开始演变,最终形成土司制度。本文使用文献学的方法对羁縻制度的弊端、元朝的土司制度、蒙古人对羁縻制度演变的影响进行研究。
关键词:蒙古人;羁縻制度;蒙古人土司制度
蒙古人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较之中原封建王朝,他们在物质上不能自给自足。与汉地进行贸易、掠夺和扩张是他们生存的需要。随着扩张的进行,他们需要改变原有羁縻制度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松散的管辖。
一、羁縻制度的弊端
蒙古人崛起之前,羁縻制度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施行了千年。何为羁縻制度?《汉官仪》阐释道:“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受羁縻也。”[1]羁縻制度就像是拴牛马的绳子,是一种约束少数民族的工具。但这种“约束”,是象征性的约束。“中原封建王朝”[2]并未直接对其进行统治和管理,对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3]受羁縻的少数民族亦只是名义上的“臣服”。他们在军事、经济、法律等方面完全自治。既不用上报户口,也不用纳税,只需要进行不定时的朝贡。羁縻制度隐患很大,少数民族的态度往往根据中原封建王朝的國力而发生改变。中原封建王朝国强则臣服,国弱则大举进攻、攻城掠地,国不强不弱则进行周期性的“聚而为寇,抄掠边户”[4]。因羁縻制度的弊端带来最惨痛的代价便是因胡人南侵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大乱世。
二、元朝的土司制度
随着蒙古人的崛起,羁縻制度逐渐衍变为土司制度。关于土司制度,目前史学界认为:“土司制度产生于元代,盛行于明朝,衰落于清代。”[5]而元朝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政策,是成吉思汗中亚扩张政策的具体应用。李世愉说道:“元朝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实际上是直接沿袭蒙古帝国对待降附民族的自治政策。”[6]忽必烈十分重视对成吉思汗政策的继承,他挑选继承人的一大准则便是必须要熟知《札撒》。《明史》对元朝的土司制度有详细的记载:“洪武七年,西南诸蛮夷朝贡,多因元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大率宣慰等司经历皆流官,府州县佐贰多流官)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7]与羁縻制度象征性的约束不同,土司制度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施行和内地行省相似的税收政策。“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8]二、由天子负责处理不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矛盾。三、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宜慰使司、宜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和长官司等官职,当地的长官由朝廷任命。“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9]
三、蒙古人对羁縻制度演变的影响
(一)强有力的管辖
不同于中原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象征性的约束,蒙古人对其施行了强有力的管辖。蒙古人的领土极其辽阔,人口却很少。《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说道:“在现代地图上,成吉思汗征服了包括三十个国家和超过三十亿的人口。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成就基于其所控制的整个蒙古部落人数仅一百万。他从这一百万人口中征兵,其军队仅由不足十万的勇士组成。”[10]随着战争的进行,人少地多的矛盾迫使成吉思汗在占领区任命达鲁花赤进行全面管辖。达鲁花赤,亦做“答鲁合臣”、“达鲁噶齐”。蒙古语,意为“镇守者”[11]。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basqaq),在波斯语中则译为“沙黑纳”(shahna)[12]。汉文文献称“监”、监某州、监某府、监某路,《世界征服者史》称之为“少监”,赵翼称其为:“掌印办事之长官”[13]。成吉思汗总结了西夏被占领又复叛的经验教训后,于1209年第三次攻破了西夏并留下了达鲁花赤。“在那里留下一个长官和一支军队守卫该国。”[14]随着蒙古人的扩张,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达鲁花赤十分必要。忽必烈说道:“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曾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伐不息。”[15]忽必烈在平定大理国后,设置了宣抚使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最高长官。“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16]
(二)驿站建设
和中原封建王朝不同,蒙古人尤其重视“站赤”的建设。《元史》解释道:“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17]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断地在一条贯穿欧亚的狭长的草原地带活动。由于畜牧经济的物资缺乏,不像农耕地区可以自给自足。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和农耕地区进行贸易,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同时,为了便于管理广大的被征服地区。驿站的建设在宋元易鼎之际获得了空前的重视。驿站的建设和蒙古人的扩张、贸易同步进行。《世界征服者史》有记载:“他们的领土日广,重要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者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需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便设驿站……”[18]
(三)边疆变成内地
随着蒙古人的扩张,其国界线一直在变化,曾经刚征服的边疆在几年之后就成了内地。对于中原封建王朝而言,他们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并不紧密。蒙古人则不同,以畏兀儿部为例。他们起先与蒙古为邻,后来主动归附了成吉思汗。《史集》记载道:“为表明对哈剌契丹的敌对态度和对成吉思汗的驯顺,[亦都护]项成吉思汗派去了……他服从了圣旨,荣膺[成吉思汗]特示之垂青和恩赐而归。”[19]畏兀儿部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成为了蒙古帝国的核心地区,并不断助其东征西讨。“当成吉思汗进军大食地区时,[亦都护]奉旨带着他的军队出征……出征唐兀惕人时,亦都护曾奉旨从别失八里率领军队来为成吉思汗效力。”[20]此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此外,畏兀儿部落在文化上也贡献巨大。“哈剌和林山位于两山之间。窝阔台合罕所建的城,也用那座山的名字来称呼。”[21]他们的文字还被指定为蒙古帝国的官方文字。《元史》记载道:“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22]
(四)宽容政策
羁縻制度“约束”的对象是少数民族,而蒙古人本身就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一支。和古代的匈奴一样,他们出身于不毛之地。“黑鞑之国(即北单于)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23]相对于恪守“华夷之辨”中原封建王朝,他们对少数民族没有过多的歧视,他们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宽容政策,减少了双方的矛盾冲突。志费尼记载道:“成吉思汗因为不尊崇任何宗教,不追随任何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24]忽必烈直接称呼少数民族为“吾民”。“自今以往,咸奠厥居,流移失所者,招谕复业,有司常加存恤,毋致烦扰,重困吾民。”[25]在宽容政策的影响下,蒙古人获得了边疆少数民族的认同,为羁縻制度的演变打下了良好基础。
(五)征税
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实施羁縻制度时,不同于中原封建王朝的自给自足,他们因贸易、掠夺的需要必须征税。他们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维护“什一税”政策。蒙古人在攻打一个国家之前,总是先要求他们臣服于蒙古大汗并接受达鲁花赤在当地的统治,并且要求他们献出所有财富的十分之一。一旦被拒绝,蒙古人便一个一个摧毁他们的城市,杀光他们的子民。《出使蒙古记》有记载:“1237年12月,鞑靼人派遣使节数人到梁赞城(Riazan)——‘一个女巫,两个男人陪着她,要求他们献出‘男子、公爵、马匹、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一切财物的十分之一。当俄罗斯公爵们拒绝了这些条件后蒙古人就开始按次序一个一个地包围并摧毁了俄罗斯的城市……把居民统统屠杀掉,不问年龄和性别。”[26]
参考文献:
[1] [东汉]卫宏.汉官仪.四部备要本.
[2] 指秦汉、西晋、隋唐等全国统一王朝,以及大致奉行全国统一王朝治边策略的两宋等局部封建王朝。
[3] [东汉]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八十六.第2833页.
[4]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蛮夷三.
[5]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6] 李世愉.土司制度历史地位新论[J].重庆: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3).
[7] [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六册.职官志五.
[8] [明]宋濓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五册.地理志一.
[9]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土司传.
[10] [美]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导言.第5-6页.
[11] [元]胡抵通.紫山大全集.三怡堂丛书本.卷十五.蒙古公神道碑.
[12] 又译作舍黑捏、失黑捏。[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13] [元]姚燧.牧庵集.第十四卷;《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一部《畏吾儿地的征服和亦都护的归顺》:“当哈刺契丹〔的皇帝〕征服河中及突厥斯坦的那年春季,巴而术也落入臣服的圈套,不得不缴纳贡品。哈刺契丹的皇帝把一名沙黑纳派给他,其名叫少监。”译者注释说:“‘少监实为中国官号,少监和‘监国都是相当于沙黑纳、八思哈等的哈刺契丹称号。” 《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9《蒙古官名》,[清]赵冀著.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又,[明]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达鲁花, 犹华言荷包上压口捺子也。亦由古言总辖之比。”
[14]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兀惕部落.
[15] [明]宋濓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世祖纪五.
[16] [明]宋濓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四.世祖纪一.
[17] [明]宋濓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零一.兵志四.站赤.
[18]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第34-35页.
[19]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48页.
[20]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48-249页.
[21]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45页.
[22] [明]宋濓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二四.列传第十一.塔塔统阿.
[23] [南宋]彭大雅、王国维校.黑鞑事略.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
[24]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8.Vol.1.P.26.
[25] [明]宋濓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551页.
[26] [英]道森主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绪言.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