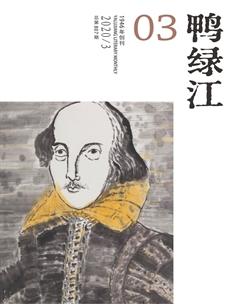免疫力
刘家朋
一
李光元跟王智仁一家人交往日渐频繁。
当智仁心里犯闷的时侯,光元便热心地说些风趣的话语给他解闷;当智仁高兴时,光元便也和他同样笑逐颜开,随着他的兴致说话;当智仁遇到了什么难办的事的时侯,光元便会热心地帮他出主意。只这些倒也不算,因李光元是个木匠,家中日子过得比较富裕,当智仁需要用钱,恰恰又手头逢艰难时,只要被李光元知道,李光元便慷慨解囊立即借钱给他。并且,李光元还常常无偿地帮智仁家干一些零碎的木工活。
智仁夫妻见李光元对他们是那样的热心相交,感动之余,对李光元也同样不错。
正月十八日这天,吃罢早饭,智仁急着到建筑队干活去了,儿子小强也上学了。为了提前为今年种花生准备好种子,媳妇银花便一个人在家忙着掰花生。正掰着,只听得院里的大门摇栓“吧哒”一声响,门摇栓被人摇开,随即“哐当”一声,门被推开。她定神一看,原来是李光元来了。
李光元比王智仁大两岁,今年四十二岁,高大魁梧,眉毛浓而黑,眼睛大又亮,留着时兴的大分头,实是相貌堂堂。再加上对银花一家总是那样的关心,见他来了,一种崇敬之情油然涌上银花的心头。
“哟,弟妹在家忙着掰花生种啊!”
“嗯,是呀!大哥快进屋坐坐。”银花笑容满面,热情地应答着李光元。
银花生的圆圆的苹果脸,柳叶眉毛下有两颗如星星般雪亮的大眼睛。她性格开朗,历来爱说爱笑,本来人就长得美,要是说话时再露出靓丽的笑容,那别提多讨喜了!
说话间,李光元很快便来到了屋里。银花一侧身,将身旁的一个马扎递给了李光元,李兴元接过马扎便坐在了银花身边。
银花随便问一句:“忙活活的,大哥怎么还有空耍呀?”
李光元说:“别人忙,我可不太忙,我那点地早就雇别人用拖拉机耕完了。”说着,两眼看着银花,不知不觉便显现出贪婪的神色。
“那,花生种也掰完了?”
“嗨,掰花生这活,天生就是娘们的活,就让你嫂子慢慢在家掰吧,我可没有耐心干这个。”李光元一边说,一边在银花那漂亮的脸蛋上左右扫视。
“那,你最近的木匠活不忙?”银花问着,羞涩地避开了他的目光。
李光元说声“不忙。”目光一直离不开银花的脸,“嗨,妹子,我这个活呀,说忙,到时侯还真忙;说不忙,只要向客户说一声,把打造用具的完工时间往后延长一些就行了,好办。”
“呵呵,大哥日子过得真自在。”
接下去,二人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继续拉些家常话。李光元一边说着话,一边仍时不时地飘向银花的脸,目光中,那贪婪的神情愈加显露。
银花本来是早已觉查到李光元的神情有些不对头,可是,自己的虚荣心偏偏又跟戒备心作对,见李光元这样放肆地瞅她,不但没引起反感,却暗暗为自己的魅力得意自豪起来。
看就看呗,男人嘛,见了对眼的女人难免就愿多看几眼,这也是很正常的事。自要自己把心摆正了,任凭他再怎么看,无非也就是过过眼瘾罢了。
银花这样想着,便装做什么也不知,低着头只管掰她的花生。
李光元砸了砸嘴,似无计可施的样子,随即便往屋子四下里端量了一番,最后目光盯在东间的东墙壁上。那墙壁上贴着一个一尺半见方的由木框镶边的针织刺绣大福字,甚是美观,他的眼光突然比起初亮起来,“喂,弟妹,你们东墙上那个大福字是你绣的?”
“啊,是呀!你看这个福字好看吗?”银花笑着说。然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中自然不自然地便帶出了亲昵的神情。
“哦,妹子的手可真巧哇!我敢说,咱们村除了你以外,能绣出这样福字的女人再没有了。”李光元借着这个话题便说起夸奖话来。
银花谦虚地说:“快别夸啦,大哥!我都觉得自己手拙得像鸭子巴掌不分路。”
李光元一时间没了言语,脑门儿微皱。
银花心里明白,他这是见自己的话语在她身上没起多大的作用,觉得无招可施了,不由得笑出声来,“嘿嘿,大哥,刚才你还承认自己日子过得自在,怎么这一阵又皱起脑门来了?”说着,脸上便不觉飞起一片红润。
“什么,我皱脑门了吗?妹子真是察人入微啊!”李光元急忙掩饰。可是,掩饰归掩饰,脸上那得意的神色,简直像打上了兴奋剂一般,根本抑制不住。
“奥,大哥可能是又在想嫂子了吧!”银花戏谑着,因为笑的幅度大,面若桃花。
忽然,李光元瞅了瞅银花坐着的那用红色尼龙绳襻的马扎,又低头看看自己坐的马扎,见马扎襻的很是美观,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奇迹:“嘿,弟妹,你们的马扎襻得太好了,又美观又结实,是你自己襻的?”
银花说:“还真让大哥给说中了,我家里共四个马扎,都是我自己襻的。”她说着,脸上便堆满了自豪的笑容。
“呀!我说的么,除了你,谁能干出这样的巧活?我当了多年的木匠,要说让我襻马扎,肯定还是襻不出这个美观的样子。”接着,他的两眼紧盯着银花的脸,“妹子长相也出众,凡是容貌漂亮的女人,手都巧。”
银花高兴极了,嘴里说着:“呵呵,大哥夸我了。”心里却兴奋得像喝了美酒,便关切地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又问他出外干木匠话是否能和一些不讲理的人闹起来,又问他天天出外当木匠,大嫂一人在家,是否能忙过地里的活来等等。李光元呢?则把自己出外见过的新鲜事儿说给银花听,说一会儿新鲜事儿,还参插讲一些动听的小故事。在讲他见过的新鲜事儿和小故事的时侯,时而捎带着夸耀银花与他所说的事件中人物类似的长处。银花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想听,渐渐听得有些入迷了……
二
原来,这个李光元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之所以对王智仁一家人热情相待,是因为早就看上了银花的美色!以前,他觉得火侯不到,不敢太放肆,现在他觉得时机已到,便开始用言语行动企图勾引银花……
傍晌天的时侯,智仁突然从石材厂回来了。当李光元看见王智仁摇开门栓,走进院里时,由于心虚,神情不由得一阵慌乱,话语嘎然而止。
“哦,大哥在这呀!”王智仁本不觉得李光元在自己家有什么不妥,毕竟以前经常来,但李光元脸上慌张神色让他不免有些疑惑。
李光元瓮声地说:“嗯,在家闲着没事干,隨便到你们这里坐坐。”
银花急忙用话语转移智仁的注意力,“咦,你中午一般不回家,怎么今天突然回来了?”智仁告诉她,听天气预报说,气温要下降,回来多穿件衣服。一边说一边再次观查李光元的神色。此时,李光元见王智仁先和气地跟他搭腔,心里像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那样轻松起来。但是,尽管这样,在智仁的两眼瞅向他的时侯,他的目光还是不由得便左右躲闪。智仁见他这样,心中愈加疑惑,不禁又想起了李光元五年前因拈花惹草所闹出的一场沸沸扬扬的风波。
五年前的一个初夏时节,李光元应邀去南面二十里外的大瞿家村,给一家户主叫瞿大江的人家打一口大衣柜。把活儿接到手后,按照瞿大江夫妻对衣柜的制作要求,李光元预算了一下,最少也得六个工作日才能完工。瞿大江夫妻见他骑自行车往返奔跑,实在是劳累,又恐他为此耽误干活,便留他食宿,直至完工。瞿大江热情地跟李光元交待:只要活儿干得对他们心意,不算吃饭住宿的成本,起初讲得多少工钱,仍给多少工钱,决不苛扣他一分一厘。不想,李光元只是嘴里表达谢意,因见瞿大江媳妇吴玉莲长的漂亮,心里便生邪念。瞿大江天天忙着去邻村一家石材厂上班,厂子老板为了让工人们抓紧生产,设有食堂,瞿大江中午不回家,到傍晚往往也是回来的很晚。吴玉莲本来就寂寞,又因着李光元长得英俊魁梧,又不停地给她送烟、斟茶水的献殷勤,又陪着他说话时间,便一时间鬼迷心窍,很快两人便做出了丑事。
常言说:鸡蛋无缝孵小鸡。李光元与吴玉莲的桃花事件不慎被邻居发觉,邻居便把这事传到了瞿大江耳朵。瞿大江愤怒之下,又要跟老婆离婚,又要跟李光元拼命。后来,在亲朋好友们的说合下,由李光元拿出三千块钱,赔偿了瞿大江精神损失费,这事才算了结。
一想到这,王智仁的疑心更重了。
“既然回来了,就在家吃了饭再回去吧。正好李大哥在这里,我炒几个菜,柜里有上好的‘竹叶青,你们哥俩一起喝上几盅。”银花见智仁那不高兴的样子,急忙想用这种方法调节他的心情。
智仁暗想:人的表情不自然,原因多去了,要是李光元心里没有什么事,很快也就心平气和了,如果心里有事,肯定会更不自然。于是便连连点头道:“好好,多少日子没和大哥一起喝酒了,今天凑巧大哥来了,那就一起高兴高兴。”
不想,李光元因怀疑自己的行为已被智仁看出破碇,急忙推辞:“不,不不!”瞅一眼银花,然后又看着智仁,“兄弟,今天中午我家里有客人,我还得回家陪客人喝几盅呢!”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迈步便向门外走去。
银花喊话留他。智仁便跟出门外拦住他,“大哥,别走别走,你不是爱吃豆瓣酱炖黒鱼嘛!我这就炖给你吃。”
“不不,兄弟,我家里今天真有客人。”急忙推辞。
智仁见他执意要走,便不再勉强。冷不丁赂南面方向看了看天空,但见,青天白日下,南河边他们家那棵高大的白杨树上的喜鹊窝周围,有两只鸠鹰为了争巢,与六只喜鹊左右盘旋,啄斗不休。智仁联想起李光元从前拈花惹草的事,再想想刚才他的一举一动,心中甚是不悦。
“怪了,李大哥今天好像不如以前那么实在了。”李光元走后,智仁对银花说。
“你没听人家说家中今天有客人嘛!人家怎么不实在了?”银花急忙解释。
智仁暂时没有回答银花的话,良久便说:“看他那表情,好像有些不自然,也不知为什么。”
银花说:“神经病!你就能瞎寻思。”
不想,智仁却是一个说话不善于讲究策略的人,开口便说:“不对,人的眼神和说话语气都是心灵的门户,只要眼神和说话语气有些不自然,心里肯定有鬼。”
“什么!”银花一听智仁说出这话,不觉气得眉毛倒竖,“你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你怀疑自己老婆偷汉养汉不成?!”
“哦,哦,不是不是。”智仁急忙解释:“对你,我是一万个放心,我是担心李大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惹你生气。”
“瞎寻思!”银花见智仁话语的矛头并不是指向她,口气稍缓和了一点,“人家李大哥虽然以前为作风问题闹过乱子,可是,近些年不是变好了么嘛!再说啦,有关他那回事,不过就是传说罢了,说不定人家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
原来,自从经过五年前那场风波后,李光元吃够了苦头,出外办事便开始小心谨慎起来,每逢与女人们见面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几年的时间过去,他与吴玉莲做出的那件丑事,渐渐很少有人议论了,即便有人偶尔提起这件事,众街坊们都认为这是谣传。似这样,他本来可以重新做人了。可是,只因一年前银花求他到家制了一个碗柜,银花每天对他热情招待。他见银花不仅长的漂亮,而且还是一个很容易动情的人,便“旧病复发”。
智仁说:“什么事都难说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风不起尘,既然当时人们对他议论的那么凶,最起码他在这方面是值得人怀疑。看表面是变好了,谁知他是真变好了,还是假变好了。”他本来不会咬文嚼字表达一些文绉绉的话语,也不知从那本戏文里学来的词句,此时竟然用上了。
“你放屁!你。”银花听智仁打得比如对她有刺激意味,顿时又来火了,“叫我说你这人凡事就是肯犯疑心病,在你没进家的时侯,李大哥跟我谈些在外见到的热闹事,说得正有兴致,你便突然回来了。人家肯定就是怕你犯疑,这才说着说着忽然停下的。因他话语停得急了些,表情本来就会不自然一些,你可倒好,胡乱怀疑人家这事,怀疑人家那事。人家这也帮咱,那也帮咱,似你这样怀疑法,要是让人家看出来,不就把人家得罪了?!”
智仁见银花气得脸色铁青,急忙便说:”好了好了,就算我得了疑心病便是。你压压火,慢慢说不行?”
银花大声呵斥:“不行!你这说法并不是在怀疑别人什么,纯粹是不相信自己老婆,你今天不把话说明白,我跟你没完!”
“你……”智仁刚要再跟她解释,只听得外面大门声响。夫妻俩不约而同地往外看去,原来是他们夫妻俩初恋时的介绍人王大婶来了。
王大婶一生酷爱读书,能言善变。进家后,先见到银花一脸怒容,又见智仁也是一脸生气的表情,便问他们发生了何事。两口子觉得王大婶是知心人,并不隐瞒,把事情发生的原委毫不保留地跟她细说一番,然后让王大婶给他们夫妻评理。
王大婶说:“依我看,你们俩光这么大动肝火抬死杠根本没用,还是沉下心找到事情的关健才能把事情处理好。”接着,她便面向智仁微笑着说:“先说你,作为一个男子汉,本来什么事没发生,你用一些侧面话语暗示一下媳妇,使她自己能引起注意就是了。人都说,打人不打脸,你可倒好,内心本来想把事情处理好,却捕风捉影地给人乱下结论,又话语那么生硬,不管谁听了,谁都受不了。”
智仁连连点着承认自己的不是。
接着,王大婶又对银花说:“银花,我看这事智仁虽然说话方式让人难以接受,不过,他说的也不是没有半点道理。你和李光元是清白的,智仁仅凭主观猜测便乱下结论,这是他的不对。但你这个做媳妇的应理解丈夫的心才对。”
“不,大婶。”银花脸色顿时又阴起来,“我已经够理解他了,他这纯粹就是无事找事!”
王大婶沉着地说:“不对,叫我说,人没有一个愿无事找事的。”
“照大婶这说法,那么,他胡乱怀疑人就是对的了。”
“这个我不是已经批评他了嘛!”
“那,我还能有什么错?”银花脑门紧皱起来。
王大婶稍一思考,忽然问道:“银花,你知道人在起初得病时,那病毒是怎么进入人体内的吗?”
“怎么进入身体的?”银花疑惑不解。
王大婶说:“人啊!在得病初期,病毒大都是乘人的身体虚弱的时侯进入人体的。而身体强壮的人呢,体内的免疫力就像强壮的士兵那样,给整个身体把关,因此,病毒就不敢侵入。作为你来说,依我看,在思维方式与处理问题的能力方面,还须增加免疫力。”
“大婶是提醒我真的需要对李大哥防备点?”银花觉得王大婶的话语不但含有瞧不起李光元的意味,同时也是对她人格的一种贬低。
“你别不愿听啊,银花。”王大婶先温和地提醒她一句,然后直言不讳地说:“做为李光元,以前曾因拈花惹草惹过祸,就等于精神免疫力低下的人得过病一样,一旦周围遇到肯犯病的环境,就很可能病情复发,并且也很容易把这种病传染给别人,咱们不得不防。”
银花不言语,心里只是觉得王大婶的话刺耳。
王大婶微微一笑,“病毒的‘味道和毒性大小各不一样,有苦的、有辣的、有咸的、有酸的、有无色无味的;有的呢?却带点甜头。那些无色无味的和带有甜头的病毒自然而然便开成了伪装的特性,它们长期围绕在人们的身边,让人防不胜防。”
接着,王大婶又说:“有些病毒潜伏期可大啦!不到把你身体摧垮,你是觉查不出来的。”
银花心里明白王大婶是在拐着弯儿劝她,忽然便说:“可是,人交人毕竟要讲究诚心啊,人家李大哥对咱不错,并且这几年也再没犯过那错,咱不可明里接受人家的帮助,暗里却对人家这么一个不放心,那么一个不放心,要是那样的话,咱自己不就连做人的人格都丢了嘛!”
王大婶说:“你做人讲究诚信,这没有错,但你要明白:人并非个个都是圣人,毕竟还是普通道德水准的人占多数。人人都可被人怀疑,人人也都可怀疑一人。他敬你们一分,你们以后可以敬他二分,这就算对他很讲诚信了,不可事事对他连半点提防心都没有。”
“怎么防!”银花心里一急,“人家就是来耍耍,要是照大婶这么说法,那就干脆跟李光元绝交算了,省得王智仁一天价瞎寻思!”
“断绝交往倒是用不着,人家对你们不错,你们不可就因为人家从前犯过错便跟人家绝交。不过,你在日常跟他见面时,还是提防着他点为好。比方说,你发现他跟你说话特别激动时,而这种激动恰恰又有些不自然,你满可以说些别的话语把话题岔开,或找个恰当借口起身干点别事,以此转移一下对方的思路,不然的话,他一时激动,扯扯拉拉的,场面就不好修拾了。真到了那一步,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大婶言重了。”银花觉得王大婶说话除了比智仁艺术性巧妙以外,同样是对她不放心。越听越心犯,因觉得王大婶是好意劝她,怕说话生硬伤了感情,忽然改变说话口气,“那,照大婶的说法,容易做错事的人又该如何增加免疫力呢?”
王大婶说:“两个途径,一是平日多向一些德才兼备的人学习,二就是需要多看书,通过吸取书中人物的间接经验教训,来提高自己处世为人的能力。”
王大婶历来对李光元看法不好。接着,她便又细心跟银花讲解具体如何防范李光元的一些细节做法,银花表面点头赞成,而内心里却一直是毫不服气。
三
李光元不愧是一只狡猾的狐狸。
对于他想得到银花这种心底,就好比黄鼠狼想吃到鸡一样的盼望,而對于他这个机警程度,恰似这条黄鼠狼偷鸡时躲避人的那种心态,一时一刻都不想让人觉查到;自从那天对银花想入非非被智仁看出破碇后,他便放慢了阴谋得到银花的脚步。他打定了主意:必须琢磨透这只鸡的抵抗能力及主人家的一切防范情况,瞅准时机方可下手。
时光易过。随着阵阵的雁鸣,节气很快到了惊蛰以后,温暖的阳光天天普照大地。众乡亲们有的用牲口或拖拉机忙着耕地;有的抗着锨镢到自己地里挖堰下渠;有的忙着用各式各样的车辆往地里拉土粪,还有的在自己承包的果园里给果树剪枝整树型;菜园里,已有人忙着种大蒜,育白菜种和罗卜种,还有人在用竹钯清理菜畦子等等。众多景象综合在一起,绘制成一幅幅繁荣昌盛的画面。然而,李光元的心里却并不繁荣昌盛,他一直都不出远门,天天只是待在家中干那些已接原料在手的零星木匠活,耐心等待再次与银花谈话的机会。他老婆张立菊见他一天价神情不自然,又突然间不再出远门,对他疑心重重。
常言说,无巧不成书。这天,智仁逢休班日。中午,有人喊他到街上打扑克,他便兴奋地出来跟大家凑凑。因李光元门口宽敞,大家恰恰聚集在那里。扑克打到兴头上,智仁兴奋地不由得身体左右晃动,不想,因坐下的马扎上面襻着的塑料绳已变质,不慎一屁股跌落在硬地面上,疼得他“哇呀”叫了两声。众人哄然一阵大笑,随后有牌友便说,“咦,咦咦,正好这儿有木匠,让光元回家再拿个小凳或马扎给你坐着,把这个破的让他取回家给你修修便是。”
而此时的智仁,自从王大婶劝说他看问题不可乱下结论那天起,他改正了遇事捕风捉影的缺点。然而,他又适得其反,对李光元言行举止竟然又粗心大意起来,因见李光元多日再没有去他们家单独找银花聊天,心中那份防范心早已消散在九霄云外。
就在智仁以求助的眼神看着李光元的同时,李光元也含笑地看着他,智仁便毫不犹豫地说:“好,好好,大哥,你就给我把这破马扎修修吧。”
李光元见智仁对他失去了防范心,心里不觉一动,“嗬,这倒是一个最能促使我与银花再相会的机会!”急忙上前扶起智仁,然后提着破马扎便回家去。一会儿,便从家中取出一个新马扎让智仁坐着继续打扑克。他便又转回家修整那个破马扎去了。
智仁因李光元给他修好了马扎,心里不过意,到晚上,便请李光元到家喝几盅。李光元故意装作反复推辞,最后见智仁执意相请,便就去了。从这天开始,李光元有时侯借口到智仁家借东西用,有时侯便装做有事要与智仁俩口子商量,隔不上三五天便会到智仁家去一次。有时侯去时还随手带瓶好酒或好吃的礼物。智仁夫妻热情相待。
晴明节将至。
在胶东半岛这个地方,每逢晴明节前后十几天内,半大孩子们都有个打秋千的风俗习惯。头着晴明节五天,小强便哼闹着非让智仁给他吊个秋千架子不可。不想,智仁平日干一些出大力的活还顶用,要是让他干一些需要巧门的活,却是个外行。小强反复哼闹,智仁只是不理不睬。吃罢早饭,垮上自行车便上班去了。小强看了看银花,哼闹着说:“妈,要不,你给我吊嘛!你给我吊嘛!”此时,银花早已把王大婶嘱咐她的话忘的一干二净,立即便说:“我不会吊,你快去村北头把你光元大爷找来,他肯定能给你吊起个好秋千。”
一会儿,小强去把李光元找来,便上学去了。
秋千很快便吊好,银花取脸盆盛了半盆水让李光元洗罢手,李光元便要告辞回家。银花忽然觉得麻烦他一顿,让他空手走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想想他是个木匠,平日里给人干活有时侯是按日工论工钱的,于是便说:“大哥别急着走,你给我干活,我不能白用你,就按你平日给别人干木匠活的工日给你钱便是。”说着,便迅速走向衣柜边,要到衣柜里取钱。李光元急忙上前拦住,“别别,别,这是谁跟谁呀!我就给你们干这么点话,你还要给我钱,这不是见外了嘛!”银花硬是要取钱,他用手拽住银花的胳膊就是不让她取。银花无奈,只得做罢,忽然想起李光元喜欢喝酒,便说:“大哥实在不收钱,我也没法,今日天气有些冷,要不我倒点酒,你喝点酒暖和暖和再走吧。”李光元点了一下头,“嗯 ,喝盅酒还可以。”
银花把饭桌放倒,取马扎让李光元坐在饭桌前歇着。然后取炒瓢到煤气罐上炒了两个菜,又从碗柜上取下一瓶烟台古酿,斟满了一盅酒,恭敬地端到李光元面前。这时,李光元喝了一口酒,又吃了一口菜,然后贪婪地看一眼银花的脸,嘻皮笑脸地说:“嘻嘻!妹子不但炒的菜可口,干起活来也麻利,炒两个菜半点都不费事的样子。”
银花便说:“大哥又夸我了,炒菜这样话,谁都会干,这算不了什么。”
李光元急忙说:“不,不不,妹子不管干什么活倒就是比一般家庭妇女干得又好又快。”
银花耳朵里听着,心里一阵喜悦。便取个小凳坐在李光元对面,准备随时给他斟酒,李光元又奉承道:“妹子想事真周到啊!还能想到天冷让大哥喝几盅酒再走。”
银花不好意思地说:“这样小事大哥别挂在嘴上,您不是给我们干过活嘛!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你既然觉得关心大哥是应该的,我给妹子干点活,自然也是应该的嘍!”李光元听罢银花的话,愈加装做通情达理的样子,
银花不由得心中跃过一个念头:这个李大哥,倒是一个与人处事很宽容的人,给我们干了半天活,就给他喝几盅酒,他便是那样的满足。”
李光元的两眼在银花身上上下打量,忽然看到银花的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力士鞋,那鞋的前头已打上了补丁。李光元便问道:“妹子,你现在脚上穿的鞋就是用来平日干活和在家时穿的吧?”
银花听李光元这么问,不由得看了看他的脚,他脚上穿着一双晶光油亮的纯牛皮鞋,不觉一种自卑感瞬间袭上心头。
“不是,我每到春秋季节里里外外就穿这一双鞋。”
“我可不敢跟大哥相比,穿黒油亮的牛皮鞋。”
“妹子喜欢皮鞋?喜欢不要紧,可以买双嘛 !”李光元试探地说。
“咱可穿不起。皮鞋都是像您这样有钱人穿的。”银花说着,差点没流下泪来。
李光元急忙便说:“这有何难!你要是想买,我借钱给你。”
“真的?”
“真的。”
“快算了吧,以前欠你情已经不少了,即使你给我借钱买上皮鞋,我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你,也是不好办。”银花脸上显现出难为情的样子。
李光元毫不犹豫地说:“嗨,妹子,还不起钱不要紧,什么时侯有了钱,什么时侯便还。一辈子没有,就一辈子不用还。”说着,他想了想,兜里正好装有四百块钱,急忙把钱掏出来,“呐,妹子,这四百块钱你拿去买皮鞋用。”“啪!”地一下把钱放在了饭桌边。
银花两眼看着钱,心里想取,但却又不好意思取,嗫嚅地说:“俺不要。”
李光元急忙取钱在手,站起身转过饭桌,硬给银花塞进衣兜里,“拿着,拿着,别见外嘛!”说着,便又夸银花能奔操过日子,她与智仁至今未发家,只不过属于时运不佳而已。被他这一夸,银花便陷入了沉思,竟然怨起自己命苦来了。她想起智仁一天价只能凭出大力挣有数的几个钱,而李光元平均干一天的木匠活,至少也挣智仁三倍的钱;并且,相比之下,智仁干点别的话也远不如李光元手巧;论说话,又比不上李大哥会说。就在这暗暗埋怨自己命苦的节骨眼上,不知不觉,她心里竟然真的对李光元盟动了爱睦之心……
她不觉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忽然又想起自己家还欠李光元两千块钱,可是,人家李光元不但不急着讨债,还不断地零碎帮自己一家人的忙,似这样的善良人实在是世上少有!不觉暗暗自语:看来,那些愿传话的人就是嘴痒,这个说人家拈花惹草,那个说人家拈花惹草,似这样的好心人肯定是那些作风不好的女人先对他动了心,事情败露后,因丢不起那个面子,又惹不起自己男人,最后翻过脸来陷害他便是……
她怕再多想会失态,急忙操起酒瓶给李光元斟酒。而就在她伸出右手到桌子边操酒瓶的时侯,肩部一阵酸痛,她急忙伸左手把酒瓶操过来,然后给李光元斟酒。这时,李光元便问:“妹子,你的右胳膊怎么了?怎么看你取酒瓶时很像是疼痛样子?”
银花说:“不是胳膊的事,我是最近有点肩周炎。”
李光元说:“嗨!妹子,你怎么不早说呢,一会儿我给你揉搓揉搓。”
银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心里一紧张,可是,刹那间又觉得有些好奇,“那,大哥在外面还学会了医学按摩?”
李光元说:“当然,我从前年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只是在自己村没给人按摩过罢了。”银花想了想,没应他的声。
李光元把酒喝足了,银花便拾掇碗筷和酒瓶。就在她把那剰下的半瓶酒往碗柜上放的时侯,因碗柜高了点,她刚用右手往上放,一抬胳膊,又觉得疼,急忙换左手放了上去。李光元这时便说:“哎呀!妹子,你就别不好意思了,一会儿还是用我给你理一理吧。缓解一下,说不定慢慢就好了。”
“昂,那就试试吧。”银花羞涩地答应下来。说着,便向院里大门那边瞟了一眼。李光元急忙奔到院里把大门关严,然后把大门的插拴“哐”的一声插上了。
李光元也的确在外面跟別人学过按摩术。银花躺在床上,任他先慢慢揉搓颈椎和肩部,银花顿时感到被揉搓的部位轻松得很,一会儿,李光元便把双手慢慢往下移动,本来是一只魔掌,而此时的银花,反觉得这只手不管触摸到她身体的任何部位,对她都是那样的温存。魔掌渐渐地触摸到银花的胸部,她本能地用两手一推,“大哥,你……”
李光元眯着色眼看着她,忽然张开双臂,一下子扑到她的身上,嘻皮笑脸,“嘿嘿,嘿嘿,你们欠的我那两千块钱,我不要了。你们欠我的那两千块钱我不要了……”
银花嘴里念叨着:“大哥别这样,大哥别这样……”全身却飘飘然,连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了。那张美丽的苹果脸蛋不由不忍地向李光元的胸前依偎过去……
四
屋子里的气氛有些肃然起来。天花板木着脸,墙壁显现出疑惑的神色,四下里的一切器俱似乎也都显露出质疑的目光……
李光元走后,银花想想智仁为这个家庭日夜奔波,并且对她也一直不错,再想想以往自己曾对智仁立过的那些海誓山盟,心里不觉为自己的失贞有些悔意。良心这个无形的评判员在遣责她。可是,与此同时,心中那份欲望天性无时无刻又在诱惑着她,她沉思默想一会儿,她把心一横,便自我安慰起来:没什么的,只要把这件事绝密,平日再对智仁加倍关心一点,自然也就问心无愧,身体是自己的,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李光元每隔六七天便到银花家揉躏银花一次。银花呢?也便糊涂地接受他。她还教李光元,以后凡是她在他身边的时侯,言语表情都要装得自然一些,李光元点头称是。于是,在没有外人知晓的情况下,二人都觉得这种做法是一种幸福。然而,他们之间毕竟没有纯洁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沟通,性欲就像小孩子们盼望吃顺口的食物一样,吃了后,便就不再如饥似渴地追求了。渐渐地,在李光元眼里,银花并非和从前那样美了,银花的言行,也不如从前那样高妙了,他不禁暗暗自叹:唉!在没得到她时,时时都觉得她是那样的美,原来,她也是很普通的嘛!此时此刻,他想起自己从前对银花一家人有求必应,不免有些后悔起来:咳,自己真是傻呀!就玩个女人,根本不值得破费那么大!他想起银花家还欠他两千块钱的事,忽然一个鬼主意绕过心头:“嘿,乘她现在跟我热乎,她欠我两千,我便找借口向她也借两千,如此,我一直不还她,不就两来无事了嘛!”
时正值1999年的时侯,在农村,乡亲们除了大面积的农活利用机械化操作外,有些小小的零碎活,还是需要牲口。大约是谷雨前后,忽然一天,李光元家的牛得病死了,到中午,便匆匆来到银花家中,装作很为难地说:
“坏了,银花,我家的牛死了,打算再买一头。你看看能不能暂时给我捣借两千块钱用?待我手头宽绰了,白给你多少都可以。”
银花笑着说:“嘿,和大哥这样富户,银行里存款有的是,你到银行里取出几千便是,这样小事何须求我呢?”
李光元说:“银行里有钱不假,可是,我都存的死期存单,要是取出来,要是不到期便取,把利息都瞎了。”
银花一听是这情况,替他着急起来。立即应声说要到银行取钱还他。其实,她家里和银行里都没有钱,打发李光元走后,去二十里外的大姐家借得两千块钱,还给了他。
太阳公公躲进云层里了,凉风习习。
这天上午,天气突变,已是阴历四月初的时节了,气温骤然下降到零度左右。李光元隔了十几天没和银花相会,便又去银花家找银花了。
银花见李光元走进院里,心里一热,什么话没说,身子一转,把他引进了里间。
“大哥最近好吧?”
“我很好,你也好吧……”
二人说着话便相互亲吻,然后,脱衣解带便抱在了一起。
就在这个时侯,忽然有人大喊:“干什么!干什么!”二人慌得魂飞魄散,抬头定神一看,竟是张立菊站到了面前。
原来,李光元和银花都大意了,银花忘了嘱咐李光元,李光元也粗心了,进屋时竟然忘了插上院门。
李光元提上裤子便溜出门外走了。还没等银花静下神来,张立菊大声骂道:“你个不要脸的骚货,你该死了你!”上前抓住银花的头发,连撕带打。银花不服地说:“你打谁!你打谁!这事是你们李光元来找我的,可不是我找他的,你要管先管好自己男人!”说着便还手也撕打张立菊,两个女人相互撕打在一起。
撕打了一会儿,两个人都累了,不知不觉都松了手。张立菊气喘吁吁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倒回头来说:“你等着,你个死X!今天来教训你这是轻的,等我回去向李光元问明白情况后再说,看看这事要是属于你先勾搭他的,我还得揍你!”
银花大声骂道:“你放屁!你放屁!”忽然觉得张立菊来得这么突然,很似他们夫妻设计害她,明明知道 这种可能性不大,也随口混淆起来:“你们两口子设计陷害我,我还要去法院告你们呢!”
张立菊走后,银花坐在床边流下泪来,越想越觉得自己挨这这顿打窝囊,抽咽了一会儿,忽然心想:“不行,决不能让这个疯老婆这么猖狂,我必须给李光元点压力,到时侯,李光元向疯婆子下跪,你个疯婆子看在自己男人面上,还得向我求饶呢!”想罢,她立即到床头操起电话机筒便给李光元打电话。那边李光元接通了电话。
“喂,银花,真对不起,谁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一步。”
“你不用多说,李光元,说不定就是你和老婆做了这么个扣子害我呢,我不能让你!”
“别别别,银花,咱们有话慢慢说。”听李光元说话的口气是想继续和她保持那种关系。
只听得话筒里“噗!”“噗!”连续两声响,随即便听到张立菊大骂:“你该死了,你!事到这般地步你还和她柔声和气的。”不用分析,那噗噗的两声响显然就是张立菊踢了李光元两脚,银花心里猜测着,那边的的电话机“哗啦”一声,电话便挂断了。
过了大约一个钟头,银花又给李光元挂电话,逢巧,她这次挂电话,张立菊不知干什么去了,还是李光元接电话。银花怒气冲冲地说:“李光元,既然你老婆对我这么凶,你得赶紧还我那两千块钱,昂!不然我跟你没完。”不想,李光元在老婆的严历管制下,终于变了良心,把口一改,“银花,你忘了吗?你们以前还欠我两千块呢,如此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
“啊!你不是说那两千块钱是给我们了么!你……”还没等银花把话说完,李光元“哗”地一声又把电话挂断了。
“骗子!”银花怒骂一声,不觉头晕目眩:自己之所以跟他好在了一起,是想得到他的真心相爱,难道就为了图他用小恩小惠欺骗然后任意糟蹋灵魂么!她一下子斜倒在电话机边,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暗暗发誓:“你等着,李光元,我会雇人把你们俩口子修拾个半死!”然而,发誓归发誓,她心里却明白,架并不是那么好打的。且不提双方打起来谁胜谁负的问题,不管谁受了重伤,都会惹起官司。官司一起,自己受到法律制裁就更不合算了。一会儿,她停止了哭声,开始沉思默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便决定违着良心把事件的真实情况胡乱一编,告李光元一个强暴妇女罪,可是,想想当时都是自己同意的,真论起法律来,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想用这个办法报复他们俩口子,那也是很愚蠢的呀!左思右想,她没了主意,只有在那里生闷气。失身丢面子倒也罢了,问题是自己觉得小脑瓜并不笨,却让别人当傻子耍了,只这些还不算,还得受张立菊那疯婆娘的气。似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忽见北墙上挂着一卷备用的如小指那么粗细的尼龙绳子,她下地摸起那根绳子,想想未曾装修的西里间露着梁,操着绳子便进去上吊。她把绳子的一端打到了梁上系紧,然后取了个板凳,双脚踏上去,把绳子剩余的一端系了个圆扣子,正要往里伸脖子,忽听的有人大喊:“混账!”喊声未绝,一脚给她把凳子踢翻。她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定神看了看,是王大婶救了她。
原来,王大婶是闻讯后特意赶来救她的。王大婶把她搀扶出里间,让她在床上坐好,便开始劝说她:
“你看看你,我以前劝你对李光元这样人要多加小心,你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内心里就是不听,事到于今果然把事闹大了。”
“既然事情已到了这般地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智仁和小强想想啊,你一死了之倒也轻松,撇下他们俩个,这以后的日子怎么有法过!还有你和智仁双方的父母,你这一死,不能为他们养老,可是大不孝哇!”
银花听罢,一头倒在王大婶怀里“呜呜”的便哭出声来。
接着,王大婶便劝说她:人生在世,毕竟是各人有各人的长处。但不管是谁,长处再多,要是心绪不正,这种长处往往就会酿成惹祸的根苗,要是心底善良,即便长处不多,也同样值得人们尊敬。别的不足,通过夫妻间相互包容,取长补短,终久会得到解决的。所谓真正的生活要靠自己去创造,正是这个道理。又给她讲解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过日子经验,等等, 等等。在王大婶 反复劝说下,银花终于想开了,立誓以后改正自己的错误,重做新人。
王大嬸见银花已想开了,心中这才松了一口气。然而,她心里终还是有些不快,虽然银花的人命已得救,但毕竟还是因未能深通人情事理而犯下了大错,再想想李光元的无德,张立菊的庸俗无智。再想想智仁的粗心大意,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这些人还是缺乏思想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