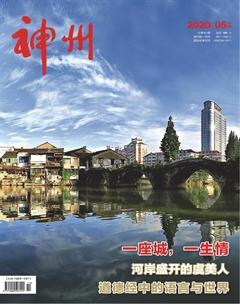道德经中的语言与世界
张玉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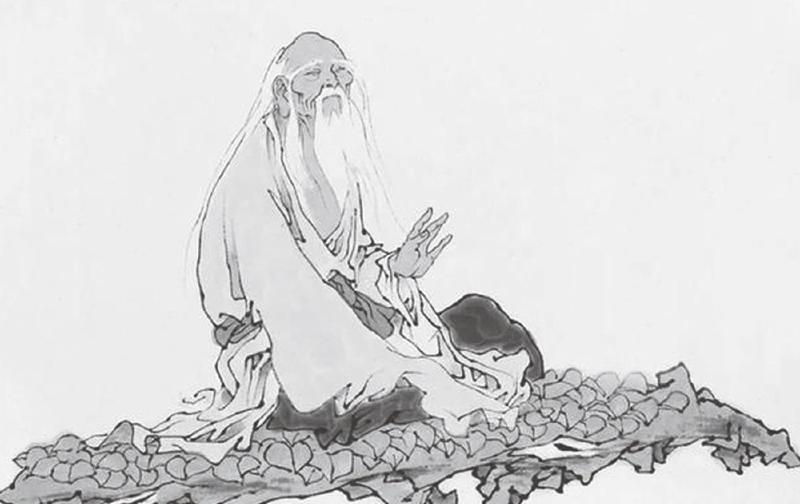
《道德经》开篇便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此言既在客观层面上表明了“常道”的不可言说性,又是他自知面临着严峻挑战的体现。这是一个智者以开天辟地的勇气而发的振聋发聩之声:他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悖论的境地,自知“道”不可言,却偏偏要以个人的勇气和智慧来迎接这个挑战——绕“不可说”而说,自著五千言以释“道”。这样的勇气和果敢,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在老子心中,恒常不变的“道”自是不可言说的,可说的就不是恒常不变的“道”。既然不可说,那老子的五千言又是在言何物呢?以我愚见,老子以五千言释“道”,实际上正是在有意识地突破语言的界限,冲破语言的桎梏,从而开启进入“道”境的众妙之门。老子以五千言描绘的,是他用自己的语言所创造的世界——一个借以通向恒常的“道”的世界。虽然“道”不可捉摸,亦无法言说,老子的五千言却是已道出的、可见的智慧,它是我们进入“道”的境界的桥梁,是我们进一步探讨“道”的凭借。
强为之名、损之又损、正言若反是老子在阐释时用到的三种方法。
强为之名,是一种明知言不能尽意却仍要为其命名的勇气。老子的“道”,是事物恒常、普遍、固有的规律,是神秘难测而又隐蔽在事物内部的东西,是不可企及、无法言说的,他以“道”为之命名,只是为了让自己有个便于指称和阐释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这只是一种尝试和努力,却并不能尽其意。损之又损,是一种坚守和智慧。老子通过这种方式,即不断地、从多个不同方面来描述“道”,在看似已抵达认知的同时,又即刻消除这种描述。不断地描述、不断地清除,老子以一腔坚毅不断前行,尽管他知道永远无法抵达真实的彼岸,可他却让真实在一次又一次的言说和擦拭中变得渐益清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正言若反,则是朴素辩证法的体现。彼此相异、互相排斥的事物在某种条件下互相包含、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彼此达到同一,这样,对立的概念便可流动、转化。老子遵循这种哲学观点的指导,正言反说,从“道”和“德”的对立面来阐释这两个概念。如所谓“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音希声”等等,都是通过正言若反来阐述事物。
老子在《道德经》中用此三种方法主要阐释了“道”和“德”这两个概念。
“道”在当时社会中,一般指的是人伦、常理之道。而在《道德经》中,“道”早已超越了世俗社会生活,而更加接近于自然法则之道。老子赋予了“道”与一般社会中的“道”完全不同的意义,“道”由是成为了老子哲学的专有名词和核心概念。在老子那里,“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它先于天地而生,周而复始,概括的是宇宙的起初和自然的本源,世间万物都是由“道”衍生而成的,故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所言之德也不同于常人所言之德。“德”在当时社会中,一般指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或德行,而老子的“德”,指的是修“道”之人必备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以及为人处世之方法。“德”是“道之功”、“道之用”,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是人们认知事物和改造事物的一种人为行为,与“道”相比,“德”是人们可以理解接受的,是可及的。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也是《道德经》开篇所言。天地初生之时,一切都是混沌的状态,却也是其本真的状态,老子以“无”称之;而天地生出,一切变得清晰后万物所具有的名,老子称之为“有”。这其实是与前文对应,也是在说万物本质的不可言说性。我们所说的话,为事物赋予的“名”,也不过是“有”,是我们借以理解和认识世界的中介,而那个“无”,才是事物本身,是我们无法抵达的边界。“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接着阐述了“有”“无”之用途,“無”让人领悟事物精深微妙,“有”则是通向“无”的桥梁。于是,在第一章中,老子实际上将语言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凭借短短数言,反复论证着“道”、“有”、“无”,深刻剖析着“道”的本质,进而描绘出一个意义隽永的“老子的世界”。
然而,语言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老子描述尽他心中的道了吗?我们理解到老子所说的道了吗?其实未必,真相也许早已在语言中流失。
但不可否认的是,老子仍是见天地悠悠而怆然涕下、是“独钓寒江雪”的智者,他站在人群前面,站在天地之间,把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告诉给他身后的人。早已在两千年前,他就向我们讲述着他毕生的智慧,描述着他心中的至高之理——“道”,描绘着他心中的理想世界。
老子为我们创造的世界,是通往“道”的本真的中间世界。透过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窥见老子深沉的哲思、语言的奇妙与局限,乃至世界本真的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