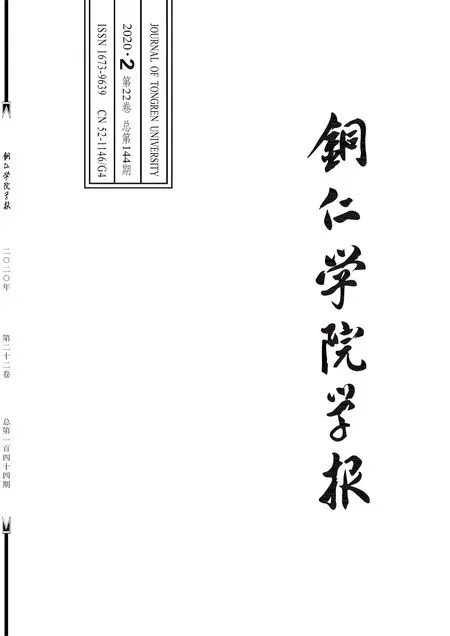文献互证:从出土文献祝由方看上古巫医文化传统
陈 宁
文献互证:从出土文献祝由方看上古巫医文化传统
陈 宁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战国祝由方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热烈讨论,但其中施祝者身份受到的关注较少。施祝者是联系“巫”和“医”的重要纽带,也是厘清“巫医”概念的关键所在,关系着“医”的起源和现实应用。从战国祝由方切入,综合出土文献和传世记载两方面材料,筛选关键信息,可以更加精确定义“祝由”概念。“巫”在先秦时代存在重大演变,上古治疗者角色具有多重性。从治疗手段、医者游历场所、患者意识等方面考察,可以确认战国施祝者即民巫。
祝由方; 巫; 医; 文化; 传统
巫的话题在中国经久不衰,涉及历史、神话、民俗、文学、医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巫医传统似与民众生活关系最密切。时至今日,农村地区治疗病患时,还有请专人唱跳念咒作法、让患者喝符灰水消灾的做法。笔者幼时换牙后,也被长辈要求尊崇民间习俗将下牙扔去屋顶,上牙扔至床底或大门之后以确保牙齿能好好生长。这些看似毫无根据但又关系人体医学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断绝,并被冠以“巫医”名号而获得令人敬畏的合法性。这启示我们可将“医”作为研究“巫”的重要切口,探索巫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面向。
学界在“巫”“医”关系上有过重要争论。不少学者持“巫医同源”的观点,陈邦贤认为:“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离。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1]范行准也认为:“治病之巫,实际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职业医生。”[2]胡新生指出:“最早的巫师也是最早的医生。巫医同源的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表现得十分突出。”[3]11-12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廖育群从两者实质出发,认为“就巫和医的实质而论,两者乃是相互对立的。不能因为某一历史时期,由某些人同时承担着双重角色就将其混为一谈”[4]。何裕民提出应该“多元性追溯”医的起源,他从动力学和发生机制的角度指出“本能医学”与“理性医学”都不可忽视[5]402-417。对于“巫医疗法”的定位,梁钊韬将巫术视作“原始人类联想的误用”,是“伪科学的行为”[6]。任继愈表示,“在原始社会,巫术是自发形成的;在阶级社会,巫术常被用作装神弄鬼进行欺骗的工具”[7]。不仅中国社会长期对此持负向态度,其他国家地区学者的看法亦相似,弗雷泽坚定认为“谬误的规则就是巫术”[8],埃文斯·普理查德在调查苏丹南部赞德地区若干年后,也观察得出当地巫医多是说谎的人,是江湖骗子[9]。而近几十年国内学者对巫术疗法又有新的检讨与反思,主动脱离“伪科学”“迷信”等探讨语境,将祝由法等巫术视作中国最原始的心理疗法[10][11]。并且随着新史学的发展推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巫医”放回历史语境下进行中肯评价[12][13][14]。
通过上述学术争论的启发,我们认为必须重新检视“巫医”概念及其历史价值,通过爬梳史籍记载和联系新材料来回溯上古巫医传统。祝由病方历来被视作巫术疗法的典型,与“巫”“医”两者勾连紧密,本文拟以出土战国祝由方作为探讨的起点。
一、何为祝由
近几十年地底出土大量医学文献,里面包含许多医方文本,祝由病方是其中重要一类。关于祝由疗法的定义,传世医籍有记载。《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云:“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15]189现在学界普遍认可王冰的理解:“古者巢居穴处,夕隐朝游禽兽之间,断可知矣。然动躁阳盛,故身热足以御寒;凉气生寒,故阴居可以避暑矣。夫志捐思想,则内无眷慕之累,心无愿欲,故外无伸宦之形,静保天真,自无邪胜,是以移精变气,无假毒药,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15]190即是一种不借针石毒药,在自然天真的状态下,通过移变精气、复强精神,再加以祝说得病缘由的治疗方法。后世医方中常有禁法,内容与《内经》中记录的祝由法相似。《千金翼方·禁经上》云:“《神仙经》曰:凡欲学禁,先持知五戒十善八忌四归,皆能修治此者,万神扶助,禁法乃行。”[16]强调学习禁法,乃要诚心诚意、守好戒律,唯能如此,才可得神相助获得禁法。《普济方·卷二百六十九》云:“言为心声,书为心尽,以夫精神交感寓于符祝……然则符祝之用有应否者,特在于正与不正之异耳。今故戴其术而冠以持受之法,使学者得于声画之间究其所以然者……彼受于邪由,精神不守所致,故在我者,当专心诚意以持之,欲致其诚心,先斋戒事以神明……用符兼以诅咒。”[17]同样要求“符祝”需诚心而发,守正精神,斋戒以事神明。这些行禁之前的要求似与王冰理解的“移精变气”具体内涵一致,故祝由法应是禁法的渊源。另外禁法中常常带有咒语,“咒”与“祝”上古皆为章母觉部字,音同义通。后世医家学者应是以“咒”来训“祝”义,将咒语与祝由语相等同。通过上述医籍记载,可知祝由似为祝祷诅咒的疗法,依靠咒说病原,并持守诚正之心、复强精神来驱赶邪祟病魔。
再检视出土祝由方的具体内容。由于祝由方在出土医籍中多见,里耶秦简、周家台秦简、北大秦简、马王堆帛书、睡虎地日书等简帛文献中均有发现。文繁不备录,特选典型文例移抄于下:
以叔(椒)七,税(脱)去黑者。操两瓦,之东西垣日出所烛,先貍(埋)一瓦垣止(址)下,复环禹步三,祝曰:“嘑(呼)!垣止(址),笱(苟)令某龋巳(已),予若叔(椒)了(子)。”而数之七,龋巳(已),即以所操瓦而盖□。

禹步三,乡(向)马祝曰:“高山高丝,某马心天。某为我已之,并企侍之。”即午画地,而最(撮)其土,以靡(摩)其鼻中。[18]
祝心疾,唾之,曰:“歜,某父某母,为某不以时,令某心甬(痛)毋期,令某唾之。”[19]
正月上卯,取豕首三,韦束一,荠(齏)之,以酉(酒)淳之,而投其宰(滓)井中,以其汁祭门户、宫四㔷。●祝曰:“啻(帝)有神草,名为豕首,冬生夏实,与啻(帝)同室,饮之以去百疾,丈父丈母,毋令百疾过某室。”●饮之,毋庸食,先少者(?)始(?)[20]
喷者,三祝曰……[21]

伤者血出,祝曰:「男子竭,女子酨。」五画地【□】之。
巢者:侯(候)天甸(电)而两手相靡(摩),鄉(向)甸(电)祝之,曰:“东方之王,西方【□□□】主 =(冥=—冥冥)人星。”二七而【□】。

在医书文献中,要判断病方是否属于祝由方并非易事。以上十例皆选录出土医书中带有“祝由”字句,根据夏德安(Donald Harper)的研究思路,将祝由语(incantations)和祝由术(ritual acts)作为判断标准[23],并以治疗疾病为目的来筛选材料。从中可总结出土祝由方的若干特点:其一,语辞。语辞内容跟驱除所患疾病有关。具体内容或涉及所患之病,如“龋”“某马心天”“某心甬(痛)”。语辞语气根据对象不同而有差异,对于假想的病魔鬼祟对象,则多命令威胁口吻;若是请天神相助,则多祈祷语气。其二,带有固定的仪式。如禹步,喷、唾、投祭、画地等。其三,带有祝由灵物。如:米、布等。其四,有特定场所。如墙垣、曲池等。其五,可能还与特殊时日相关,如正月上卯,辛巳日。其六,有祝由所治疾病的共性。据山田庆儿研究,只采取祝由疗法作为治疗手段的疾病有三条共性:与精神相关的疾病;没有适当的医术疗法治疗的疾病;只发生在特定人群身上的疾患,具有偶发性和短暂性[24]。
结合传世与出土两种文献,可看出后世医籍在祝由方的定义中对祝由术描述模糊,或径以“移精变气”概之。据上述总结,可将战国祝由方定义更加完整地表述为:祝由方是由祝由术加祝由语构成,用于治疗疾病的医方。其中,祝由术包括禹步、喷、唾、画地等固定仪式,祝由语是针对所患疾病向病魔鬼祟或天神进行诅咒或祈祷的语辞。两者结合还需配有一定灵物,如米、布、月事布等,在特殊地点、时日,对患有与精神相关、具有偶发性短暂性且无医术疗法可治愈的患者施行。
巫与祝由联系密切,在《黄帝内经》中早有记载。《内经·灵枢·贼风》云:“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何故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杨上善认为:“先巫知者,巫先于人,因与鬼神,前知事也。知于百病从胜克生,有从内外邪生。”[15]1880将巫者先知疾病的特点表述已清。且据医籍记载,巫的确具有治疗经历。《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汉人赵歧注:“巫欲祝活人……。”[25]2691《列子·周穆王》:“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谒史而卜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26]113-114皆可说明巫用“祝祷”之术治疗疾病在先秦时代非罕见之事。但据林富士研究,对于《灵枢·贼风》“先巫”的理解,历代学者看法并不统一:“能‘祝说’治病者,不外乎古代所谓的巫者,祝者和巫醫(毉)……然而还有人认为,即使是病人自己,也可以施行此术,例如,前引清代的医家张志聪便有这样的看法。”[27]林氏提到的张志聪认为:“拘于鬼神者,欲其祝由而愈病也。然祝由之道,移精变气,以我之神而通神明,有至道存焉。”[28]即主张祝由之道在“我”。张氏的理解实质上不是对“先巫”身份的讨论,而是对“话者”的推测。“话者”可以是先巫,也可以是病患本人,即是“祝由”的发明者可以亲自施祝,也可通过类似传授“禁方”的方式让病者自己施祝。故张氏关于“话者”的猜测与先巫身份的关系不大。但林氏的研究启发学界对于先巫身份的关注,如果把“先巫”的外延限于施祝者,对先巫的探讨则应放在“巫医”这个大概念下进行。必须先明晰“巫医”为何,才能确定“先巫”的坐标。
二、谁为“巫医”
“巫医”概念的关键是厘清上古社会中是谁在扮演治疗者角色的问题。典籍中记有许多上古社会的医疗事件,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25]1827这则故事讲曹共公为了复国,派侍从贿赂晋文公的筮史,让他把晋文公的得病缘由归结为晋灭掉了作为兄弟之国的曹国,并对其失信。晋文公听后果然很快恢复曹共公的君位。值得注意的是“筮史”在君王身边有时担负医疗者的身份,起着确定病由的作用。可以推测,筮史看病定应与施行筮法息息相关,可算作“巫医”的一类。《左传·昭公元年》:“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25]2023由此可知晋平公患病后,是由“卜人”确诊病因,且病患原因不易理解,连太史也不知其为何物,叔向只能请教前来探望的郑国子产。实沈、台骀传说为高辛氏与金天氏的后代,他们死后都成了晋国的保护神。把他们归于晋平公的病因,应是卜人据占卜加之联想发挥所得出的结果。《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其春,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竟死。”[29]3432放马滩秦简《日书》中记有大量巫医治疗的情状,何双全在考古综述中记道:“《巫医》59条。讲巫卜问病之说。以时辰投阳律,按生肖问病情,有无诊治办法,纯属巫医之说。如:旦至日中,投中大簇,虎也。韱色大口,长腰。其行延延矣,色赤墨,虚,善病中。”[30]除以上医例以外,先秦时代也有非巫疗法。如已所举到《列子·周穆王》:“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谒史而卜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祷之所祷,非药石之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26]113-114可见“医”是区别于卜人、巫人的治疗者,其疗法是用药石,即药物和砭石进行人体内外的治疗。《战国策·秦策二》:“扁鹊怒而投其石。”高诱注道:“石,砭,所以砭弹人痈肿也。”[31]也记录了扁鹊这位后世尊崇的医祖所善用的砭石疗法。
上古医疗者角色的多元实与此阶段巫史的发展有关,“绝地天通”的大变革是对其影响深远的大事。不烦移录于下,《国语·楚语下》云: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32]512-516
“绝地天通”事件意义重大,李零先生对此有精到的总结:他认为“绝地天通”使得天、地二官分工,人事和神事也有所分工;巫的地位下降,位于祝、宗、卜、史之下,而后者又位于王之下,这样的政治格局自商以来就已确立;他还具体分析了巫地位下降的几点原因,如常常被作为牺牲,并被官僚知识界和古代法律所鄙视等[14]76-78。其他学者对此亦有讨论[3]9-10,[5]213,[33]。笔者以为,这段史料意义重大,长期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探讨,需要不断细绎其中深意。“巫”无疑是这段史料的精髓,对此理解则显得尤为重要。
据《国语》记载,古时民神各自有序、不相混杂,他们的交流赖于“巫”。“巫”指的是“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理解文意,“巫”首先是“民”,并且是衷正比义、圣明聪慧的智者。这其实规定了“巫”的性质,是阶层身份的指称,指从民众中被选拔出的“智识群体”。他们需要负责制神位次、规定牺牲等工作。文中还谈到选拔专业人员司职履责的程序,“而后使先圣之后……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为之宗”,此处“先圣”“名姓”究指何人?笔者以为仍指代“巫”阶层。《春秋繁露》云:“择巫之洁清辩利者以为祝。”[34]已经说明祝是从巫中而来。且《说文》解此二字为“祝……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巫,祝也”[35],也说明二者关系紧密,似为一源。不仅是“祝”,本文重点讨论的医与巫在文字学意义上也联系紧密。《广雅疏证》云:“故醫或从巫作毉,《管子·权修》篇云:‘好用巫毉。’”[36]《说文》里许慎解“醫”字也说“古者巫彭作医”,表示“毉”从巫,于文有征。上例说明祝、宗、医等职可能皆是巫人,再者《楚语下》已道“(巫)其圣……其明……其聪……”也似呼应后面所提“先圣”“名姓”。如若笔者推断可行,即说明文中反映九黎乱德之前,在“巫”这个智识阶层里选择天地神民物等五官,分别为祝、宗等。笔者认为此处只说“祝”“宗”,不全五官,或有脱文。据下文“家为巫史”,至少还应有“史”官。并且据徐元诰引《路史·疏仡纪》:“小昊氏衰,玄都黎氏实乱天德,贤鬼而废人,唯龟策之从。谋臣不用,喆士在外,家为巫史。”[32]515或可说明“史”最初应从事与占卜相关的工作。既然“巫”最先似指身份阶层,“祝”“宗”“史”才是具体的职阶,便可解释后世多有名为“巫+名词”的情况,如《山海经·海内西经》提到“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大荒西经》中提到“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37]。其中“巫”不太可能是指官职,虽名号都带“巫”,但职能相异,周策纵将《山海经》与《周礼》中的二十二巫按工作性质分为五类,便即说明巫非一职[38]93,或是身份的象征。“巫”后的“咸”[39]38“即”“彭”等字,笔者猜测或是其名,“身份标志+名”似为最原初的名字构成。这也可说明为何后世常常“巫祝”“巫史”连用,应亦是此理。
而“绝地天通”之后,整个人世格局发生巨变。《楚语下》云:“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即颛顼受命重整秩序,让南正重掌天官、火正黎掌地官。天地系统恢复九黎乱德之前面貌。“绝地天通”的意义非限于恢复天地秩序,因为秩序仅是回归如初并无实质变化,真正的巨变体现在政治结构方面。颛顼通过任命使得天官地官系统收归在自己的行政体制内,巫内部选择天地之官的权力让渡于王权。王在这次变革中无疑是最大受益者,周策纵认为:“颛顼的政策则是恢复严格的巫祝制度,通过巫祝,利用职权,来巩固统治集团的既得地位。当时巫祝工作只许官办,也许有点像秦始皇垄断教育,要人民‘以吏为师’……”[38]82这也可理解为何商王掌政时常常进行卜祝,卜辞中常见“今日王祝”“王占曰”等语,“王为群巫之长所演变而成的政治领袖”已成研究共识[40]。然王非必是巫人,或可理解为商王想通过染指巫阶层,获得更多王权的合法性。故而商周以降,“巫”的意义也渐由泛化的阶层指称缩为后世的具体一职,《周礼·春官·宗伯》中列“司巫”“男巫”“女巫”等官即是其证。至此,可对“绝地天通”变革的意义稍加总结:一是政治结构的巨变,王权从“巫”人分权,至周代而世俗权力完全控制整个官僚体系。二是“巫”的内涵外延在“绝地天通”前后皆发生变化,由阶层泛称渐渐缩为一职,与祝、宗、卜、史、医并列而居,且在后世地位不断下降。
由是可知巫、卜、祝、宗、筮、医等官的发展进程,后面数者皆是“巫”人,均各司其职。而任巫官一职者应杂聚原巫人各官之技能,故后世典籍中巫时祝、时卜、时医。卜和筮史依恃原有技艺占病卜疾,而医官至东周仍未成主流并取代巫、卜、筮等官的治疗功能[41]。在此阶段,多种治疗者共同工作维护着社会个体的健康和安定。探明治疗者的并立及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对于确立施祝者身份无疑厘清不少思维障碍。
三、谁是祝者
因为《灵枢·贼风》中“先巫”的概念比较模糊,所指之“巫”不明是何历史阶段的“巫”,故由施祝者代其所指。由上述论证可得战国祝由方施者的可能性角色很多,既可为巫术疗者也可是非巫疗者,需要从祝由方的特点出发予以判断。无论是筮史可“以曹为解”作为病因劝告晋侯,还是卜人诊断晋平公害病源于“实沈、台骀为祟”,两者多是以“卜筮告疾”的方式来参与医疗事件。比照祝由方定义中“固定仪式”“咒祷语辞”“灵物配合”“特殊时地”等要素,卜人、筮史仅对疾病原因的联想式探索显然与之无关。而巫不仅可如赵岐所注用祝活人,还能视鬼祝祷。依《新语》记载,名医扁鹊在卫国欲救人子,却遭婉拒、被巫所咒:“(病者之父)退而不用,乃使灵巫求福请命,对扁鹊而咒,病者卒死,灵巫不能治也。”[42]“巫”在此求福咒人的形象与祝由方中“仪式”“语辞”的施者确有相似之处,可惜典籍勾勒未细,此处医疗情景的细节不能一一窥清。“医”虽以药石攻治疾病,从人体内外驱病疗疾,但也有文献记载:“吾闻上古为医曰茅父。茅父之为医也,以筦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43]依此,“医”也有可能成为“发言祝之”的施祝者。欲析清施祝者的身份,还需对“医”“巫”两者的行医事迹详细考察。
先看甲文中的医事资料。胡厚宣考证出殷高宗武丁时甲骨刻辞中的“疾”字[44],被学界高度认可,从而引起学者对殷商社会中医疗领域的关注研究。据胡氏考察,“贞亡降疾”“贞今日其雨疾”“隹(唯)且(祖)辛害王目”[45]“疾齿,不隹(唯)父乙害”等记录表示殷人认为疾病的原因在于“天神降疾”或“祖妣作害”。严一萍则认为殷人对于病因的看法共有四种:“天帝所降”“鬼神祟祸”“妖邪之蛊”“天象变化”[46],比胡氏研究更进一步。从严氏的总结可知,除天神祖先降祸降疾外,蛊祸与自然天气的变化也是致病的重要因素,这或可说明殷代先民意识中疾病起源于两途,一是主观联想中的神灵降灾,二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47][48]。胡氏根据卜辞继续考索殷人治疗方法,除告疾于祖,“祷于祖妣”外,他还依据考古实物与龟甲卜辞记录发现针砭、药物、灸法、按摩等皆为殷人治病手段。内蒙古包头市东郊阿善遗址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骨针和骨针筒,疑为古代医用器物[49];1973年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桃仁及郁李仁等药品实物[50];及甲刻辞中存有大量药物治病的文字记载[51][52],都可证明殷人疗法也有两途:祝祖祷告与药砭攻治。并且甲骨刻辞记载中殷王身边还设有管理疾病的官职,且负有治疾的职责。
《周礼》记载更为明显。《天官》中有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官“聚毒药以共医事”“掌养万民之疾病”,名义上负责王公及民众的疗疾之事。且此时的医官制度已初成规模,“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十,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25]666-667,可见医官俸禄已和其治疗成效相关。另《春官》中还列有司巫、男巫、女巫等巫职,他们除协助祭祀,招求福祥、举行祓祭之外,还负责“春招弭,以除疾病”[25]816,不过未见其除疾去病的疗法过程。《夏官·巫马》中更见“巫马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贾公彦疏:“巫知马祟,医知马病。”[25]861巫与医共同治疗马疾,这说明医巫两者在周代虽分立两官,但职分确有交叉。故巫、医时常并举。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25]2508
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善为舍。[53]
医乎巫乎!其知之乎?[26]215
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54]
故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29]3361
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冀祸消,盖有益也。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良如扁鹊,终不复生,何则?[55]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56]
寝疾,不信巫、祝、卜、医,数敕绝祷祀。[57]
医、巫两者的疗法手段,上述讨论已有涉及。医者主要采用药治和针砭,而巫则多用祷告求福以消灾疾。可再看典籍记载:《左传·成公十年》:“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麦。”[25]1906《庄子·应帝王》:“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祸福寿天,期以岁月旬日若神。”[58]《韩非子·显学》:“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59]故巫常用咒语、降神灵物(糈藉是精米,似为祝由方中的灵物)、卜测、祷祀等仪式治疗。胡新生依《鹖冠子·环流》中“积往生跂,工以为师;积毒成药,工以为医”并认为“往”通“尪”,“工”或写作“王”,“《鹖冠子》的意思是说一瘸一拐的丑陋步姿演化成为一种独特的巫术步法,那些本来无人理睬的跛者靠着这种跛步反而成为统治者信任的大巫,就像使用毒物者经过长期摸索熟悉了药性,反而被任命为医生一样。”[3]39胡氏推测医巫两者任命为王官的不同原因,也即说明两者的特点不同。
巫在殷商似还受商王器重,《尚书·君奭》云:“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25]223可知巫人仍任重臣,襄助王室治理政事。然至周代则愈发式微,由王官而逐渐下移民间。《逸周书》云:“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百草以备五味。”[60]《周礼》中关于“巫官”人员组成的记录是:“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男巫,无数。女巫,无数。其师,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25]755而关于“祝官”的记录则是:“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丧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诅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25]755狩野直喜由此认为巫的地位比祝低,不仅体现在祝的官衔级别高、配员更多,而且在分职种类更多、更完备[39]47。
巫虽在王官式微,但在民间似乎非常盛行。《楚辞·东皇太一》:“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61]依王逸《章句》:“灵,谓巫也。”故从《楚辞》可窥战国时代民间巫者尤众。《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魏文侯时,邺城长官常常勾结巫祝,以为河伯娶妻的名义大肆搜刮百姓,并且抢夺民女,“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取”。可见民间巫风之盛[29]3872。《风俗通义》也记有故事:“汝南鮦阳有于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车十余乘经泽中行,望见此麏著绳,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鲍鱼置其处。有顷,其主往,不见所得麏,反见鲍君,泽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为神,转相告语,治病求福,多有效验,因为起祀舍,众巫数十,帷帐钟鼓,方数百里皆来祷祀,号鲍君神。”[62]商车中的人途经大泽中,见有一麏,于是在麏主未在时将其牵走,又在原地留下鲍鱼。麏主回来见鲍鱼而不见麏,认为此鱼有神力。后周围民众听说后皆来求福,还兴修祭祀场所,“众巫数十”共来祷祀。从这些细节也可见民巫活动的盛况。笔者以为这与淫祀的兴起有关。《礼记·曲礼》:“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25]1268“淫祀”是指对不应该祭祀的神灵进行祭祀,这种祭祀得不到福报。虽是如此,淫祀在民间祭祀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史记·封禅书》:“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时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29]1651-1652说明官方对民间的祭祀已经放开。刘黎明依据蒲慕州的观点认为:“也就是说,县以下的祭祀听任当地人自行处理,这就为淫祠的发展留下空间。”[63]这也为民巫的盛行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和机会。
巫相对于医,在治疗手段方面更具非理性特点,近于祝由方记载的治疗程序。并且巫在民间的盛行也为其能在民间担任主要治疗者提供可能性。相比之下,医者在先秦典籍中大多为扁鹊一般的游医角色,无法与巫的影响相提并论。客观条件上,巫比医更可能成为施祝者,而从主观选择而言,亦是如此。马王堆帛书中《十问》记载:“俗人茫生,乃持(恃)巫医。”说明大多民众蒙昧而不懂保健知识,只迷信巫医,而此处“巫医”当指巫而言。反观《韩诗外传》《说苑》提及的“上古为医曰茅父”中的医,则应视作战国概念下的“医”而非“绝地天通”之前的医官,茅父也应属于上古社会中的巫人群体。也即表明上古社会的医疗者是巫人中的茅父,其治疗手段主要是“北面而祝”,“发言”即可治病。
综上讨论,战国祝由方施者的形象已渐清晰。从治疗者角色的厘清梳理,确定时间坐标,缩小可能范围;再从治疗手段、游历场所、患者意识等方面进行检视,最终认为民巫成为战国施祝者最具合理性。
四、结语
巫在早期中国社会影响巨大,对先民的信仰、习俗、卫生、艺术的形成发展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由巫史看巫医,旨在尽可能厘清上古传统中一些混沌的疑惑。最后探析出“巫”的含义应经过一次大的嬗变,由身份意义的概念发展至后来的具体官职,这启发我们看待“巫者”应具历史视角和观念。“巫医”在今日看来角色比较单一,但在巫祝宗史混同的时代,“巫医”角色则为集合概念,里面有众多子集,就连后世针药攻治的医也牵涉其中。另外,经验医学和巫术医学也非泾渭分明,出土祝由方中同样包含药疗成分,而后世医官体系也容纳祝由一科即是其证。现代学者需要反思在现代医学和科技文明的语境下如何看待“巫医”历史和存在,只有坚持还原历史语境的立场,搜集资料分析重要角色和场域,才能接近当时面貌,揭清文明起始时的混沌问题。
[1]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37:7.
[2]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0.
[3]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4] 廖育群.岐黄医道[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11.
[5] 何裕民,张晔.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4.
[6] 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16.
[7]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486.
[8] 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汪培基,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77.
[9] E·E·埃文斯·普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M].覃俐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8.
[10] 袁玮.中国古代祝由疗法初探[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1).
[11] 王正凯,刘明军.祝由:原始的心理疗法[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8).
[12] 林富士.汉代的巫者[M].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
[13] 李零.中国方术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4]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5] 龙伯坚,编著,龙式昭,整理.黄帝内经集解[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16] 孙思邈,著.李景荣,等,校释.千金翼方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441.
[17] 永瑢,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普济方:卷269-卷272[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3.
[18] 张雷,编.秦汉简牍医方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75,85,92.
[19] 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J].文物,2012(6).
[20] 田天.北大藏秦简《医方杂抄》初识[J].北京大学学报,2017(5).
[21] 和中浚,李继明,等.老官山汉墓《六十病方》与马王堆《五十二病方》比较研究[J].中医药文化,2015(4).
[22]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6[M].北京:中华书局,2014:89,217,227,254.
[23] Donald Harper.[M].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88:152.
[24] 山田庆儿,编.新发现中国科学史资料の研究:论考篇[M].京都: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261.
[25]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 杨伯峻,撰.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7] 林富士.“祝由”释义:以《黄帝内经·素问》为核心文本的讨论[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2012,83(4):698.
[28] 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卷二下[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9.
[29] 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0]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J].文物,1989(2):27.
[31] 刘向,辑录.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47-148.
[32]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3] 陶磊.从巫术到数术: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21-23.
[34]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428.
[35]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201.
[36] 王念孙.广雅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6.
[37]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352,453.
[38] 周策纵.古巫医与“六诗”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9] 狩野直喜.支那学文薮[M].东京:弘文堂书房,1927.
[40]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J].燕京学报,1936(20):535.
[41] 金仕起.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M].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298.
[42] 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0.
[43]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345-346.
[44]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03-306.
[45] 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10.
[46] 严一萍.中国医学之起源考略:下[J].大陆杂志,1951,2(9):14-15.
[47] 詹鄞鑫.卜辞殷代医药卫生考[J].中华医史杂志,1986,16(1).
[48] 李宗焜.从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与医疗[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2001,72(2):375.
[49] 李经纬.中医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12.
[50] 耿鉴庭,刘亮.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J].文物,1974(8).
[51] 袁庭栋,温少峰.殷虚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3:338-340.
[52] 严一萍.中国医学之起源考略:上[J].大陆杂志,1951,2(8):21.
[53]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16:574.
[54]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548.
[55]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965-966.
[5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88.
[57]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24.
[58]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297.
[59]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3:462-463.
[60] 皇甫谧,等,撰.陆吉,等,点校.逸周书[M].济南:齐鲁书社,2010:37.
[61]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56-58.
[62]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403.
[63] 刘黎明.灰暗的想象——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巫术信仰研究[M].成都:巴蜀出版社,2014:210.
Mutual Document Verification: Exploring the Ancient Culture Tradition of Witch Doctor from Early Unearthed Medical Prescriptions
CHEN Ning
( School of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The unearthed Zhu You medical prescription of the Warring States has caused a heated discussion in the academia, but the identity of the prescriber was less concerned. The prescriber is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Witch” and “Doctor”. It is also the key to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Witch Doctor” and relates to the origi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octor”.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Zhu You medical prescription of the Warring States, combining the materials of unearthed and handed down transcripts, screening key information, and define the “good wishes” concept more precisely. Secondly, from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Witch” group, we should re-examine the major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Witch”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role of the ancient healer. Finally, through the discussion from treatment methods, the doctors’ travel places, and perception of patient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folk witch may be the most reasonable prescriber in the Warring States.
Zhu You medical prescription, witch, doctor, culture, tradition
I206.2
A
1673-9639 (2020) 02-0011-09
2020-03-1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15AZW004)。
陈 宁(1995-),重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战国简帛文献。
(责任编辑 肖 峰)(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