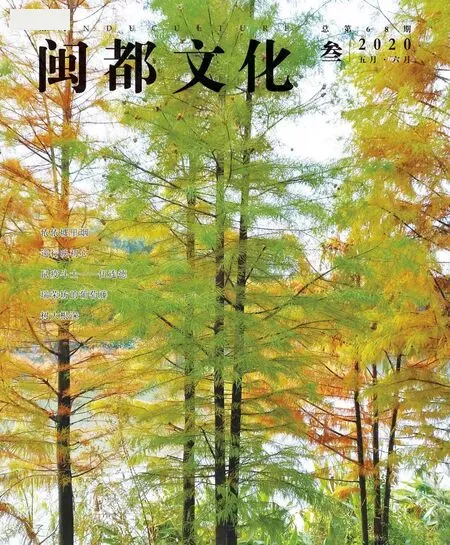瑞荣坊的葡萄藤
蔡 林
1
瑞荣坊拆迁了。报纸上的一张图片映入眼帘,矾红色的石牌上“瑞荣坊”三个大字依然清晰,端庄的楷体刚劲有力。目光从牌坊下穿过,瑞荣坊里一片狼藉。视线停留在中部,那里一片绿荫,阳光下掌叶舒展,闪着生命的光芒。那是一架葡萄藤,在这片废墟中从容地撑着一片绿。记忆越过这葡萄架,延伸出图片,在坊道尽头的围墙外是我曾住过的地方——义和花园楼。从楼上的西窗口可以俯瞰整个坊,坊里住着发小、同学、画友……少时的印记很深,以至于若干年后遇上曾住在瑞荣坊的画友韦先生,还能清晰地聊起那画面,从而得知这架葡萄是他栽下的。
韦先生是瑞荣坊的少主,老太古洋行福州分行的大老板韦锦川先生的孙子。

2007年的瑞荣坊一片狼藉 小飞刀/摄
2
辛亥革命前夕,一个深秋的早晨,韦锦川身着一袭烟青色长衫,上套一件半新的藏青厚呢马褂,伫立在海关埕码头,凝望着一艘向东远去的机帆船。那船上是他刚刚送走的香港太古洋行福州分行的洋老板一家。洋老板患病已久且担心辛亥革命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决意撤离福州回英国。然而,几十年积累的商贸业务,不是一时可以撤掉的。他看上了跟随他十多年、诚实精明的韦锦川先生,拒绝了香港总部的派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快速转让了太古洋行福州分行的茶厂、航运、仓库以及所有的外贸业务和场所。
韦锦川目送着远去的帆船渐渐地融入天边的水雾。流淌的闽江水在升起的阳光下闪着金光,那捉摸不定的金光里有他的梦想。老家广东中山的他,十几岁就开始随着父兄学习如何与洋人做生意,凭一口流利的英语闯入香港。他具有华人诚实、勤劳、坚忍的品格,又精于生意场上的每个环节。
这次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降临。他倾其所有,借遍了所有可以借的地方,质押了所有可以质押的货单,凭着良好的人品,一个月内凑足了7万块现大洋,从洋人手里盘下了他极为熟悉却从未奢望的太古洋行福州分行所有的家当。
7万块大洋,他心里默念着这个数字,轻轻地扯了下毛了边的褂襟,转身把目光投向南面,海关大楼后面的建筑群就是太古的家当,那里有洋楼、茶厂、仓库……他加快了脚步,走向了属于他自己的帝国。
3
瑞荣坊是韦锦川最成功时创下的产业。韦锦川自接手太古洋行福州分行后,筚路蓝缕,小心经营着出口茶叶,进口白糖、冰糖的生意。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太古总部需要大量的桐油、麻袋、棉花、绳索等战争后勤用品和医疗原材料,品种多货物杂,韦锦川凭着经验,辛劳地完成了每一笔交易,将货源源不断地运至中国香港、印度等地。他又精于茶叶加工,参股船运。很快,他还清了所有的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攒了不少银圆在几个镶着铜包角的大木箱里。于是,他从没落的同乡手里,购入了瑞荣坊南侧的地皮,建起这12间广式排屋。
在这之前,那位没落的同乡已陆续将北面地块转让出去,自己落在东北角上。北面先盖的排屋,由于多家业主,风格不一,不及南面后起的韦氏排屋整齐气派,但不妨碍瑞荣坊整体格局的构成。
早先瑞荣坊南北排屋之间是一条不小的水沟,两岸之间以厚木板为桥连接。这水沟属海关浦水系,沟宽可以撑小船。这沟水自西往东流经瑞荣坊中轴,绕义和楼西围墙,经碧琳花园汇入环绕水系,由义和花园北面围墙通往新民街,而后回到闽江。我小时候曾顺着义和楼花园里的水道打开围墙后小门,见沟水绕墙根东去。“文革”期间,我住到了楼上,从二楼西窗口俯瞰瑞荣坊时,已无水沟,只有一条中轴通道。
瑞荣坊南面韦氏排屋12间,砖木结构,每间结构面积基本相同,宽4米,进深二十四五米。入门一天井,过天井入室,侧有约1米的过道。行五六米,有一采光井,高八九米,深约4米。侧壁设木梯通往二楼,上有玻璃雨棚。过采光井又进入过道,仍有侧室,室后设有小木梯。二楼有南北两房,每间房大约20平方米,成排的玻璃窗,采光极好。步出二楼南面房间的门,是一方4米见宽的阳台,阳台栏杆由齐齐排列着的蓝釉色花瓶柱支撑,站在阳台上,可见马路对面的茶厂。阳台下小花园外是排屋的南围墙,正与茶厂隔街相望。围墙中部有一道门,可通行,我常经过这里,去坊里找伙伴玩。
韦锦川共育有七男八女,这12间排屋是为成年儿女们置办的。除了大女儿住茶厂旁的小洋楼,他和夫人带着幼小和伙计、员工一大家子,住在太古洋行建筑群里。瑞荣坊建成后,韦锦川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视瑞荣坊为吉宅。20世纪30年代末,他带头与在榕的广东商贾一道,为修建临江广东会馆捐资,并为抗日义捐,购入徐悲鸿和一些名人画作。画友韦先生曾留有他祖父认捐的徐悲鸿画作《葡萄》,或许这就是他偏爱种植葡萄藤的由来。

19世纪20年代末,韦氏全家福,中间老者是韦锦川先生
1941年4月21日,福州第一次沦陷,太古洋行福州分行生意败落,韦锦川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和逼迫,于1943年含恨而死。1944年福州再次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两次的沦陷,家道中落。国破家亡,大女儿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大女儿积极说服赴香港办理洋行事务的母亲,放弃香港的产业回来。20世纪50年代初,韦锦川的三夫人与小儿子一同回到福州,积极处理福州太古洋行的产业,使之国有化。韦锦川家族和中国许许多多的民族资本家一样,参与共和国建设,融入滚滚的时代潮流。
4

“凤鸣三山”雕像
闽江大桥是福州城跨闽江的第二座桥梁。这座桥始建于1970年,1994年改建,桥面从原来的18米增加到了27.2米,是一座可载重的大桥。
驱车沿着六一中路南行过桥到仓山区,迎面而来的是由三面巨擘托起三只腾空而出的凤凰雕像,这寓意着“凤鸣三山”的地标似乎翘盼着、迎接着每位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韦先生说:这个立着三只凤凰的地方,就是原来太古洋行的建筑群。20世纪50年代初还有七八栋两三层红砖结构的英式洋楼花园。后将产业转给了政府,拆了修路。
从闽江大桥南行,绕过三只凤凰左拐向东是朝阳路。20世纪60年代初,闽江大桥还未建,三只凤凰塑像处还是一片很大的空地。朝阳路的西头接着这片空地,茶厂就在路的南侧。记得当时在这条路上的前段有一个离地约6米高的木廊屋,横跨于茶厂与北边的红砖楼之间。韦先生说:这原是太古洋行的监工调动货物、监视工人的办公点,后来也一起转让给国家。红砖楼边有棵大白玉兰树,树冠荫着木廊跨楼,夏季开满了飘香的玉兰花。楼的背面是东西走向的巷子,东连瑞荣坊。巷子西头的海关埕5号是一个单位的仓库,常有大车进出。少时记忆,边上还有所小邮局,包裹、信札漫出了屋子。
转过海关埕5号往北几十米就到闽江边海关埕,著名的海关大楼就矗立在那里,楼前通往机帆船码头有一片小空地,这里的人称平坦的空地为“埕”,那是孩子们的乐园。夏天的傍晚,这里可热闹了,大人来洗洗涮涮,孩子们来乘凉游泳,大胆的男孩在那里扎猛子,小女孩坐看大人洗衣,把脚浸入江水,吹着风,感受水的流动,还有小鱼轻轻袭来的惊喜。住在瑞荣坊的韦先生,紧挨着那里,是常客。童年的我时而也是其中的一员。
“文革”前,已归国有的原太古茶厂仍然在生产。每逢夏夜,茶厂券廊式建筑围墙上的拱形落地窗就会卸下,露出直条条的铁栅栏,可见铁栅栏内的生产车间灯火通明,汗流浃背的工人们用木掀往巨大的木制窨箱倾倒茉莉花。夏夜,正是茉莉花绽放的时间,那沁人心脾的花香飘满夜幕中的整个街区。这些香味的记忆,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直至今日,依然是那代人的身份符号。
如今,朝阳路原茶厂不知何时已搬走,那围墙轮廓却依然从北侧路口向东延伸。至于那过街的木廊屋和红砖楼、玉兰树,早在“文革”前就不见了踪影。朝阳路南侧的海关埕也只留了虚名,一座座高档建筑拔地而起,海关巷的路牌也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
5
“一只安静的猫,安详地蹲着,见了生人,也不吭声,也不惊慌,你走近,它不动,眼神清澈沉默,再靠近,触手可及了,才轻巧地一跃,并不即时消失,也许在左近……忍耐地、无辜地、善良地蹲着,叫路人自敛……收手离去。”这是2007年瑞荣坊拆迁前,记者采访韦先生的父亲而写的《静默生存》的开篇,这一段瑞荣坊里的“猫”的描写,预示了瑞荣坊主人的生存哲学。
韦先生的父亲是韦锦川的小儿子,他和瑞荣坊同时出现在韦锦川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韦锦川视他为福星,爱如掌上明珠。按家族重教育的传统,韦先生的父亲从小受良好的教育,善珠算,爱书画,懂洋文。到了晚年老人很享受瑞荣坊的宁静,直到老屋即将消失,老人先它而去。也许是不忍见到与自己相伴近百年的瑞荣坊老屋在挖掘机下呻吟,或许确实不愿自己比老屋活得更久,或许没有或许,他把对老屋的情结留在了纸媒上。

瑞荣坊拆迁前的广式排屋 小飞刀/摄
韦先生说:广式排屋其实不好住,福州人说“吹火筒”,夏季屋面瓦片吸热传导室内,冬季寒风凛冽地穿堂而过,夏热冬寒,尤其二楼更是住不得。瑞荣坊的广式排屋也因年代久了,韦氏二代兄弟姐妹中,败家的,生病的,发达的,卖的卖,租的租,几经易主,大多业主对此地已无感情也无眷恋。唯有韦先生说起留下的那架葡萄藤,眼里的清澈,让人想起那只瑞荣坊的猫,忍耐地、善良地、乐观地接受时代变革。
韦先生至今保留着祖父韦锦川的象牙印章和金边眼镜,还有一两件逃过“文革”抄家的英式家具。这些是韦氏瑞荣坊的念想,它们也随着拆迁安置,一起搬进了离海关埕不远的新家。说起这些,韦先生是很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