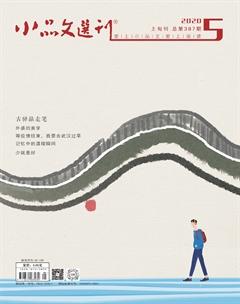又见红姑娘
焦淑梅

紅姑娘别名红灯笼、灯笼果、挂金灯等,学名酸浆。红姑娘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药食草本野生水果。《药性歌括四百味白话解》中记为:酸浆苫塞、清肺治肝、咽喉肿痛、热咳能安。
红姑娘的记忆,最开心的事就是那次去儿时伙伴小芳家玩。
我在小芳的院子里看花,看菜,看草,看蝴蝶翩跹,看麻雀飞起落下,看不远处青黛的南山像龙一样静卧,看高高的蓝蓝的天。院子没围墙,我们的叫闹声常常惊得从院前路过的大人跑来瞅瞅,看到是小孩子在斗闹,笑着摇头走开,我们也会回复好奇的大人们一个鬼脸。
小芳爸爸有正式工作,平时不在家,她妈是个美妇人,据说很风流,也常不在家。八十岁的奶奶带着小芳和生下来就有点智障的妹妹。五六岁的小女孩也有正常儿童的顽皮天性,断然不会老老实实呆在家,于是,她奶奶就常追着她妹,满屋子跑。气喘吁吁追赶着喊:“丑女,别摔着了,等等奶奶……”这喊声贯穿我童年少年的耳膜,直到后来我走出村子。
追逐中,在小芳家院里一个角落,发现了从没见过的一丛丛植物,盈盈绕砌,一二尺高,密密麻麻,每株上倒挂着稠稠的像小灯笼一样的果实,绿中透红。其别样的形态很招人喜欢,我们各摘了几个放在手心细细端详。小芳一脸自豪地说:“别小看这红姑娘,厉害呢。爹说了,下火,治疗嗓子疼、扁桃体发炎有奇效。”撕开那如麻纸一样的薄皮,根底卧着一枚指头肚大的圆果,青橘色,娇翠欲滴。咬一口,酸酸的,瑟瑟的,苦苦的,化开,有芝麻小的许多种子粘在舌上,麻麻的,并不难吃。于是,剥了一颗又一颗,有滋有味地品尝那复杂的况味。
三十多年了,这是我对红姑娘的最深记忆。长大后出嫁在外,离开村子,有关故乡的记忆,味觉尤其清晰,这包括在小芳家院里玩耍时吃过的那一枚枚红姑娘果子。
前几天,突然嗓子疼,多年来都是粗心大意地过活,并未在意。自己去药店买了一些药,胡乱吃了十几天,有“蒲地蓝消炎片”“灵丹草颗粒”“草珊瑚含片”“慢严舒柠颗粒”等,还买了胎菊、金银花、胖大海、罗汉果等分别泡水喝,效果不明显。又去医院雾化了几次,咽炎依然顽固。我有点担忧,和家乡的一个挚友说了苦恼,他怪我不早点告诉他,他有独门神药。我惊讶,他说:“等着,我马上给你寄。”
三天后,当几十枚红彤彤熟透的红姑娘飞落我案头时,那火焰般天然的美真让我颤抖,真让我不忍下手下口。办公室一帮人围观那小山般的一堆红,爱不释手,啧啧称奇。原来好友给我寄的是久违了的红姑娘!在明媚的阳光下静观,一枚枚红姑娘外衣上有突出的五角棱线,有纵横交错,脉络分明的网状叶脉,温婉的红,透明的黄,淡淡的清香,让我仿佛一下子就触摸到了儿时的岁月。后来,听说小芳的娘跟人跑了,她的傻妹长到十四五岁,病重后无药可救也没了,随后他爹也没了,不多久她奶奶也追随儿孙老去了。我和小芳三十余年没见面,看着眼前的红姑娘,和当初在小芳家院里吃的红姑娘没什么两样。当年一起玩耍的女伴都出嫁了,各有了不同的人生。可红姑娘依然是红姑娘,红姑娘的美,文人墨客是不会轻易把她忘记。清代第一词人纳兰性德有词《眼儿媚·咏红姑娘》:“骚屑西风弄晚寒,翠袖倚阑干。霞绡裹处,樱唇微绽,靺鞨红殷。故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朱颜。玉墀争采,玉钗争插,至正年间。”说的是元朝棕搁殿前曾有大片野红姑娘果子。王朝的周期似乎以几百年为限,野果依稀尚存,元王朝却沦为历史陈迹,才华超逸的纳兰路过此地,无限惆怅,情义婉曲,借咏红姑娘抒发了今昔对照之感。纳兰性德生活在满汉融合时期,他虽侍从帝王,却向往平淡的生活,有铮铮铁骨,不与时代同流合污,写词寄情,竭尽全力张扬自己个性生命的芳华。他出身权贵之家,以当时的评判标准来看,他不是个听话的孩子,但他的词赋,却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华章。
朝代更迭,时事变迁,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只有甜中有苦的红姑娘,一直赐予我们口舌无限的回味。烧一壶开水,在精致的玻璃杯里冲泡几枚红姑娘,等温凉了,大口饮下。如此,饮下了希望,饮下了阳光,饮下了纯朴的乡野气息,饮下了记忆中温馨的好时光,当然也有深厚的友情。友人说,这是他自己专门栽种的纯天然红姑娘,没有丁点儿化肥农药。连饮几天,有扶正祛邪之效,果然神清气爽,咽炎好了许多。
也有人说红姑娘是林黛玉的化身。它们之间怎么会有交集呢?原来,红姑娘其形是“外垂绛囊,中空如桃,子如丹珠”,把这些描述性的文字删去,缩减成两个字,就是绛珠;身为草属,是为绛珠草。而绛珠草之名,世人无不熟悉,《红楼梦》第一回便见此大名:“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林黛玉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已经坚固地树立在广大读者的心中,比真实的存在还要深入人心。世外仙姝寂寞林,表面的繁华并不能遮掩她作为孤儿寄养在外祖母家那种不能言说的苦痛挣扎的情怀,临了,她凄惨的结局更让一代代读者泪目。林黛玉的美和苦与红姑娘是何其相似,只是红姑娘是苦别人,以良药的身份解世人疾苦。
又见红姑娘,让人一番感慨。一直在读《纳兰词》,在看《红楼梦》,儿时笑闹声也仿佛一直萦绕耳畔,美好的时日竟那般哗哗流水就过去。唯有,有些友谊,经年,依然在。
选自《光明日报》